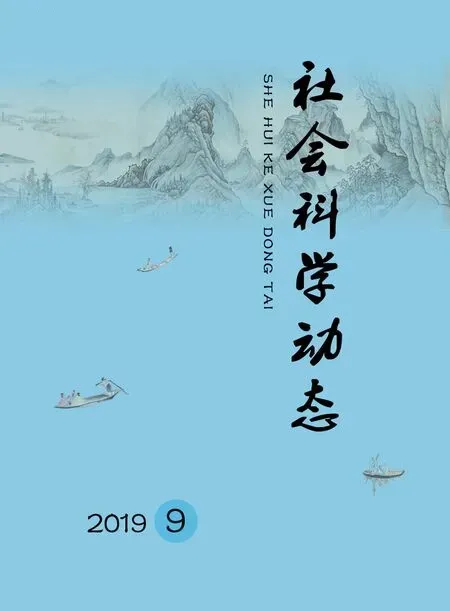射击影子的方法
廖海杰
曹军庆最新问世的小说集《向影子射击》收录了其近年的代表作品,也体现了其创作的新变。在众多的评论中,曹军庆常常被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看待,这自然是因其创作中无处不在的现代或后现代技巧,但“先锋”这一大概念下亦有不同的小路数——先锋可以像《褐色鸟群》那样不及物,也可以像《冈底斯的诱惑》那样置于远方。曹军庆的路数令人想起20世纪拉美文学大爆炸中的主将胡里奥·科塔萨尔——如其《南方高速》《正午的岛屿》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等名作所展示的,科塔萨尔路数不光意味着“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从高度写实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滑向荒诞,恰如隶书书写时的一笔“蚕头燕尾”,起笔时回锋隆起作蚕头,似生存之重,到尾上却不知不觉轻逸上扬,在这种上扬中可能存在非现实的、甚至冒犯的成分,但文学不就是在这一点超越性中显现?
《向影子射击》中的故事,发生于县城。事实上,对于整个中西部的中国而言,县城一头连接农村,一头又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外省或准备区,是转型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显形之地。县城是混杂的,在混杂的社会生活、经济形态、文化力量的多重形塑下,充满着这一时代的张力和复杂性。立足县城中国的现实展开文学想象,曹军庆新近演化出的路数正如本书的名字所示——向影子射击。
一
“影子”意味着对模仿观念的反叛。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将人之所见均视为投射于山洞岩壁上的影子,而理念的真实世界不可知,因此认为诗人无非模仿“影子的影子”,必须被赶出理想国。现实或现象是否是某物之影,对个人而言并不重要,我们所能体验思考的无非也就是这层影子,重要的是人们一直以来的观念中“影子”似乎是一个比本体低一级的替代品。影子不同于镜像,它是一个变异的、粗略的模仿,正如在图像叙事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文字叙事也变得越来越像现实的变异的、粗略的影子,但影子一定低于镜像、低于现实吗?这就仿佛说文学低于影视、影视低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低于短视频、在抖音中潜藏着最深刻的时代精神一般,充满着荒诞的幽默感。或许,在现存的高度复杂的人类协作体中,在高度复杂的现代性面前,文学可以依靠的正是显形影子、观察影子、射击影子的方式,对现实作出回应——照出现实的影子,捕捉现实的影子,才能让我们更贴近现实。
曹军庆的这部小说集执着于对县城中国的“造影”与“捉影”。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问题,如《滴血一剑》 《云端之上》;乡村开发问题,如《风水宝地》 《我们曾经海誓山盟》;腐败问题,如《请你去钓鱼》 《时光证言》;底层生存问题,如《请温先生喝茶》 《和平之夜》 《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当然,我们不能简单以XX问题给这些小说安上所谓主题,小说自身的流动性、多义性不能适用这样的粗暴切割,就像影子难以被确切框定为像狗或像兔。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小说都基于坚实的现实生存之体验,都关注着县城中国人们生活中、细节处的烦忧与愤怒。在这之中,《胆小如鼠的那个人》便是非常优秀的一篇对县城进行“造影”与“捉影”的作品,讲了一个颇为传奇的“翻身”故事:动不动就脸红的老同学杨光标可谓是一个超级老实人,也由于这份循规蹈矩的老实和害怕争辩的性格,杨光标四处被人欺负,终于在卖鱼的过程中被鱼贩子们教训,出了大丑——被霸道的蒋三当街用鱼抽了耳光。文中有一段描写相当精彩:“到底是鱼贩子,抡起鱼来就像抡着两块木板子或是两只鞋。但是鱼又活着,在空中能自由摆动,蒋三却有本事直直地把它抽到杨光标脸上。第一下击中后,杨光标的脸就开始红肿。他差点跌倒,摇晃几下又站定了。蒋三拿手上的鱼攻击杨光标,鱼和人的脸皮撞击居然能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①
杨光标被教训后,便老老实实和妻子开起了麻将馆,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又出了一档子事:杨光标在自己的店里赢了钱,外面便有人开始传言麻将机有问题,杨光标得知之后紧张不已,竟主动退钱给同桌打麻将的另外三人,结果这反而坐实了麻将机有问题的猜测,简直是窝囊透了的行为结果。小说的焦点也在此离开了杨光标,后半段集中笔墨到近年来幸福县崛起的强人光头良身上。光头良出身黑道,拥有县里最大的商城和最气派的楼盘,作为纳税大户,现在是书记县长的座上客。社会上的传言都说光头良杀人不眨眼,他曾经在一次酒局中途出去一趟,解决了一个对手,回头来喝完了那顿酒才开始逃亡,最后又洗白了身份,光明正大地重新回到县城活动。总之,就是这么个狠角色,到最后小说尾部发生了情节的反转——光头良竟然就是杨光标的儿子。不过,若是光论情节的曲折传奇,本作还谈不上精准的“造影”与“捉影”,真正有意思的是其叙述结构设计:杨光标是“我”的小学同学,而关于他后来的故事,都是“我”另一个做官的同学顾维军当作笑话讲的。前后两段故事的衔接来自于“我”的故事,即“我”被父亲鄙视,而父亲崇拜光头良,侄儿也成了光头良的亲信。最后是“我”在幸福县驻武汉办事处的团拜会上碰见光头良,才解开了他是杨光标儿子的秘密。那么这个叙述者“我”是什么角色呢?“我”外出求学后在省报任记者,但多年来并无一官半职,被长居县城的父亲鄙视,认为没混得个出息。事实上,“我”这个角色和杨光标构成对位的结构,“我”正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杨光标。“我的故事”、“父亲的鄙视”、“侄儿的经历”,在前后两段传奇故事的转捩点,照出并捕捉了县城文化之“影”——父亲作为退休教师,深以自己作省报记者的、“没有能力”的二儿子为耻,但却以做小混混、因为碰巧搭救了光头良而混得有头有脸的孙子为荣。小说写道:“我父亲开始主动找他孙子也就是我侄子搭讪,他这么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去巴结自己的孙子干什么?……他一定认为他才是我们家庭的希望,能给我们带来某种荣耀。”②在“我”家内部,“我”成了另一个杨光标,侄子成了另一个光头良,而平凡的、一辈子生活在县城的退休教师父亲,深深地向往着乃至崇拜着后者所代表的“县城意义上的成功”。这一段情节看似不长,但却是全文的亮点所在,正是因为有这段情节的存在,给前段杨光标、后段光头良两段极端化、传奇性的情节增加了厚实的生活底色,使得小说并未沦为一个“故事会”式故事。父亲的崇拜,寥寥几笔,却在小说叙述的转捩点上捕捉到了那萦绕在整个小说中的县城文化魔影——奴性的、对强权的崇拜,即使这种强权只是弱肉强食的原始野蛮。胆小如鼠、老实到极点杨光标之所以要忍辱负重培养出光头良这样的儿子,不正是为这种原始野蛮的文化氛围所逼?与《胆小如鼠的那个人》相似的,还有《和平之夜》 《请温先生喝茶》 《一桩事过境迁的强奸案》等几篇作品,不论是中学生对所谓帮派决斗的向往、神秘的民间仲裁者,还是能杀人的街巷舆论,曹军庆都在“造影”与“捉影”的虚实之间对县城中国的小角落作深描,这样的“先锋”不仅生长于藏污纳垢的民间,又有厚实的现实关怀、切实的生存经验为依托,无疑是更及物的。
二
及物的写作与批判本是共生的,曹军庆的文学之根既然扎在县城中国,自然也意味着对这一责任的肩负。只是,在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已不“流行”的今天,“造影”与“捉影”之后,射击影子的方法就变得更为重要。曹军庆在这部小说集中,通过虚实之间的曲笔和留白,完成着对影子的射击、对现实的批判。
“射击”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强烈”情绪指向的词,《风水宝地》和《请你去钓鱼》两部题名平和的作品中,便暗藏这种行将爆发的势能。《风水宝地》中,作为作家的“我”,到行将消失的柳林村,借住于毛支书家里养病和静心创作。几天后“我”便发现一个女人来给死去的儿子烧纸,交谈中,“我”得知其子死于草皮虫病,她因留守在村庄缺乏娱乐,天天打麻将而耽误了儿子的治疗。后来,毛支书告诉“我”那个女人叫孙素芬,当时嫁到村里来闹洞房时曾被以鳝鱼调戏,毛支书准备把鳝鱼闹洞房的恶俗作为民俗文化打造旅游项目,但自称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再后来,“我”又从毛支书夫人吴大姐处得知,孙素芬早就死于自杀,因为儿子死后她无法再生育而被丈夫抛弃,而之所以无法再育,则是因为当年被毛支书作为计划生育典型拉去医院做了绝育手术。“我”写完小说后离开了柳林村,但后来又从镇长处得知,“我”去柳林村时毛支书已死,实际上只有吴大姐一人在照顾“我”的起居。《风水宝地》看上去带有志怪色彩,又因为“我”本是患病需要休养的作家,使不可靠叙述者得以产生。那么,故事中的种种惨剧及其背后的现实根源——民间的恶俗、简单粗暴的乡村计划生育、留守妇女和儿童的困境、农村的空心化、隐藏着各种欲望的商业旅游开发等等——都成了或许是幻觉里、或许是鬼怪色彩包裹下的故事内核,连柳林村也成了不再存在的村子,但鬼气和幻觉中农村的种种黑暗,也给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这可谓一种“射击”。《请你去钓鱼》中,“我”的朋友瞿光辉是县里身兼要职的官员,他包养了一个叫方小惠的风尘女子,正准备给她买套房子,诱其帮着再生个儿子,但方小惠却突然失踪了。瞿光辉深受打击,此后却爱上了去某个特定的鱼塘钓鱼。因为领导的这一爱好,吸引了县里其他机关的“积极”跟进,鱼塘老板收入大增,对他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后来“我”得知,鱼老板就是方小惠的哥哥,难怪瞿光辉对他别有照顾。但一次醉酒之后,“我”将鱼老板送回鱼塘,他突然破口大骂,说要放狼狗咬死这些人、毒死所有的鱼。在这个故事中,方小惠为何失踪、鱼老板是否知道瞿光辉与其妹的关系等等,都是未展开的情节留白,但在这留白之中,一种紧张的两个阶层间的对立关系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钓鱼活动的平静之下是暗流涌动,正如鱼老板忽然的爆发,正如那两只“绝对不可能咬人”的狗竟然让汽车无法挪动,而这一暗流也对位地解释了方小惠无缘无故的失踪:这也是她的反抗,只是瞿光辉自己觉得无缘无故而已。在强权者被自己的恩惠所自我感动的时候,在其察觉不到之处,被侮辱者已积累起巨大的反抗欲望。
在虚实之间通过曲笔和留白,制造出巨大的想象空间又带有强烈批判性的,正是本集中的同名小说《向影子射击》。在这篇小说中,曹军庆写了一个看上去有些超现实的、但又并非没有现实根据的故事。云嫂生下孩子后,被医生引荐去了一个神秘院落做奶娘,在这里,先生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何要以人奶为食?与夫人之间又是怎么一种关系?小说里都没有交代,始终让这个小院处于迷一般的场域中。不过,这个初看起来颇为架空的故事,却丝毫不给人任何虚幻之感,相反它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这意味着它实现了一种基于融贯的文本内真实性。而“向影子射击”的意象则出自于先生对云嫂唯一说过的一段话:在合约期将满之际最后一次哺乳时,先生告诉云嫂他小时候是个孤独的人,唯一的爱好是用手指比划成枪的形状,向随便什么影子射击。有意思的是,云嫂的孩子小仁也莫名地有了向墙上影子射击的爱好,云嫂发现了儿子与先生的相似之处十分高兴,还专门为他买了三把玩具枪。这里射击,也就是枪的意象,意味着反抗的权力,在小说中显然代表着云嫂一类底层人对那位上过电视、被神秘女人控制、要吸人奶为生的大人物(及其背后的强权)的反抗。但在小说的结尾,当云嫂又一次被保安粗暴地扔出医院,她为儿子买的玩具枪也摔在路上被往来的汽车碾了个稀烂,这意味着底层反抗的完全失败。更可怕的是,先生在那唯一的交谈中还告诉过云嫂:他最早也是摆地摊起家的。也就是说,吸人奶为生的怪物,曾经也是出自底层。地摊,摆在地上的非正式的商业行为,可谓是最贴近地面的底层,那个在孤独中用手作枪射击植物、房屋和人的影子的孤独小孩,最终在实现了阶层跃升后却又再次成为了加害者。新的被碾碎的枪,要射击的是抢夺孩子哺乳权的怪物,但这个怪物本身却也曾是一个底层的反抗者,这真是可怕的历史循环。此外,小说中塑造出了小院深不可测的吞噬力。云嫂在提供服务一年里迷恋上了先生以及其所代表的生活。这个小院像一个漩涡、一个深渊,一个会回以凝视的深渊,云嫂被小院所吞噬,她一次又一次试图回去却沦为笑柄,而乳房再也流不出洁白的乳汁,只能流出变色的污水。这里,让云嫂所代表的下层与小院的关系除了枪所暗示的对抗,还有一厢情愿的爱慕,两种互相矛盾的情绪扭结纠缠,再次成为奇妙的循环:底层渴望成为上层,成为新的吸人奶的人,枪被碾得粉碎,畸形的爱只造就乳头流出的污水和肥胖变形的上身……在对循环和吞噬的书写中,《向影子射击》可谓示范了射击现实之影的方法:用敏锐的感觉制造出文本世界的内真实性,用直击人心的意象和隐喻,让读者在接受中自然感受到隐含的、强烈的现实批判张力。
曹军庆在小说集《向影子射击》中实现了对县城中国现实的“造影”、“捉影”及精准射击式的批判。其中的寄托不禁让人想起阎连科所呼唤的“神实主义”,虽然这一理论未必那么精密而富于学理性。在2011年出版的《发现小说》中,阎连科写道:“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杂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散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汞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③
也正因为中国现实前所未有的丰富、复杂,使得曹军庆式的“向影子射击”之创作倾向,有了更多的时代性,“向影子射击”不是凌空蹈虚,不是纯形式的游戏,而是基于对县城中国中个体的生命体验、时代感受细致入微的体察。当然,“向影子射击”常常要在虚实之间切换,这对于作者构建文本内真实性的功力是一个极大地考验,如学者赵毅衡所说:“文本要取得这种融贯性,就必须为此文本卷入的意义活动设立一个边框,在边框之内的符号元素,构成一个具有合一性的整体,从而自成一个世界。有了这个条件,真实性才能够在这个文本边框内立足,融贯性才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中起作用。不仅如此,文本的此种融贯性,也必须与接受者的解释方式(例如他的规范、信仰、习惯等)保持融贯。”④在这部小说集中,如《滴血一剑》和《云端之上》对网络游戏世界的想象,就可能存在融贯性上的问题——对部分熟悉游戏世界的读者而言,可能会产生出作者对网络游戏缺乏常识的怀疑,进而造成整个文本内真实性质疑的可能。当然,“向影子射击”既游走于虚实之间的艺术,中间偶有不尽完美之处也再正常不过。我们相信作者在不断的尝试和进步中,艺术创作一定能达到更为炉火纯青的境地。
注释:
①② 曹军庆:《向影子射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308页。
③ 阎连科:《发现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④ 赵毅衡:《文本内真实性:一个符号表意原则》,《江海学刊》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