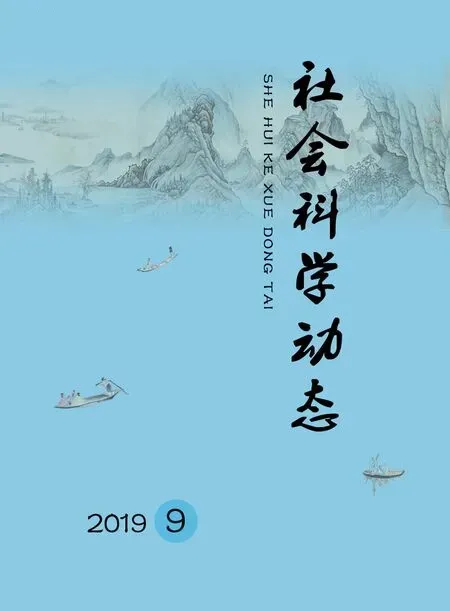论方方小说对武汉的城市书写
梁桂莲
在湖北作家中,方方是致力于描写武汉、表现武汉的著名作家。从最初的《“大篷车”上》 《风景》 《黑洞》,到后来的《水在时间之下》 《民的1911》 《武昌城》等,三十余年来,从青春到“新写实”,从女性命运探讨到知识分子写作,从凡俗人生表现到历史题材展现,方方孜孜不倦地用文字记录着武汉城市的沧桑变迁,书写着武汉人民的喜怒哀乐,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她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中的武汉,一个在历史中行走的武汉。
一、历史与记忆
武汉是一座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从最早的盘龙城遗址到东吴孙权设置夏口,到近代汉口崛起成为“东方芝加哥”,再到辛亥首义成为革命中心……千年的历史发展,使得武汉历史文化与商业文化富集,革命记忆与商贾人生同在,既是历史现场,又是繁华商埠。但遗憾的是,“生活在这时光层表层上的人们,成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竟对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一无所知”①。有感于此,方方以小说的形式沉潜过去,讲述武汉历史,重构武汉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武汉。
方方对武汉历史的书写,是从武汉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入手的。在《民的1911》 (2011年)中,方方再现了武昌起义从筹备、发生、取得胜利的全过程。在小说中,“民”既是无处不在的观察者,通过他的眼睛和活动,方方俨然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或在场者,全知全能地将历史风云悉数纳入笔下。同时,他又是一个象征者,既是普通之“民”,又是革命者及先驱者们活跃、觉醒的“民魂”,寓意着辛亥之后人民的成长和觉醒,历史从帝王之国迈向民众之国。这种虚实相生的写法,不仅全景式展现了武汉辛亥首义的历史,同时也传达出方方所持的民本主义立场,诠释出“历史改变民众、民众推动历史”的思想。写于同年的《武昌城》以两个独立的中篇来讲述1926年秋北伐军与守城的北洋军在武昌城下对峙40天的历史。在这部小说中,方方将攻城方和守城方同时纳入历史视野,在还原北伐战争中武昌之战这段历史的同时,也对武昌城的历史进行了打捞、唤醒。在历史的演进、叙述中,方方依然将“民”、“民众”推向前台,不仅通过对战争中无数生命个体的描写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叙述,讲述战争的残酷、历史的惨烈、人性的挣扎和生命的韧性,以此思量战争影响下历史的常与变、人的生与死、城市的荣与毁、生命的长与短;而且也再次将“民”作为历史的推动者予以生动展现。别尔嘉耶夫说:“世界可能正在走向最高的和谐,走向普遍的协调,但这并不能补偿过去无辜者所受的痛苦。”②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方方的《武昌城》扬弃了宏大叙事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从“攻城篇”中北伐军一路克胜和满目所见的尸体、攻城的惨烈及无数将士的牺牲,到“守城篇”中成千上万的人因围城生活受影响、生命受重创,到最后马维甫选择以一己之遗臭万年来换取百姓生命,其内心道义和良知终于战胜军人天职,民众命运成为战争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关键抉择。因此,这场持续40天的围城战的结束,与其说是北伐军在军事较量上的胜利,毋宁说是道义的胜利、民众的胜利。在这方面,方方并没有将“民众”的力量简单地约减为所谓的民心向背,而是说,战争中民众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意义的。带着这样的思考,方方的历史书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的道德评价,也超越了为传承而书的史家笔法,进而洋溢着人道、人性的力量,具有了更广袤的人性空间。
同样以个人视角书写城市历史的,还有《水在时间之下》 (2009年)。在这部小说中,方方借汉剧名伶水上灯沉浮起落的一生来演绎民国时期汉口兴盛衰微的一段历史。“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武汉。它的背景以及诸多细节几乎完全真实”,如1931年汉口大水、1937年汉口空战、抗战时期“献金”运动、武汉沦陷等历史事件,因此,这本小说与其说是水上灯沉浮起落的个体生命史,毋宁说是一曲汉口往事,一部汉口自开埠以来繁华鼎盛到沦陷恢复的城市发展史。在小说中,城与人相依相衬,城市命运推动人物命运发展:1931年汉口大水导致水滴失母(养母),走上从艺之路;1937年汉口空战、沦陷导致水上灯从大红大紫走出乐园避进租界,结果被张晋生骗婚……正是有了汉口这座城市为依托,水上灯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才得以完成。同样,也正是借助人物命运发展的自然逻辑,汉口才得以展现出它繁华辉煌、斑驳陆离的历史。在小说中,“时间”是个关键词,它既是作品的叙述顺序,从时间出发,方方将附着于历史表面的尘埃层层剥离,对近代汉口、对汉剧的兴衰繁盛进行了历史还原与重述。同样,时间也是人物命运和城市命运发展的推手,它将一个旦角变成了鸡皮鹤发、蓬头豁齿的老妪,也将一城繁华化为风平浪静,它埋没了一段段爱恨情仇,也埋葬了一切的荣华富贵。方方说:“这世上,最是时间残酷无情。”透过时间的迷障,方方不仅完成了对“汉口往事”和汉剧历史的寻觅、打捞,而且也接触到历史的真相,不是“水在时间之下”,而是“历史在时间之下”。
在方方的历史书写中,时间承载了历史,时间的不断流动,造成历史的层叠。但历史从来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它反映在日常一切可见的物象中,也折射在每一个在场的个体生命上。在方方笔下,历史既是日常的,也是贴肤可感的,每一场巨烈震荡的历史变革,都演变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这“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历史悄然发生着巨变,并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个人命运的转变。《武昌城》中因为僵持的攻城战,数万士兵牺牲,数万人民由于饥饿挣扎濒死于生命边缘,固若金汤的武昌城墙也于战后被拆。《水在时间之下》中因为汉口大水,水上灯走上了从艺之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水上灯避进租界,嫁给了张晋生,为了保护爱人,她害得水文被抓,水家由此败落。而在《乌泥湖年谱》 (2000年)以及《中北路空无一人》 (2005年)等作品中,因为“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国有体制改革等事件,个体生命更是在历史的推动下发生着惊心动魄的变化,而应和着历史变革的,则是城市翻天覆地的改变和时空的不断变迁。
作为历史纪实,方方的历史书写,显然是想为武汉这座城市留存一份历史备忘录,因此,其“纪实式”的书写和对“真实”、“历史”的追求,并没有使她陷入“时光倒流”、“沉溺过去”的历史呓语和喟叹。相反,在对历史在场的叙述中,方方不仅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地点示人,还始终坚持以个人视角观照历史,着力发掘历史境遇中的人间万象,日常情态,在呈现历史事件、展现历史风云的同时,又充满生命力地唤醒了武汉这座城市的记忆,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看到了历史活动中的人生世相、城市旧貌和都市风情。不仅如此,方方还将波澜壮阔的历史融进日常生活百态,将个人命运放到历史际遇中去考量,使得大历史与小人物交互辉映,常与变互为表里,在展现历史风云的同时,为我们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史。
二、日常与在场
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说:“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③方方也说:“因为我就是吃武汉的粮、喝武汉的水、呼吸武汉的空气、汲取武汉的营养长大的,无论我写什么,我都会带着武汉的气味,这种味道或许就是汉味。”④从童年开始,方方的人生就与武汉紧密相连,高中毕业后的四年装卸工生涯和此后的记者生涯,更是让她深入到武汉的各个角落,接触到各个阶层的市民群体,体验到他们的困苦哀乐。带着这样的情感经历,方方始终将武汉市民世界作为自己写作的核心,为此,她摒弃了都市浮华虚文的外表,隔绝了灯红酒绿的物欲生活,自觉地选择与“社会转型、结构调整、利益再分配所造成的种种矛盾与痛苦的实际承担者”们站在一起,用文字表现他们在时代、社会夹缝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虽然,方方的这一创作路径,与90年代以来兴起的表现城市生活和欲望、都市冒险和奇观,展现都市异己的“都市文学”在精神和气质上相距甚远,甚至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或“城市文学”,但事实上,在“城市流浪者”作为都市表象、都市欲望成为城市生活表象拼贴的城市书写中,市民生活正是城市文学最隐秘最核心的所在。对此,学者杨东平曾经指出:“城市不是供人观瞻的,而是让人生活的,中国城市应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家园,而不是奢靡的公园,城市最好还是要返璞归真,不能轻佻浮华。”⑤对于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而言,方方笔下对武汉市民生活和精神困境的表现,对他们在时代改革、社会转型期间的贫与病的发掘,无疑是触到了武汉这座现代老城的灵魂,展现出了其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阵痛和涅槃。
方方对武汉市民生活的描写,是从家庭关系入手的。在《风景》 (1987年)这篇小说里,方方描写了居住在“河南棚子”里一家十一口人近乎动物般生存的生活样态。在这个家庭里,父亲打妻子儿女就像喝酒打架一样频繁、兴奋;母亲对待子女毫无慈爱之心;兄弟姐妹之间毫无关怀之意,整天窝在狭小的空间里用最恶毒的话咒骂彼此。这样的家庭,毫无温情可言,有的只是冷漠、自私、残暴、丑陋。在《风景》开头,方方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晰地看到那些奇异的世界。”⑥透过现代文明的幕布,透过不同家庭的窗口,方方看到了现实生存中的荒蛮原始和人性中的自私残忍。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七哥,无疑是这个丑陋家庭里的“恶之花”。为了改变命运、出人头地,七哥变成了一个冷酷、自私、功利的利己主义者,他踩着爱情、尊严上位,毫不犹豫地抛弃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转身投入年纪比他大且不能生育的高干子女的怀抱。他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成了从“河南棚子”走出的人人艳羡的“人上人”。对此,方方说:“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差不多是他这种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该谴责该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⑦的确,环境的恶劣,生存的卑贱,亲情的沦丧,关爱的缺失,这样的情感荒野,必将滋生出人性、道德沦丧的恶果,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或如蝼蚁被践踏碾压,或出于本能对他人进行兽性掠夺,家的温情被人性的自私、恶所遮蔽,取而代之的是为了生存而罔顾亲情、血缘的原始人性的肆意滋长。
从生存环境出发,方方以冷静的笔触展现了底层社会因为住房问题而引发的家庭矛盾和生存困境,由此对爱情、亲情、家庭等神圣化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质疑和消解。《落日》 (1990年)中丁老太一生含辛茹苦,为子孙劳心劳力,年老了却被子孙视为负累。在只有十二平米、四世同堂的生存环境中,丁老太的存在,不仅挤压了子孙的生存空间,而且也阻碍了儿子丁如虎再娶的幸福。因此,在丁老太喝了“敌敌畏”之后,子孙们一致合谋将原本可以救活的丁老太送进了火葬场,上演了一场弑母的家庭伦理悲剧。方方以“家长里短”的日常叙事,以冷静的笔触,将传统家庭中的亲情、血缘撕裂开来,让人看到,由于贫困、狭隘所导致的亲情之困、人性之恶。《风景》中被父亲的粗暴和母亲的粗俗养育大的七哥,自始至终身体里都流着自私、冷酷的血液;《出门寻死》 (2004年)中的何汉晴,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尊重,挣扎、徘徊于生死边缘,以致于想“出门寻死”;《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在告发丈夫致其跳江之后被儿子、公婆仇视,挑起一家重担却被儿子赶出家门,内心千疮百孔;《黑洞》 (1988年)中的陆建桥因没有房子寄居在姐姐家,昔日亲密无间的姐弟关系反而因此疏离,陆建桥望房欲穿却又不得不陷入生活的“黑洞”……在这些作品中,方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底层社会的苦难生存图景,反映出小人物在时代政治、经济潮流下的物质和精神困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原有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受到剧烈冲击。在这个变革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张、矛盾关系。对此,方方一方面通过作品展现人在异化现实中与生活搏斗时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另一方面又通过底层社会贫瘠的生存样态反思当下社会现实的无序、混乱和不合理,并以此诘问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在对武汉市井人生的描绘中,方方摒弃了90年代以来盛行的城市文化代码如饭店、酒吧、歌厅、舞厅等场所的描写,而将隐匿的日常生活搬到了台前。方方始终以“在场”的姿态,以日常生活流的形式书写武汉底层社会的粗鄙陋俗,烦屑琐碎,单调苍白,残酷窒息,以此展现武汉市民生活的苦痛及无望挣扎。《中北路空无一人》 (2005年)中的郑富仁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年男人,每天不得不为房租、饭钱、儿子的学费生活费等发愁。为了生活,他起早贪黑,脚踏破旧的自行车,往返奔波于装修公司与家之间。但生活并不因他的勤劳而改观,也未因他的善良而得到善待。在给父亲送鸡汤去往医院的途中,郑富仁意外捡到一袋羊毛衫而遍寻失主,但没想到,找到失主后他却因为妻子刘春梅不知情私自卖掉货物,赔偿不了货款而被告上法庭,由此,原本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陷入危机。
透过城市的繁华、热闹,方方描绘出了武汉底层市民卑微的人生和无尽的烦恼,展现了他们在时代、社会政治逼迫下生活的卑琐、无奈和精神的麻木。在其笔下,无论是为房子发愁的陆建桥,还是为生活忧虑的郑富仁,以及万箭穿心过、无家可归的李宝莉和陷于生死两难选择的何汉晴……他们都无法真正主宰自我,相反,“严酷的现实和被挫折的理想使得生活严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眼前。改变现实的无力变成了无奈和厌倦”。⑧作为被时代碾压的贫困者,他们注定要为物质生活挣扎,为家庭生活奋斗。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他们的努力似乎注定无奈而徒劳。对此,方方对他们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与关怀,但也绝不给他们制造廉价的希望或机遇,相反,每一次看似希望的“转机”,实则是人物走向深渊的开始。这种看似“残忍”的书写,使得方方在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广场进入里分,在原汁原味展现武汉底层市民的本真生活时,却又始终带着知识分子的冷静和睿智。为此她以在场者的姿态书写日常,却并不沉溺、认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市民生活及其哲学,她同情、理解底层市民生活,却又始终质疑、追问这种生活的合理性和意义,虽然这种追问是没有答案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方方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操守,以及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追寻和对建构健全、文明的人类社会的企盼。
三、批判与救赎
方方被称为新写实作家,有评论认为她对武汉城市生活的描写体现了“零度情感”。但作为从大院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方方又始终保留着知识分子的清醒。她事无巨细地对底层生活进行原生态的白描和还原,却并不因琐碎、庸常而淹没、稀释其作品意义,相反,她的作品总是在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雅斯贝尔斯说:“悲剧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展示人生的不幸,而是要展示人的精神对悲剧的超越,这是对人的内在生命力量的自觉认识,也是人存在的意义所在。”⑨戴锦华也说:“方方的小说有一种描摹和一份记录,但在这人间景象背后,是她的一颗无法自已的拳拳之心与秘而不宣却跃然纸上的追问。”⑩确实,在对武汉市民生活描写的背后,在对弱势群体关注的目光中,方方始终在思考着市民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吁和对理想生活的追寻。
作为从大院里出来的作家,方方一直将知识分子生活作为自己笔下的题材。学者王春林说:“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究与思考业已构成了方方无以解脱的一种思想与艺术情结。”⑪对此,方方表示:“因为他们和我接近,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写知识分子是我比较熟悉的题材。应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但是知识分子这么多年所走的路又是一条惨不忍睹的路……我和他们一样,在生活,在思考,有困惑。但是我也要提出一些问题,表达我的困惑。”⑫为此,方方不仅在《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 《定数》 《行云流水》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展现出他们在时代、社会变革中无所适从的人生和精神困境,也对造成这一困境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祖父在父亲心中》 (1990年)是方方书写祖、父两辈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文本。在父亲心中,祖父高大、伟岸,以浩然正气傲立于时代之中,不为时代折腰,不向权势困境低头。在帝国主义的暴力专制下,祖父铁骨铮铮,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淫威,他不肯屈服,慨然写下“匹夫不能为国拒敌,有死而已”的豪言壮语,最后被敌人残酷杀害。祖父虽然死了,但其大义凛然的言行和不畏强权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对恶势力不屈不挠。父亲继承了祖父的理想、才情,但却在历次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和斗争漩涡中,慢慢磨掉了自己的血性和勇气,人格、精神逐渐萎缩,最终只能在日复一日的不安和煎熬中度日。在小说中,方方通过书写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展现出了两代知识分子身处不同时代语境的不同命运和精神境地。对于祖父辈来说,外寇的入侵,敌人的迫害,不仅没有压垮他们的灵魂,相反更激起他们的独立人格,而对于父辈来说,历次政治运动的高压,没完没了的检查材料,不仅磨灭了他们的人格、志气,也使得他们由内到外、从精神到行为,时时都处于精神的囚笼中。类似的人物还有《乌泥湖年谱》 (2000年)中的苏非聪、丁子恒、皇甫白沙等。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身处政治运动漩涡中被不断改造、精神萎缩的心灵悲剧。对此,方方说:“改造是没有砍头没有上酷刑没有流血,但却让你灵魂死掉了的一种方式。壮烈而死的人,肉体没有了,灵魂犹存,他们总是激励着后人对恶势力不屈不挠。改造而死的人,灵魂没了,肉体却还存在,他们将这种没有灵魂的肉体遗传下来,他们也在影响后代,好死不如孬活着。”⑬
如果说,《祖父在父亲心中》 《乌泥湖年谱》描写的是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深受政治压迫心灵受屈受辱的悲剧,那么《白梦》 《白雾》 《白驹》(“三白系列”) 《行云流水》 《无处遁逃》 《惟妙惟肖的爱情》等作品则写出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的迷茫和困窘。《白梦》 (1986年)中的家伙既不认同社会上庸俗、势力、浅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愿虚伪地带着面具示人,只能玩世不恭以戏谑的态度看待生活;《无处遁逃》 (1992年)中的严航不想赶潮流,也不想捞什么好处,只想攻博,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学问,但其无处不在的书卷气息和只做学问不涉交际的派头,不仅在妻子眼里显得苍白和渺小,而且也在学院和社会上格格不入,想出人头地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想出国攻博却在签证时被拒之门外,最后只觉得自己陷入无边的孤单;《行云流水》 (1991年)中的高人云老实、本分,做事认真,待人诚恳,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却事事不顺,处处碰壁,仿佛跟这个时代生活上的齿轮错了位,处处是尴尬、窝囊,他想保持自尊但生活却将他的尊严碾得粉碎,他想清高却不得不处处求人……在这个物质化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高人云所固守的理想、气节、尊严终于被现实击打得粉碎,最终因体力不支而病倒。
生活始终在嘲笑高人云这样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万事不求人,但现实却又逼迫着他们放下身段,放下尊严。高人云们一方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一方面却又固守着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与理想的撕裂中不堪重负。借用《惟妙惟肖的爱情》 (2014年)中人物的话说:“这个时代根本不是让老实人好好活下去的时代。”时代在弯曲,知识分子却偏要走直线,这怎么能走顺?时代虽然改变不了他们,却能淘汰他们、贱看他们、无视他们。处身于学院的高墙之下,方方对学校、对知识分子的切身处境深有体会。如果说,禾呈、言午、金中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因为中国政治运动而造就精神发育不良、生命萎缩的话,那么,惟妙、惟肖、严航这一代,则是经济大潮下造就的精神失衡、灵魂真空状态。小说通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困境,映照、折射出时代的疲病、失序。为此,方方一面痛惜严航、高人云们不懂社会,为时代碾压的尴尬处境,同时也谴责时代潮流下学院的腐化、变质和追名逐利。当最后一方净土被污染,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也就是“定数”中“无处遁逃”的人生,一切都难以逆转。
除知识分子之外,女性命运也是方方重点探讨的话题。早在《船的沉没》 (1987年) 《随意表白》 (1992年) 《暗示》 (1996年)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1999年)等作品中,方方就表现了隐藏在身体里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对男女情爱的神圣诗意进行了颠覆和消解。不仅如此,方方还超越性别意识,将女性命运放到社会、经济、文化的范畴中思考,由此呈现出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生命本体意义。《出门寻死》 (2004年)中的何汉晴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侍奉公婆尽心尽力,帮助邻里热心快肠,但就是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却始终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温情。她想以死来反抗生活的痛苦和无奈,换取生存的自由和权利,但最终无法超越现实的束缚和制约,只能在生与死的两难抉择中,以“生死有命”来为自己生存的意义寻找支撑,继续烦闷而无奈地活着。借《出门寻死》,方方探讨了城市普通女性的出路和生存的意义。对于像何汉晴这样饱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的城市普通女性而言,照顾家人、孝敬公婆无疑是其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她虽然感受到自己人生的压抑和命运的困缚,想寻死以求解脱,但这种“寻死”的反抗更多地是一种“潜意识”行为,在生死不由自己而在社会限定的框架、规则下时,对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意识瞬间压倒了其“向死”的决心,她重回到了家里,回到了社会舆论和家庭道德的规范之下。
作为《出门寻死》的姊妹篇,《万箭穿心》(2007年)更是以谶语般的宿命展现了城市女性在婚姻、家庭、社会生活中的悲剧命运。与何汉晴的贤惠、善良不同,李宝莉个性要强,性格泼辣,脾气火爆,由于一念之差,她报警抓了有外遇的丈夫,这不仅毁了丈夫的前程,也毁了自己的人生。为了弥补过错,李宝莉毅然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但靠她养活的三个亲人,却个个拿她当外人看。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更是不顾母子亲情,将李宝莉赶出家门。如果说在《出门寻死》中,何汉晴还可以用“生死有命”、家庭需要来劝慰自己,让内心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话,那么《万箭穿心》则是彻底打破了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幻境,揭示出底层女性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忍字当头”的无力和无能。表面上看,李宝莉心慈嘴狠,泼辣要强,在家庭中事事以自我为中心,但内在来看,她勤劳善良、洁身自好,且极为认同母亲的隐忍哲学,这种矛盾的性格,不仅成为她生存之困的根源,而且也使她注定无法以“忍”获得生活的和解。但即使这样,饱受“万箭穿心”之痛的李宝莉并没有向生活、向困难低头,相反她迎难而上,直面生活的利刃,坚持“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的生命哲学,努力克服家庭、亲情的伤痛、背叛,实现了对自我命运的主宰。
除何汉晴、李宝莉外,方方还在作品中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女性悲剧:《落日》中丁老太一生为儿孙操劳,到老却被子孙合谋杀死;《一唱三叹》 (1992年)中的晗妈年轻时支持国家建设,送儿女到边疆工作,老了仍被道德绑架,经济拮据、住房窘迫、生活艰辛,只能与孤独思念为伴;《水在时间之下》中李翠为了好的生活条件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孩子,玫瑰红、水上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放弃爱情……从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女性身上,方方不仅看到了底层女性因为环境、时代逼迫老无所养、老无所终的现实,也看到了城市女性在家庭、社会双重压迫下茕茕孓立的人生悲剧。这一方面是受城市文化浸染所形成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城市环境、时代社会息息相关。方方在《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中说:“人本来都有正常美好的生存方式,只不过有些后天的因素改变了人……改变人的因素其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人自身,人不能离开自身的遗传基因、兴趣、性格以至天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人摆脱不掉这两种因素对自我存在的困扰。”⑭相比其他城市而言,武汉女性脾气火爆,个性鲜明,敢爱敢恨,这样的性格及作为女性的命运,注定了她们在自我和家庭、性别身份和职业发展中难以两全,为此她们忍辱负重、身陷囹圄(何汉晴、晗妈、李翠、李宝莉等),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因她们的忍让而善待她们,相反,生活的苦痛、家庭的矛盾、现实的冷酷仍一步步将她们逼入绝境。萧红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地,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⑮但即便是因袭着重负,武汉女性仍努力克服自身局限,面对生活的困境表现出了大爱与担当。何汉晴虽觉得生活烦闷、压抑,但面对一家老小的需要,仍任劳任怨照顾家人;李宝莉在丈夫死后,用十几年的时间赎罪,养活公婆和儿子……通过这些作品,方方不仅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期女性面对社会现实和家庭生活的困境和苦闷,也表现出了对女性生命价值及意义的追问,以及对其命运及出路的探索。
四、地域与超越
作为一个武汉本土作家,方方熟悉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情不自禁就会把人物放在武汉的背景下”,“希望城市的文化气息能更强盛一些”⑯,这使得方方自写作以来,就一直有意识地将武汉及武汉人纳入自己的视野,其作品也由此充满了地域色彩和汉味特征。在其散文集《阅读武汉》 《汉口的沧桑往事》等作品中,方方从武汉的历史、地理、人物、文化、建筑等方面勾勒了武汉的全貌,展现了武汉独特的气质。而在小说中,方方通过市民生活的描写,筛选出的城市风景、富有汉味的语言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武汉城市历史和精神文化,在展现文学武汉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升了武汉城市文学的品格和空间。
首先,方方通过精心筛选出的城市风景,打开了武汉的审美空间和地域文化视野。阅读方方的作品,宛如打开了武汉的历史地图,走进了武汉的大街小巷。河南棚子、司门口、汉阳门、大东门、昙华林、中北路、武昌火车站、民众乐园、古琴台……在作品中方方不仅借这些我们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地方景观营造出真实可感的城市自然空间,而且借助这种有辨识度的地理空间的书写、描述,展现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改革变迁。柯提斯·卡特说:“城市是自然的一个特定空间。城市提供了一个代表了人类价值和兴趣的建构了的环境……城市中的建筑、商业、政府、制造工业、交通和文化生活都为审美参与提供了可能性。”⑰在方方笔下,无论是混乱、肮脏的河南棚子,还是热闹繁盛的民众乐园,抑或是寂寞、老旧的昙华林,旧貌换新颜的中北路,这些城市地理空间,不仅与市民生活休戚相关,而且也承载了城市的历史、未来。在这方面,方方避开了富有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和日新月异的城市新区,而选取了那些相对落后的老城区,显然,在对这些城市风景的描写中,方方不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这些地名进行了审美观照,而且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元素进行了唤醒、发掘。如方方对昙华林的描写:“昙华林在武昌老城墙东北角下……昙华林夹在武昌城边的两座山间。山并不高,但也足够挡人视野。一座山叫花园山,一座山叫螃蟹岬。花园山是座找不到山顶的山……山上有座天主教堂,站在那里已经一百多年,只有它见过树林变房子的全部过程。”⑱寥寥数笔,不仅点明了昙华林的地理位置,也写出了它承受岁月变迁饱经风霜的历史感和沧桑、寂寞。在对城市地名、空间的描写中,方方还加入了与这些地名、空间相关的历史风云、改革发展、文化风俗、历史掌故等。如《水在时间之下》对汉剧历史、科班和班规班法及各种眼法、各种曲目表演的介绍,《落日》对武汉茶馆的介绍等,不仅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也赋予了武汉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其次,方方通过“汉味语言”的运用,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地域特色,而且也真实可感地塑造出武汉的市民性格和文化性格。何祚欢说:“地道的方言是地方文化的反映,表达的是地域特点和地方性格。”⑲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语言融汇,自然形成了一套以武昌官话为基础,杂交各种方言的个性鲜明的武汉方言。方方对武汉方言的纯熟运用,一是口语方言化,即注重对语言本真色彩的运用,在对话中经常直接以原汁原味的方言入文,真实贴切,既具有生活的质感,又生动传神地描写出了武汉市民的性格特征。如在《黑洞》中,同事柳红叶骂陆建桥“邪货篓子,一肚子坏水”,说他油嘴滑舌就像“那张嘴今天早上搽了几两油”,几句话就写出了武汉人爱开玩笑、随和、幽默的特点。又如《出门寻死》中何汉晴的内心活动:“我死了,看哪个给你们做饭,看哪个给你们洗衣,看哪个为你们满街买药,看哪个给你们换煤气,看哪个坐汽车帮你们抢座位……”⑳一连串的排比句式和口语化语言,说得快意、酣畅淋漓,不仅写出了何汉晴心直口快、勤劳善良的性格,也写出了何汉晴为家庭无私付出而不被理解的苦闷。二是书面语言化方言,即将日常化的口语与书面语融汇,使之成为更具表现力的“汉味语言”。如《黑洞》中写陆建桥因为没睡好,“眼白上的红丝像地图上的公路线”,《落日》中写王加英“大堆的家务事使她像个陀螺,一天到晚地转个不停”。这种既生活化又富有文学味的语言,不仅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状态,而且也符合武汉人善于夸张、调侃的性格特点。此外,在表现人物性格和身份上,方方也不避俚俗,大胆将方言、俗语乃至“汉骂”融进作品,并充分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表现出武汉人爱耍嘴皮子及粗鄙、泼辣的性格特点。如写武汉人吵架,“话来得比曹正兴的菜刀还厉害”(《落日》),损起人来,“凭着那两片薄唇,活生生地能刮下对方的皮”(《黑洞》),无不生动传神地写出了武汉人受码头文化、商业文化浸染,火爆热烈、好勇斗狠的性格特点。
再次,通过对武汉市民生活的描写,方方展现了武汉人热情、坚韧、豁达的性格特点。常言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是说湖北人精明。确实,居中处优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贸文化,使得武汉人在待人接物上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精明、算计、不肯吃亏的性格。如《黑洞》中陆建桥姐姐就说:“找老婆就得找这样的。不光自己吃不了亏,而且还能占到别人的便宜。”㉑就是兄弟之间、夫妻之间,武汉人也把这种精明、算计发挥到极致。如《落日》中丁如龙、丁如虎因各自利益对寡母的算计以及兄弟彼此之间的算计等。在方方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有女人悲春伤秋,也很少看到有男人不务正业,相反,为了房子,为了生活,为了子孙后代,武汉人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把面子、生死这些虚文的东西看得很穿。不仅如此,武汉人的性格还像武汉的天气一样,时怒时喜,时暴躁时幽默,高兴起来拍腿打椅,恼怒起来捶胸顿足、操爹骂娘。这种多方杂糅的性格,的确有点像“九头鸟”的多重性格。因之,现在的武汉人提起九头鸟,已无任何贬义,相反还颇有一丝洋洋自得的自豪感。
独特的文化,孕育独特的城市和文学。站在地域文化的角度,方方一方面以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景、语言和市民生活书写城市命运和历史变迁,为中国城市文学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她又始终坚持理性精神,对武汉城市发展及市民生活予以审视和批判。方方对城市市民生活的书写,既不像池莉那样不无赞许,也不像王安忆充满怀念与追忆,相反她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打量武汉这座城市,通过底层社会粗砺的生活形态揭示人性病变、亲情沦丧、社会失序的荒芜现实。因之,方方的小说虽被称为“汉味小说”,但无疑,其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对武汉粗鄙民风和市民粗糙人生的袒露,不应该单单被视为地方文化的还原和地域民俗风情的展现,相反其所揭示的底层生存困境和人性之殇,无疑超越了地域而具有普遍意义。如《黑洞》中对陆建桥无房可住的生存现实的描写,在当下中国“以房为家”的文化传统中,无疑是最大的民生之艰;《风景》 《落日》中所展现的恶劣生存图景及人性、亲情、家庭伦理的消解,无疑反映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秩序下传统伦理崩溃、人心浮躁、人伦失常的社会现实;《春天来到昙华林》 (2006年)主人公华林对原始淳朴乡土气息的寻找,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被抛离熟悉的传统之根,被动接受现代文明、精神无处安放的“断裂”之痛;《出门寻死》写何汉晴因受不了生活压抑“出门寻死”的故事,折射出当代家庭妇女的生存之痛……站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方方对当下生活及生活中的人性病变作了“病理切片”式解读,但“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方方几十年如一日的武汉城市书写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对武汉地域文化的生动再现,还有她对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存发展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状、未来的反思和探索。
注释:
① 方方:《武昌城后记》,参见《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②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8页。
③ 茅盾:《茅盾全集》卷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271页。
④ 方方:《武汉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
⑤ 参见《上海不是榜样的26个说法》,《新周刊》2003年9月4日。
⑥⑳ 方方:《方方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3—144页。
⑦ 方方:《我眼中的风景》,《小说选刊》1988年5期。
⑧方方:《这只是我的个人表达》,《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⑨ 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⑩ 戴锦华:《涉渡之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
⑪ 王春林:《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非亲历性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⑫⑯ 方方:《我的人生笔记:一个人怎样生活无需要问为什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124页。
⑬ 方方、姜广平:《按自己的所观所感去写作——方方访谈录》,《教研天地》2009年第5期。
⑭ 方方:《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⑮ 聂绀弩:《和萧红在西安的日子》,《鲁迅文艺月刊》1946年第1期。
⑰ 柯提斯·卡特:《作为符号的花园:自然/城市》,《外国美学》第21辑,杨一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⑱ 方方:《春天来到昙华林》,《中国好小说·方方》,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版,第198—199页。
⑲ 何祚欢:《江城民谣》,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方方:《方方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144页。
㉑ 方方:《黑洞》,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