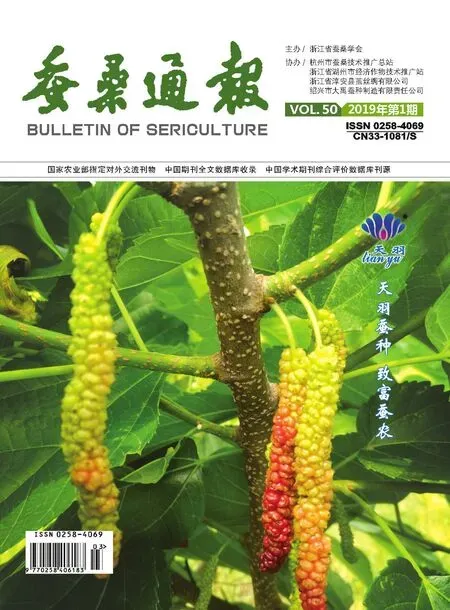隋、唐、五代时期的蚕业
蒋猷龙
第一节 隋代的蚕业
隋自公元581年代北周以后,至公元589年中定南朝的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以结束,中国又取得了统一。
隋文帝在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争得以停止,民众得以休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间(581~604),“平徭赋,仓禀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人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间宴如也”,与隋朝以前的漫长岁月战乱纷呈的情景相比,形成鲜明对照。
隋代重视发展农业,其中包括蚕桑,统治者每年行“祭先农蚕、亲耕桑之礼”,从农民种桑养蚕缫丝中所得的劳动果实,以“调”的形式征为己用。
对农民征调农产品,包括粮、绵、丝、麻,建立在均田的基础上。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农产品的征收。文帝在夺取了北周政权以后,首先就颁布了新令实行均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①《隋书》“高祖纪下”。受田的办法是:“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田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②《隋书》“食货志”对一般农民授予永业田和露田。按北齐的办法,即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每丁又给永业田二十亩,所以一夫一妇之家共可受用一百四十亩。永业田为桑田或麻田,露田以外的田可以买卖。虽是推行均田,绝不是将所有的土地都拿来进行还受分配,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得到土地或得到应分的土地,受田不足的情况很普遍。
农民所要负责的租、调、力役标准是:“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调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③《随书》“食货志”。这个赋役标准,较北齐、北周的“绢一匹,绵八两”有所减轻,且隋时有时对租调力役也作出适当的改变或减免,如开皇三年(583)“减调绢一匹为二丈”,这样的租调标准,并不是很高的,颇得农民的拥护,不少荒地得以垦辟,人民生活安定,对恢复和发展业起到一定的作用,蚕业也有所发展。故在开皇年间(581-600),“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国家积累大量的物资,文帝在灭陈以前,“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及至灭陈(589)以后,每年赏功赐臣所用的绸绢达“数百万段”,而还是“库藏皆满”,不得不建造左藏院来堆放,还是无处存放,就在公元592年下诏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隋炀帝即位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④《隋书》“食货志”。当时蚕丝生产极为兴盛,河北的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一带的农民,“其俗务在农桑”,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山东的一带农民也“多务农桑”,梁部则更以绫锦闻名⑤《隋书》“地理志”。江浙赣一带(扬部)“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颇同豫章”,而“豫章之俗颇同吴中,……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⑥《隋书》“地理志;《资治通鉴》卷177“隋记”
隋代曾是一个富饶的朝代,这种富饶的根源,就是黄河和长河两大流域的统一,经济和文化比起秦汉以至南北朝来,有很大的发展,但文帝传到炀帝——历史上少有的奢移皇帝,民众辛勤地积累起来的财富迫不及待地消耗尽了,加以连年出兵远征,死者十之八九“桑农咸废”,百姓“始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以至于亡。
第二节 唐代的蚕业
唐代前期,社会得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安宁状态,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补救前代破坏的创伤,并主要表现农业生产上,这就为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至唐代中期,藩镇叛乱,战争连年不息,黄河流域遭受战祸;而长江流域则保持相对的稳定,工商业业发达,为朝廷支付巨大的财政费用;提供了经济来源。国际问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为祖国赢得崇高的声望。国内经济、文化也在发展。正由于统治阶级的大量消费,在商业兴盛的同时,农民遭受的剥削日趋严重,农业不断衰落,待至唐代末年,朝廷内部分裂愈烈,长江流域发生割据战争,统治力量大为削弱,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死亡。
隋末战乱之后,“百姓离残,弊于兵甲,田亩荒废、饉飢荐臻”⑦《全唐文》卷2“高祖劝农诏”,唐初人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⑧《旧唐书》“高昌传”。唐高祖(618-626)在“申禁差抖诏”中说“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在劝课农桑,招徕难民号召下,武德七年(624)颁布了均田令,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并为政府收取赋税固定了来源。
均田的一般标准是:“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二曰口吩。丁之田二分永业,八分为口分。”⑨《唐大典》卷3“户部尚书”人无,永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按照北朝以来的制度,永业田种桑或麻,解决衣的总是,口分田种粮食,解决吃的问题。
劳动民众经营了这些土地以后,负担的赋役“有四:一日租、二日调、三日役、四日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一作二匹),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由于唐代可以缴纳绢布等实物来代替力役,这叫做庸,所以通称唐朝的赋役办法为“租庸调法”。当时江南的办法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供春綵”⑩《新唐书》“食货志”,这种租庸调法,并按年成的好坏规定减免的办法,“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年”⑪《新唐书》“食货志”。
唐代以人口为收税的单位,对蚕丝来说,每个“丁”(21岁以上至59岁)负担的税额是:
调:蚕乡输绢二匹,绫、絁各二丈,外加丝绵三两;
庸:每年劳役二十日,不劳役时,统治者收取代价每天绢三尺,共六丈。但也可以因国家多事要延长劳役时间,如超过十五日,则免收调绢。
在天宝年间(741~756),统治阶级的收入统计,每年“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丁计两匹,按此均将力役交绢布计算),绵则百八十五余万屯(六两为屯)……,大凡都计租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⑫杜佑《通典》卷6“赋和丁”,绢绵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占六分之一强。
根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各地贡献丝织品的情况如表1。
农民交纳的绢绵是靠自己养蚕织绸而来的,养蚕靠桑田,桑田就是每丁所受的二十亩永业田(非蚕区,这二十亩永业田种麻,统治者则收布)。这桑田可以子孙继承,也可买卖,并不因年老而分出,这对多年生的桑树管理是有利的,对促进蚕业的发展有作用,“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0)斗米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齎粮,民物蕃息”⑬陆龟蒙《甫里先生集》卷9,表现出国泰民安,繁荣富强的景象。农村忙着蚕事,正是“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维桑半顷麻,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缫车”⑭《唐书》“食货志”的情景。
本来,均田制是统治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征收赋税的一种手段,唐初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仅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把一些熟地或荒地给民众垦种,得不到土地的人,仍只好自己觅地,统治者对这些人说淡不上均田,但他们也要负担租庸调,更在官僚、豪商、地主三位一体的强行霸占侵夺下,土地兼并,以致“制度弛紊,疆理堕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米价腾贵,斗易一缣”⑮陆贽《堕宣公奏议》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所以到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均田制的作用已经消失。农民既然失去田地,不得不大批逃亡,转成为私人地主的庄客佃户,因此,到唐高宗时“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瞻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息,烦徭细役,并出其中”⑯《唐会要》卷83“租税上”。官家逼租、索丝的惨景历历寸见,“二月卖新丝,五月粜(tiao)新谷”⑰聂夷中诗《伤田家》;“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⑱柳宗元诗《田家诗》,都是当时蚕丝生产的现实写照。武后时,逃户问题严重起来,虽然他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到要“劝农桑,薄赋徭”,但农民已失去了立足之地,民众根本无法负担租庸调的苛刻剥削,生产不能发展,统治阶级的赋税收入也顿形枯竭,特别是“安史之乱”⑲公元755-763年,唐朝大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为争夺政权而发动的一次叛乱以后,均田制破坏,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法根本不可能执行,“农桑废于征呼,膏血竭于笞捶”。就在建中元年(780)由扬炎的建议改行两税法,即以户为纳税的单位,全年交夏税和秋税(一说为户税和地税)。两税的弊端是“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折价不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⑳陆贽《陆宣公全集》卷2政府这种给钱少而输绢多的办法,比商人纳剥削更苛重。农产品刚刚收获,“丝不容织,粟不容舂”,通过高利贷商人立即转入官府,农民困景到达顶点,“典桑卖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㉑白居易诗《杜陵叟诗》,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杜陵叟老实一家的情景。
两税法非但不能促进蚕丝业的发展,仅是中饱豪富,引起朝野人的反对。当时统治阶级对农民栽桑不限于永业田,而要求每亩田种桑两株㉒《唐书》“宪宗本纪”,以便征收绢绵,并限令不得砍桑作柴薪㉓《旧唐书》“武帝本纪”,可见到唐末,农村的蚕业基础已破坏殆尽了。
唐代的蚕业地区,以各地的贡赋中可以了解到约有一百多州郡,几乎遍及全国的十道,西部的陕西,甘肃和黄河东的山西,只有个别的州郡略有蚕桑生产,但据天宝十二年(753)记载“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似乎西北的蚕桑也已可观了,又把桑和蚕种传播到新疆,从近代发掘新疆的地下文物证明新疆在唐代生产蚕丝已有一定比重。
蚕丝生产较普遍的是华北大平原和河南一带,四川也相当发达,南方的江南道产丝绢己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但都密集在江苏、浙江和福建,其余还只是另星生产,浙江在唐初有意识地迎娶北方缫丝妇女成家,传授技术,在开元至贞观的一百年间,丝织技术进步很快,越州(包括会稽、山阴、诸暨、萧山、剡县、上虞)相当于现代钱唐江南岸绍兴地区一带,已成为南方的丝织中心㉔《新唐书》“地理志”,“安史之乱”以后杭州也开始繁荣起来,除台州外、湖州、杭州、睦州、婺州、衢州、处州、温州和明州都有丝和绵的生产,德宗时(780-805)“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㉕《旧唐书》卷129“韩晃传”,南方丝织乃开始超驾北方;淮南地区在唐的后期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一部分。总之,在唐代,江南蚕丝业发展很快,“旷土尽辟,桑柘满野”,“丝绵布帛之绕,覆被天下”(沈约语)。
在西南地区,云南自古饲养一种拓蚕并利用其丝茧,技艺则另一体系,“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蚕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紡丝,入朱紫以为常服,锦文颇有密緻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㉖樊绰《蛮书》卷7。,同上书中记载着:“(鸟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施蛮)男以缯布为缦裆裤”,“(粟栗两姓蛮)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ye)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女,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可见当地产丝甚多民众在唐代就以丝绸为常服了。
唐代后期与当时的南诏交往很频繁,许多工巧将丝织技术转入云南,大和三年(829)南诏人至成都掠去当地子女工技数万,所诏“驱尽江头濯锦娘”㉗徐凝蛮诗:《入酬后诗》。,这也是使云南丝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西藏地区也因文成公主出嫁时(641)带去蚕种和工匠,借以发展蚕丝业,并从此更加强了汉藏两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丝绸和绵不仅作服饰的主要原料之一,且由于丝绸等可以代替劳役,在两税制实行后又可代替钱币,因此,在市场上流通甚多,劳动民众除把应缴的丝绸部分上缴外,还把多余的在市场上换取生活用品。农村除生产普通的织物外,还在发展传统技术的基础上,生产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统治阶段为了特种需要,限令农民或招收官奴生产高贵的织物以供挥霍。织工技艺在这一时期中,有了出色的造诣,丝绸纹样讲究造型的完美、写实和精神的刻划,并能正确地掌握形象,达到雍容美丽的程度,其价值真要“缲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㉘杜甫诗:《白丝行》。。
政府对各地丝织品按传统货量严格地分成等级。“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八等”㉙《唐六典》卷2”少府寺”。。产绢地区和等级为:
一等:宋、毫;
二等:郑、汴、曹、怀;
三等:滑、卫、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
四等:沧、瀛、齐、许、豫、仙、埭、郓、深、莫、洛、邢、恒、定、赵:
五等:颖、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
六等:益、彭、蜀、梓、汉、剑、遂、简、绵、襄、褒、邓;
七等:资、眉、邛、雅、嘉、陵、阆、普、壁、集、龙、果、泾、渠;
八等:通、巴、蓬、金、均、开、合、兴、利、泉、闽。
中唐开元以来,国内商业已蓬勃向前发展。商业性质,从偶然交换或特产品的贩卖发展到固定的城市商业,有常设的市肆和店铺,有专门从事商业供应的行帮如绢行和织经锦行,甚至农村中还有定期的集市如蚕市(《茅亭客话》春9)。
贸易的媒介,从铜钱和布帛杂用向金属货币过渡,主要通行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日本银币。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法的建立,丝绸商人乘机兴起,“自初定两税,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俞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新唐书》“会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