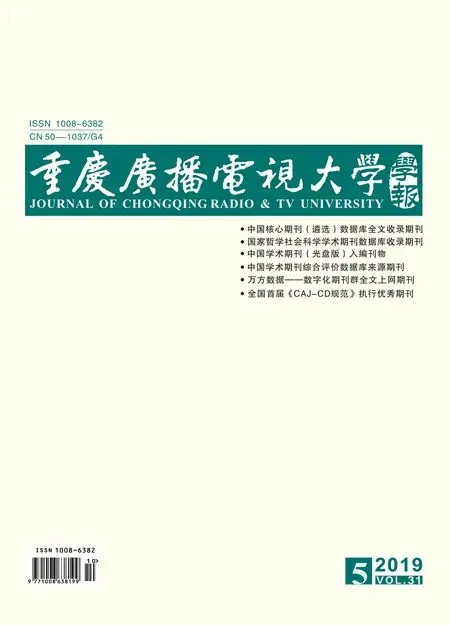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奖征文”文学活动考察
杨华荣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有奖征文”文学活动最早开始于晚清,伴随着现代报刊的发展而发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出版业发展迅速,为文学生产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物质媒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播和阅读方式。“有奖征文”这一文学现象正是适应新的体制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机制。征集者通过发布启事,广而告之文学创作的主题、宗旨以及遴选办法等,通过经济激励引导大众的创作方向,最终实现从征集者创作意图向应征者创作意图的转换。“有奖征文”这一特殊文学生产方式从实践上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繁荣与发展,它所提供的诸多历史细节深刻反映着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变革,以及社会普罗大众在面对这些变革时的思考与回应。
一、“有奖征文”文学活动的缘起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有奖征文”活动自19世纪末便开始萌发,从1874—1907年的《万国公报》有奖征文,1895年5月的“傅兰雅有奖中国小说”,到1907年的“《时报》小说大悬赏”,“有奖征文”活动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持续发展的过程。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奖征文”文学活动因其数量庞大、名目繁多、发展迅猛,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殊文学现象。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有奖征文”文学活动最繁盛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恰恰与抗日战争的时间线高度重合,1931—1945年这段时期,中国大地尽管战乱连连,生存多艰,但“有奖征文”文学活动反而有增无减,如国统区举办的“蒋夫人征文比赛”“《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稿”,解放区举办的“《红军》故事征文”“华北军民誓约运动征文”“《长征记》征文”等。通过对上述文学征集活动的考察,不难发现文学与政治的缠绕,征集者的政治立场与审美企图或隐或显地在其中呈现。抗日战争时期,各方在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紧了在意识形态与话语空间上的相互渗透与角力。于是,文学征集活动的政治功利性与文学观念的政治化,在此特殊时期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奖征文”活动与文学奖励制度,对于梳理贯通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丰富中国抗战文学的内涵有着显著的特殊意义。
本文将尝试打破政权与地域的描述格局,仅以1931年到1945年(战略反攻期时间较短,本文不作考察)的“有奖征文”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契合抗战主题的征文活动,试图寻找出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权力话语下“有奖征文”活动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各自对于战争局势的推动与回应。
二、局部抗战时期的主要“有奖征文”文学活动考察
1933年,上海《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策划和实施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无疑是局部抗战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新年的梦想”的征稿活动,主编胡愈之在征稿函中写道:“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咒诅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的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因此我们特发起,在一九三三年的新年,让我们大家来做一回好梦。对于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各人应该有各人不同的梦。我们打算把这些梦搜集起来,在《东方杂志》新年号发表[1]。”此次活动共发出征稿函约400份,引发了社会空前的关注,共征集到142人的来稿,其中不乏有如茅盾、周作人、冰心、郁达夫、老舍等教育界、文化界名流的稿件。《东方杂志》记者随即对应征者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以地域看,上海来稿最多,为78人,约占总数的55%;从性别来看,男性应征者138人,女性仅4人;以职业分,大学教授、作家、新闻记者、教育家等知识分子居多,占到总数的90%。此次征集,“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个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2]。这些梦深刻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件”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与思想取向。在时间节点上,1933年元旦正是中国历史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日本侵略者图穷匕见,在华夏大地上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让外部环境不断恶化,而国内局势亦不容乐观。国民党在军事上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在文化上则加紧对意识形态的管制,特别是对“左翼”文化的围剿以及对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既对国民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软弱与不抵抗感到深深的屈辱,又对其专制统治深觉厌恶与压抑。民间早已积累起强烈的不满,急于寻找释放的出口。在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历史转折点,《东方杂志》的新年梦想征集活动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让人们可以通过梦来释放对当下社会不确定性的焦虑与压抑,传达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与愿望,同时也让人们借此机会隐晦地批判和揭露现实的种种不合时宜。
在整个局部抗战阶段,从1933年到1937年,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同样举办了一系列名目众多的“有奖征文”活动。1933年,为推动革命诗歌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布“征求诗歌启事”,征集那些反映广大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诗稿,并计划编印《革命诗集》。此次诗歌征集活动共征集到65首歌谣、诗歌,汇编成《革命歌谣集》。早在1929年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中提到各政治部负责征集编写有关反映群众情绪的各种歌谣。此次征文活动正是毛泽东文艺政策的贯彻实施。1934年,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发布征稿启事,征集反映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实际情形和群众文化生活,表扬模范工作以推进落后区域工作的论文和文艺作品。1936年,《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央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征求艺术作品启事”:征求苏区内的对于目前的政治任务及一般的文化教育有宣传鼓动作用的歌曲、戏剧、活报、京调、小说、绘画等各种艺术作品。1937年3月15日,人民抗日剧社为开展戏剧运动,在《新中华报》上公开征集各种剧本,并承诺对入选作品予以一定的经济酬劳:“征求剧稿一经本社审查采用后酌奉薄酬——剧本自二元起至十元止,歌舞活报自五角起至二元止。”[3]1936年8月5日,毛泽东起草并与杨尚昆联名发出了一封电报,主题为《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电报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4]
启事引起了热烈反响,截止到1936年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总字数50余万言,来稿者中大多数是刚刚学会写字作文的年轻战士。作家丁玲和时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的成仿吾一道负责此次征文活动的文稿编辑工作。丁玲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中,并被稿件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丁玲后来回忆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5]1937年2月22日,《红军长征记》在延安编制完成,全稿30余万字,收录回忆文章110篇,歌曲10首,以及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幅。
除上述提及的征文活动以外,解放区举办的其他大型的主题征文活动还包括“给家乡写一封信”和“一日”系列征文。解放区的征文活动总体上只强调作品的通俗易懂,把“通俗活泼,易于阅读”[6]作为创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以求能够为工农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无论是官方话语的鼓吹呐喊,还是民间文学的描写讲述,一切的文艺活动无不围绕着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主题展开。一方面,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都需要普通民众对抗战这个主题有深刻的认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庸常生活也因为各式各样的集体创作被赋予非凡的意义,每个独立个体都能深刻地感知被凝聚的力量,共同完成对时代的想象和塑造。1936年5月,以茅盾和邹韬奋为核心的“中国的一日”编委会在《申报》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就是这样的集体想象共同体的典范。“中国的一日意在表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这确定的一日是随便指定的。我们现在指定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一日。凡是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于中国范围内海陆空的大小事故和现象,都可以作为本书的材料。这一日的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人物动态,无不是本书愿意包罗的材料。”[7]按征集者所说,此次征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此书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横断面,从中看到全中国一日之间的形形色色的一个总面目。
根据茅盾后来的回忆,“然而到了6月10日左右,从全国各处涌到的投稿之众多而且范围之广阔,使我们兴奋,使我们感激,使我们知道穷乡僻壤有无数文化工作的无名英雄对于我们这微弱的呼声给予热忱的赞助,并且使我们深切地认识了我们民族的潜蓄的文化的创造力有多么伟大!”[8]茅盾同时也提到:全国除新疆、青海、西康(1955年撤销)、西藏、内蒙古而外都有来稿,除了某些特殊人群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庞大的来稿堆中占了一个位置。
自“九一八”事变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东北的白山黑水已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国家前途有累卵之危,党派斗争不断加剧,举国上下均沉浸在悲哀情绪中。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急需一种提振全民士气的运动,“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全民总动员的大规模集体创作活动,文学本身的审美意义变得不再重要,它的真正意义指向在于其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大,使无数个普通人的生活样貌与心理状态被赋予了超越平凡的意义,并最终构建起一种民族的国家想象,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创作者都渴望获得被历史记录的资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将个体的感受融入整个民族的共同情感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凝聚着的中国的力量。
综合考察局部抗战时期的“有奖征文”文学活动,无论是哪个政治力量举办的征文比赛,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不如说是一种文学造势运动。征集者并不是想通过民间征集的方式来获得经典,其真实意图在于要将普通民众的庸常生活与当下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相融合。通过有意识的创作引导,让个体弱化,让集体彰显;让“我”变成“我们”,让“我”的生活与感受变成“我们”的生活与感受,让“我”获得身份的认同与归宿,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潜在的征集者意图向显性的集体创作意图的转换,最终实现文学创作从私人化写作到民间书写或集体创作转向。在整个局部抗战时期,集体创作对于整个抗战局势的推动无疑是有意义的。集体创作开启了共同记录时代、见证历史的叙述功能,有助于构建民族想象共同体,并最终实现凝聚思想、共谋抗战的政治动员目的。
三、战争防御时期与战争相持时期的“有奖征文”文学活动考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举世震惊,这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日军在正面战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击,从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短短15个月内,国民党损失了100多万军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陆续沦陷,其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供给不足,日军也逐步停止在正面战场上的军事进攻,抗日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迅速开辟,八路军、新四军利用日军进攻正面战场无暇多顾的有利时机,深入华北、华中,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基于此,日军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军事进攻重心转向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战争这朵“恶之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也促成了全民族觉醒与团结。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在漫长的八年时间里,中华各界始终未放弃对希望的坚守,文学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宣传力、号召力为抗战摇旗呐喊,不断提振民族信心与战斗士气。率先为此发声的征集者是一家在沪美国报纸“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1937年12月4日,《密勒氏评论报》在其所附印的“战事特刊”第一期上发布征稿启事。参照《民族诗坛》的转述:“该刊编者以二千伍佰元美金征求一首含义严肃而幽默,或讽刺之最佳诗篇,该诗之题材以述中日上海方面战事为限。收稿期定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首名得奖外,并另以一千美金之奖给予第二名。”[9]61根据《民族诗坛》后来的介绍,此次诗歌征集活动评出的第一名是一位名叫Silex的外籍人士,诗歌题目为“War”。编者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案此诗并不如其他诗稿,专述关于上海之中日战争,其所以能获第一名者,因所采格律及其诗之中心思想,皆为凡厌恶战争及屠杀之人所共感者也”[9]61。此次《密勒氏评论报》征文活动的参选作品均采用英文写作,因此在获奖名单中仅伍守常一位为中国人,其他皆为外籍人士。《密勒氏评论报》发起的这次“有奖征文”活动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奖征文”发布的时间为1937年的12月4日,距离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全面沦陷不足一月,在中华各界疲于迎战的阶段,《密勒氏评论报》以新闻报刊的敏锐性迅速做出反应,并眼光独到地在英语使用者中征集反映淞沪会战的诗篇,以“他”者的视角来谴责暴行、揭示真相,并凭借其美国新闻媒介的立场与影响力将日本侵华事实在全世界范围传播与揭露。此次征文事件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遭遇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谴责。
抗战时期,团结与凝聚是压倒一切的话语。相对于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塑造民族共同体处在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而在这一共同体框架下的每一类成员的情感、活动无不以抗战叙事为前提。1938年5月,“新运妇指会”(“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领导人宋美龄在庐山召开有共产党员邓颖超等人参加的妇女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纲领,1940年3月8日,“新运妇指会”以宋美龄的名义创办“蒋夫人文学奖金”并发起征文比赛,该奖项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凡关于妇女问题、妇女工作、妇女修养、妇女运动等研究著述,凡以在抗战中的妇女,妇女活动为中心题材”[10],均可报名参赛。随后,湖南、贵州两省相继效仿,分别创办“薛夫人湖南妇女文学奖金”和“吴夫人贵州妇女文学奖金”。“薛夫人”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夫人方少文,“吴夫人”则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夫人陈适云。
作为抗战时期专门针对女性群体设立的文学征文活动,“夫人文学奖金”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选拔女性作家。“夫人文学奖金”的征文宗旨明确规定应征者需要以“抗战建国”为叙事主题,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必须围绕抗战建国这一主题展开思考。从《时代妇女应有的自觉和解放》《妇女修养》《抗战期中我国妇运的中心工作》等获奖论文篇目来看,在危重的民族境遇之下,女性的生活与工作必须与国家、民族之需要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活动无疑是有意义的。
此外,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根据战争的发展形势也陆续开展了“华北誓约运动”“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 ”“抗战八年”等一系列文学征集活动。由冀中抗联组织发起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是该时期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创作活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开始筹划发动太平洋战争,拟向英美开战,为了把中国华北地区变成战争补给的重要基地,日军迅速调整作战策略,“把作战矛头指向华北,妄图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首当其冲,敌我‘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异常激烈”[11]。战争形势更为复杂,但广大八路军战士和敌后群众的抗战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为进一步激发军民的斗争意志和爱国热情,由冀中抗日根据地军区政委程子华提议,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确定1941年5月27日作为征文写作日期。征文活动在作家王林、孙犁等人的主持下有序开展,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应保证党政军民各部门及全体党员依照征稿办法供给稿件,按期寄交。”[12]417“下级同志不能写稿者,可自述意思,发动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代为记录,尽可能做到全党同志能写文章者,都写稿,不能写稿者,亦能口述思想,请人记录成稿。”[12]417因此,“冀中一日”征文活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地由各级组织落实到了每一位战士、每一座村庄。征文共收到来稿5万余篇,应征者从党员干部到普通士兵,从识字班的家庭妇女到乡绅秀才,甚至于,还有很多不识字的老人也通过请人代笔的方式参与到这场规模宏大的集体创作中来。从应征的稿件来看,有的揭露日军的暴行,有的歌颂战士的英勇,有的描绘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与建设。在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发生在成千上万的应征者身上的独特故事,共同构建起冀中平原宏大的抗战叙事体系。无论从应征规模还是从影响范围来看,我们今天依然认为“冀中一日”征文活动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冀中人民的生活与斗争”[13],再现了敌后根据地军民抗战的严酷性,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征文活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发了斗志,团结了民众,文学也逐渐从创作本身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斗争样式,起到了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的效用,为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凝聚了人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支撑。
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中最为煎熬的一段时期,敌我力量的悬殊、战事的复杂变化、英美救援的遥不可及等客观现实的接踵而至,使部分国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与恐惧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相持阶段举办的“有奖征文”文学活动更加强化其积极的宣传功能。无论是“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还是“冀中一日”写作运动,都是应对抗战形势变化做出的及时宣传与回应。总之,抗战时期“有奖征文”文学活动的主旨就是消除谬误,统一思想,动员和团结各界力量,凝聚共识与人心,为战争服务,为战事服务。
四、结语
考察抗战时期不同政治权力话语下迥异的政治导向、意识形态和激励机制,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变,丰富和拓展抗战文学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关注到,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介入,让原本各自为政的权力话语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作态势。尽管事实上,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评奖机制各有侧重,官方机构和民间媒体的选拔标准不尽相同,但在“抗战救国”大旗之下,团结和凝聚成为各方共同的主题,文学创作就不再是私人化的审美体验,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集体意义的塑造过程,“有奖征文”文学活动也不再是一种激励手段,而是一种动员与鼓动的政治宣传。正是通过不同党派或官方或民间对于“有奖征文”活动的精心策划,普通大众才参与到集体书写中来,也正因此,国家民族的集体想象才不断地被唤醒,不断得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