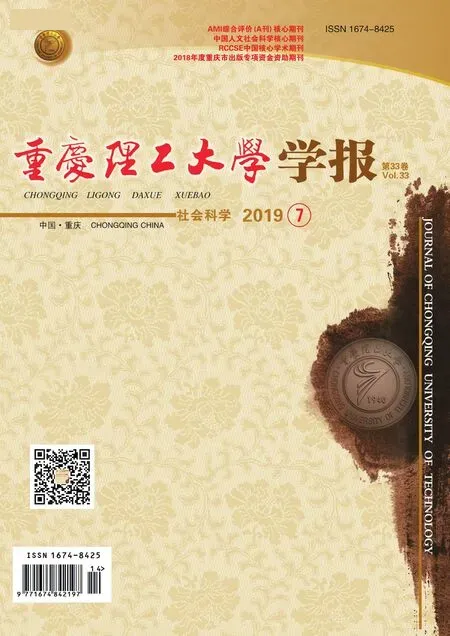《越南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规定变迁及启示
李 健,聂 菊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知识产权学院, 重庆 400054)
中国和越南两国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贸易、教育、文化等方面,更体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智力成果的交流与保护上。深入了解越南知识产权制度是减少两国合作壁垒、贸易摩擦的基础。本文拟结合现行《越南民法典》《越南知识产权法》、其他国家民法体例及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分析《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定的演变及特征,以期为我国知识产权“入典”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国外知识产权入典模式
法典是集体系化的思维与现行法律部门之大成,民法典是集民事法律规范的系统性立法文件[1]。世界各国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选择主要有单行法、纳入民法典、单独成典3种。从各国知识产权“入典”的典型立法例可知,目前世界各国在“入典”的立法范式选择中,主要有3种模式:纲领式、全面引入式、融合式。笔者拟结合这3种范式对越南及其他国家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定的模式进行梳理。
(一)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变迁
越南早期知识产权制度入典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从全面纳入式到纲领式的转变。《越南民法典》的起草始于1980年,经过15轮的草案稿送审,1995年《越南民法典》 审议通过,1996年7月1日正式生效。在后期的实施过程中,《越南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不相适应,随着2000年越美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美国施压要求越南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称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1995年越南提出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愿景,在入世谈判中,WTO成员国对越南法律制度提出了质疑,1995年《越南民法典》系统性、稳定性、适应性明显不足,与新的民事法律规范相抵触。迫于前述重压,2005年《越南民法典》第一次修订,并于2006年生效。《越南民法典》将知识产权以专编的形式纳入,相较于1995年的版本,2005年版虽沿用了旧民法典的编排体例,但在知识产权部分对其权利主体、客体、内容及转让等方面作出了更为详尽、全面的规定。但2015年,《越南民法典》第二次修订时,考虑到知识产权法典的体系化已相对成熟,知识产权入典最终被“单独成典”所替代,知识产权从民法典中移除。由此,越南知识产权法完成了从单行法到入典再到成典的发展历程。
(二)其他国家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立法模式
1.纲领式入典。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最早在民法典中规定了知识产权,《意大利民法典》采用的是以纲领式的形式总领各单行法,抽象出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共性纳入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笃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但该法典尚未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编排,涉及的权利客体有限,仅涉及作品与发明,缺乏包容性[2]。2004年1月生效的《乌克兰民法典》对知识产权的规定沿用了意大利的纲领式立法技术,如以专章的形式设立知识产权一般规定,包括知识产权的概念、与传统财产权的关系、主客体、权利取得与处分及侵权责任等方面的内容[3]。
2.全面纳入式入典。《俄罗斯民法典》采用了全面纳入式的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2006年底,《俄罗斯民法典》第四部分以全面纳入式的编排体例将智力成果和区分标志编入,前期制定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相应被废除,至2014年,该民法典已历经10余次修订。《俄罗斯民法典》以9章327条的编排糅合了与国际条约Trips协议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包括著作权及邻接权、育种成果权、集成电路布局设计、生产秘密权、区别标志权及智力活动成果权,并就权利的内涵、取得、处分(使用)及保护等方面做出了细致的规定。从辩证法角度考察《俄罗斯民法典》第四部分以纳入式立法代替单行法规定知识产权的立法选择,该法典虽使知识产权的规定更具稳定性和体系化,但权利类型、权利保护等规定上不免暴露出弊端。例如,从商业秘密的本质属性出发,其能否被视为一种权利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国际惯例上无商业秘密权的说法。再从权利的保护角度考量,民法典主要调整的是民事关系,而权利的保护离不开行政规制和刑法的救济,而在民法典中纳入行政或刑事规范是否会引起法律的冲突是值得思考的。
3.融入式入典。1995年《蒙古民法典》对知识产权的规定采用了融入式模式。在总则编、所有权编、债权编分别糅合了知识产权,该法典总则编的一般原则部分规定了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的依据之一是“创作智力成果”,所有权编的一般规定部分则阐明了智力成果为所有权的客体之一,并规定了智力成果的客体类型主要包括发明、发现、作品、实用新型及商标,还规定了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产生等方面的内容,债权编则规定了智力成果权可以成为转让标的物,为他人占有和使用。
4.民法典与知识产权分离模式。在知识产权入典问题上,也有国家采取分离式,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与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法德采用分离式是囿于历史因素的限制,两部法典的编纂基于以罗马法的债权、财产权为内容的民法体系,而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在民法典制定前已采用了单行特别立法的模式。而越南、俄罗斯、意大利等国采用知识产权入典模式是法律现代化与体系化的要求,是现代民法典的范式[4]。
结合前文对知识产权“入典”典型国家立法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全面引入式和融合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基于知识产权私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入典”将成为立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技术性等特征,在现行的立法技术下,始终难以与民法体系的稳定性相契合。知识产权是否“入典”既需要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基于此,纲领式“入典”模式对知识产权作出概要式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纲领式“入典”的典型国家包括越南,《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的规定呈现出阶段化特征,笔者将在下文对其编排体例做详尽分析。
二、《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定的立法架构演变:从“纳入民法典”到“单独成典”的历程
(一)1996年越南知识产权规定从单行法向全面纳入民法典演变
《越南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呈现阶段化特征,经历了从知识产权“入典”到知识产权“去民法化”的转变。《越南民法典》在1996年生效后,于2005年和2015年修订两次。1996年民法典出台后,即废除了前期制定的《工业产权法》《著作权保护条例》《技术转移法》等单行法,此阶段越南采取的是全面纳入式的知识产权“入典”模式[5]。而在历经10年的实践检验之后,越南在面临外部强压、内部法律适应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对1996年版民法典进行了实质性的修订。
(二)2005年知识产权规定从全面引入向纲领式引入民法典演变
2005年《越南民法典》仅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主客体、内容及转让做出了概要式规定。而具体的内容,如权利的取得与保护的条件、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则由单行法《越南知识产权法》以18章221条的形式对版权及邻接权、工业产权、植物品种权及权利保护这四大部分作出了详实的规定。
2005年《越南民法典》第6编仍是关于“智慧所有权与技术转移”的规定,但采取了纲领式的知识产权“入典模式”,同时期,越南也加紧了知识产权法的立法进程,于2005年颁布了《越南知识产权法》。2005年《越南民法典》第6编以3章22条的形式对知识产权作出了概括式规定。其第1章为著作权及邻接权的规定,主要是关于作者、著作权的主客体、内容、权利人、合作作品的权利归属及权利转让这几方面的规定,相较于1996年版,2005年版的规定更为明晰和具体,比如对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划分更为清晰合理。第2章为工业产权与植物品种权的规定,主要包括了权利的设定、客体、内容及转让4个方面的内容。第3章是关于技术转让的客体及例外,以及转让合同的规定,该部分的规定更具原则性,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依注册取得的工业产权技术转让合同采用登记生效制。
(三)2015年知识产权专编从《越南民法典》移除
2015年,《越南民法典》将知识产权专编移除,2017年1月新民法典生效后,知识产权的权利取得、维持、行使及保护等所有内容将依据《越南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越南虽作为经济较落后国家,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制定出与国际条约与惯例基本一致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广泛的保护客体、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巧妙衔接及法律体系严密等方面均体现了越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6]。
(四)越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不足
从《越南民法典》以及《越南知识产权法》可知,越南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如权利界定不明晰、规定与国际惯例相冲突等。2005年《越南民法典》以及《越南知识产权法》均明确规定了“商业秘密工业所有权”[注]《越南民法典》第751条规定了工业产权与植物品种权的内容,第2款规定了商业秘密权,原文为: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s to business secrets shall belong to the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that obtain the information to be lawfully…详见Civil Code,No:33/2005/QH11,day 14 month 06 year 2005.,而Trips协议对未泄露信息的保护并未授予实体性权利,这样的规定显然是违背国际惯例的。值得肯定的是,越南知识产权“入典”的理念是先进的,但立法技术不仅与国民法律素质有关,也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7]。再如《越南民法典》及《越南知识产权法》规定地理标志权属于国家,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仅有使用权,此处强调的是地标标志的公权性,而根据《巴黎公约》与Trips协议的规定,国际惯例定义的地理标志的权利特征应表现为集体性权利,地理标志的非私权性和非公权性的本质特征并不因其被纳入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而改变。
三、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定“去繁就简”的阐释
在19世纪民法典制定的早期,由于历史原因,《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并未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法德采取了分离式的立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果这种新型财产的社会地位日趋重要,基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需求,部分国家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选择了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的立法模式,意大利、俄罗斯、荷兰及乌克兰等国成为在民法典编纂中纳入知识产权规定的典型代表,知识产权规范尚未体系化是这类国家采用入典式立法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执行力角度考量,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入典”模式都存在不足:采用纲领式“入典”的意大利、越南等国,过于原则性的规定执行力较差,更具象征性;采用“纳入式”的俄罗斯,由于知识产权不仅涉及民事规范,还涉及刑事及行政规范,仅在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典中悉数规定尚有缺陷;采用“融入式”的蒙古国,由于知识产权与传统的所有权、债权的性质有差异,知识产权的无形性、特殊性、易变性更明显,难免存在无法适用的情况。然而,从辩证角度看来,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入典又是成功的,经过数载的实践检验,各国都有加强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的趋势。越南作为知识产权“入典”的典型代表,下文笔者将从法律关系、国际环境及法律体系化发展等角度分析越南知识产权“入典”及民法典移除知识产权编的立法动因。
(一)基于知识产权与民法的关系分析入典的动因
1.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为私权。相对于其他民事权利而言,知识产权产生的历史比较晚,但是到目前为止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Trips协议肯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地位,知识产权“入典”不仅在于突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更致力于以更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知识产权,缺乏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的民法体系将是不完整的。越南在加入WTO时就做出了按照Trips协议调整知识产权法律及条文的承诺,越南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入典是回归“私权本位”的必然要求。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同为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两部法律体现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基于此,《越南民法典》总则就阐明了民法典调整的范围涉及民事关系中的人身或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是对其私权地位的肯定。
2.调整范围的核心为民事法律关系。从《越南知识产权法》可知,知识产权不仅涉及民事规定,还涉及行政规定,如《越南知识产权法》第100条涉及的工业产权登记程序属于行政程序。知识产权也涉及刑事规定,如《越南知识产权法》第18章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补救措施。从法律制定的宗旨角度看,知识产权法或民法制定的目的在于调整平等的社会关系,行政程序旨在规范权利的取得与义务的履行,刑事规范旨在为民事权利提供保障。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民事法律规范,但是知识产权并不因存在知识产权行政规范或刑事规范而不能纳入民法典。
3.知识产权与民法具有同样的财产属性。知识产权在市场交易中的经济地位不容小觑。知识产权质押、信托、融资、出资等投资方式的兴起更加体现了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基于罗马法的历史影响,现有的财产理论限定在有形财产上,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财产将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地位。财产形态并非财产的本质决定因素,财产所指的利益才是财产权益的共同指向,由此可知知识产权应是广义上的财产[4]。因此,从调整的法律关系及法律本质角度看,2005年《越南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纳入规定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笔者在我国学界关于知识产权“入典”的讨论中亦发现,学界反对“知识产权”入典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知识产权中公法性规范与民法的私权属性相冲突;(2)知识产权的易变性与民法的稳定性相抵触;(3)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及知识产权单行法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等。基于上述民法与知识产权法关系的分析,前述反对知识产权“入典”的理由难免存在不合理之处。
(二)基于国际环境分析入典的动因
民法典乃一国百年大计,民法典应包括哪些规范内容应是充分准备和审议的结果。《越南民法典》是集众多法律英才、汲古今内外之精华而完成的事业。越南在制定民法典的前期准备中,主要参考了《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立法模式[8]。荷兰及俄罗斯都是采用知识产权“入典”模式的典型国家,我国民法通则的作用类似于民法典,亦对著作权、专利权及商标权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成为越南知识产权“入典”选择的一大外部因素。
此外,经济全球化决定了一国不可能在封闭环境内发展,与域外的经济、政治及文化交流的多样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越南早在1995年之前就提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鉴于自身知识产权立法水平明显落后于世界通行公约,基于与世界接轨的需求,越南不得不对现有法律进行大刀阔斧的修订。在立足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越南出台了包容性更强、架构更合理的现代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的规定纳入。越南在历经10年的谈判协商并不断提高立法水平后,于2006年如愿以偿加入了WTO。
(三)基于法律体系分析从“入典”到“去知识产权编”的原因
2015年《越南民法典》明确将知识产权编删除,但民法典仍肯定了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地位[注]详见2015年《越南民法典》第8条: Bases for establishment of civil rights:…4.Outcomes of labor,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r creation of subj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知识产权纲领式“入典”模式正式被知识产权法典所取代。《越南民法典》中取消知识产权编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法律适用的实践检验,知识产权法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旧民法典对知识产权的原则性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明显不足,且知识产权的私权地位并不因从民法典中移除而改变。笔者下文将结合知识产权的体系化及知识产权入典存在的问题,分析2015年《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编被移除的原因。
1.越南知识产权法律的体系化。从2005年《越南民法典》中知识产权部分的规定可以看出,越南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与国际公约及惯例基本一致,体现出较高的立法水平。2005年民法典增加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几乎囊括了与国际公约一致的保护对象。在知识产权入典实践中,越南承认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本位及财产权属性,将知识产权纳入最具体系化、稳定性的民法典之中,为知识产权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越南民法典》第一次修改时,越南知识产权法同年颁布,并于2009年修改了部分法条。越南知识产权法对版权及相关权、植物品种权、工业产权及权利保护的民事、行政及刑事方面的内容作出了详尽的规定,权利义务内容完善、保护对象全面、保护措施严密等特征突出,以总则与分则相衔接的体系使得知识产权法律更加体系化、稳定化。越南知识产权单独成典的立法选择正是知识产权体系化、稳定化发展的结果。
2.知识产权纲领式入典的缺陷。《越南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从繁到简的转变,不仅是知识产权法本身体系化发展的结果,也是2005年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定的缺陷与不足所致。从其具体规定可知,2005年《越南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原则性规定与具体性规定的衔接与适用存在着法律漏洞与法律冲突等问题。2005年版《越南民法典》制定的时间早于《越南知识产权法》,对于民法典中知识产权部分新增加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之前的单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不连续性可能导致法律出现断裂或漏洞。另外,虽然民法典第6编基于保证民法稳定性的目的而做出了概要式规定,但始终未以条文的方式明确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顺序,遑论过于原则性的规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差异性显著,以共性抽象法提取知识产权的公因子规则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是值得考究的。除此之外,知识产权“去民法化”旨在减少法律冲突,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毫无争议,但对他人创作的智力成果的保护也离不开行政与刑事的公权力规范,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必然导致存在法律冲突或者民法典不能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等问题。
四、越南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规定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民法典编纂如何回应知识产权的发展,笔者认为越南从“纳入民法典”到“单独成典”的历程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无论是“入民法典”抑或“单独成典”,均为知识产权制度化的路径。但从立法技术的选择来看,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零散性特征明显,知识产权制度理论发展较不成熟,尚无单独成典的立法基础和技术条件。而“概要式入典”的立法模式实际最为可取,如同 2005年《越南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专编仅对知识产权作出概要式规定,细化规定则交给了国会随后起草的《越南知识产权法》。这种立法技术既协调了《越南民法典》的稳定性和知识产权的易变性特征,同时又删除了关于具体制度和行政属性的条款,回应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也确保了知识产权领域法律关系的调整不致出现断层[8]。越南2015年起草的《越南民法典》才移除知识产权编,完全形成了“去民法化”的知识产权体系,这是长达10年的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探索与检验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分则编纂需要讨论的重点不在于知识产权是否纳入民法典的问题,而在于知识产权怎样纳入民法典。
我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3月1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民法典分则各编的制定顺势被提上议程。为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的号召,我国学界对“知识产权入典”的讨论十分激烈,各界关于知识产权是否应纳入民法典以及纳入民法典的立法模式争论不一。囿于《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立法价值取向,知识产权应是优先于债权、所有权的财产权益,因而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编纂议程的第二步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科学的。笔者下文将梳理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关于“知识产权入典”的立法模式构想。
(一)我国现行知识产权的立法选择
单行立法模式衍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制定的专门法律制度,在成文法体例国家则表现为民事规范下的特别法[9]。与编纂专门法典或纳入民法典的立法体例相区别,我国采用了分离式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笔者下文将结合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情况及《民法总则》对知识产权的规定,分析“入典”是我国必然趋势的现实理由。
1.修订知识产权单行特别法的边际成本递增。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单行特别立法是通常做法。我国关于知识产权规定的立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商标权及专利权三大方面。除单行立法外,我国不仅制定了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植物品种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方面的保护条例,还出台了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规定、司法解释等。依据各国的立法情况,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工业产权、著作权及相关权两部分构成。因此,各知识产权法律部门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共性。虽然我国单行法规较为健全,但各法律部门不成体系,权利规范界限不明晰,法律规范之间重复、适用冲突、相互矛盾的情况明显。另外,在立法成本上,若从法律部门的角度看,单行法的修订成本明显低于“入典”或“成典”模式,但法典更具稳定性,修订的成本主要在于首次制典时的成本,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定单行法修订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2.《民法总则》对知识产权的定性规定及适用空间。相较于《民法通则》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民法总则》过于简单,仅第123条[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3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涉及知识产权。《民法总则》第123条第1款规定了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基于此,可以明确的是,我国在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就以宣示性方式明确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和财产属性。第2款规定了知识产权“7+”种客体形态,第8项为兜底条款,采用了严格的法定主义,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这与现行知识产权单行法律相冲突。如《著作权法》关于作品范围的规定兜底条款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而《民法总则》将行政法规予以排除。值得肯定的是,《民法总则》中的规定仍为法律适用及立法留下了额外的空间[10]。由第1、2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民法总则》对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是概括性的,承认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地位及民事属性,这与Trips协议等国际公约及通行惯例一致,《民法总则》与知识产权相关法表现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3.知识产权“入典”是复归传统和反映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伟大的法典总是与政治、社会及技术变革遥相呼应[11],传统的有形财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逝去,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形态,新兴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扩张了传统的财产类型。民法典作为最具包容性、稳定性的民事法律规范,始终保持着时代适应性,知识产权应在民法典中享有一席之地。从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来看,我国知识产权各法律部门相对零散,且存在冲突,如著作权的权利取得制度与专利商标的权利取得制度的差异。缺乏体系化思维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最主要的障碍,而民法典是最具体系化的制度,从知识产权制度规则中可以抽象出与民法的共通性规则[12],诸如本质是私权、调整范围是民事权利、知识产权仍具有财产形态等,民法的稳定性有助于知识产权体系化发展。基于此,知识产权“入典”是回归私法本位的必然要求。
(二)关于“知识产权入典”的立法构想
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实情况来看,民法典编纂的开篇之作已肯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和民事属性。我国知识产权起步较晚,立法理念及立法技术更应在立足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编排体例的研究应聚焦于如何选择知识产权“入典”的立法技术,即采用纳入式、纲领式、列举式3种之一还是另辟蹊径[注]我国目前主张的知识产权入典模式主要有3种:① 纳入式,即将知识产权法规整体移入民法典,易继明及徐国栋为主张纳入式的典型代表;② 纲领式,即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单独设编作出原则性规定,具体规定交由知识产权特别法,吴汉东为主张纲领式的典型代表;③ 列举式,仅民法典总则对知识产权作出概要式规定,不单独设编,梁慧星为列举式的典型代表。。笔者认为,相较于纳入式与列举式,纲领式为知识产权“入典”模式的最佳选择。列举式的规定过于开放,将导致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名存实亡;纳入式的规定过分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民事财产属性,实则知识产权是融合了民事、行政、刑事的法律部门,整体搬迁式将导致僭越法律规范;纲领式以专编概要式地对知识产权权利的性质、主客体、内容、使用与保护等作出一般性规定,更具操作性与科学性。下文笔者将结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对知识产权“入典”提出如下构想:
1.防止知识产权 “入典”后的规范冲突与重复。2017年9月中旬,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课题组推出了《民法典》知识产权编建议稿,强调了制定《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的总体思路是避免冲突与重复[注]历时四月,三易其稿,民法典知识产权编学者建议稿,http://news.zhichanli.com/article/4702.html.。若在民法典中构建纲领性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旨在将民法的体系化思维、原则及精神映射到各知识产权特别法中去,知识产权编的结构应符合民法作为一般法,而将知识产权作为特别法的关系。因此,若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体系,避免重复立法与法律冲突是重要的立法考量因素。
2.正确对待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我国各界关于知识产权 “入典”问题的争论包括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关系,即 “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公权抑或私权”。对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郑成思教授按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决定而负责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知识产权专篇。虽然年底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第31次会议并未按原计划将“知识产权”作为专篇,但包括郑成思教授在内的诸多法学家均认为知识产权中的行政及刑事作用与管理公权力的行政及刑事作用的规范目的、宗旨并不相同,不能将知识产权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本质相混淆[13]。刘春田教授在“‘十三五’时期知识产权焦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知识产权的私权特性决定了知识产权的血统为民事权利[14]。吴汉东教授亦认为知识产权已经渗透到传统私法的各个领域,如权利的继承、质押融资、许可合同等[15],而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正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或人身关系。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是知识产权“入典”编排的前提与基础。知识产权法作为补充型特别民法,符合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原则及立法价值取向[16]。我们应从辩证的角度理解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它们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使得其发展与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密不可分,知识产权的权利取得、行使及保护的稳定性需要强制力保障,这也导致了知识产权的公权色彩逐渐扩张,但知识产权入典是回归“私权本位”的必然要求。
3.提高立法技术。知识产权的私法本质使其完全具有了入典的资格,至于在民法典中如何编排和架构,笔者认为,《越南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专编对知识产权作出概要式规定的方法值得我国借鉴。在具体内容上,吴汉东教授提出的点面链接模式值得参考[15]。《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部分已肯定了知识产权的民事属性及客体范畴,此即以点定性。在知识产权专编中,仍有必要设立总则,总则对知识产权作出一般规定,如明确定义;而在分则中,则应根据知识产权的权利取得、行使、限制、保护等方面作出与单行特别法相衔接的概要式规定。
五、结语
我国《民法总则》是民法典与知识产权的衔接,《民法总则》已经提纲挈领式地肯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及财产权地位,知识产权“入典”是《民法通则》的立法传统,又是民法典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回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求。至于立法技术问题、入典的编排结构和条文,则要求在进一步提高全民素质基础上,加大知识产权法宣传力度,加强立法论证,提升立法质量,科学合理地安排知识产权“入典”的编排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