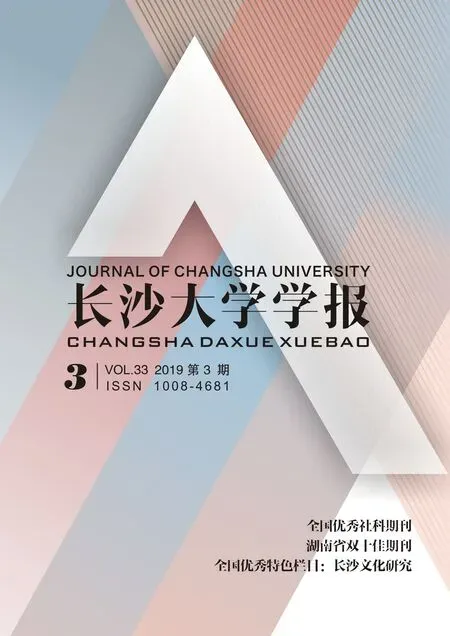自我怀疑及其本土化研究前瞻
宫黎明,张俊杰
(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自我怀疑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自我怀疑就一直存在。作为元认知的一种,自我怀疑是伴随着认知过程而产生的情绪体验。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对自我怀疑的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而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分析了自我怀疑的内涵、应对策略等研究热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自我怀疑本土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 自我怀疑的内涵
在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心理学家看来,追求确定性和清晰性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动机,它们与理解的需要一并处于人类动机系统的中心位置[1]。人们希望能够快速、清晰地了解事物并预测事物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是现实往往相反,很多时候,人们对自己都不能准确地认知和判断,陷入到不确定(Uncertainty)的状态,导致自我怀疑的产生。
Van den Bos 和 Lind认为自我怀疑是怀疑自己的行为或状态,它是一种“主观的对自我看法的怀疑或不确定”[2]。当人们对事物的真相或现实不确定时,这种(主观的)状态会导致对事件真相的怀疑;当这种不确定状态涉及到自我,就是自我怀疑。
自我怀疑与自我价值、自尊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自我价值包括两个方面:自我悦纳(Self-liking)和自我胜任(Self-competence)。自我悦纳是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客体进行评价,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自我胜任是对自己一般自我效能感的评估。Tafarodi 和 Swann在2001年的模型中指出:自我胜任是自尊决定性的、独特的维度[3]。而自我价值和自尊又是自我的核心成分。依据上述模型,自我怀疑就是对自我胜任能力的质疑。在此基础上Matthew D. Braslow等人提出:自我怀疑主要指对自我所认同的能力的不确定感[4]。按照这一观点,自我怀疑就是对自我能力的元认知,具体来说,自我怀疑被认为是对个人能力不确定性的元认知表现。
前人在研究中成功地揭示了自我怀疑与能力的关系,明确了自我怀疑与能力不确定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能力、自主与归属感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三大基石”[5]。拥有能力是人类内在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是根深蒂固的。能力需求的实现与否是决定个体内在动机的根本,能力需求同样也是成就动机的核心。Susan Fiske强调:控制或能力需求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跨越了社会心理学的范畴[1]。同样的,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也具有强烈的动机性质。
二 自我怀疑的研究热点
当前,西方学术界对自我怀疑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这些方面。
(一)自我怀疑与自尊等的关系
能力和价值是自尊的两个基本维度。如果一个人把自我价值与其能力相对应,那么自我怀疑可能就会伤害到他(她)的自尊。当个体对重要的能力不确定时会引发到自我价值的怀疑,这就可能威胁到他的自尊。西方大量的研究发现:自我怀疑与自尊呈中等程度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从-0.44 到 -0.68[6]。自我怀疑高的个体,自尊水平相应较低[4,7]。除了与自尊的负相关,自我怀疑还会引起不同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大量的研究认为,长期的自我怀疑与消极情绪、低自尊水平、无价值感等负性心理状态相联系[4,6-7]。
(二)自我怀疑的应对策略
如果个体对在特定情境中需要做出反应的能力不确定,即意味着可能面临失败,会引起防御性、保护性行为。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个体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自我设限(Self-handicapping)和主观高成就(Subjective Overachievement)是两种最常用的解决长期自我怀疑的应对策略[6,8-9]。
1.自我设限
自我设限[10]作为一种事前就准备好的预防性保护策略,指的是个体在活动之前,就找好借口,一旦失败了就将失败归因于其他原因而不是能力,比如说,身体不好、睡眠不足等影响了成绩。如果个体对自我能力不确定,对自我产生怀疑,他们的成功愿望和自我形象就会受到威胁。自我设限为个体提供了混淆失败真正原因的机会,它用各种障碍(药物、酒精、拖延症等)来解释失败,而不是个体的能力不足。实际上,这些障碍干扰了行为结果,以牺牲成功的代价保护了自我怀疑者的能力观。对自我设限者而言,对失败归因暗示的关注超过了对成功的渴望,对他们而言,结果的影响往往比结果本身更有分量。但是,自我设限策略的使用并没有减少自我怀疑,反而导致自我怀疑常态化,个体也因此难以获得关于自身能力水平真实、有用的信息。
近三十年对自我设限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到个体学习、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学业自我设限[11]的研究最为深入。
2.主观高成就
主观高成就是另外一种应对自我怀疑的策略,与自我设限的自我破坏策略不同的是,主观高成就者采用额外的努力来避免失败,确保成功;其特点是高度关注能力表现与高自我怀疑相结合,这种策略进一步破坏了对个体能力的正确归因。在经历自我怀疑时,如果个体关注的是他的能力,可能就会采取自我设限策略(例如更少的练习);如果个体关注的是良好表现,可能就会采用高成就策略(例如更多的练习与努力)。但是,与自我设限策略的结果一样,高成就者一旦取得成功,就会混淆表现与能力之间的关系。虽然主观高成就者往往都能获得积极的结果,但他们无法得知是自身的能力还是努力,或是两者的结合,还是运气使然带来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对自身能力不能正确地认知和判断。
3.自我能力否定倾向(Imposter Phenomenon,简称IP)
这种策略很少被提及,但却是自我怀疑最常见的经历。最早是由CLance和Imes于1978年提出的[12]。按照客观标准评价,自我否定者是成功的,可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成功;他们的成功只是“成功”地欺骗别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是有能力的。当自我否定者取得成功以后,会把成功归结于其他因素(如幸运或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他们的自身能力。因此,他们认为自己不配拥有需要能力的位置。自我否定者在获得成功时,也会短暂欣喜,但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的不当归因,成功的经历并不会减少他们的自我怀疑,反而会导致他们的自我价值更加不稳定,而这又可能会使个体反复经历自我怀疑。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自我否定倾向现象与个体不良应对策略、低自尊、神经质相关[13]。自我否定与自我怀疑之间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8,与自我设限相关也很高[14]。
4.防御性悲观(Defensive Pessimism)
防御性悲观是Norem 和 Cantor于1986提出的一种应对自我怀疑的策略[15]。为了应对可能的失败,个体故意降低期望和目标,减少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防御性悲观者“凡事先往坏处想”,他们把悲观当成是一种管理焦虑的策略,通过运用“降低期望”等做法,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防患未然之上,来消除心中对自我能力不确定的紧张。对于防御性悲观的个体而言,持有消极预期会减少失败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一旦取得成功,意外的惊喜会给个体情绪更长久的影响。尽管对成、败情感反应的预期作用似乎对防御性悲观者来说是积极的,但这种对成败结果的归因模式,很可能让防御性悲观者将失败归因于能力,将成功归因于诸如运气之类;而归因的这种变化又导致了自我怀疑的延续,不管成败结果如何,自我怀疑可能会一直存在。
除了自我设限、高主观成就等策略,还有像拖延症、抬举他人现象等,都反映了人们对于能力的自我怀疑,为了避免丧失自我价值感,导致自尊水平下降,而在心理和行为上采取的管理策略。
(三)对自我怀疑的干预
随着对自我怀疑内在结构的揭示以及对自我怀疑应对策略的了解,人们开始尝试运用心理干预治疗技术,消除或减少自我怀疑。
1.合理情绪行为疗法在自我怀疑上的运用
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合理情绪行为疗法(REBT)来干预、消除自我怀疑。合理情绪行为疗法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不是由事件本身引起,而是由于个体对事件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引起的信念,导致在特定情景下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后果,个体不当的认知和信念才是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直接原因。
运用合理情绪行为疗法来干预自我怀疑,主要使用四个标准技术来改变不合理的认知信念。它们分别是功能辩论、经验辨析、逻辑分析、哲学思辨[16]。功能辩论技术是试图让自我怀疑者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信念与感觉良好的目标之间的不相容之处;经验辨析技术指的是要求自我怀疑者提供证据来评估自我怀疑相关的认知;逻辑分析技术是对自我怀疑者进行追问,通过对不同结果的追问、反思让其质疑所持的观念;哲学思辨目的是为了说明自我怀疑者的怀疑对他/她的经验的限制。通过这些技术,让自我怀疑者对自己所持的绝对观念、不合理信念进行辨析、纠正,从而消除、改善自我怀疑。
2.正念技术对自我怀疑的干预
正念(Mindfulness)[16]指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On Purpose)、将注意力引导在当下(In the Present Moment)及不做判断(Nonjudgemental)。正念的特点之一是开放,即使对消极的想法也是开放的,当个体没有正念的时候,情境性因素可能会诱发个体采取自我设限或主观高成就的方式来试图减少因自我怀疑而导致的焦虑;但是,如果个体有了正念,不仅仅是对这些想法和感觉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当它们与不合理信念相联系的时候,更有可能谨慎而不是盲目地做出反应。个体考虑事情的本质,会深思熟虑地做出反应,而不会受到个体自我介入的影响;这样可能会减少自我怀疑和无效的安全行为之间的联系,比如自我设限。
正念干预技术可以减少对预期结果敏感而产生的大量负面影响,这种技术对高水平自我怀疑的治疗疗效较好。通过研究发现正念干预技术能有效缓解个体的焦虑水平,降低自我怀疑,正念干预部分调节了自我怀疑对自我设限影响,相关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
三 自我怀疑的本土化研究
对于自我怀疑的研究始于西方,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分析,大多数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以西方被试来进行的。中国心理学界对于自我怀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人对自我怀疑的认识。
(一)自我怀疑内涵、结构的本土化
自我怀疑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中西方个体都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在西方以“自尊”为本的文化语境下,自我怀疑主要是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由于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不确定,诱发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自尊水平,所以对西方对自我怀疑的研究是基于能力之上的,关注的是与能力不确定而引发的个体元认知体验以及与此相关的情绪、行为和认知策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化社会,自我的结构中包含了家人、朋友,与西方人的自我结构有较大差异,对自我的认识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注重他人的评价,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面子”。为了保全“面子”,免得“自我”受到损伤,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对自我言行进行怀疑,这种怀疑更多的是作为动机的力量来帮助他人提升自己,所以在对自我怀疑现象进行中国本土化研究时,需要在“面子”文化的前提下,分析“自我怀疑”的内涵,厘清中国人“自我怀疑”的内在结构,探究其与西方语境中的“自我怀疑”有何异同。
(二)自我怀疑量化工具的本土化修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自我怀疑现象开展研究,需要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Oleson(2000)等人的自我怀疑分量表[17]进行修订编制。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不是特别理想,在删除了2 个区分度不良的项目(5、7) 后的问卷α系数才达到了0.74[18]。除此量表,国内尚无其他关于自我怀疑的量化工具,而Oleson的自我怀疑分量表是在构建主观高成就(SOS)问卷的框架下编制的,其理论依据完全是西方语境下对自我怀疑的解读。对中国人的自我怀疑现象进行研究,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下,基于自我怀疑的本土化内涵,开发更有针对性,信效度更有保证的工具。
(三)中国人应对自我怀疑的策略及特点
不同的文化对自我结构、自我认知有很大影响,同样对自我怀疑的认识也可能会有差别。在面对自我怀疑时,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思想上、行为上有什么样的表现,与之相应的中国人应对自我怀疑的策略和手段是否与西方人一致,有哪些异同点,这些是今后在对自我怀疑现象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探讨的。
(四)关于自我怀疑的跨文化实证研究
早期对自我怀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负面效应,但最近的研究发现,自我怀疑并非一无是处,对于不同个体而言,自我怀疑受到个人内隐能力观的调节[19],对于不同能力的个体,对能力持有渐变的观点改变甚至逆转了自我怀疑对活动成效、心理健康、任务参与度等的负面效应。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大多数都以西方人为被试,而自我怀疑在东方儒家文化里具有什么样的含义,中国人的自我怀疑水平呈什么样的状态,中西方个体的自我怀疑现象有何异同,还需要进一步的探析。所以在对自我怀疑的研究中,跨文化的实证研究非常重要,通过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不同样本的对比,了解自我怀疑在不同文化个体身上的表现,分析他们在面对自我怀疑时的反应,对待自我怀疑的态度,这些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探索自我怀疑的实质,从而寻找有针对性的、恰当的缓解自我怀疑的措施。
(五)寻找与自我怀疑相关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除了个体内隐能力观会调节自我怀疑水平对活动成效的影响外,在自我怀疑与各种应对策略之间,人的个性特征、社会环境因素起着什么的作用,还有利用认知行为疗法对自我怀疑进行干预,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干预的效果,干预措施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慢慢厘清的。寻找自我怀疑相关变量之间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只有对自我怀疑现象有了全面的了解,弄明白它的作用机制,知道哪些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才有可能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避免自我怀疑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