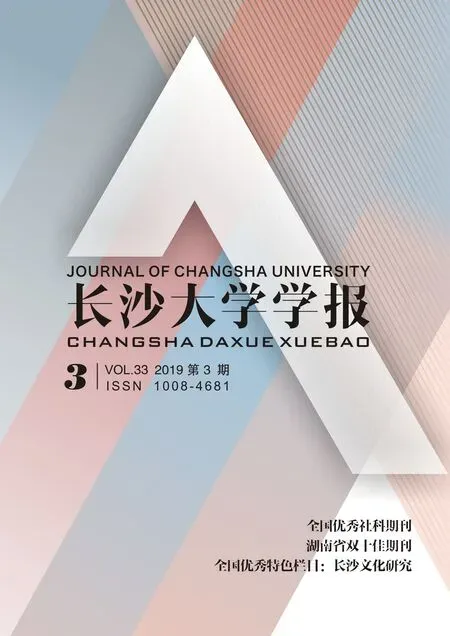狱读瑜伽与转俗成真
——黄宗仰对章太炎佛学研究的推助
麻天祥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详细追述了其思想变迁的三个阶段,概述了其法相唯识哲学的从入之途。他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孜孜以求经国之政术,因而奉荀、韩之说为圭臬,此即所谓“俗”的第一个阶段。“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触发了他求“是”求“真”的兴趣。后因苏报案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及其他法相宗典籍。“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与这位朴学大师的思维方式最相契合,因而“转俗成真”,开始了其学术思想的第二个阶段,即谓之“真”的纯思辨的道路。他援西入佛,“格以大乘”,以佛解庄,“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为其法相唯识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又援佛入儒,“以庄证孔”,进而确认孔子之学,根本也在破除一切主观成见,“本以菩萨利生为务”。于是通过对名相的具体分析,达到了对世界的宏观把握,使其平生所治朴学和经国之术得以理论上的升华,终又“回真向俗”,搭建成法相唯识哲学的理论构架,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转俗成真、回真向俗,显然同佛教哲学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二阶段,囚系上海,专修法相唯识之学,实在是和黄宗仰的佛学因缘而结的哲学之果。
宗仰上人,亦名中央,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俗姓黄,字宗仰(亦名中央),江苏省常熟市人,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辛酉岁十月十日生。自幼读书,颖悟异于常人,博览群籍,尤工诗古文辞。稍长就学于翁同龢,时翁已举进士,阅宗仰文章,辞茂义幽,莫测其际,因谓之曰:“子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傥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宗仰有感而悟,遂栖心内典,视功名如粪土。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年十六岁时,投本邑三峰寺,依药龛和尚落发出家。
三峰寺,全称三峰清凉禅寺,因合乌目峰、龙母峰、中峰而得名。乌目山僧亦得名于此。相传建于南朝齐梁之间,亦为明末禅僧汉月法藏住锡之所,常熟之首刹。清军入关,法藏门下多抗清义士,而被雍正旧案重提,视之为魔及魔子魔孙而予以口诛笔伐。丁闇公有诗颂之曰:
三峰汉月古禅堂,钟板飘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门竟有蔡忠襄。
上述蔡忠襄,亦抗清义士,由此可见法藏门下不甘屈辱的民族气节。同样说明三峰寺夙有反清传统,宗仰以缁衣投身革命,也是三峰寺民族气节长期熏染的结果。
宗仰于禅修之余,研习英、日、梵等文字,旁及诗、书、画及金石之学,卓荦绝俗。受戒于金山江天寺,法名印楞,世称宗仰上人。1901年即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活动,为早期同盟会会员。1903年,著名的《苏报》案发,以主论名在清廷通缉之列,因而东渡日本,继续反清的民主革命。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曾继蔡元培之后,任中国教育会第二任会长。其佛学融合禅教,以禅宗而讲华严,也曾主刻《频伽精舍大藏经》,并创华严大学。于佑任称其:“实佛门之龙象,亦吾党之瑰奇。”
早在1902年,宗仰与章太炎夙未谋面,但对章太炎的学问、志向钦敬有加,而神交已久。宗仰尝赋诗《赠太炎》曰:
神州莽莽事堪伤,浪藉家私脏客王。断发著书黄歇浦,哭麟歌凤岂佯狂?
“断发著书”、“哭麟歌凤”,但在宗仰的眼里并非披发佯狂之士,诗中充分表达了对章太炎的理解与推崇。翌年三月,章太炎与黄宗仰结识于爱国学社,后经“苏报案”遂成生死之交。章氏身陷囹圄,宗仰除设法多方营救外,并指引章氏学佛,因而成就了一个以庄解佛,借法相唯识的资料实现哲学革命的国学大师。宗仰曾有《寄太炎》诗两首,云:
凭君不短英雄气,斩虏勇肝亿倍加。
留个铁头铸铜像,羁囚有地胜无家。
飒飒风霜点铁衣,音容憔悴须发肥。
稔君狱读瑜伽论,还与书信理合非。
应当承认,佛学作为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于清末民初已经蔚为时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父章浚“中年颇好禅学”,其师俞樾也“茹蔬念佛”(《章氏笔述》《制言》第43期)。但极有个性的章太炎,起初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身于佛学思辩之海,既不把佛学作为经世之武器,更缺乏对佛教的真信仰。二十七岁那年,精通法相且为其至交的夏曾佑曾建议其购览佛典,欲引为佛学之同道,但章氏“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之后,对佛家仍然持一种拒斥的心理和批判的态度。他对谭嗣同《仁学》援引佛典、谈心说仁甚不以为然,而有“怪其杂糅,不甚许也”(《自定年谱》)之言。他还撰写《公言》,批判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宗教之士”“阻塞人之智虑,使不获公言”,由是慨叹佛教“犹不免欲上古野人之说”(《干蛊》)。至三十岁,宋恕促其读《三论》,仍然不能引起他对佛学的兴趣。其后,偶读《大乘起信论》,似有所悟,“常讽诵之”(《自定年谱》)。同年(1903年),章氏因苏报案囚系上海狱中, “私谓释迦玄言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菿汉微言》),因而沉浸在繁难艰涩的佛典和无边无际的玄想之中。在狱中,章氏多方罗致佛典,“晨夕研诵,乃悟大乘深义”(《自定年谱》),而“达大乘深趣”(《菿汉微言》),终于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章氏有《狱中致黄宗仰论佛书》,可窥其学佛的心得,以及以佛学推进哲学革命的思路。摘要如下:
宗仰大师左右:得梵文阿弥陀经后,即复一函,并略举所得求诲。
间取哲学诸书以与内典对照,则彼熔合无少分相异者。夫见识、现实,名相虽殊,而实际最难分别。心王、心所,体用有别,而他书无此名词。详细思之,堪德(即康德)所谓“事前之识”者,即能见;所谓“事后之识”即能现。此说自堪德发明后学者无不奉为圭臬。削宾霍野尔(今译叔本华)立“认识充足义”,分四范畴,其中所谓先论理的真理、“先天的真理”者,亦皆此能见。有此三说,而后内典大明。庄以俗情言之,能见则当时已现,能现则当时已见,何见、现之殊也?
自佛家观之,色心不二,则识中本自有物。而凡人思想所及者,即不得谓其物为无有。此非主观武断也。今之所见不过地球,华严世界本所未窥,故科学所可定者,不能遽以为定见(此亦陆野儿(或译罗素)之言),况世间常识耶?夫此地球龟无毛,兔无角矣,安知宇宙之大,不更有龟毛兔角。以所未见,而谓之无,此非特于主观不合,亦于客观不合也。龟毛兔角,犹曰恒理所有。今使设一念曰:有石女所生之儿,有一物亦方亦圆亦三角,此理所必无也。然而既有此念,则不得谓无此事。即使遍游华严世界,初不见此事,而此事仍不得言无[1]。
显然,此信写在宗仰赠梵文阿弥陀经之后。文中所谓事前之识、事后之识,应当指先验(先验感性、先验知性,以及先验理性)和自在。至于能见、能现都是佛学中的特殊范畴,用哲学的语言大致相当现象与本体,或者通俗地说现象的存在与生成万物的本原。用龟毛兔角说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突出佛学对有限科学性的超越。所有这些都说明,章太炎在狱中因得宗仰的指引与帮助,完全沉湎于对法相义理的系统反思,并以之求教于他的指路人了。于此,他不仅品味把玩佛典,而且取西方哲学家之言与佛家学说对照,以至于内典大明、茅塞顿开。他强调,佛学中的名相分析与西方哲学不谋而合,人的感知或直观素材,同摄取、识别这些感知对象和素材的能力,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相对而无差别。并通过对宇宙无限与“凡人思想所及”有限的比较,证明“色心不二”、“识中有物”的唯心唯识观念,告诉人们认知无限的可能性。一场求真求是,以西方哲学对校、诠释佛学名相,进而以佛学改变传统思维的哲学革命,便在大墙下面的囚室中孕育成长起来了。狱中的章太炎,一反过去厌佛之常态,托友人四处罗致佛典,得《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法相典籍,以及梵文《阿弥陀经》,晨夜研诵,手不释卷,由是而悟佛家奥义,与佛学结下终身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他还诱导邹容学佛,要用佛家的心性之说,以解邹氏三年牢狱之忧。对佛学异乎寻常的关爱,与前此以往判若两人。后来他在《支那内学院缘起》一文中告诉人们说:“中遭忧患,而好治心之言,始窥大乘,终以慈氏无著为主”,正说明他由儒入佛、儒佛兼治的思想转折,以及借法相唯识资料实现哲学革命的心路历程。
毫无疑问,这里也有宗仰的一分贡献。就现有的资料看,对章太炎狱中学佛,融汇中西的色心观念等,宗仰上人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对于章、邹二人的革命气概和蹈死如饴的大无畏精神又给予高度赞扬,有《寄太炎》[2]诗曰:
大鱼飞跃浙江潮,雷峰塔震玉泉号。
哀吾同胞正酣睡,万籁微闻鼾声调。
独有峨嵋一片月,凛凛相照印怒涛。
神州男子气何壮,义如山岳死鸿毛。
自投夷狱经百日,两颗头颅争一刀。
宗仰的这首诗,显然是为章太炎和邹容二人所作。首联以浙江名物——钱塘江潮、雷峰塔震赞颂太炎;颈联以峨眉山月凛然相照,形容邹容做大狮子吼。尾联“自投夷狱经百日,两颗头颅争一刀”,不仅把章、邹二人气壮山河,重义轻死,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烘染得淋漓尽致,而且也让当时呼吁睡狮猛醒、肇兴中华、推翻帝制,将共和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精神跃然纸上。
另,民国四年,袁世凯欲做皇帝,诱骗章太炎至北京,幽囚龙泉寺。囚禁中,章太炎白天读经,夜则梦入地狱做判官,连续四十日,于是有致宗仰上人书数札。其中,虽事涉鬼神,却以佛法论之。其中《报宗仰和尚书》[3]原文如次:
仰上人侍者,快接复曹,神气为开,所问幻梦事状,今试笔述,愿上人评之:
去岁十二月初,夜梦有人持刺,请吃午餐,阅其主名,则王鏊(王鏊,震泽人,明武宗时贤相)也。走及门外,已有马车。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饷;旁有陪客:印度人、欧洲人、汉人皆与。各出名刺,汉人有夏侯玄、梅尧臣。
余问王公:“读史知先生名德,而素无杯酒之欢。今兹召饮,情有所感。”王曰:“与君共理簿书事耳。梅君则总检察,吾辈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与君,则主亚东事件者也。”余问王曰:“生死为寿量所限,轮回则业力所牵;大自在天尚不能为其主宰,而况吾侪?”梅氏答曰:“生死轮转,本无主者,此地唯受控诉,得有传讯、逮捕事耳。传讯者不皆死,逮捕则死矣。既判决处分后,至彼期满释放后,又趣生诸道,则示非此所主也。”
余念此论,颇合佛法,与世俗传言焰摩(阎罗王)主轮回生死者不同。因复问言:“铁床铜柱,惨酷至极!谁制此法者?”皆答曰:“此处本无制刑法之人;吾辈受任,亦是阎浮提(指地球)人公举,无有任命之者。法律,则参用汉、唐、明、清及远西日本诸法,本无铁床铜柱事也(一切皆是唯心所现,唯业所感;且阴间是鬼道,不同于地狱)。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则有百年。而笞杖之与死刑,皆所不用。吾辈尚疑狱卒私刑,以铁床铜柱,困苦狱囚,因曾遣人微服往视之,皆云无有。而据受罪期满者所言,则云确受此痛。”
余曰:“狱卒私刑,非觇察所能得。吾此来当与诸公力除此弊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圣贤同具慈悲心)遂返。
明日,复梦到署视事。自后夕夕梦之,所判亦无重大案件,唯械斗谋杀,诈欺取财为多。如此幻梦不已,而日曜(星期日)之夜,则无此梦。余甚厌之。去岁,梦此二十余日。一日,自书请假条焚之,夜亦无梦。
一夕,尽换狱卒,往询囚徒,云:“仍有铁床铜柱诸苦。”因问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视之则不见,归而大悟 (唯心之道)。佛典本说此为化现,初无有人逼迫之者,实罪人业力所现耳。余之梦此,是亦业感也。 今春以人参能安五脏,买得服之,并于晚饭后,宴坐观心一小时顷,思欲去此幻梦,终不可得。
来示谓不作圣解,此义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瞋心所现故耳。吾辈处世,本多见不平事状。三岁以来,身遭患苦;而京师故人,除学生七、八人外,其余皆俯仰炎凉,无有足音过我者。更值去岁国体变更问题,心之瞋恚,益复炽然,以此业感,而得焰摩地位,固其所宜。息瞋唯有慈观,恐一行三昧,亦用不着。慈观见《涅槃经》,虽说其义,而无其法,亦如竟无从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所瞋之事,有何体性?能瞋之心,作何形象?未尝不随念观察,而终不能破坏。
章炳麟和南 三月三十日
应当说,这是章太炎向宗仰上人请求开示的信函,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能获得宗仰回复的信件。章太炎狱中论佛书同样如此。但这封信中说:“来示谓不作圣解”,足以说明,此前宗仰已经有信回复章太炎,并告以“不作圣解”,所谓“来示”者也。章太炎显然也是以佛学“唯心所现”、“唯业所感”的唯识学理论解析这一现象的。章太炎认为:以比量观照,知其幻妄;从现量而论,却不能息其噩梦,实在是“由瞋心所现故耳”。也就是说,是由于愤怒不平的怨恨之心,日复一日,炽然而盛,以此业感,化现而成阎罗地狱之相而已。故唯有以慈悲之心,方能息瞋恚之业,只是不知具体方法如何,而无从下手。以此求教上人,显然还是没有理解“不作圣解”的深意,哲学家和禅僧的差距也就洞若观火了。
综上所述,章太炎因苏报案囚系狱中,对佛学的兴趣不发则已,一发则穷源究委,倾全力营造起他的哲学体系。《读佛典杂记》是他在狱中“晨夜研诵”的结晶,而《狱中致黄宗仰论佛学书》及《报宗仰和尚书》等,则是其“转俗成真”的真实记录。在此他不仅品味把玩佛典,而且取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的著作“与内典对照”,“而后内典大明”。其意在说明,法相宗的名相分析与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不谋而合;人的感性印象,或直观素材与摄取或识别这些印象素材的能力,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相对而无差别。同时通过对宇宙的无限和“凡人之思想所及”有限的论述,证明“色心不二”、“识中有物”的唯心唯识观念,表明认识无限的可能性。一场求是求真,以西方哲学对校、诠释佛学繁难名相,以佛学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便在大墙下面的囚室之中孕育起来了(关于章太炎的法相唯识之学详见拙著《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相关章节)。
由此还可以看出“转俗成真”是章太炎思想上的重要转折,而佛学,特别是法相宗的名相分析,则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思维基础。同样可以肯定,黄宗仰对章太炎学佛的诱掖、推助,正是章太炎“转俗成真”的哲学革命的助缘。而从章太炎在宗仰的指引,或者说影响下钻研佛法的成就,也可以看出,佛教哲学对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渗透,以及思想家,或者说哲学家公然为佛弟子而研习佛法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