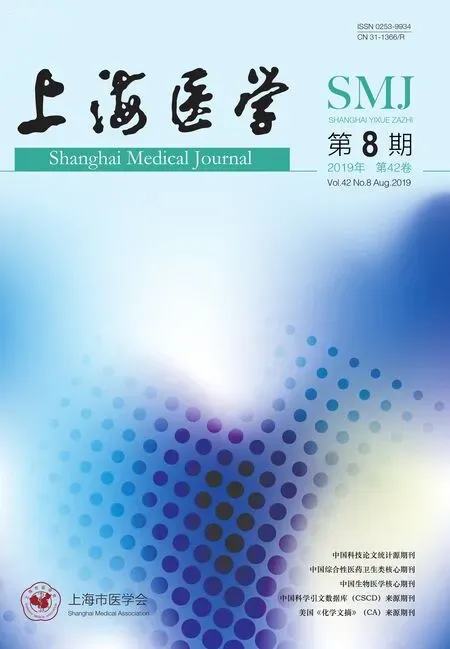药物性肝损伤的影响因素和预后评价
刘成林 万远太 曹丽娜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由药物和(或)其代谢产物引起的肝脏损伤,发病率约为0.014%~0.019%[1]。DILI是最常见和最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是导致急性肝衰竭(ALF)的主要原因。随着临床新药的不断出现,以及药品滥用现象增多,近年来DILI发病率呈上升趋势。DILI预后一般较好,停用肝毒性药物后,多数患者能逐渐恢复乃至痊愈,约有5%~10%的患者可发展成慢性肝病,约10%的患者因ALF死亡或不得不接受肝移植[2]。在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对DILI预后判断的相关因素和预后评分工具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影响DILI预后的相关因素
1.1 年龄与性别 高龄、女性可能与DILI预后不良有关。老年患者基础疾病较多,服用药物种类更复杂,器官功能衰退,同时机体抵抗力下降,一旦出现DILI,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杜水仙等[3]认为,年龄是与住院时间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越大,DILI发生率越高,预后越差,住院时间相应延长。Chalasani等[1]研究发现,65岁以上患者胆汁淤积型损伤更常见,但与65岁以下患者相比,其病死率和需接受肝移植治疗的比例却无明显差异。Bonacini等[4]的研究对27例因蘑菇中毒所致的DILI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65岁以上老年患者预后差的比例(40%)明显高于年轻患者(10%),3例死亡和1例接受肝移植的患者均为女性。年龄与性别对DILI预后的影响有待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
1.2 药物特性 刘丽娜等[5]研究显示,中成药和中草药在所有引起DILI的药物中所占比例最高,且预后较其他类型药物更差。国外对草本植物和膳食补充剂(HDS)所致的DILI进行研究[6],结果提示,HDS比非HDS所致DILI的预后更差,死亡或接受肝移植患者达13%,而非HDS仅为3%。而Vuppalanchi等[7]认为,DILI的预后可能更多与宿主反应有关,而不是药物特性。他们分析了383例由单一口服处方药引起的DILI病例,发现肝毒性药物在不同剂量、不同肝代谢比例或不同溶解度的条件下,DILI患者病死率和肝移植率无明显差异。
1.3 合并基础疾病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有慢性肝病基础的患者更易发生DILI,但合并有基础肝病的DILI患者常较无基础肝病患者的预后更差[8]。Chalasani等[1]研究亦提示,合并基础肝病的DILI较无基础肝病的DILI有更高的死亡风险(16.0%比5.2%)。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DILI预后不良。Schutz等[9]研究结果表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并发DILI患者的预后较差,院内病死率达27%,3个月病死率高达35%。而杨君洋等[10]研究发现,AIDS合并DILI患者的预后无明显差异,预后不良情况包括病情危重放弃治疗、要求自动出院,以及死亡,但不良的预后均由基础疾病引起,与DILI无直接联系。上述两项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可能与制定的病例入选标准不同有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肠道菌群失调与各种肝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密切相关。肠道菌群与肝脏通过门静脉在解剖和功能上有着紧密联系,被称为“肠-肝轴”。肠道菌群失调时易产生肠道细菌易位,细菌产生的内毒素对肝细胞有直接毒性,同时激活单核巨噬细胞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促进肝衰竭的发生;另外,肠道菌群是肠道内氨产生的关键因素,氨中毒是肝性脑病重要发病机制之一,肠道菌群紊乱可使产氨增加,促进肝性脑病的发生[11]。Li等[12]通过大鼠实验发现,肠道病原菌感染亦可明显加重急性肝损伤。有研究[13]结果表明,补充益生菌可以通过恢复肠道菌群平衡,增加对致病菌的定植抗性,减轻肝脏损伤。
1.4 临床表现与病理类型 DILI临床表现多样,包括乏力、纳差、恶心、呕吐、皮肤瘙痒、肝区不适、黄疸等,部分患者有皮疹、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关节酸痛等过敏表现[14]。伴黄疸的特异质性DILI患者中约有10%死亡或需要接受肝移植[15]。Chalasani等[1]认为,严重的皮肤反应往往预示着预后不良,在9例伴严重皮肤反应的DILI患者中,6例为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3例为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结果4例死亡,1例发展为慢性肝损伤。Ichai等[16]发现,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的严重DILI或肝衰竭患者的预后较差,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不能改善。DILI的病理改变几乎包含了各种肝脏病理变化,不同病理改变对DILI预后的影响少见报道。Bonkovsky等[17]对26例肝活组织检查(简称活检)提示为胆管消失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伴胆管损伤DILI患者的病死率高达27%,故认为胆管损伤程度与预后密切相关。
1.5 临床分型 根据受损靶细胞的不同,DILI可分为3种临床类型:①肝细胞损伤型,丙氨酸转氨酶(ALT)≥3×正常值上限(ULN),且ALT与碱性磷酸酶(ALP)升高程度比值R≥5[R=(ALT实测值/ALTULN)/(ALP实测值/ALPULN)];②胆汁淤积型,ALP ≥2×ULN,且R≤2;③混合型,ALT≥3×ULN,ALP≥2×ULN,且2 1.6 肝功能指标 传统的反映肝损伤的指标包括血清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ALP、总胆红素(TBil)、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等。血清TBil水平升高、白蛋白水平降低和凝血功能下降均提示肝损伤程度较重[14]。Zimmerman很早就提出,若用药期间患者出现了血清ALT/AST>3×ULN和TBil>2×ULN的肝细胞型黄疸,则约10%可发展为ALF,即著名的“Hy’s法则”。另有研究[21]提示,轻、中度DILI(血清TBil水平<85.5 μmol/L)发生ALF的可能性极低。最近Hu等[20]的研究同样提示,血清TBil峰值水平是DILI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Kim等[22]对23例蘑菇中毒所致DILI的研究发现,高TBil水平和APTT延长与病死率显著相关,所有第3天血清TBil水平>85.5 μmol/L或APTT>50 s的患者均在医院内因ALF死亡。传统的肝功能指标仍是目前临床判断肝损伤严重程度和预后的重要标准。 1.7 生物标志物 线粒体功能障碍是DILI肝毒性的重要机制之一,谷氨酸脱氢酶(GDH)、线粒体DNA (mtDNA)和核DNA片段(nDNA)常作为线粒体损伤的生物标志物被测量。Mcgill等[23]研究发现,对乙酰氨基酚(APAP)所致ALF死亡患者的血清中这3种生物学标志物含量均高于存活患者,而两组ALT值相似,提示血清GDH、mtDNA和nDNA用于预测患者预后可能比ALT更可靠。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 (CPS1)是肝脏线粒体中最丰富的蛋白质,在线粒体基质中催化氨和碳酸氢盐转化为氨基甲酰磷酸盐,这是尿素循环的第一步和限速步骤[24]。Weerasinghe等[25]研究发现,血清CPS1水平能反映肝脏损伤严重程度,在ALT持续偏高时,血清CPS1水平快速下降提示预后良好,表明CPS1也可以作为预测肝损伤预后有价值的标志物。 目前认为,免疫反应在DILI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最近有研究提示各种免疫因子对其预后有预示作用。Steuerwald等[26]检测了78例DILI患者发病时和发病6个月后血清中27个免疫标志物,包括14个细胞因子、7个趋化因子和6个生长因子,并与40例健康志愿者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9个免疫标志物有差异表达,4个免疫标志物[IL-9、IL-17、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bb、调节激活正常T细胞表达分泌因子(RANTES)]和血清白蛋白的低值能预测早期死亡,显示先天免疫相关细胞因子的高表达与预后不良有关,而自适应细胞因子的高表达则提示预后良好。 微RNA(miRNA)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较小,且具有调节作用的非编码RNA。肝特异性miRNA包括miRNA-122、miRNA-21和miRNA-192,这些分子会抑制相应目标信使RNA,从而调控特定的细胞蛋白和细胞表型[27]。肝源性miRNA可能是具有高敏感度和特异度的APAP肝毒性的生物学标志物,同时对APAP过量所致DILI患者的预后判断有重要意义[28]。有研究[29]通过对角蛋白18(CK-18)的分析测量,发现高血清浓度的CK-18对APAP过量致DILI的不良预后有预测作用,入院时CK18水平可以预测早期急性肝损伤患者的后续发展。同样,早期的GDH升高也可以预测后期肝损伤加重。另外,与那些自行恢复的患者相比,在死亡或接受肝移植的患者血清中,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水平也更高。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CSF1)能促进肝巨噬细胞生成,而肝巨噬细胞是有效肝细胞增殖,以及来源于门静脉系统致病物质清除的必要条件[30]。Stutchfield等[31]发现,接受肝脏手术的患者血清CSF1水平升高程度与肝切除的程度成正比,同时低水平的血清CSF1与APAP诱导的ALF的病死率升高有关。半乳糖凝集素9(Gal-9)是库普弗细胞产生的一种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在肝病患者尤其是DILI患者中明显增多[32]。Rosen等[33]对比了149例DILI导致的ALF患者和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个体的临床数据,发现ALF患者血浆中Gal-9水平高于健康者,若Gal-9水平≥386 ng/L,则更有可能为发展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在Gal-9水平>690 ng/L时死亡或需行肝移植的风险明显增加。 另一个潜在的早期标志物可能是甲状腺激素[34]。当广泛的肝细胞死亡时,甲状腺激素可能刺激肝细胞复制并激活祖细胞[35]。甲状腺功能亢进可继发于ALF早期,一项研究[36]认为这将提示ALF预后不良,但尚需要在更大的患者群体中进行验证。继发性肾脏损伤也是ALF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之一。肾损伤分子-1 (KIM-1)已被证实是急性肾损伤的高灵敏度和特异度的生物学标志物。最近的研究[37]已经证实,在APAP诱导的急性肝损伤死亡或需行肝移植的患者中,血清KIM-1水平显著升高,并且比血清肌酐更敏感,能更准确地预测患者预后。 2.1 Hy’s法则及其改进 Hy’s法则是临床试验中预测药物引起严重肝损伤最常用的方法。它首先由Zimmerman博士提出:伴有黄疸的肝细胞损伤型DILI患者病死率约10%。之后,Robert博士为其制定了正式的生物化学检测标准(血清ALT/ AST>3×ULN和血清TBil>2×ULN)。美国FDA将其作为评估新药肝毒性的重要指标之一。Robles-Diaz等[19]试图对Hy’s法则进行优化,比较了3种Hy’s法则的标准方法,包括TBil>2×ULN和ALT> 3×ULN,ALT与ALP升高程度比值R≥5,新的比值(nR)≥5[nR=(ALT最高实测值或AST最高实测值/对应ALTULN或ASTULN)/(ALP实测值/ALPULN)]。发现在确诊DILI的时间点,使用R和nR标准预测ALF特异度分别为67%和63%,而单独使用ALT水平预测ALF特异度仅为44%;ALT和nR标准的灵敏度均可达到90%,R标准则是83%。他们认为在DILI确诊的时间点,Hy’s法则的nR标准提供了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最佳平衡。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新的复合算法(AST>17.3×ULN,TBil>6.6×ULN,AST/ALT>1.5),它预测患者发展为ALF特异度为82%和灵敏度为80%。另外,最近的研究[21]提示,Hy’s法则预测ALF的特异度可达92%,但灵敏度仅为68%,并开发了一种基于血小板计数和TBil水平的评分方法(药物诱导肝毒性ALF评分=-0.006 912 92×血小板计数(×109/L) +0.190 915 00×TBil(mg/dL,1 mg/dL=17.1 μmol/L),当得分>-1.081 41时,提示发展为ALF的风险高,其灵敏度为91%,特异度为76%。 2.2 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和英国国王学院标准(King’s College criteria,KCC) MELD是由Malinchoc等对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患者的预后分析后首先提出,后经Kamath修改完善,计算公式为R=9.6 ln [肌酐(mg/dL, 1 mg/dL=88.4 μmol/L)]+3.8 ln [TBil(mg/dL)]+11.2 ln(INR)+ 6.4 ln(病因:酒精性或胆汁淤积性为0,其他为1),结果取整数。该公式用来判断晚期肝病患者的预后,R分值越高,提示病情越严重,短期内死亡的可能性越大。Jeong等[38]研究了MELD评分在DILI预后的预测价值,他们收集了2010年1月—2012年12月在韩国首尔的Asan医疗中心被确诊为DILI的患者数据,对首次就诊后30 d内行肝移植或死亡的患者进行分析。在213例DILI的患者中,预后不良的患者占13.1%。多因素分析表明,MELD评分和血红蛋白水平是30 d内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MELD评分单独C统计值为0.93(95%CI:0.89~0.97),联合血红蛋白水平后为0.94(95%CI:0.90~0.97)。MELD评分的最佳截断值为20.5,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9%和84%。最近6项研究[39]共纳入了526例ALF患者,使用MELD评分截断值30.5~35.0,汇总灵敏度达77%,特异度达72%,阳性似然比为2.76,阴性似然比为0.31。美国胃肠病学协会(AGA)最新指南建议将MELD评分为30.5用于预测ALF的预后[40]。为了进一步提高MELD的准确性,研究者提出了众多改进方案,包括MELD联合血清钠模型(MELD-Na)、MELD联合血清磷模型(MELD-P)、MELD联合肝脏供体年龄模型(D-MELD)、动态MELD模型等,但其准确性和适用范围仍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证明。亦有研究提示,将MELD评分和某些生物标志物组合能取得更好的预测结果,如CK-18或Gal-9,但因技术手段受限,目前难以在临床普及。 KCC是O’Grady等基于对588例ALF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构建的。对于APAP引起的ALF,动脉血pH值、PT和肌酐水平与预后显著相关;而在非APAP引起的ALF,病因、年龄、TBil水平、PT和起病方式(急性或亚急性)均与预后相关。在美国的一项前瞻性研究[41]中,对275例APAP引起的ALF患者进行KCC测试;结果仅完成40例,其中19例死亡,6例接受肝移植。研究证实,KCC对不良预后的预测有较高的特异度(92%),但灵敏度较低(26%)。KCC的高特异度意味着符合标准的病例中,被不必要移植的患者较少。然而,他们的灵敏度较低,表明大量不符合标准的病例在早期未能识别,可能错失肝移植的机会。Karvellas等[42]最新的试验发现,KCC联合血清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FABP1)能显著提高KCC预测准确性。确诊第1天单独KCC ROC的AUC为0.552,KCC联合FABP1为0.711;在第3~5天时,单独KCC的AUC为0.604,联合FABP1为0.797。 近年来,鉴于KCC灵敏度较低,有专家认为其应该被MELD取代。Devarbhavi等[43]比较128例DILI致ALF患者MELD评分和KCC评分与病死率的关系后,认为MELD判断ALF患者预后比KCC更可靠。MELD和KCC的AUC分别为0.76、0.51,MELD评分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2%和74%,KCC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仅为41%和51%。然而,McPhail等[44]在最近的meta分析中评估了APAP和非APAP诱导ALF患者的KCC和MELD评分,发现KCC和MELD的整体诊断准确性仍具有可比性,MELD不能完全取代KCC,MELD评分对非APAP诱导的ALF的预后评估中更有用,而KCC评分在APAP诱导的ALF中更可靠。 KCC和MELD评分因其临床生物化学检测简便性,目前仍然是应用最广泛ALF预后评分工具,但它们并不完美。MELD的低特异度和KCC低灵敏度已被许多研究证实,它们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也需进一步研究。尽管研究者提出了众多改进模型,但是仍未能在较大的试验中进行验证或受限于实验室条件难以普及。考虑到ALF临床过程中的波动,在一个特定时间点的数据收集可能具有有限的效用,任何预后模型评分仅能反映肝功能受损的当前状态,对于其预后判断需要重复计算,考虑可变的临床过程。此外,模型中涉及的临床指标,可能是ALF过程的二次反映或会受到治疗过程的影响,如血清肌酐受患者血容量不足、利尿剂过度使用等因素影响;INR也可因胆汁淤积造成维生素K吸收不良而延长。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评分结果产生偏倚,因此,在临床应用和评估时也需一并考虑。 总之,尽早准确预测DILI患者临床转归和预后,有利于临床医师选择正确治疗方式,以免延误肝移植的时机。而对DILI预后判断仍有许多因素有待商榷,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虽然预后评分工具能为医师判断提供直接帮助,但临床工作中仍需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分析,以做出最佳临床策略。2 预后的评价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