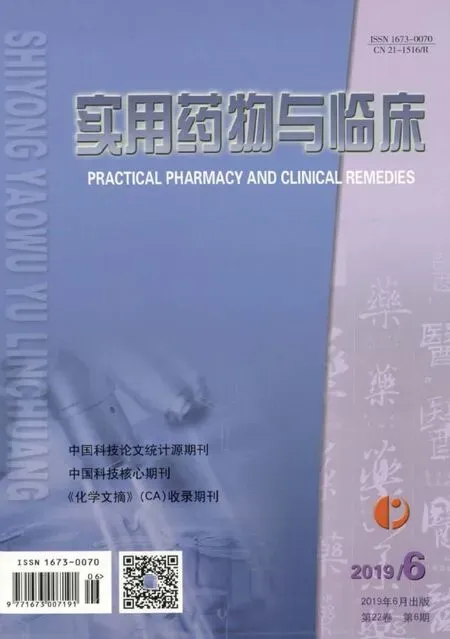生物制剂治疗炎症性肠病的进展
关雅迪,郑长清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慢性、进行性、可致残的疾病。虽然氨基水杨酸、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等大多数非生物制剂药物能改善症状,但不能阻止潜在的炎症过程,也不能改变疾病进程[1]。抗肿瘤坏死因子α(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α,anti-TNF-α)药物(包括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赛妥珠单抗)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IBD的治疗方式,改变了2种疾病的病程,降低手术率、住院率,提高黏膜愈合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2-3]。然而,仍有大约30%的患者对抗肿瘤坏死因子α原发性无应答,随着时间的推移,另外1/3的患者将继发性失应答[4]。抗肿瘤坏死因子还有局部或急性输液反应和迟发性过敏反应、机会致病菌感染,甚至恶性肿瘤的风险[5-6]。考虑到这些问题,新型生物制剂和口服小分子药物已经或正在开发。
目前已批准用于治疗IBD的6种生物制剂:4种抗肿瘤坏死因子制剂,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戈利木单抗(Golimumab)和赛妥珠单抗(Certolizumab-pegol),以及2种抗整合素制剂,那他珠单抗(Natalizumab)和维多珠单抗(Vedolizumab)。本文介绍在IBD中使用生物制剂的实际见解并回顾这些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介绍了治疗IBD中生物制剂的国际指南以及成本问题、患者偏好和目前正在开发的制剂等。
1 抗肿瘤坏死因子
促炎细胞因子TNF在引起IBD的慢性肠道炎症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目前在开发的大多数治疗IBD的生物制剂都是为了中和TNF。2013年之前,欧洲仅批准了英夫利昔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美国、瑞士和俄罗斯批准了赛妥珠单抗[7]。
英夫利昔单抗是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有效但昂贵的药物,监测英夫利昔单抗的谷值水平和抗英夫利昔单抗抗体(Anti-infliximab antibody,ATI)的形成,可以使英夫利昔单抗治疗更具成本-效益。第1次基线水平英夫利昔注射后85%的患者症状缓解,第2、3次输注根据治疗算法得出剂量的英夫利昔后,88%的患者缓解,并且每年药品成本减少7.4%[8]。约55%的患者在停用抗肿瘤坏死因子后复发,CD和UC患者的平均复发时间分别为32个月和18个月。用同样的抗肿瘤坏死因子进行再治疗的成功率为84%[9]。Inokuchi 等[10]发现,首次用IFX治疗和首次用阿达木单抗治疗的患者的无类固醇缓解率和无手术率没有显著差异。先用IFX治疗的患者可能因不良事件而停用药物,而先用阿达木单抗治疗的患者可能因治疗失败或失应答而停用药物。
与英夫利昔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相似,戈利木单抗被FDA和EMA批准用于治疗类固醇和硫唑嘌呤都不敏感的UC。戈利木单抗是一种皮下注射的全人类抗肿瘤坏死因子抗体,被批准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和银屑病性关节炎。在一项Ⅱ/Ⅲ期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诱导研究(PURSIT-SC)中,对常规治疗无应答的中重度UC患者随机分为安慰剂组和戈利木单抗治疗组,在第6周,戈利木单抗显著提高了临床反应、临床缓解和黏膜愈合率,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11]。在维持性研究(PURSIT-M)中,有临床反应的患者接受戈利木单抗治疗,在第54周时,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戈利木单抗治疗的患者获得了更显著的持续缓解率和黏膜愈合率[12]。
首次批准后,研究者对抗肿瘤坏死因子制剂的安全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一项针对CD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包括13项随机对照试验和>4 000例患者),除了增加恶性肿瘤或严重感染的风险外,抗肿瘤坏死因子降低了严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SAEs)的发生率。并且阿达木单抗治疗组的SAEs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英夫利昔单抗、赛妥珠单抗治疗组的SAEs发生率与对照组相似[13]。
2 抗黏附分子
在IBD中,炎症表现主要以肠固有层的白细胞浸润为特征[14]。因此,抑制从循环系统到肠道炎症部位的白细胞聚集过程可能是控制炎症级联的可行策略。白细胞聚集过程主要通过此过程:内皮细胞通过白细胞表面的L-选择素与其在内皮细胞上的配体(Pand E-selectins)之间的相互作用捕获白细胞[15]。然后,属于整合素家族的次级黏附分子允许白细胞通过血管壁迁移。T细胞释放趋化因子,然后激活选择素或整合素,除了选择素和黏附分子外,白细胞还通过特定的趋化因子受体(Chemokine receptors,CCR)与趋化因子相互作用[14]。
那他珠单抗是一种抗α4整合素的特异性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虽然初期那他珠单抗可诱导和维持CD临床缓解,但由于JC病毒的激活,那他珠单抗增加了致命的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Fatal 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PML)的风险[16-17],2005年,那他珠单抗退出市场。随后市场上推出一种不激活JC病毒的肠道选择性α4β7整合素拮抗剂—维多株单抗。
为证实维多珠单抗在UC诱导和维持缓解中的作用,GEMINI 1临床试验[18]纳入了800多例中、重度UC患者(梅奥评分6~12,内窥镜评分≥2)。该试验包括2个诱导队列:第1个双盲队列,包括374例在第0周和第2周随机接受静脉注射安慰剂或维多珠单抗的患者;另一个队列,纳入521例开放标签接受维多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为产生所需数量的应答者,以满足维持缓解阶段试验中样本量的要求。纳入条件为对类固醇、免疫抑制药物或抗肿瘤坏死因子α治疗没有应答或不能接受上述药物所引起的不良事件。
在第1个队列中,接受维多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在6周时临床有效率(47% vs.25.5%,P<0.001)、临床缓解率(17% vs.5%,P=0.001)和黏膜愈合率(41% vs.25%,P=0.001)明显高于安慰剂组。在第2个队列试验中,维持缓解阶段的第52周,维多利珠单抗治疗组的临床缓解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44.8% vs.15.9%,P<0.001),并且具有更高的黏膜愈合率和无类固醇缓解率。在第52周,维多珠单抗能够使>50%内镜下愈合的患者达到病理愈合,还能使肠道免疫相关基因表达不完全恢复[19]。
Feagan等[20]发现,在未接受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治疗和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治疗失败的患者中,维多珠单抗诱导和维持治疗UC的疗效好于安慰剂,并且在接受维多珠单抗治疗的第6周,未接受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治疗者的治疗效果优于接受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治疗失败者。
GEMINI 2临床试验[21]证实了维多珠单抗治疗中、重度CD的作用。入选的CD患者需满足疾病活动指数(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为220~450,并且符合以下至少1项:①血清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2.87 mg/L;②结肠镜下≥10个阿弗他溃疡,或≥3个大溃疡;③粪便钙卫蛋白>250 μg/g,结合计算机断层扫描或磁共振肠镜检查、小肠造影或胶囊内镜检查可发现CD溃疡。纳入的患者同时需对类固醇、免疫抑制药物或抗肿瘤坏死因子α治疗没有应答或不能接受上述药物所引起的不良事件。在第6周进行评估,发现接受维多珠单抗治疗的患者的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14.5% vs.6.8%,P=0.02)。接受维多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在第52周(本阶段的主要终点)的临床缓解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36.4% vs.21.6%,P=0.004)。维多利单抗治疗组的类固醇缓解率也显著高于安慰剂组。
GEMINI 2临床试验中对维多珠单抗诱导治疗6周后缓解的461例应答者进行分析,153例(33%)患者有造瘘病史,57例(12%)患者至少有1处活动性引流瘘。第14周,28%的维多珠单抗继续治疗者与11%的安慰剂继续治疗者实现了瘘管闭合,第52周瘘管闭合率分别为31%和11%,接受维多珠单抗持续治疗的患者瘘管闭合时间更短[22]。
Etrolizumab是一种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选择性结合异二聚体整合素α4β7和αEβ7的β7亚单位。Ⅱ期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与那他珠单抗和维多珠单抗相似,Etrolizumab在中、重度活动性UC患者中是有效的[23]。在这一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性的研究中,募集了11个国家40个研究中心的对常规疗法无应答的患者。124例患者被随机分成3组:在第0、4、8周服用100 mg Etrolizumab,第0周服用420 mg(负荷剂量),第2、4、8周服用300 mg;安慰剂组。结果显示,100 mg Etrolizumab和300 mg Etrolizumab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21%和8%,安慰剂组无缓解。Etrolizumab的治疗效果有待于正在进行的第3阶段试验确认。一项荟萃分析指出,Etrolizumab和英夫利昔单抗在临床缓解和严重不良事件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此外,Etrolizumab的不良反应明显少于英夫利昔单抗[24]。
3 抗IL-12/23
IL-12和IL-23是具有共同p40亚基的促炎细胞因子。IL-12(p35+p40)可诱导Th1分化,而IL-23、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和IL-6可诱导Th17分化[25]。IL-12和IL-23在自然杀伤细胞和CD4+T淋巴细胞的活化和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阻断其作用有助于治疗慢性炎症性疾病,如斑块型银屑病、银屑病性关节炎和CD等[26]。乌司奴单抗是一种抗IL-12/IL-23的p40亚单位的单克隆抗体,被FDA和EMA批准用于治疗银屑病和银屑病关节炎[27]。
已有试验证明,乌司奴单抗对CD患者诱导和维持缓解是有效的。研究者通过3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对乌司奴单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即诱导治疗的UNITI-1和UNITI-2,维持治疗的IM-UNITI。在UNITI-1试验中,741例患者接受了至少1种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并经历了1级或2级无应答或出现不良反应。在第6周,乌司奴单抗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33.7%、21.5%(P<0.01),第8周的缓解率分别为20.9%、7.3%(P<0.001)[28]。
UNITI-2试验中,628例患者治疗失败或常规治疗出现了不可接受的不良反应(68.6%的患者未接受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而其余患者至少接触过1种抗肿瘤坏死因子,且没有经历不可接受的不良事件或初级/次级无应答),在第6周观察到乌司奴单抗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55.5%和28.7%(P<0.001),第8周的缓解率分别为40.2%和19.6%(P<0.001)[29]。完成这些诱导试验的患者被纳入IM-UNITI,其中397例对乌司奴单抗有反应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皮下维持注射90 mg乌司奴单抗或安慰剂,另外884例患者进入了IM-UNITI,但没有进行随机分组。在第44周接受乌司奴单抗治疗者的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53.1% vs.48.8%)。值得注意的是,在44周内,只有2.3%的受试人群对乌司奴单抗抗体呈阳性[30]。
UNIFI[31]是一项3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组、多中心研究,旨在评估在8周内静脉输注乌司奴单抗(130 mg或6 mg/kg)对中、重度活动性U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在44周的维持治疗中,评估乌司奴单抗对诱导治疗有反应的UC患者每8或12周皮下注射(90 mg)的维持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随后有1个持续3年的扩展研究[32]。
4 JAK抑制剂
Janus激酶(JAK)1和JAK3参与IL-2R和IL-6R细胞因子的转导过程,使抑制Janus激酶/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子(JAK/STAT)信号通路成为IBD的潜在治疗靶点。托法替尼(Tofacitinib)是JAK家族的一种口服的非选择性抑制剂,主要影响JAK1和JAK3,可调节大量促炎性细胞因子(如IL-2、IL-4、IL-7、IL-9、IL-15和IL-21)的信号传导[11]。这些细胞因子是淋巴细胞活化、功能和增殖的组成部分。托法替尼目前已被FDA批准用于治疗对甲氨蝶呤无反应或对药物不耐受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2012年第1项托法替尼治疗IBD的第2阶段研究评估了不同剂量的托法替尼治疗中、重度UC的疗效[33]。中、重度UC患者随机接受4种托法替尼治疗方案(0.5 mg,3 mg,10 mg,15 mg,2次/d口服)或安慰剂,持续8周,在194例随机治疗患者中,接受0.5 mg、3 mg、10 mg和15 mg剂量托法替尼治疗者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13%、33%、48%和41%,而接受安慰剂者的临床缓解率为10%[33]。3 mg组内镜下缓解率为18%,10 mg组为30%,15 mg组为27%,而安慰剂组为2%[15]。2项第3阶段的诱导研究(OCTAVE 1 和 OCTAVE 2)和维持研究(OCTAVE Sustain)中也证明了托法替尼的有效性,在第8周,接受10 mg、2次/d口服治疗的患者的缓解率和黏膜愈合率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34]。与安慰剂相比,托法替尼的总感染率和严重感染率更高,OCTAVE Sustain试验中,5 mg组3例(1.5%),10 mg组10例(5.1%),安慰剂组1例(0.5%)。目前1项正在进行的Ⅲ期诱导和维持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仍在招募,旨在评估托法替尼治疗UC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15]。
托法替尼治疗CD的第2阶段研究结果差强人意。治疗4周后,托法替尼组与安慰剂组的缓解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并且在长期随访后发现,托法替尼诱导和维持CD治疗的2个阶段均未能达到事件终点[36]。
5 结论
随着研发手段、对疾病认识程度的进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治疗炎症性肠病的药物,使得在可用的生物制剂中选择有效的治疗药物成为一个难题。希望各大诊治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生物制剂间头对头试验,制定关于一线生物制剂选择的决策,并确定在对第1种生物制剂的1级或2级应答失效后,是选择在同一药物类别内切换还是切换成其他药物类别。最后,随着生物制剂使用的增加,将改变IBD治疗的格局,并使治疗方法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