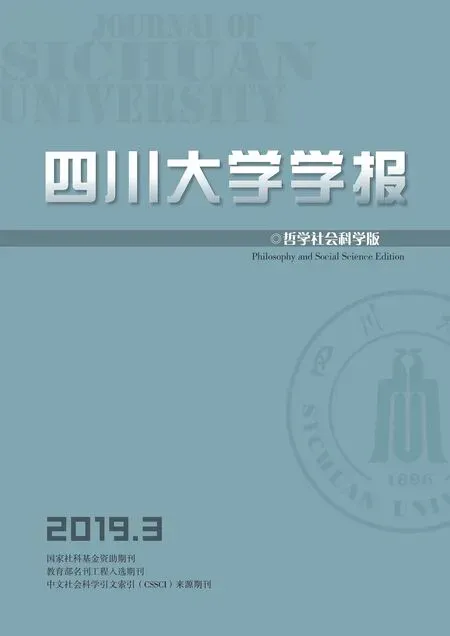族裔历史重构:加拿大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的唐人街叙事
加拿大是华人移居海外较多也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858年,位于加拿大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就建起了第一条唐人街,它在北美的历史仅次于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此后又陆续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地修建了唐人街。历经百年沧桑,唐人街不仅成为加拿大华裔历史的见证者,更孕育了加拿大华裔文学。发韧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华裔文学,至今历史虽然不到50年,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加拿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同属北美华裔文学,或许由于历史较短,加拿大华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远不及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者也相对较少。而事实上,加拿大华裔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并不逊于美国华裔作家,尤其是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所创作的以唐人街为背景的经典作品,曾经屡获大奖,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并被选入权威文学词典或文学教科书。目前,国内对于加拿大华裔文学的研究为数不多,并且主要涉及单个作家或作品,[注]如赵慧珍 :《论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李斯嘉的〈残月楼〉》,《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21-127页;朱徽 :《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赵廉博士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第126-136页;赵庆庆 :《语言·隐秘·重构:加拿大华裔作家崔维新的〈纸影:唐人街的童年〉评析》,《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第116-123页;等等。笔者也曾撰文讨论加拿大华裔文学的起源及发展,但仍有许多值得关注和挖掘的问题。笔者注意到引领加拿大华裔文学发展的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以其“唐人街叙事”重新建构了华人族裔历史,这一点对于理解加拿大华裔文学和历史至关重要,对此学界尚没有专门探讨,本文即尝试考察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所创作的经典作品中的唐人街叙事。
一、唐人街记忆与华裔文学
唐人街对于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而言,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文化场域,它曾为初来乍到的移民提供了生活便利及生存平台,也为他们营造了精神上的家园。在加拿大,从温哥华的片打街(Pender Street)到多伦多的登打士街(Dundas Street), 散落各地的唐人街是加拿大华裔历史的缩影与见证,它的兴衰反映了加拿大华裔社区的演变。如今唐人街旧貌依然,却已今非昔比。作家崔维新(Wayson Choy,1939-2019)在其代表作《玉牡丹》(JadePeony, 1995)的引言中指出:
我们把居住的地方称作“唐人街”英文表达是“China-People Street”,后来,我们不想模仿鬼子的语言(Demon talk),直接把它称作“华埠”(Wah Fauh),也就是“China-Town”。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单从英文表达的变化可以看出,“People”一词已经没有了。[注]Wayson Choy, The Jade Peony,Vancouver/Toronto: Douglas & McIntyre, 1995, Preface. 本文所征引英文文献译文,除特别说明,均为笔者自译。
确如崔维新所言,随着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华裔与主流社会进一步融合,大量华裔人口逐步迁出唐人街,这一昔日封闭的华人社区不再是一块流亡的飞地,它已经成为一段族裔记忆,一道历史景观。翻开由加拿大第一代土生华裔创作的文本,即可发现“唐人街”是反复出现的母题,对于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而言,唐人街是他们个人成长和族裔建构的起始,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和鲜活记忆。正如作家李群英(Sky Lee,1952- )在《残月楼》(DisappearingMoonCafé, 1990)中所言:“你可以把她从唐人街带走,却不能让她忘记唐人街。”[注]Sky Lee, Disappearing Moon Café,Vancouver/Toronto/Berkeley: Douglas & McIntyre, 1990, p.221.无法忘记的唐人街成为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创作源泉。
1858年,弗雷泽河谷(Fraser Valley, 位于现在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金矿的发现,把美国加利福利亚的华裔移民带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约一年以后,又从中国广东等南方诸省吸引到大批移民加入这股“淘金潮”,特殊的地缘优势使维多利亚成为早期华裔移民的主要登陆港口。“淘金热”减退后,华裔开始向经济更发达的城市迁移。1911年,温哥华取代维多利亚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华裔聚居区,华裔们把它叫做“咸水埠”(Hahm-sui-fauh)。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以温哥华唐人街为代表的华裔社区已具有相当规模,却仍是相对孤立的“城中之城”,长期处于比较封闭、落后的状态。[注]See The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eds. , Jin Guo :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 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19.
唐人街是华裔移民艰苦岁月的见证, 它的发展也与华裔移民的重要历史时期相呼应,大致可分为 萌芽阶段(1858年-19世纪70年代)、发展阶段(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衰落阶段(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及复苏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注]参见乔国:《加拿大唐人街的历史嬗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4-16页。在萌芽阶段,维多利亚唐人街是华人首选聚居地,大部分居民是淘金者,因缺乏教育及生存技能而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只能固守于唐人街;之后随着“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1881-1885)的修筑,大批中国苦力涌入,唐人街逐渐兴旺,社团、寺庙、教堂、学校等相继建立,形成了与白人社会相隔离、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再后来由于人头税(Chinese Head Tax, 1885-1923)和《排华法案》(TheChineseExclusionAct,1923-1947)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以及土生华裔受西方文化影响,渴望融入主流社会,逐渐搬离,唐人街走向衰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政策在加拿大逐步实施,华裔文化作为多元化的一支,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唐人街不再是以前穷困、封闭的形象,进入了复苏阶段。
随着唐人街的复苏,华裔作家们意识到书写族裔故事、重构社区历史的重要性,于是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文学团体、结集出版作品等方式,以积极的行动“让历史性的沉默转化成立足于华裔社区的当代加拿大华裔文学”。[注]李晖:《笔尖在枫叶国舞蹈:华裔加拿大文学的起源及发展》,《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第122页。在华裔文学发韧之初,成长于唐人街的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是最活跃的群体,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朱蔼信(Jim Wong-Chu, 1949-2017)[注]朱蔼信出生于香港,4岁时作为“纸儿子”移民加拿大,是加拿大华裔文坛的元老级人物,参与创办“亚裔加拿大作家工作坊”,编写了几部重要的加拿大华裔英文文集:《多嘴的鸟:当代加拿大华裔作品集》(Many Mouthed Birds :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1991)、《云吞:加拿大华裔诗集》(Swallowing Clouds : An Anthology of Chinese-Canadian Poetry, 1999)及《敲响:当代加拿大华裔小说集》(Strike the Wok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anadian Fiction, 2003)。他擅长诗歌,代表作品有诗集《唐人街幽灵》(Chinatown Ghost, 1986),一些作品被收录入《与众不同:加拿大多元文化文学》(Making a Difference : Canadian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1996)等文集中;并曾为多个文化项目担当历史顾问。及前文提到的崔维新、李群英等,他们联合日裔作家创办了首个亚裔文学团体 ——“亚裔加拿大作家工作坊”(Asian Canadian Writer's Workshop,1976)。作家们通力合作,对主流文学的霸权地位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成立当年,“工作坊”汇集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集《不可剥夺的稻米:加拿大华裔及日裔文集》(InalienableRice:AChineseandJapaneseCanadianAnthology,1979),它标志着加拿大华裔、日裔文学的诞生。文集的主标题旗帜鲜明地显示了作者的族裔身份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呼声。
此后,越来越多优秀作家涌入文坛,华裔文学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多嘴的鸟:当代加拿大华裔作品集》的出版发行,更是标志着华裔文学走向成熟阶段。“多嘴”一词不但表现了作家们创作风格的多样性,更反映了他们“渴求打破沉默,抒发自己感受的强烈诉求”。[注]李晖:《浅议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教学》2008年第24期,第95页。“(虽然)说出来可能招致麻烦,……(但是)并非可耻,而是源于内心的歌唱(a few songs straight from the heart)”。[注]Bennett Lee & Jim Wong-Chu, eds. , Many-Mouthed Birds :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 Vancouver/Toronto: Douglas & McIntyre, 1991. p.8.文集中有不少篇幅聚焦于唐人街往事,如安妮·朱(Anne Jew)的《唐人街上每个人都大声说话》(EveryoneTalkedLoudlyinChinatown,1991),以及李群英的《残月楼》、郑霭龄(Denise Chong,1953- )的《妾的儿女》(TheConcubine'sChildren, 1994)和崔维新的《玉牡丹》中的选段等。唐人街叙事成为加拿大华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后来的华裔移民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张翎的《金山》(2009)。[注]该书的英文译名为Gold Mountain Blues : From Kaiping to Vancouver,由企鹅出版社于2011年10月出版,后被崔维新、余兆昌、李群英及郑霭龄等指控涉嫌抄袭。
加拿大华裔作家根据其成长背景大致可以分为土生作家和移民作家。[注]参见李晖:《穿越族裔的屏障:加拿大华裔文学发展趋势研究》,《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第48页。所谓土生作家,是指出生或成长于加拿大、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其中20世纪30至5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裔,是登上华裔文坛的第一代土生作家,他们中除了朱蔼信、崔维新、李群英、郑蔼龄及余兆昌(Paul Yee,1956- )等优秀作家外,其他如弗雷德·华(Fred Wah, 1939- )和方曼俏(Judy Fong Bates, 1956- )也取得了较高成就,尤其是弗雷德·华的散文诗集《等候萨斯喀彻温》(WaitingforSaskatchewan,1986)还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但是由于这两位作家成长于加拿大小镇,华人相对较少,没有形成固定的华裔街区,他们的作品主要描写小镇华裔的移民生活,所以本文没有把他们的作品纳入唐人街叙事之列。而60年代及其后出生的华裔作家,如黎喜年(Larrisa Lai,1967- )、胡功勤(Terry Woo,1971- )、马德莲·邓(Madeleine Thie,1974- )、林浩聪(Vincent Lam,1976- )等,一般称之为第二代土生作家。至于移民作家,又称“新移民作家”,则大都是在80年代或其后移居加拿大,除少数几位用中英或中法双语进行创作外,多数用中文写作,代表作家有赵廉(1950— )、李彦(1954— )、张翎(1957— )、应晨(1961— )等。第二代土生作家及新移民作家因缺乏在唐人街生活的经历,故作品中鲜见唐人街叙事,他们的作品多涉及身份问题、文化冲突与融合等。
二、唐人街回望:历史的召唤
早期的华裔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各省农村,受限于语言和教育等因素,基本没有文学创作的能力。而且,对于屈辱、辛酸的过往,很多人不愿意提及,甚至宁可忘记。“加拿大并不是对所有的移民都一视同仁,华裔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最不受欢迎、受到最苛刻对待的人”。[注]Jin Tan & P. E. Roy, The Chinese in Canada, Ottawa: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5, p.3.长期被严重歧视和边缘化,华裔社区早已经习惯了缄默不语。郑蔼龄曾坦言,她的《妾的儿女》刚出版时,并不受本族裔欢迎,根本原因在于它“道出了华人群体生活的挣扎”。[注]庄建、虹飞:《打开看望外婆之门:华裔作家郑蔼龄访谈》,《译林》2011年第3期,第211页。诚然,唐人街曾是华裔移民蒙受耻辱的印记,宛如一块历史的伤痕,揭开它会经历苦痛;但是,缄默并不能磨灭那段关于族裔历史的记忆,更何况“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华裔文坛的领军人物——第一代土生作家们意识到建构族裔历史、确立文化身份、彰显华裔在加拿大的历史贡献是他(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余兆昌是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兼作家,曾就读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专业,然而他在本科及硕士阶段却没有读到过一本正面书写加拿大华裔历史的书籍,这让他在震惊之余产生了重写加拿大华裔历史的迫切愿望。[注]参见章文君:《论加拿大华裔作家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6页。他意识到图书馆里一些关于华裔移民历史的介绍,主要从白人的角度来讲述,并且其中有很多错误的刻画。“所以我非常想从另一面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研究的动机是为了弄清社区里发生了什么, 以此来反对那些在社区外的人对华裔所作的一切”。[注]陈中明:《陈中明访问余兆昌》,韩文静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2期,第78页。于是他开始着意于收集早期移民的历史资料,大学毕业后又曾先后在温哥华城市档案馆和安大略省档案馆做文献管理工作,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其实,和当时唐人街多数人一样,余兆昌在60年代搬离了华裔社区。此后,他几乎不与华裔圈子联系,有意无意间淡忘了自己的族裔身份,直到在高中快毕业那年,导师让他去协助一场主题为“身份及意识”(identity and awareness)的加拿大华裔青年会议,尽管很不乐意,但是碍于情面,他只好去参加。当时,会上有人提及修筑铁路的华工, 余兆昌冒然打断:“你说他们干什么? 他们只是一群苦力(a bunch of coolies[注]Coolie一词在17世纪中期起源于印度,后来用于欧洲人对亚洲不熟练劳工 (尤其是印度或中国这类移民) 的轻蔑称呼,早期移民加拿大的契约劳工也被称作“苦力”。)!”话音刚落,全场哑然。虽然没有人当面指责他,但是他明白自己说错了话,意识到自己与族裔身份的疏离。从那以后,他重新回归温哥华的华裔社区(“reborn”into Vancouver's Chinese community),和社区的积极分子们一起在唐人街的中华文化中心做义工,收集口述的历史,帮助中心募捐、举办关于华裔历史的展览等。[注]Paul Yee, “RAILWAY NOVEL:‘...just a bunch of coolies...’,” http:∥www.paulyee.ca/blogDetail.php?12, 2014-11-20.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着手华裔历史的写作,并且深刻认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及作家对社区肩负的责任感:因为“我们拥有中国人的体征, 我们将永远被视为华裔加拿大人、加拿大华裔作家,无论爱它与否,我们都的确属于社区”;既然“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我们要帮助它, 更好地理解它, 去找到它的不足并使之发展壮大”。[注]陈中明:《陈中明访问余兆昌》,韩文静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2期,第79页。
1986年,余兆昌创作了《三叔的诅咒》(TheCursesofThirdUncle,1986),同年,他为中华文化中心100周年诞辰组织图片展览,后来他根据展览中的200张相片撰著了第一本关于华裔历史的画册《咸水埠:温哥华的中国人》(SaltwaterCity:AnIllustratedHistoryoftheChineseinVancouver,1989)。画册以生动、纪实的方式重建了社区档案,获得“温哥华图书奖”(City of Vancouver Book Award),成为研究加拿大华裔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他还创作了《金山传说:华裔在新世界的故事》(TalesfromGoldMountain:StoriesoftheChineseintheNewWorld,1989)。90年代后,余兆昌更是毅然辞职在家专攻写作,以书写华裔历史为己任,先后创作了《斗争和希望:加拿大华裔的故事》(StruggleandHope:TheStoryofChineseCanadians,1996) 、《鬼魂列车》(GhostTrain,1996)及《拾骨者之子》(TheBoneCollector'sSon,2003)等。其中,《鬼魂列车》获“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s Literary Award[注]加拿大文坛最具权威的文学年度大奖,1936年由加拿大作家协会(Canada Author's Association)创立,从1959年起,改由加拿大文化委员会(Canada Council)主持评审和颁奖活动,奖项也从英语文学扩大到法语文学,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三大类别,成为在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奖,在世界文学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及“温哥华图书奖”等诸多重要文学奖项。
在强烈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余兆昌还将目光投向了儿童教育,成为加拿大华裔儿童文学的开创者。他曾经对主流媒体谈起创作儿童小说的目的:“我写作是为了让更多人更直接地了解历史(to make history more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写作中确实带有教育的目的 (pedagogical motivation)。我想灌输一些东西,成年人可能会排斥,但是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应该意识到中国人为加拿大所做的贡献,因为下一代将会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肌理(social frabric)。”[注]Lien Chao, Beyond Silence :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oronto: TSAR Publications, 1997, p.63.
余兆昌的创作侧重于社区历史,并且带有明显的教育目的,而崔维新的写作风格虽与余兆昌有明显不同,却又“异曲同工”:善于从孩子的角度讲述华裔历史。崔维新出生于温哥华的唐人街,和余兆昌一样曾就读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然而相比于余兆昌,崔维新却显得大器晚成。他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多年,直到1995年才因长篇小说《玉牡丹》一举成名。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出版了自传体小说《纸影:唐人街的童年》(PaperShadow:ChinatownChildhood, 1999)及《玉牡丹》的续集《在乎的一切》(AllThatMatters, 2004)。《玉牡丹》出版后,连续数周高踞《环球邮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1996年度“温哥华图书奖”,并且被《加拿大文学评论》(LiteraryReviewofCanada)评选为“1945—2004年间最有影响力的100本加拿大书籍”;《纸影》入围1999年度“总督文学奖”的决选名单,被《环球邮报》列为1999年度推荐作品,并且获得“温哥华图书奖”;《在乎的一切》则获得“吉勒文学奖”(Giller's Prize)提名,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因为其精彩的文学创作,崔维新被称为“加拿大最有讲故事天赋的人”。[注]赵庆庆 :《郁郁哉,温哥华的华裔文学》,《文艺报》2005年9月27日,第 2 版。
崔维新的三部经典作品都是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温哥华唐人街为背景,通过孩子们的视角讲述华裔移民家庭如何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求生存的故事。作为第一代土生作家,在温哥华唐人街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给崔维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和创作源泉。他在作品中不但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普通华裔一家的生活,并且巧妙地穿插了华裔经历的特定历史事件,如买纸移民、修建太平洋铁路、缴纳人头税、为抵抗日本侵华战争募捐等。在对家族离散生活的书写中,他把个人经历与族裔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勾画出早期华裔在唐人街的生活状态,反映了第一代土生华裔在成长过程中对先辈历史和文化的困惑,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从崔维新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三四十年代的唐人街是一个相对封闭,具有民族特色、自给自足的海外“中国城”:从餐馆、商店、学校到戏院,唐人街几乎涵盖了华裔所需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产品,华裔们的业余活动包括打麻将、听戏等。早在淘金时期,维多利亚唐人街就有常驻的粤剧班[注]粤剧从19 世纪下半叶在北美洲已经持续上演,粤剧社遍布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它们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八年抗战、侨乡水灾旱灾等。演出,而崔维新的亲生父母可能就是唐人街的粤剧演员,他们不知何故把儿子遗弃,后来,好心的养父母收留了他。崔维新的养父是海轮上的司厨,时常出差在外,很多时候他都是跟在养母身边,养母喜欢带着年幼的他去朋友家打麻将、聊天或者去唐人街的剧院听粤剧。在崔维新的记忆中,养母经常带他去剧院找一个可能就是他生母的女人,这样的细节在《纸影》中都有描述。
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是华裔们团聚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纽带。宗族不仅包含血缘和亲缘关系,甚至可以扩大到同姓关系。1923年,温哥华的唐人街一共有26个宗族组织,12个同乡组织。[注]Paul Yee, Saltwater Cit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Vancouver/ Toronto: Douglas & McIntyre, 1988, p.54.早期的移民登陆加拿大总是首先投靠同宗同族,当同宗族的人到一定数量,便出现了宗族社团。《玉牡丹》中的三叔就是因为国内的妻儿及国外的亲戚相继过世,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帮助他照看在加拿大的货栈生意,才在家族亲友的联络下找到虽是同姓、但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小说中的父亲,然后设法让他们全家用“纸身份”[注]受《排华法案》限制,只有加拿大国公民在海外出生的子女以及豁免人员(学生、商人、外交人员等)不属被禁止移民之列,于是很多人便通过购买伪造的出生证明进入加拿大。“买纸”移民成为当时华裔为了移民采用的特殊手段。移民到了加拿大,因此小说中的陈家其实就是典型的靠宗亲关系组建的“买纸家庭”(bought-paper family)。而《纸影》的命名也是影射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买纸”是华裔蒙受种族歧视的一个印记,是唐人街的一个公开的秘密。《玉牡丹》中年幼的孩子似乎察觉到了大人们的秘密:“唐人街上的宗族会馆(clan building)通常有三到五层楼那么高,我知道垒起它们的每一块砖都像万里长城一样守护着家族的秘密。那些先前从中国来加拿大的老华侨(lao wah-kiu)把过去的历史藏在里面,只有‘纸历史’(paper-history)还见得着,只有他们经常念叨的历史(talk-history)还听得见。”[注]Choy, The Jade Peony, p.51.尘封的历史,挥之不去的记忆,唐人街的生活,一代又一代,走出去的人仍在频频回首,那一段历史让人回望和深思。
三、唐人街女性:“属下中的属下”
加拿大华裔曾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历史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而作为边缘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华裔女性的历史更是鲜有提及。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曾指出:“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注]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陈永国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批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这里,所谓“属下”(Subaltern)指的是没有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文化群体。如果说加拿大华裔曾经是加拿大主流社会中的“属下”,那么加拿大华裔女性就是“属下中的属下”,她们的历史曾被深深湮没。然而,正如“安大略多元文化历史协会网”所陈述的一个不争事实:“早期华裔女性的人数虽然较少,但是她们和男性一样为社区和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Despite their low numbers, they were able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ommunities and country)。”[注]“‘These were extraordinary women.’—Germaine Wong, Chinese Canadian Women, 1923-1967 interviewee,”http:∥www.mhso.ca/chinesecanadianwomen/en.作为历史存在,华裔女性及其历史贡献不能、也不会被遗忘。
在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中,如果说以余兆昌、崔维新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用自己的创作重构了社区及家族的历史,那么以李群英和郑霭龄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则是从女性的角度讲述家族故事,重新建构了专属华裔女性的历史。《残月楼》是首部加拿大华裔长篇英文小说,也是第一部加拿大华裔女性主义作品,不仅获得“温哥华图书奖”,而且获得“总督文学奖”提名。作者李群英在小说中以温哥华唐人街为背景,描写了1892到1986近百年间一个加拿大华裔家族四代女性的不同命运。《华盛顿邮报》曾盛赞《残月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加拿大华裔,并且是女性, 那么《百年孤独》就会和《残月楼》相似。”[注]Lee, Disappearing Moon Café, the Back Cover.该书被视为研究加拿大华裔历史和文学的必读书目,成为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
《残月楼》反映了加拿大华裔女性一百年来的生活变迁:前两代女性由于种族及性别歧视的缘故,生活一直囿于唐人街;第三代女性在成年后搬离了唐人街;第四代女性则一直生活在唐人街以外。女性是民族文化、尤其是家族文化传承的主体,移民初期她们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到了加拿大,但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束缚女性发展的一些中国传统正在逐渐地消失,正如小说的题目“残月楼”所寓示的那样,“月亮”自古以来就象征着女性,“残月”喻指了华裔女性的过往故事,并且象征新的一轮明月即将升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掀起第二次浪潮,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作为其中的一股力量在60年代末蓬勃发展,[注]蓝仁哲主编:《加拿大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残月楼》中王家的第三代女性正是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更加迫切地想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争取独立自由的生活,不愿再像前两代女性那样被动地接受父母安排的一切,远远地搬离了唐人街。而第四代女性则在思考自己文化身份的同时,开始挖掘族裔往事。作为加拿大第四代华裔女性的代言人,李群英在书中发出如此感慨:“这也许是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我们在自己四周修建了一堵无形的、沉默的高墙。这沉默中潜藏着一股力量,帮助我们抗拒苦难。如果把我们的历史昭之天下恐怕会遭人谴责,然而,我还是违背了这个沉默的原则。为什么不说出来?虽然后果不可预知,但总是一种改变!”[注]Lee, Disappearing Moon Café,p.242.
加拿大华裔女性曾经处于无声的历史角落里,成为“他者中的他者”“属下中的属下”,但第一代土生华裔女作家们不再墨守陈规,她们利用文学话语权打破女性沉默不语的禁忌,书写唐人街女性的历史记忆。继李群英之后,郑蔼龄创作了传记体小说《妾的儿女》,该书出版后获得“总督文学奖”提名,“温哥华图书奖”“加拿大纪实文学奖”及“女性文学奖”等一系列重要文学奖项,并曾连续数周位列加拿大图书销售榜首,在德国、荷兰、美国也成为畅销书,现在已经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文字。这种基于华裔女性个人真实经历的非虚构写作在当时很罕见,读者也把它作为纪实而非小说来读。重要的是,该书的成功使得曾经排斥提及过往的华裔前辈逐渐乐意分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惨经历,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
《妾的儿女》的写作,据郑蔼龄在访谈中所称,是为外婆“讨回公道”。幼年时郑蔼龄在家中的阁楼里发现一些老相片,由此对家族尘封的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后来,她断断续续从母亲那里听说了家族往事。成年后,她陪同母亲回中国找到了位于广东中山县乡下的祖居,亲眼目睹了由外公设计、靠外婆当侍女挣钱盖起的碉楼。然而,祖屋的墙上只悬挂着外公和嫡妻的相片,外婆却被“隐形”了,这让郑蔼龄感触颇深,她决定把外婆的故事写出来。起初,她的想法遭到亲友们的反对,因为在别人的眼中外婆虽然长得漂亮却是个生活放荡的酒鬼、赌徒,是丑陋、可耻的人。[注]参见庄建、虹飞:《打开看望外婆之门:华裔作家郑蔼龄访谈》,《译林》2011年第3期,第212、211页。为了还外婆一个清白,郑蔼龄阅读了大量家书,并且找到当年和外婆一起当侍女的姐妹(其中有两位已经快满百岁),艰难地“掏出”了外婆的故事。
郑蔼龄的外婆生活在20世纪初的唐人街,那时唐人街上女性很少,除了难得露面的商人的妻子、少数女佣及妓女外,几乎见不到女人的身影。在这样的“单身汉社会”[注]早期的加拿大华裔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单身汉”组成,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困扰加拿大华裔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唐人街的酒店和茶馆很难找到侍女,老板们就和一些单身汉通过买妾达成了“一举两得”的交易,于是老板有了赚钱的工具,单身汉们也有了生儿育女的工具,他们双方都可以赢利,而小妾们的利益却被剥夺,她们的身体成为男权社会剥削的资本。郑蔼龄的外婆在国内被父母卖给一户人家后,又被转卖到加拿大。作为旧时代的女性,外婆深受压迫又别无选择,便只好认命,因为“她不可能摆脱儒家社会礼教的束缚(Confucian sense of social order),这种束缚居然一路跟着她跨过太平洋来到了加拿大”。[注]Denise Chong, The Concubine's Children, Toronto: Penguin Books, 1994, p.30.
加拿大华裔女性不仅是东西双重文化中的他者,也是中西方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权利的边缘。她们在移居他乡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而且还要面对来自种族及性别的双重歧视。早期的华裔女性多数为家庭妇女,生活局限在唐人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自身经历的文字。所幸的是,在当代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她们的后代有机会接受了高等教育,通过积极的文学创作,为先辈代言,构建了属于加拿大华裔女性的独特历史。
结 语
一百多年前,华裔移民远涉重洋到加拿大寻找谋生的机会,唐人街是他们能够感受到乡土文化且相对安全的暂居地,他们无法、也不愿意融入主流社会,始终把加拿大当作异乡,而非故乡;来自主流社会的长期歧视与排斥,也加重了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的“失语”,在长久的缄默中,他们曾沦为“没有历史的人”。然而,“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注]艾勒克·博艾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华裔只有积极陈述自己的历史,赢得话语权,才可以成为族裔历史话语的主体,从而打破主流话语的垄断。因此,书写唐人街社区历史、解构主流话语成为第一代土生华裔作家们的主要创作倾向。他们通过回溯、书写和重构,让历史的真相得以再现,填补了早期华裔移民史的空白,颠覆了把华裔扭曲、丑化的殖民话语,找到了华裔的中国文化之根,树立了华裔的正面形象,实现了“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标示出属于华裔位置的主张(stake a claim on this country's history)”。[注]Elisa Oreglia, “Interview with Paul Yee,” http:∥www.papertigers.org/interviews/archived_interviews/pyee.html, 200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