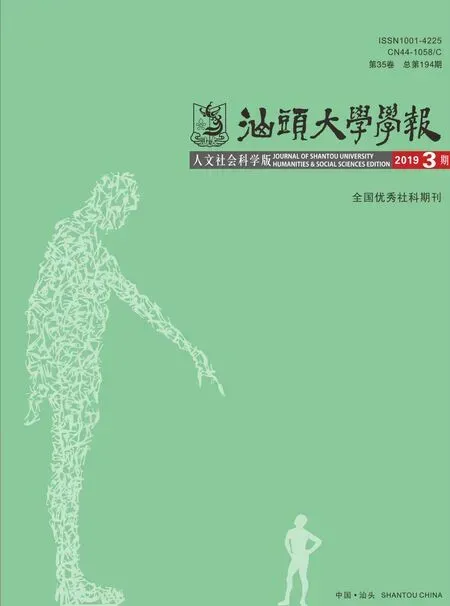明遗民的坚守与担当:徐枋文史创作综论
温世亮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世籍长洲(今属江苏苏州),明崇祯举人。甲申(1644)国变之后,绝不与清廷官员往来,坚拒满清的爵禄恩赐,以耿介的志节屹立于遗民之林,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并称为“海内三遗民”。作为明季遗民的典范,徐枋在文学、史学、画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明末清初文化思想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小腆纪传》《前明忠义别传》《明史》《清史稿》《国朝先正事略》《南疆绎史》《碑传集》《国朝画识》《涧上草堂纪略》等史学著述多有表彰;罗振玉更是亲自为其编撰《徐俟斋先生年谱》,以示对其“志弥贞,遇弥苦,学弥醇”之“景仰”(《徐俟斋先生年谱序》)[1]525。学界对徐枋的研究侧重于其遗民思想和画学成就的探讨,对其文史成就尤其是史学成就的论析则相对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就徐枋的诗歌创作和史学著述置于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综合论析。对于明遗民文化的深入探讨而言,这一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一、“案上诗编新甲子”:徐枋诗歌创作的遗民志节
徐枋出身于“声华披海内,天下率奔走”[1]415的苏州名门世家,甲申国变打破了其生活的平静,而坚贞的志节操守则使他成为明遗民的典范。徐枋今存《居易堂集》20卷,其中收录各体诗近200首。与徐枋的遗民身份相对应,坚贞志节的抒写则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核心内容。对此,我们可以从诗歌题材的角度逐一展开论析。
怀旧诗在《居易堂集》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徐枋常借助这一类诗的写作来抒发浓烈的故国情怀。而《怀旧篇》[1]429-433长篇,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全诗计1,400字,历叙诗人50年的身世交游和亲知故交,在对这些忠烈、遗民的哀思中显露出揪人心扉的亡国之痛。其中有句云:
平居怀旧意惝怳,五十年间似反掌。耆旧于今无一存,音容历历犹堪想。余年十四歌采芹,蜚声早擅青云上。郑庄有客大父行,张楷造门皆父党。……忽然丧乱倾家国,痛哭天崩复地坼。先公殉国汨罗游,止水无从居土室。人师独羡紫阳尊,婴城亦继彭咸则。当年贻诗勖忠孝,临风读罢还悲泣。稚齿即多长者游,况今避世荒江陬。……论交欲得意气真,交满天下无多人。延州后人称国器,咄哉琨逖斯其伦。……亲朋凋谢岁月驰,怀人拊景宁能追。当时垂髫今白首,俯仰歘忽成吾衰。岁寒后凋意自勉,硕果不食心相期。
从少年得隽的意气风发到遁隐荒江土室的孤寂苦闷,那些贞节守志的师长朋辈的奖掖勉励确实给予诗人莫大的精神鼓舞,使他终能苦节自鸣、不食心期。只是“中原遗民竟谁在,独立宇宙能委蛇”,他们的逝去难免会是一种心灵的阵痛,继之而来的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生命孤独感。此诗作于诗人63岁时,也就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时满人统治已趋于稳定,加上亲朋知己多半凋谢的现实,使徐枋越发感觉到知音难求,而那种曾经有过的恢复怀想自然随之成为泡影。然而,诗人的河山之悲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更改,相反愈显强烈,诗中“情深一往不能已,缅怀邈若悲河山。黄公酒垆山阳笛,人生有情泪沾臆。诸公往矣那复得,草堂寂寂无颜色”云云,无疑成为这一情感最为形象的表达。于此诗,朱用纯《书徐俟斋怀旧篇后》称道:“故于生死之际,叙至淋漓,一篇之中,而国难家忧、人品物态、伦常性情学问悉可概见。此六经所为立教,而俟斋特于诗发之,夫岂后世文章家所易几者?”[2]卷十一就实际而言,怀旧只是诗人意念中的杂曲,借此以赞誉友人的风骨高致,寄托自己的拳拳赤子之心方是诗人的初衷所在。朱氏对此诗思想内涵的评骘,无疑是准确的。
除此之外,其五古长篇组诗《怀人诗》九首,同样能将天崩地坼后的兴亡感融入到对友朋的追思感念中。试读《怀人诗》之二:
呜呼鲁仲连,屈强不帝秦。区区蹈东海,大义终能伸。胡然天帝醉,金苻被强嬴。眇焉匹夫节,而与天帝争。十年遍天涯,四海谁情亲。一心贵有托,岂敢轻死生。故人在畎亩,揽涕为屏营。念子不成寐,落月空盈庭。愿言入我梦,梦见遥吞声。[1]405
借鲁仲连的义不帝秦喻友人不仕清,鲁仲连亦是诗人效仿的楷模。在长歌当哭的倾诉中,既完成了对忘年知心的由衷礼赞,又深切地体现了诗人对个人尊严的高度重视。此诗能入选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自是吻合了徐氏明遗民“朱嘱之歌”“清修自好,不坠宗风”(《晚晴簃诗汇凡例》)[3]卷首的选诗标准。
徐枋亦惯用咏怀诗来表达坚贞的遗民操守。明遗民遁隐逃禅乃清初的一大文化现象,但并不可视之为简单的逃生之举。他们以这一特殊的形式来对抗清廷的统治,以逃为抗则是其本真。正如归庄《赠徐昭法》所云“僧装儒行皆相似,绝俗离群我不如”[4]154,游身于佛门净地,却恪守着儒家的规范,徐枋即这样一位守志以抗的逃遁者。其实,在徐枋《徐次洲画像赞》“景山中圣,孝克逃禅。所谓怀文抱质,而抗志箕山者非耶。吾知其人,无忝家声。南州高士,东海遗民”[1]483云云,已透过对朋友的赞叹将自己逃禅的深层旨趣作出了最为真实的揭示,这在其诗中也有所体现。如查检《居易堂集》,我们发现诗中“渔”字句达29处,若加上相近的“鱼”“舟”之目,数量则更为可观。实际上,这些字眼无不是一个个内涵饱满的意象——或指向隐者其人,或指向隐者的生存环境,或指向隐者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通过守约固穷渔父形象的创设来寄托“以逃为抗”的心迹,恰是徐枋咏怀诗的题中之义。如卷十八《舟行堰中即事》一诗:
回首春游今再过,江湖秋水又生波。蒹葭岸岸风涛阔,杨柳枝枝烟雨多。楼阁已看衔暮景,汀洲何处起渔歌。此身直付轻鸥外,一棹沧浪奈若何。[1]443-444
因景感怀,意谓宁做一个萧然物外的渔者,也不愿受世俗尘纷的侵扰感染。尾联“一棹沧浪奈若何”,当是其何以“此身直付轻鸥外”的间接回答,此中包含了几多的辛酸与苦涩自是不言自明。如果说此诗的表意还略显晦涩,那么《怅望》其二所云“垂纶不为鲈鱼美,书帛难凭雁羽通。人事年年多错迕,谁云吾道已终穷”[1]444则非常清晰地展露了诗人的深衷隐曲——逃遁本非其愿,诗人并不甘心老死无为于水边林下,面对现实世事的风云变幻①顺康朝虽多取怀柔之策以巩固其封建统治,但文字狱、奏销案等高压之举亦递相发生,诗人所谓“人事年年多错迕”,盖于此而发。,对潜藏于心底的信念依然充满着希冀,忠于故明、誓不与清人为伍的抗争心态依稀可见。其它如《卜居》《有客》《怅望》等诗作,将“渔人”“渔父”“一钓舟”“渔樵”等富于意味之词置于诗间,会同诗人所处的物态情景含蓄地表达出那份高洁的遗民怀抱。
在以山水图画为对象的吟咏中寄托遗民情思,也是徐枋之擅场。对徐枋的品行操持,其挚友昆山归庄尝赋《赠徐昭法》诗为赞,云:“为望同云住半途,连朝晴旭丽高衢。知君素有回天志,急扫吴山飞雪图。”②此诗归庄《归庄集》未录,转录于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卷下,见徐枋《居易堂集》615页。内中“住半途”“回天志”之谓,对徐枋蓄势待发、以图恢复的志向给予了最为真实的描述和揭示。而《自题山水画幅》③此诗《居易堂集》不录,转录于柳亚子《分湖诗钞》之《寓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91页。一首,乃徐枋流寓吴江汾湖时所作,末尾所云:“寂静淡无垠,万里堪极目。浩气澄素秋,忧怀寄林麓。”即通过幽寂而不乏苍劲的环境描写,含蓄地体现了诗人那份矢志以抗的怀抱,同样是诗人最为本真的心曲心声的反映。又如以下两首题画七绝:
流水衡门隐者家,石梁山径逐溪斜。仙癯自是甘肥遁,尽日松风吹落霞。(《题画即事》)[1]453
千春流水渺无津,万树桃花好避秦。高卧此中堪白首,不知人世有红尘。(《题画八首》其二)[1]452
国变后,有感于家仇国恨,借助山水题咏来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慰藉,确是遗民诗歌表达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而通过僻静幽雅山水环境的描绘,透露出宁可享受山间的滴滴清凉,甘做一个“不知人世有红尘”的隐者,也不愿为清廷所牢笼的胸怀,正是两诗的内涵所在。再如《题孤楫溯江图》一首,乃作于其甥吴商志省亲金陵时,诗人通过“孤楫凌江涛,行行溯杨子”的叙述,激励其“进不避难,退不规利”,以“遂其亲高翔千仞之志”[1]413-414。张元济所谓“读之者其能无引领涧上草堂,而兴山高水长之思乎”[1]附录,虽乃就《居易堂集》整体文辞来谈读者接受的效果,然其笔下类此之山水题识,完全可视为重要的例证。
综上观之,无论是怀旧还是述志,抑或是题画写心,徐枋都能立足于明社既屋的社会现实,将自己作为前朝之孑遗的那份深沉的忠义节概蕴蓄其中,显示出浓烈的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诗歌创作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也因此得以更好的彰显。
二、“井中书续旧春秋”:徐枋史学著述之经世内质
自甲申(1644)国变之后,流寓漂泊、隐迹山崖也便成为徐枋生活的代名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保持忠节的同时,徐枋亦倾心于历史著述,并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自己于世间人事的关注。在《与葛瑞五书》中,徐枋清晰地交代了自己国变后二十年中的著述情况:
然以二十年幸生而自谓尚可与兄披襟解带而无愧者,非独以杜门守死为然也。此二十年中所成书,《通鉴纪事类聚》三百若干卷、《廿二十一史文汇》若干卷、《读史稗语》二十余卷、《读史杂钞》六卷、《建元同文录》一卷、《管见》十一篇,计成书亦且几百卷矣。[1]25-26徐枋成长于以《春秋》为尚的苏州瓜泾徐氏家族,因受“家学”的深刻影响,深明《春秋》之大义④关于苏州瓜泾徐氏的《春秋》家学传统,可参阅拙文《家族精神的文学传承——以近世苏州瓜泾徐氏家族为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大致而言,徐枋的史学著述也贯彻了“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因此其字里行间所展露的经世意识同样极为深刻。一方面,面对“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着力于探讨国家治乱的根源是这些著述的重要特点,显示出作者揪心于志节忠义,力图以重振旧的封建道德传统来挽救颓废的世道人心的意愿。例如《古今人不相及》一篇,论述北宋王继忠陷于契丹事。徐枋认为,王继忠虽羁留北国而未死于国事,但能感戴赵宋爵禄之恩深,故终能拳拳于故国而不忘。而“□□明崇祯中,亦有大臣陷阵降虏,而以死绥闻,赠恤优厚十倍于宋之待继忠。而其人后从□入陷两京,凡所以□□明者,无所不用其极,是不啻继忠之罪人也”。后来他又说:
近有□明大臣,降□为□镇南都,从虏兵斩伐陵木,致忧葱三百年者,一旦遂同赤地。而长陵一抔土,不免震惊,是又朱泚之罪人也。以二事观之,则其人之肉,狗彘不食者矣!吾安得手刃之、寸磔之,而灭其骨也。[5]350-351
内中“其人”,陈起病谓指洪承畴[6]338。徐枋认为,受明朝之恩遇,国危之际不能学王继忠“不忘本朝”,却作叛逆倒戈之悖行,实乃唐末朱泚类的千古乱贼。在古今对比中,徐枋不仅委婉地表露了自己的高尚志节,同时也对前朝史实予以评判,从一个侧面强调了涵养士人的忠诚节义精神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
又如《读史稗语》中《靖康之祸》一文,论述“靖康之祸”的根本原因。在此徐枋能另辟蹊径,从道德层面立论,指出其祸之本,诸儒虽已道之甚详,但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于“绍圣诸奸”,也不在于“王安石新法害民,骚动天下驯致”,而在于“废《春秋》”之举措。进而又言:
圣人之所以诛乱贼,辨华夷,而天下恃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春秋》也。顾且毁为断(煨)朝报,一日废之而不恤,焉保其不用夷变夏,臣事左袵,俯首于不共戴天之仇,而灭其君臣父子之伦也乎?[5]366
从维护君臣父子之纲常或封建秩序的目的出发,将祸之根本归之为“废《春秋》”,立论显然有固守程朱以恢复旧的道德传统来挽救危亡的偏颇。但若结合徐枋所处的时代现实来看,其信守《春秋》之微言大义、贬褒据实的立场,确又是隐含着“鉴往所以训今”(《答徐甥公肃书》)[7]138,借宋事以言明亡的意味,有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另一方面,这些史学著述也表现出鲜明的为天下、为黎民、为后世服务的意愿。置身于河山易主的历史背景之中,徐枋身上实不乏时代所赋予的特质。他虽然无心于新朝,栖身于草野山林,拒绝为清廷服务;但那种服务天下苍生的理念并未泯灭,借助于史笔得以传达出来。一如《致巢孝廉端明书》所言“士君子不得志于时,往往著书立说,以垂教于后世。弟之无似,心窃慕之”[1]50,徐枋写作《通鉴纪事类聚》的初衷或者目的即在于通过参订司马光《资治通鉴》、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三部史书,考析前人治国理政之得失,并“独立义例,比事相引,较悉毫厘,人以事分,事因类聚,凡分为若干事,聚为若干部”,以备“有国家者资为殷鉴,掌典故者奉为元龟”“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通鉴纪事类聚》[1]101-106。至若《廿二十一史文汇》《读史稗语》《读史杂钞》《建元同文录》《管见》等史述的创作鹄的,亦不出此畛域。如《管见》11篇,乃徐枋读《管子》之心得,虽早已散佚,今天已难见其本来面目;然而,透过朱用纯“胸怀日月之明,笔有风霜之气”[8]卷上的评述,却依然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其间所蕴蓄的入世志尚。而《读史稗语》一书,乃徐枋史学著述中仅存的一部,“或摘古人之行事,窃志微辞;或探义类之玄赜”,究其撰述之原委,正在于“上可以穷天人消息之数,此可壮君国黼黻之猷”(《读史稗语序》)[1]107-108。
探析徐枋相关的史学文本,同样能寻绎其深厚的服务天下黎民的理念。如《米价》乃《读史稗语》的开篇之作,其开首便明确指出“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故米价之贵贱,足以征其时之治乱也”[5]273,并以时代为序,反复列举史实予以诠释,强调了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又如《民心》一篇,起句即称“民心戴政统而恶乱贼,内中国而外夷狄,千古所同也,贵在因人心而用之耳”[5]293;而《复租税》[5]293一篇,则将汉光武帝与宋武帝相比,借此探讨赋税之轻重与国祚之长短的内在关系,实际都关涉民心向背的问题。至于《封建论》一文则是一篇带有政论性质的散文。对此文,陶白先生认为能够从“适乎时”“宜乎民”的角度探讨“封建制”过渡到“郡县制”的必然性,内中包含的经世意识是明显的,相较柳宗元的《封建论》,包含着更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9]298-299。此外,明末清初为文士所乐道的井田、君臣、公私、华夷、学校、府兵、租赋、廉贪等问题,《读史稗语》亦多有涉猎。这些论述,虽说未必都是直接涉及明清时事,相反更多是着眼于历史故实和历史人物的品评来间接地阐发自己的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然而,与其生活的年代——故国风雨飘摇、民族压迫深重、人民生活困顿——却有着紧密的关联,通古以及今,实际又是立足于当世之务而发,作者借历史的论述来指摘当下、探讨明亡的历史教训,以及服务于后世的意图,可以说非常的清晰。在《与葛瑞五书》中,徐枋尝言:“二十年读书课文,编辑之中盖亦有得于身心之学焉。”[1]26诚然,“身心之学”乃阐扬己见的自得之学,其中除了徐枋高洁的民族忠义发抒外,当然也不乏其经世见识的阐扬。
总体而言,透过这些史学著述以及相关著述旨归的表述,我们不难发现:于流寓漂泊中著书立说以垂教于后世,而并未因隐迹山野而忘却世间俗务,积极践行以史经世,实乃徐枋的一大心曲。余英时先生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一文中明确指出:“‘经世’必究心于史,尤须注重当代之史,这是明清学人的共同看法。”[10]4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世实乃其史学著述的本根所在。
三、“血泪纵横炳大文”:徐枋文史创作之文化意义
在那个世变急遽、血火遍布的明清易代之际,遗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谢正光《明遗民录汇辑》,像徐枋那样能做到不降其身、不辱其志的“孑遗余民”,其数量当在两千五百之上,正所谓“洎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前仆后继。永历帝殉国后,遗民不仕新朝,并先后图报九世之仇者,踵趾相接,夥颐哉!”(钱仲联《明遗民录汇辑序》)[11]卷首同时,在这些明遗民的身上无不印刻着深厚的时代痕迹,这也使他们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最富有文化内涵的群体。
就人生志向而言,明遗民往往执着于“夷狄大防”的儒家正统观念,坚守“忠臣不事二主”的人生信条,毅然决然地与清王朝划清界限,他们宁可栖身于草野,也不愿臣服于来自于白山黑水间的满人统治。因此,诸如流亡、隐逸、逃禅一类稍显消极的对抗方式,自然成为他们最为普遍的生存方式或际遇。与此相适应,抱道以守志,为改旗易帜的河山而伤,为逝去的英灵而悲,也便成为明遗民诗人们普遍的艺术追求。而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状态,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遗民诗人们更多地将其诗笔径直伸向他们的心灵世界,用其饱浸风霜的文辞来揭橥他们的复杂心绪,抑或是那种浸润、裹挟着泣血抗争、铁骨忠贞和酸楚色彩的人生性灵。
在此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遗民作为朱明王朝之所遗,虽说啸傲林泉、耻事新朝是他们最为突出的人生态度;但是,并不可就此将他们视为纯然的不关世情的出世者或者厌世者,也不可将他们视作单纯的只懂得枕戈泣血的悲悯诗人。相反,他们只是选择了不同于仕籍新朝的其它方式来寄寓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期许和诉求。在他们的身上,既显示出志节坚守的忠贞,也散发出勇于担当的光芒,如果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那就是“(明遗民)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12]12。就实际而言,通过史学撰述来表达自己于社会人生的关注,则是明遗民展露其淑世情怀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恰是在这些胜国遗民的推波助澜下,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渐次衍生出一股蔚为壮观的经世思潮。
在这样一个思潮中脱颖而出——能以诗歌创作和史学著述来言情见志的明遗民文士,实又不乏其人。据赵洋《调和与冲突: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初的历史书写》[13]16统计,清初近八十年间,明遗民史家群体的总体数量达141人(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如徐枋、魏禧等名流均未纳入其统计范围)。其中荦荦大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等,他们大抵能执诗、史两端,在歌吟郁结愁苦和山河破碎的同时,亦不忘经邦济世之志的表达,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续命人。作为明遗民声誉度最高的文士顾炎武,于朱明的忠贞尤见贞烈。入清后,他游走于南北之间,强项不屈,以恢复明统治为职志,对那些首鼠两端的变节者更是深恶痛疾,尝谓“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广宋遗民录序》)[7]36同样,他能以诗鸣志,今所存的《亭林诗集》六卷,一如清人沈德潜所谓的“词必己出,事必精当”,而每见“风霜之气,松柏之质”[14]300。顾炎武亦肆力于学,且能在“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7]93思想的指引下发为经纬天下的恢弘文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可以说都是这样的杰作。至于一样具有铮亮志节的遗民历史学家黄宗羲,他虽不专力于诗,但其《南雷诗历》五卷,往往能“以真情思驱遣文字”[15]195,内中所蕴含的故国情衷自然不会轻薄。在史学观点上,黄宗羲倡导“先经后世”“经体史用”和“有体有用”,而他所编撰的《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明夷待访录》等一系列的史学作品,实际又是“凝聚着他的家国之恨,贯穿着他的历史眼光,渗透着他的经世史学思想”[16]41-45。相较于黄宗羲,明遗民王夫之的诗歌创作则甚夥。其《畺斋诗集》中的《落花诗》99首,实乃伤时感事之作,而每见饮恨吞声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内含的“政治意识”极为鲜明[17];所以,对其诗陈田《明诗纪事》有“其遭时多难,嚣音屠口之作,往往与杜陵之野老吞声,皋羽之西台痛哭同,合于变《雅》、《离骚》之旨”[18]卷首之谓。王夫之的史学著述同样极其宏富,《尚书引议》《春秋家书说》《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等,林林种种,实不下数十种。不过,据要而言,王夫之撰史的目的与顾、黄实相仿佛,强调“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亦不出经世致用的范畴。
对徐枋的志节与文史成就,前贤多有咏叹,如杨昌言《寄祝徐俟斋先生六十》云“案上诗编新甲子,井中书续旧春秋”[19]47,徐达源辑《涧上草堂纪略》所录沈嘉魁赞诗亦有“血泪纵横炳大文,千秋亮节贞珉记”[1]681云云。确实,于前文分析可知,以诗歌抒写铮亮志节的坚守,以史笔展示于家国民族的关注担当,自是徐枋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题旨。而作为明遗民的重要代表,在这一点上,徐枋的文史创作与明遗民的思想潮流无疑是相吻合的,显然具有不可轻忽的时代文化意义。质而言之,以诗写心,以史经世,实乃明末清初的时代思潮,而绝非徐枋所特有;但是,徐枋所具有的引证这一时代文化思潮的典范意义又是毋庸置疑的。以此而论,无论是徐枋的精神品相还是诗歌创作,抑或是其史学著述,均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