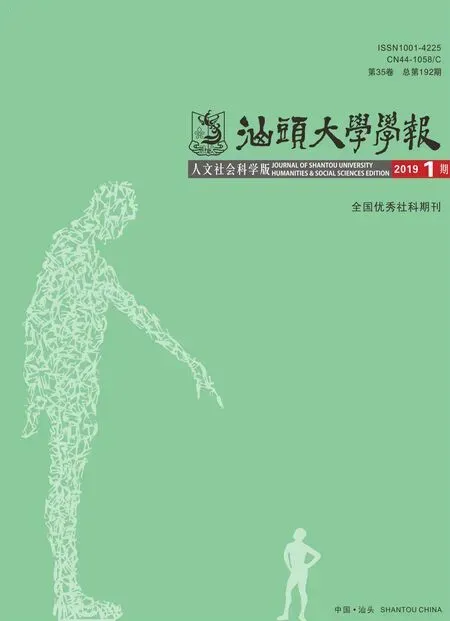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王 凡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高罗佩(1910-1967),荷兰著名汉学家。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虽辗转亚洲多国任职,却毕生痴迷于中国文化。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汉学研究,著述颇丰,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推理探案小说集《大唐狄公案》。这部由二十余个故事篇章构成的小说作品在着重表现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彰善除恶的传奇经历之时,亦有意凸显了其作为儒家士人的形象特质和精神品格,并通过这一艺术形象所潜隐出的内在文化意蕴投射出高罗佩本人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辩证思考与独特认知。
一、狄仁杰儒家士人形象的独特呈现
作为唐代的中兴名臣,狄仁杰不仅在当时受到武则天的倚重、群臣的敬服以及百姓的爱戴,而且亦成为后世文学家的重要表现对象,其身上所体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更是成为了文学书写的主要方面,这在明清小说戏曲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明代戏曲《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就通过“望云思亲”“抗节不阿”“力救无辜”“复招庐陵”等曲段,对狄仁杰“从忠孝仁义四个方面进行了塑造,力图塑造一个具有传统伦理纲常的完美的忠臣贤士艺术形象。”[1]277而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中,作者通过“六里墩杀人案”“周氏通奸杀夫案”的侦破突出了狄仁杰推理断案的不俗能力,更以“痛击恶奴张宗昌”“惩治奸僧薛怀义”“还招唐中宗复位”等情节展现了其不畏权贵、为民做主、惩奸毙恶、复兴唐氏等重要事迹,彰显了这位历史名臣祛邪扶正、辅国安民的儒家精神品格。而在将中国古代文学题材与西方侦探小说手法有机融合的《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也同样以自己独特的文学笔触展现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士人的形象特质与理想化的人格精神。
(一)狄仁杰儒家士人形象的多层次彰显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时常强调狄仁杰作为儒家士人的形象特质和思维方式。《御珠案》中,面对浦阳民众祭祀河神的活动,高罗佩就写道“狄公是个坚定的正统儒者,他对这种俗祭淫祀一向深恶痛绝。”[2]139《黄金案》言及狄仁杰“同孔子先师一样对鬼神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3]21《迷宫案》中,当狄仁杰与鹤衣老人交谈之际,也写道:“狄公寻思,主人对他所问避而不答倒也罢了,不期却又进而贬低儒家经典,心中很不是滋味。”[4]213《朝云观》中,在与持道家理念的道士孙一鸣探讨时,狄仁杰言:“道德真言、柱下旨归固然有深刻的哲理,究竟孔子才是人伦之师范,万世之楷模。”[5]43而《飞虎团》则提及狄仁杰深谙孔子的“乐教”理论。可以说,高罗佩有意从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主导思维等不同方面来对深受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影响的狄仁杰其士人形象给予多层次的点染。
作为《大唐狄公案》的主人公,狄仁杰的两性情感世界是高罗佩对其进行性格刻画的重要方面。《铁钉案》中曾两次表现狄仁杰对女牢典狱郭夫人的微妙情感。第一次是作为下属的郭夫人在向狄仁杰例行公事、汇报女牢近况之后,“狄公深深感佩郭夫人的精明干练,也微微被她那意态风神撩起一点迷惘。”[6]210第二次则通过更多的篇幅笔墨细腻铺排了狄仁杰的内心活动:
狄公坐在书案前拿出一卷公文阅读,但他的头脑却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忽然他记起郭夫人说的那首吟咏梅花的故事,诗的题目是《玉人咏梅》,出自二百年前南朝一位著名诗人之手,他不禁兴奋地一句一句地背诵了起来:
人境雪纷纷,一枝弄清妍。孤艳带野日,远香绕天边。玉色宁媚俗,真骨独自寒。飘落疑有声,蛾眉古难全。
狄公忍不住责备自己为何适间在药师山上面对郭夫人却一句也背诵不上来。他长嘘一声,深恨自己记性太糟,往往应记住的东西却忘却了,待不需要记时却又如泉水一样奔腾激涌而来。想到此,狄公不禁又喟叹频频,自怨自艾了一阵。[6]228-229
作品在此细腻展现了狄仁杰忆及前日在药师山与郭夫人偶遇时后者所提及的咏梅诗作,以及他本人不由自主地自责、惋惜自己在当时未能吟诵出这首自己本已熟知的诗作,尤其强调了其甚至还为此“喟叹频频、自怨自艾”的独特心理活动,而这正是由于狄仁杰对未能在偶遇郭夫人时吟诵出她的心仪之诗这一过往之事的耿耿于怀,他的介怀之意并非是忧心自己被郭夫人窃笑为无知之徒,而是因未能借此与郭夫人形成一种有机契合的交流而抱憾不已,由此足见其在内心深处对这样一位容貌非凡而又精明强干的女子所具有的特殊情愫。可以说,高罗佩通过狄仁杰投射于郭夫人的这一富于柏拉图式意味的情感表现,一方面在狄仁杰志虑忠纯、祛邪扶正、断案如神等形象基调中为其平添了真实生命个体所应具有的细腻情感变化和复杂人性纠结,另一方面,狄仁杰在面对感佩爱慕之人所表现出隐忍持重之意也曲折幽微地传达出儒家传统观念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独特理念,由此也从人物情感表达方式上使狄仁杰与儒家士人的生活处世思维更为贴近,令其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古代士人的形象特质。
由于“中国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所以他们的生活情趣多样、高雅、充实而且有意义。”[7]21作画、习字、对弈、抚琴都是士人日常书斋生活的重要内容,从事这些文化艺术活动既可舒张与凸显自己的才情,又是士人获取高雅精神享受的主要途径,更是其排遣愁思意绪、躲避世俗喧嚣的特殊方式。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浸润的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也穿插性地表现了狄仁杰与传统士人一般无二的文化修养和闲情雅趣。例如《紫光寺》中,狄仁杰曾言:“作画尚需心境,应物斯感,意态勃萌,或由于虚静之澄虑,或由于媒介之触机,胸中油然沛然,意内山水重叠,方能运笔生气,泼墨豪宕。”[6]80由此足见其在书画方面的艺术素养。《四漆屏》以狄仁杰的视角来对冷德、银莲合写的情诗进行了诠释:“它用逝水落花来比况人生短暂,欢乐难久,很可能就是暗喻这种私会的关系,且写得不落俗套,甚有意境。”[8]102由此从侧面展现了狄仁杰的诗歌鉴赏力,而《飞虎团》则借狄仁杰夤夜抚琴来向读者展示其在古乐弹奏方面的喜好。可以说,狄仁杰的这一形象特征也寄托着高罗佩的某种文化理想。正如学者陈之迈在谈及高罗佩时所言:“他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雅士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的生活。”[9]6中国古代士人精通诗画琴棋可以说是被高罗佩高度认可和赞许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他本人对中国古代的琴棋书画十分痴迷,其终身研习中国书画,精于古代书画的辨伪识真,且学习弹奏中国古琴和创作古体诗词,并与当时的书画大家交往甚密。高罗佩之所以在工作之余沉醉于这些文化生活,既是由于他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由衷喜好与热爱,更是他对古代士人精熟于各种艺术并以此陶冶情操、寄托意趣的独特生存状态十分向往的无形投射。可以说,从对狄仁杰艺术才情及审美素养方面的独特彰显来看,高罗佩力求令自己笔下的狄仁杰呈现出儒雅士大夫的形象侧面,而这一形象也成为了追慕中国传统士文化的高氏本人其中国古典文化情结的某种承载与象征。
(二)狄仁杰儒家理想人格的着意刻画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不仅从诸多方面展现了狄仁杰儒家士人的形象特征,更有意彰显了其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这主要表现在其具有的儒家倡导的“博施济众”、抚民安邦等士人所应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为它灌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10]25可以说,儒家自孔子以来一直都倡导济世救民的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勇于任事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因此,“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品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7]6孔子提倡和高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1]79的精神,孟子同样指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12]297清代的黄宗羲更是表示:“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13]288这些先贤都十分重视儒家士人所应具有的历史责任感。而深重的忧患意识则既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对国家民生问题的社会关怀和自我承当意识”,又“与士人渴望辅佐君王、为国家建功立业而追求不朽的愿望是连在一起的。”[14]17“忧患意识来源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源于他们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7]7可以说,这种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儒家精神品格也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高罗佩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这从他所塑造的狄仁杰形象身上便可窥见一二。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不仅通过富商自戕之谜(《四漆屏》)、尸身调换之谜(《紫光寺》《飞虎团》)、密室杀人之谜(《红阁子》《迷宫案》)、地下帮会之谜(《湖滨案》)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案件凸显了狄仁杰的超凡智慧,更于其间投射出他除奸扶善、忧国爱民、忠直宽仁的儒家精神品格。《广州案》中,狄仁杰之所以密赴广州查察钦差柳道远的踪迹,全因位列三卿、权掌中枢的柳道远其踪迹牵动着朝局变化、人心向背,狄仁杰正是希望通过查清其踪迹来维稳朝局;《柳园图》中,面对“时疫流行,圣驾西行,人心惶恐,国步维艰”[15]60的特殊时局,狄仁杰主动请缨,留守京师,从而在危急之时愈发凸显出他替上分忧、劳心国事的责任感;《铜钟案》中,狄仁杰言道:“当今皇上好佛道,天下僧寺道观无数。僧尼道士倡异说,乱儒典,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最是国家之蠹虫,人伦之大患。”[5]149从而不仅对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更对佛道兴盛所潜存的社会隐患及统治危机不无忧虑。高罗佩在展现狄仁杰呕心沥血于国家社稷之际,亦不忘表现其虑念普通百姓的生死、疾苦。《飞虎团》中,高罗佩就展现了在洪水阻道、匪患围城、外援不济的危境中,狄仁杰不惜亲身涉险,救助自己偶遇的庄客、难民:
他有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他必须救出这庄园里无辜的人和那些嗷嗷待哺的难民。他甚至想去强盗面前暴露自己的姓名,以朝廷里最高司法官员大理寺正卿的身份与强盗对话,做一番劝谕宣导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他将作为一个人质去冒一场不可预测的风险,很可能也会被那群暴徒割掉耳朵、手指,甚至头颅。[15]15
而《柳园图》则对狄仁杰有如下一段心理揭示:
凶恶的疠疫如何发生、蔓延我所知甚少。临危受命半个月来,疠疫未能抑制,死人有增无减。眼见着尸骸遍地,人怨鬼哭,我于心何忍?[15]56
深受儒家影响的正直之士在注目于现实弊政与生民疾苦,并怀抱救民宏愿之际,亦时常表露出发自内心的自省自咎意识。白居易在目睹百姓田间劳苦之时,不忘感喟:“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16]22而在《大唐狄公案》中,作为京城留守的狄仁杰因感自己无法遏制瘟疫蔓延,以致百姓罹祸而愧疚自责,其可以说与白居易一样透露出具有强烈人道意识的传统儒家情怀。
通过在《大唐狄公案》不同篇章中对于狄仁杰的形象展现,高罗佩着意彰显了其作为儒家士人所具有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7]195式的强烈忧患意识和“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1]161般的责任感和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高罗佩正是通过对这位作品主人公的儒家精神品格的独特呈现昭示了其本人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和积极影响的肯定与褒扬,进而在通过自己作品来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加以表现和传扬的过程中投射出前者对于其本人的无形浸润与深刻影响。除此之外,由该书中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形象特质也可见出高罗佩对于这一历史人物文学形象塑造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明清小说、戏曲作品在展现狄仁杰的儒家形象时,更注重从主流政治的层面呈现其忠君爱民、忧心社稷等儒家精神品格,而高罗佩在塑造狄仁杰的形象时也承袭这一人物特征;另一方面,高罗佩又从人物的言行举止、思维意识尤其是个人情感表达等方面凸显了狄仁杰的儒家形象色调。由此,既反映出高罗佩在自己的小说中更为全面、多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人物的儒家形象特质,也反映了《大唐狄公案》与明清小说、戏曲在狄仁杰的儒家形象塑造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及明显的差异。
二、狄仁杰形象塑造中所折射的儒家诗教观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展现了上至达官公卿、下至贩夫走卒这一丰富复杂的形象谱系,而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也成为高罗佩文学观照的重要对象,其中《黑狐狸》中的玉兰、《朝云观》中的宗黎、《四漆屏》中的银莲都是独具风姿的诗人形象。与此同时,高罗佩还通过作品中涉及诗歌、诗人的情节来呈现主人公狄仁杰的某些形象侧面,并将自己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认知潜隐其中。在《黑狐狸》这一诗歌艺术氛围极为浓郁的故事篇章中,曾有狄仁杰拜谒前辈阁臣邵樊文一节,二人间的对话也可谓别具意味:
“狄仁杰,你也写诗吗?”
“晚生只写过一首诗。昔时也刻苦学过一点儿金针诗格,奈何天分陋薄,总不见有甚长进。以后忝身县务,更无暇及诗了。”
“狄县令许多诗人正是以一首诗万口脍炙,成了万古绝唱而流芳波名的吗?不知你这一首诗是什么题目?”
“大人,这是一首《劝农诗》,五言百韵,无非是指出农为国家之根本,百行之首要。”大学士好奇地望着狄仁杰:“你为何要取这个题目?”
“晚生只是想将劝农重本的道理用诗歌来表述,押韵又富于节奏,普通人都能听懂,农夫或许更喜闻乐见。”[2]27
表面上看,作品在此仅是展现了狄仁杰与邵樊文这一后辈官吏和前辈显宦的礼节性会晤,二人关于诗歌创作的谈论也似乎意在从侧面突出邵樊文喜好作诗之甚,然而在这段对话中,狄仁杰的对答却意蕴丰富。从狄仁杰的角度来看,其针对邵樊文所问之事的对答表明了他本人虽精于断案,但于作诗则是既无兴趣,也不擅长,但狄仁杰通过所作的《劝农诗》却昭示了其对诗歌及作诗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一方面诗歌作品应展现世态民生、关注百姓疾苦、有益于国家社稷,这既应是诗歌创作的基本题材和方向,更应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为了实现上述社会功用目的,诗歌表达应通俗易懂,以此能使其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而绝非邵樊文所谓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之作。同时,辞藻、声律、格套等方面虽在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但其却是为实现上述功用目的而服务的。因此他潜在地反对为作诗而作诗的创作初衷,认为诗歌从根本上只是揭露社会弊端、反映现实问题的媒介与工具。狄仁杰针对诗歌创作这一态度与《四漆屏》中他翻看同僚滕侃之妻银莲的诗作时所表现出的思想活动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艺术契合:
他开始从头一首一首读起来,很快他就被吸引住了。他非常欣赏这本诗集,其伦理纲常关乎世道人心,讽喻比兴切合诗旨三昧,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且锻字炼句、音韵声律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狄公早年也写过一首劝农的长诗,他一向对那种螭红拈翠、专门描写男女间恩恩怨怨的个人喜怒哀乐的诗不感兴趣,对那种叹老嗟悲、无病呻吟的诗更是头痛。[8]112
可以说,《黑狐狸》狄、邵论诗谈话中所反映的狄仁杰有关诗歌的认识在上述一段话中已被体现得无以复加,并由此折射出一向以狄公自比的作者高罗佩针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总体认识:即肯定、认同那些反映现实问题、关注社会人生且情感真挚丰沛、格调朴实无华的诗歌作品,而对那些视野狭窄,只关注一己之悲欢,罔顾黎民疾苦,或是一味追求诗歌技巧、而忽视思想主题的诗作则相对轻视、鄙弃。这一观念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儒家传统诗教观的无形折射。“孔子身处东周王权衰落,诸侯国起而争雄的时代,孔子并没有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徘徊不前,而是树立了‘克己复礼’的重要理想,毕生以拯救家国为己任,再加上孔子论诗是在春秋诗人‘断章取义’以赋诗之后,就使得孔子对诗的阐释具有强烈的功用主义倾向。”[18]212其所提出“兴观群怨”说就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并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高罗佩通过狄仁杰所欲阐发的诗歌应观照社会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诗歌审美观念则可以说是发源于“兴观群怨”的理念,“兴观群怨”之说所包蕴的诗歌可起到观察社会现实、反映世风盛衰得失,诗歌亦可干预现实,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与不良的政治等内容都已尽皆为高罗佩认可并吸纳。除此之外,孔子所提倡的诗歌应“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等观念也一并为高罗佩所接受和汲取,从而在其小说情节的建构中被曲折隐幽地呈现出来。由此可见,高罗佩本人对于儒家提倡的上述诗歌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风雅”精神即中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审美传统秉持着一种肯定、褒扬的基本态度。
可以说,高罗佩正是以一种“草蛇灰线”的含蓄方式投射出自己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认知:对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审美传统的重视,对中国古典诗歌强调社会功用这一理念的肯定,进而反映了其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关注社稷民生这一基本理念以及儒家所提倡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等诗歌观念的认同与传承。
三、狄仁杰“侠”形象呈现中的儒家文化思辨
从《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对于儒教诗歌观念的肯定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诗歌作品应针砭现实、关注时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潜在认同,进而反映了“他经常以儒家士大夫阶层的观点去看中国,他对儒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怀着崇敬的感情。”[3]16然而这并不代表高氏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全盘接受,在对儒家诗教观及其倡导的以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理念表示认同之时,高罗佩也通过狄仁杰的形象塑造投射出其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理性审视和辩证认识。《大唐狄公案》在突出狄仁杰忧国忧民的儒家精神品格与屡破奇案的超凡才具的同时,也别具意味地刻画了其武艺精深、力战群敌以及以特殊手段来惩裁罪恶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汤哲声先生就曾针对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这一形象特征指出:“狄公与包公等人相似,也是一个县官,但是他身上没有什么‘官气’,倒有更多的‘侠气’。”“他文武双全,文能察言观色,判案断案,武则武功出众,寻常匪徒不是他的对手。”[19]在《迷宫案》的开篇伊始阶段,路遇剪径盗匪的狄仁杰就展示了其颇为不俗的武艺:
两张戴黑面纱的脸突然在狄公的车窗口出现。不容分说,其中一人抡起棍子便向洪参军脑门击去,只一下他便昏晕过去。另一名强人则举枪向狄公刺来,狄公猛一闪身,正好躲过,又一个急转身,双手风驰电掣般伸出去,将对方枪杆死死抓在手中。对方在窗外拼命拽拉,以期夺回武器。狄公紧拽不放,随即顺着对方拽拉的方向向前猛一推,那强人便摔了个四脚朝天。狄公趁势将枪从强人手中夺了过来,跳下车,手中长枪上下翻飞,左旋右转,两名强人欲上前拿他,只是近身不得。打昏洪参军的强人手中仍拿着那根棍棒,举枪欲刺狄公的强人此时从腰间拔出一把利剑,二人一前一后,一个舞棍,一个挥剑,两面夹攻,奋力厮杀。狄公见两名对手如此拼命,自思此战必须速胜,若稍迟延,则很难对付得了这两个亡命之徒。……此时狄公的对手只剩下那名持剑的强人。于是,狄公挺枪加快了进攻。他先对强人虚晃一枪,对方急举剑招架,他又突然改变打法,将手中枪飞轮般在空中旋转起来,终于用枪杆将对手打晕了过去。[4]10-11
这段颇具武侠小说艺术神韵的武打情节描写不仅细腻呈现了狄仁杰高超非凡的武艺、顺势而动的应变能力,亦在紧张激烈的打斗中生动表现了他冷静机智、有勇有谋的一面。《黄金案》《飞虎团》《玉珠串》等故事篇章也同样不乏狄仁杰凭借精湛武功击杀悍匪的情节描写。
在《朝云观》中,当狄仁杰面对朝云观荼毒少女案的元凶罪魁——道士孙一鸣而又无法将其绳之以法时,他借与孙一鸣独处之机,施以巧计令其毙亡。这段情节描写看似表现了无法通过正常法制途径来制裁罪犯的狄仁杰转而以某种特殊手段来惩恶扬善,体现出“作为一个执法者,他有着强烈的伸张正义、誓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决心”[20]123,然而这种邪不胜正、大快人心的结局无疑与狄仁杰作为律法代言人和执法者而应秉持的法治原则是有所抵牾的,反而通过这种以游离于律法制度外的特殊手段来惩治奸邪的表现令其透射鲜明的传统“侠”意识,使其本人在这一锄奸行为实施过程中更似一个以武犯禁、除暴安良的传统义侠形象。可以说,若将狄仁杰的上述“侠”形象特征与其儒家士人形象相结合来看,便鲜明地反映了高罗佩欲将儒家士人和传统侠士的诸多特征融注于狄仁杰形象的创作意图,对此,他也曾借书中人物凌刚之口加以形象而含蓄的说明:“论其体魄,这位县令当不媲咱们乔、马二校尉,然他亦是凛凛一躯,威仪赫赫,很有些军官气象,与多数斯文士绅自是不同。”[4]86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侠文化虽无法与儒、释、道文化相提并论,但其亦是源远流长,并对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在国家政治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虽存在“儒重名誉,侠重义气”,“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20]67的差异,然而,不少文人儒士却都对侠文化不乏推崇、倡扬之意,文人崇武的现象更是历代不绝,然而这“只是儒者重侠的一个比较表面的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蕴藏着某种深意,那就是对于侠者注重行动而摒弃空言的人格内涵的衷心企慕。”[22]416“儒者重侠的另一深层涵义,是在于透露了他们对自己与生俱来的依附性格的反思和批判。”[22]417从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演进来看,“儒家由于过于重视社会群体的稳定性,于既定的制度、规范、权威等,每易安于故常、惮于更张,更不鼓励个人对传统的反思及挑战,因此,儒家在面对‘世变’或因应‘世道’之时,往往就缺乏勇猛精进、卫决网罗的魄力,流于迂腐、保守、不切实际等弊端。”[23]147聂绀弩先生就曾指出:“士大夫既然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24]76对此,高罗佩也在《大唐狄公案》中通过具体的艺术典型来诠释这一文化现象。《黑狐狸》中的罗宽冲可谓是诗界文坛的风流人物,其虽身居庙堂,但却酷爱作诗,既与诗坛同侪、宿耆交往颇多,还热衷于组织诗会、切磋诗艺。虽然罗宽冲未因诗歌喜好而怠慢政务、嬉游无度,但其却并未被塑造成为一个勤于政务而又风流儒雅的完美人物,而是时常表现出临事诿搪、遇事失措的特征,如在宋一文被杀案案发后,作为一方父母官而总领县务的罗宽冲却是“沮丧地坐在太师椅上,面对着面前的一堆案卷双眉紧锁,面色阴郁,狄公走进书斋时他正在怨骂。”[2]31而在府衙诗会命案突发、由自己保释的女诗人玉兰背负杀人嫌疑后,罗宽冲不仅瘫软座椅、目光呆滞、绝望无助,更因担忧自己受到牵连以致丢官罢职,甚或身首异处而惊慌失措、泪流满面。可以说,罗宽冲作为一个追求儒雅、喜好诗文的官员型士人,其一遇突发事件便无从应对、镇定全失,更遑言以冷静的心绪、非凡的魄力来应对变故了,从而鲜明地映射出传统士人在性格方面缺乏果敢、担当精神而畏事迂迟的不足之处。《红阁子》中与青楼女子银仙两情相悦的秀才贾玉波本有机会通过和富豪千金结合来改善生活现状,但其却并未作始乱终弃的薄幸郎君,体现出他为求真爱而宁愿舍弃攀金附贵之机的可贵品质,然而与此同时,当无法为银仙赎身时,他宁可选择与爱人共赴黄泉、殉情而亡,也未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这实际上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罗宽冲相似的性格特征和行事思维。可以说,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士人虽抱有齐家治国、济世经邦的强烈愿望,但在面对非常状况之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他们不仅时常缺乏临机应变之策,更表现出委决不进、逡巡踟蹰、犹疑退缩的性格特征,而“豪侠之气恰可补足儒者所最为缺乏的阳刚素质,因此对于儒者,正是提升其人格品位的重要因素。具有侠气的传统知识分子,往往较少儒者普遍的弱点和缺陷。养成这种更为健全的人格,乃是许多古代知识分子内心自觉不自觉的要求。”[22]409-410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家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自觉地投射出对侠精神的憧憬思慕之情,从司马迁《史记》中“借儒形侠”[25]75“援儒称侠”[26]334的《游侠列传》到曹植、王维、崔颢等人的《白马篇》《少年行》《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诗作均折射出这种普遍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李白更是仗剑远游,其虽一生坎坷,但却始终身负“侠”气,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中亦是“以侠士与儒士对称”[27]379。尽管高罗佩在其著述中对侠文化并未留下只言片语的理论探究,然而他却通过狄仁杰性格、行为中侠义色彩的彰显投射出自己对传统侠文化的认同,更潜在地反映了其欲通过传统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弥补和健全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乃至儒家文化思想所客观存在的内在不足这一潜在希冀。故而,狄仁杰这一兼有儒士与侠客两面性特征的文学形象,表面看来仅是寄寓着高罗佩本人对“文武兼修”这一理想英雄人物的认同与期慕,但实际上更体现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的同时,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文化、思想在某些方面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负面作用。可以说,《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形象的儒家文化塑造和“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折射出高罗佩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和独特感知,并由此凸显出这位具有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在热衷呈现、钻研探究中国文化之时所具有的理性思辨精神与积极扬弃态度。
荷兰学者巴克曼与德弗里斯在其合撰的高罗佩个人传记中曾指出:“由高罗佩描绘的学者型官吏狄公这个人物,是他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28]214可以说,高罗佩在通过《大唐狄公案》对狄仁杰这一自己钦服仰慕、甚至被自己视为行为楷模的历史人物加以文学诠释的过程中,不仅着重展现了狄仁杰“专断滞狱、勘破如神”[8]6的非凡智慧,而且也呈现了其作为儒家士人的形象特征,令其凸显出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并含蓄地展现了其对儒家倡导的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基本理念的认同,从而曲折地反映了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和积极影响的肯定与褒扬以及儒家思想、文化对其本人的无形浸润与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作品更在突出狄仁杰儒家士人形象特质的基础上匠心独运地表现了他武艺精深、力挫强敌以及通过特殊手段来惩治罪恶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表述在使狄仁杰缜密推理、识奸辨恶这一完美智慧人物更显性格多面化之际,也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多将其塑造成为能臣、清官这一纯粹文人化呈现的审美窠臼和创作藩篱,继而在狄仁杰文学形象的演变历程中留下了颇具创意的一笔。更为重要的是,狄仁杰的这一形象书写体现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的同时,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文化、思想在某些方面对于传统士人群体的行动思维、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儒家文化中的白璧之瑕加以修正、健全的潜在希冀。可以说,《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作为高罗佩本人古典文化情志的一种无形载体,折射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殊体悟和感知,并由此凸显出这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在展现、诠释深厚沉潜的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科学客观态度和理性思辨精神。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