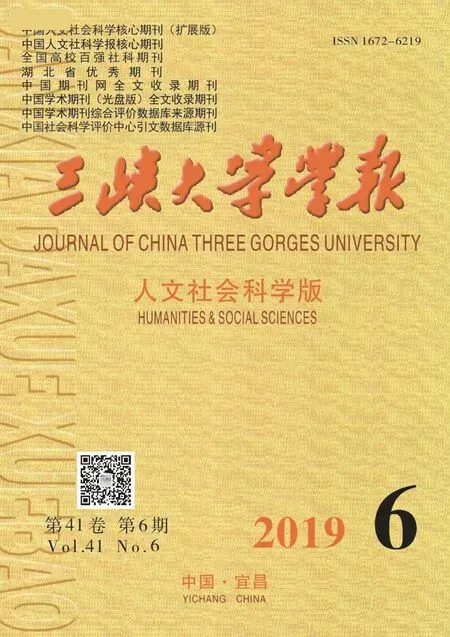回忆世界的建构
——论《浮生六记》的电影式回忆叙事
张银玲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沈复(1763-?),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人(今江苏苏州),出生于姑苏城南沧浪亭畔士族文人之家。十九岁入幕,此后四十余年流转于全国各地。他与妻子陈芸伉俪情深,因遭家庭变故,夫妻曾旅居外地,历经人世坎坷。沈复现存的文字除了《浮生六记》之外,流传下来只有七律两首:《望海》、《雨中游山》。随着对《浮生六记》文本研究逐步地深入,其文体属性是历来研究者探讨的内容,散文或是小说的认定是其争论的焦点。因此,厘清《浮生六记》的文体,对其进行正确定位是文本研究的起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去探讨文本的内涵才能正确把握它的价值。
“从传统的目录学角度而言,《浮生六记》可归为‘小说家’类,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小说家类’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1]浮生六记》主要记叙沈复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妻子的琐碎往事,确实符合“小说家类”的标准。但从现代小说的标准来衡量,《浮生六记》并不属于小说文体。现代小说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主要是指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情节叙述、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浮生六记》记录的都是真人实事,与小说虚拟的人物事件不同;《浮生六记》每一记都可以作为独立的文本存在,与小说叙述完整的情节线索不同;《浮生六记》记录实事平淡哀婉,与小说讲求情节冲突高潮不同;《浮生六记》记事描景主要是为抒情,与小说以叙事为主、以环境渲染刻画人物形象不同。因此,从现代小说的概念出发,《浮生六记》并不属于小说文体。
罗书华先生认为“我国的‘散文’概念经历了词体、语体、文体三个发展阶段。”[2]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于南北宋时期形成,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篇章的构成。“散文”是与韵文和骈文相对而言的,《浮生六记》作为无韵之文、散行之文与古代散文的概念是相符的。随着散文的发展,“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之后,与诗歌、小说、戏曲并称的文体散文概念这才最终定型。”[2]现代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真情实意’是散文的重要属性;‘真人真事’则是散文的本质属性;而文学体裁则是散文的外延。”[3]是不可否认的。散文的本质属性是其与小说相区别的核心,《浮生六记》投注作者的真情实感,记录自己生命中真实的事件,描绘与妻子动人的爱情故事,与现代散文的属性是相符的。《浮生六记》无论是从古代散文还是现代散文的角度来思考,都可将其认定为散文,且是一部忆语体散文。在桐城古文兴盛的清代,《浮生六记》并不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而是用贴合生活的浅近文言,用个人笔墨书写生活情感,树立个人风貌,其影响可以延续到五四时期。
回忆叙事是电影中一种常见的叙事艺术手法,主要是指按照主人公或非主人公的回忆进行现实与回忆间的交叉叙事,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很多作品也运用到这种艺术手法。《浮生六记》(因最后两卷失佚,不作讨论研究)是沈复撰写的回忆性散文,采用电影回忆叙事的艺术手法,沈复以回忆者的身份娓娓将自己的平生遭遇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都是对往事的追忆,浸透着对往事的怀念之情。回忆与现实之间相隔着一段时间、空间的距离,它只能无限靠近记忆中的人事,却无法完全靠近,“首先产生的是往事给人带来的心生摇摇的向往之情,随后它有了某种形式,某种约定俗成的,与相逢有关的反应方式”[4]10。
一、旁白式的叙事语言
旁白是指戏剧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对观众说的话语,也指影视片中的解说词。说话者并未在画面上出现,但直接以语言来介绍影片内容、交待剧情或发表议论。影视片中的旁白大多具有预见性,旁白讲述者对剧情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情况了然于胸,因此在讲诉的过程中始终带着“已知”的状态来看待影视片中的人和事。在《浮生六记》中就有很多旁白式的叙事语言,文本中的旁白并非由存在于故事时间中的作者,而是存在于文本时间中的作者说出,如同画外之音,让人感觉作者的声音从文本中发出,又像是从文本外传来。这种文本外的声音既与文本有联系,又可以独立存在,如果对其进行删减,虽然不会影响正常的回忆叙事发展,但却让这场回忆失去遥远时间所带来的魅力。旁白式的话语前是回忆的场景,旁白式话语抒发的是现实的情绪情感。正是因为旁白语言的存在,才能让现实情绪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回忆中,让读者真切地感知作者行文时的情感变化。
以沈复讲述与陈芸之间的故事时使用的抒情旁白为例:鬼节赏月后,沈复与陈芸染病,沈复哀叹“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5]21沈复索陈芸的诗稿来看,“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5]4迁居马桥后,夫妇二人请人画月老图,后遗失,沈复发出感慨“‘他生未卜此生休’,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耶?”[5]27陈芸在居住张士诚王府废基十日之后,想与沈复居住于此,“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5]29陈芸与憨园初见,“自此无日不谈憨园矣。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5]36陈芸和家公误会解除,与沈复欣然归宅,正当团圆之际,沈复又叹“岂料又有憨园之孽障耶!”[5]62在萧爽楼与友人小酌行令,但往日场景已然逝去,叹“今则天各一方,风流云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非所谓‘当日浑闲事,而今尽可怜’者乎!”[5]50当沈复回忆起其起居饮食时,“余之小帽领袜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东补西,必整必洁。”[5]58陈芸因绣《心经》,加重疾病,“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5]65陈芸因公公责骂,与沈复远赴华山友人之家,与儿女别离时,“解维后,芸始放声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诀矣!”[5]68陈芸死后,沈复“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5]79作者以旁白式的语言一步一步带领着读者去观看他与陈芸的爱情悲剧,每当回忆起与陈芸的恩爱往事时,作者现实中的声音就会传来,预示这场爱情故事的最终命运,然后发出沉重的叹息。
在《坎坷记愁》和《浪游快记》中,沈复也是以旁白形式来交代行文的时空背景和表现他在坎坷与浪游中的情绪情感。《坎坷记愁》开篇就发出议论,“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5]59陈芸回魂之日,“出告禹门,服余胆壮,不知余实一时情痴耳。”[5]80《浪游快记》也是开篇就点明浪游的时空背景:“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5]90父亲和陈芸的病痊愈后,“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5]97记忆起于与鸿干的相遇,“此余第一知己交也,惜以二十二岁卒,余即落落寡交,今年且四十有六矣,茫茫沧海,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鸿干者否?”[5]97在海宁王明府时,沈复曾遇到自己生平第二知己,但“惜萍水相逢,聚首无多日耳。”[5]105与妓女喜儿离别后,“噫!‘半年一觉扬帮梦,赢得花船薄幸名’矣!”[5]118
从《闺房记乐》到《浪游快记》,旁白式的声音总是会出现。这与李少红导演的《大明宫词》相似,以老年太平公主的视角,旁白式的语言来讲述太平公主从年少到老年的一生的故事,每当太平公主面临人生重要的事情时,老年太平公主的声音就会出现,告诉观众接下来公主的悲剧命运会如何开展。剧中老年太平公主与《浮生六记》中的沈复一样,两人都担负着旁白者的角色。通过这种旁白式的叙事语言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读者的情绪会被这种声音所牵引,不自觉地陷入作者营造的回忆场景之中,那些场景就像一个个情感漩涡,明知道陷入会动情万分,却不忍抽身离去。以现实的声音来叙说回忆往事,这种时间空间带来的距离感在现实与回忆声音的叙说之下被无限地放大,遥思往事,娓娓道来,又觉世事沧桑。
二、时间蒙太奇的叙事结构
蒙太奇是指通过对影视作品的镜头有目的、有逻辑的组接,在其间建立联系,从而产生丰富意义的电影创作手法,关于时间的剪切就是时间蒙太奇。回忆与记录现时发生的事不同,回忆片段犹如一个个“电影镜头”,作者可以对这些记忆片段进行人为的编排联结,且无需按照严格的时间与事件发展顺序,记忆之所起,情意之所至,记忆通过回忆的形式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故事情节层层推进。
整部《浮生六记》运用时间蒙太奇的叙事结构,作者可以在现在、过去、未来三种时态间进行切换,让回忆更加自由地穿插于文本之间,将同一时刻内的不同事件,或不同空间中的不同事件加以切割组合,表现作者的行文意义和潜在的情感韵味。这种打破时间顺序的交叉式叙述,在回忆与陈芸的生活时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闺房记乐》点出陈芸死亡的原因,这是事件的现在时态;而陈芸死亡的具体经过却是在《坎坷记愁》中详细写出,这是事件的过去时态;但在《浪游记快》中,陈芸却依旧“活”在未来的文本中,这是事件的未来时态。在《浪游记快》中,陈芸与憨园“重新”相遇,而陈芸与憨园相遇本就是导致陈芸死亡的重要原因,进而形成一个记忆的圆圈,似乎按照时间顺序在发展,但又回到事件的原点;似乎重返美好的回忆,却又不自觉地引向必归的死亡命运。每一卷都穿插着沈复与陈芸的生活点滴,渗透着沈复与陈芸之间感人的爱情记忆。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展现其意识变化以及与陈芸死亡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映射出作者眷恋于回忆的内心世界与对陈芸的无限深情。
时间蒙太奇对时间进行切割重组,但并未让回忆变得支离散乱。作者对个人的回忆进行切割,挑选了生命中重要的记忆片段,将其归结到不同的板块之中,以人生的时间碎片来重新组合起记忆整体,建立起记忆中的时空关系。以此进行叙事,让记忆线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将这六记勾连起来,展现沈复每一阶段的生命历程,感受过往的百态人生。《闺房记乐》从作者十三岁与陈芸相遇说起,《闲情记趣》从作者童稚时期说起,《坎坷记愁》从乾隆乙巳年,作者跟随父亲到海宁官舍服侍说起,《浪游快记》从作者十五岁拜师说起,不同的时间起点延伸出不同的记忆生活,牵引出每个记忆板块中的各项人事,纵横交错,脉络分明,织成一张坚韧而又密集的网。读者进入这张“网”中,便被所有的记忆包围,跟随着作者的记忆脉络而行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最让人感到无力把控的事物,一旦消逝便无法重回。回忆的渗透使《浮生六记》充满着时间流逝的感伤情调,对回忆进行时间蒙太奇式的处理,让回忆片段不断地闪现、消逝、重组。记忆的闪现,唤起过往的深情与悲凉;记忆的消逝,产生深深的人生漂浮感和生命幻灭感;记忆的重组,又让欢乐与苦痛交织,在回忆与现实中来回奔走,挣脱不出回忆的过往。这种回忆被唤起又被割破重组的过程,是作者对往事不断祭奠的过程,即使在叙述与陈芸的甜蜜生活、童稚的嬉戏玩闹、与友人的畅游享乐时,作者都会在欢乐结束后发出时间消逝、物是人非的哀叹,“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5]88。
三、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
“电影中的叙事空间是指电影制作者创造或选定的、经过处理的,用以承载所要叙述的故事或事件中的事物的活动场所或存在空间。”[6]8而在文学文本中也有叙事空间的存在,《浮生六记》是沈复根据自己真实的回忆撰写的作品,但其结构安排都是反复思考后的结果,文中所展现的叙事空间也是作者“选定的、经过处理的,用以承载所要叙述的故事或事件中的事物的活动场所或存在空间。”[3]8文本中的空间经过回忆的浸染,与现实空间之间相隔一段文字与时间的距离,让其空间叙事带有虚实两种不同的特点。
沈复一生颠沛流离,曾居住过苏州沧浪亭、马桥仓米巷、鲁家萧爽楼、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华氏府邸、大悲阁、夏揖山家雪鸿草堂等地,并辗转习幕于奉贤宫舍、维扬、吴江何明府、海宁王明府、徽州克明府、青浦杨明府,也曾到广东靖海和东海经商,经历了生活种种不易。但在记忆的最深处,最无法割舍的还是自己的出生地——苏州沧浪亭畔。“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5]1出生在“太平盛世”“衣冠之家”,居住于“苏州沧浪亭畔”是沈复认为上天眷顾自己的重要原因。在文本开头,就直接点出沧浪亭畔之名,可见苏州沧浪亭畔对于他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沧浪亭畔中,沈复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生活,观两虫斗草间,将蚊虫作鹤观。还有恬淡的闲情生活,观赏园亭楼阁、静室焚香、喜剪盆景。最重要的是与陈芸的恩爱时光,新婚之夜的美好,讨论小说诗歌,享受传统节日的欢乐。在“沧浪亭”这个空间里,作者沉醉于回忆中,回忆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随着空间的转移,回忆的情绪又有了不同的转向。
迁居仓米巷后,“屋虽恢宏,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5]22“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沧浪风景,时切芸怀。”[5]28当老妪提到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时,陈芸说道“自别沧浪,梦魂常绕,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妪之居乎?”[5]28等到了与沧浪亭畔相似的张士诚王府废基时,“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知己沦亡,可胜浩叹。”[5]29离开沧浪亭畔后,不止沈复怀念之前的“沧浪风景”,而陈芸也是时时梦之、怀之。但在文本的叙述中,沧浪亭畔的实物风景却很少提及,更多的是人事的种种“风景。”可见,沈复真正怀念的是在沧浪亭畔的无忧生活。沧浪亭畔,甚至是沧浪亭畔的“替代品”张士诚王府废基,都寄托了沈复和陈芸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期待。沧浪亭畔是沈复个人的小世界,也是他与陈芸的小世界,沈复以沧浪亭畔为回忆故事的原点,也以沧浪亭畔为回忆故事的转折点,所有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而所有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转折,一旦脱离这个空间,却陷入了不断“沦亡”的过程。沧浪亭畔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而沧浪亭畔外则是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复杂的家庭矛盾,困顿的家庭情境、寂寥的个人生活、颠簸的坎坷浪游,犹如暴风雨般一并袭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显现,带领着这场回忆叙事走进苦乐相交的情感漩涡之中。
回忆营造出一种无法把握住的空间,正是这种虚无、无法捉摸的逝去感,让人觉得美丽、心动又不忍。“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4]6《浮生六记》中的空间叙事泛起诗意。旁白式的叙事语言、时间蒙太奇的叙事结构,让文本中的回忆与现实之间相隔着一条时间和记忆的鸿沟,那是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正是因为无法逾越,所以《浮生六记》的读者,包括作者本人都只能“旁观”着事件的发展,看着作者的亲人陈芸、逢森、父亲一个个地逝去;看着作者经历少时的无忧,成家后的坎坷经营;看着作者浪游各地山河,却又发出感慨物是人非的叹息。作者带领着读者在回忆空间中游走,回忆中的人也在自己命运长河中游走前进。可是时间从不停歇,作者只能在现实中看着回忆故事不断发展,最后的结局却不可避免地走向感伤,这种在回忆与现实空间之间流动的无力与伤感成为《浮生六记》中回忆叙事的基调。
文字的力量是奇妙的,它让记忆蕴含于笔墨之间,让画面人物重新浮现于前。作家通过文字将记忆中让人或欢乐或忧伤的场景记录下来,表现自己的情感,让世人与之同欢同悲。沈复的《浮生六记》不同于传统的散文叙事,将叙事视角转向日常琐事、夫妻生活,具有浓郁市井文人的气息。文本采用电影回忆叙事的艺术手法,以旁白式的叙事语言、时间蒙太奇的叙事结构、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来展开回忆的叙事,这些都给《浮生六记》中的回忆叙事架构起一道略带“磨砂”的屏障,朦胧之中与读者之间产生一种距离感,并带来审美上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