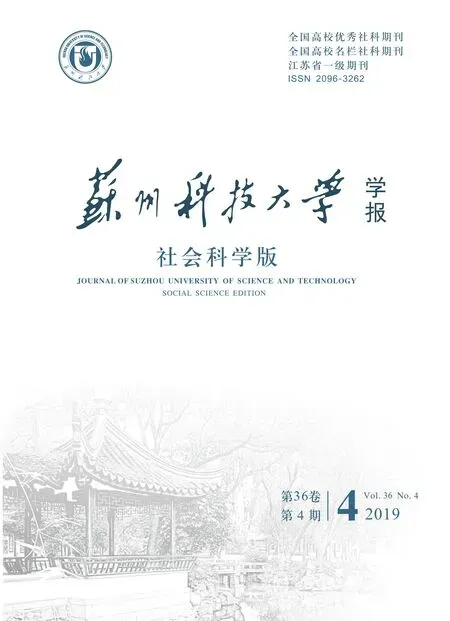张英与方苞交往关系考论
张体云
(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在桐城文派数百年研究史上,人们对于桐城文派的兴起原因从学理、文论、地域文化影响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到目前为止,成果丰硕。人们对于桐城文化、桐城世家大族如张氏家族、方氏家族、姚氏家族等也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张英全书》《张廷玉全书》等相关文献陆续出版,桐城张氏家族正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张英、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父子宰相的出现和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文派的兴起,是清代历史上两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但人们对于这两种现象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一直感到很疑惑,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涉及。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桐城宰相张英与桐城文派鼻祖方苞之间的交往关系的考述,揭示张英在桐城派兴起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张英与方苞之间的交往关系
1.张英早年与方氏族人的交往
自明以来,张英所在的桐城宰相张氏与方苞所在的桂林方氏都在桐城世居,是桐城望族。桂林方氏从方学渐开始到方以智、方文、方孝标,无论是科举还是功名,都是方氏家族史上的巅峰阶段,相对于其他家族来说,仕途功名和文化声誉都相对显达。张英青少年时期,自然受到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如康熙初年,他和父亲一起修纂《张氏族谱》时就学习借鉴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的体例。明清易代之后,方氏家族基本上是倾向于明朝统治,不接受清廷,易代情绪比较强烈,方氏名人或隐逸或移居南京,如方以智埋名隐姓流寓他方,方文隐居南京等。张英年轻时与方氏家族有交往,可考的有诗人方文[注]方文,原名孔文(1612—1669),大铉长子,字尔识,更名文,字尔止。明亡后,更名一耒,号嵞山、明农、忍冬、淮西山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正月初九日,天启诸生。有《嵞山诗文集》五十卷。他在当时诗坛影响很大,其诗号“嵞山体”。,《文端集》卷六有《重晤方明农先生赋赠》:“桃渡诗人宅,春水生柴门。未到已七年,相忆劳晨昏。壁间画梅竹,斑剥今尚存。百卷嵞山诗,古调无纤尘。”诗题中的“方明农”即方文。李圣华《方文年谱》将此诗系于康熙八年(1669),从诗中“未到已七年”来看,张英去拜访过方文,且他们之间早有交往。[1]
从现存作品来看,与张英关系最密切的方氏族人是方畿,《文端集》中有《同四松先生木厓叔兄如三游画溪得音字》诗[2]347,这是康熙九年(1670)张英在桐城时写的,他们能够在一起结伴游玩,说明关系比较熟。另外,《文端集》中还有他们的《寄怀》与和韵之作,张英有《答四松先生寄怀诗即次来韵二首》[2]449,其一云:
纸阁秋阴日影迟,琳琅四壁寄予诗。
不嫌小草劳相忆,幸有芳兰慰所思。
青幕车中春雨路,黄金瓦上晓霜时。
难将烟火人间语,酬和柴桑绝妙词。
其二云:
芒屩青山雪满颠,高吟落落度余年。
平生酷嗜惟之子,百卷新诗定许传。
松菊远寻鸥鹭外,琼瑶常寄雁鸿先。
桃花潭水情无限,作赋思乡愧仲宣。
从其一“幸有芳兰慰所思”来看,他们之间有较深的朋友关系;从“酬和柴桑绝妙词”和“平生酷嗜惟之子,百卷新诗定许传”来看,他对方畿的诗歌评价很高,认为必传。
不过,这两位有文字可考且与张英有交往的方氏族人都去世较早。方文于康熙八年(1669)秋去世,方畿于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初七去世。此外,张英与方氏交往无考。
2.方苞中贡士之前与张英的交往
由于明末清初政局动荡,桐城遇乱,世家大族曾纷纷避乱南京,方苞家族在曾祖方象乾时避乱,侨居南京上元县由正街,方苞(1668—1749)即于康熙七年(1668)出生在南京。张英(1637—1708)长方苞三十一岁,世居桐城,明末清初动乱时曾短暂流寓南京,但很快又迁回桐城。张英于康熙六年(1667)中辛未科进士,此前基本都在桐城度过,此后基本都在京师为宦,不能随便外出,有时可随皇帝出行。
方苞和张英初识,应该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游太学时,时二十四岁的方苞随恩师高裔入京师游太学,并馆于高裔家。此时,张英在京师为官,以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教习庶吉士。游太学期间,方苞主要和王源、戴名世、刘言洁等人交往甚密,意气相投。康熙三十二年(1693)后,诸人陆续离开京师,方苞以南京为中心,游馆各地谋生。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中江南乡试第一,主考官为韩城张廷枢、太原姜木肃。据方苞《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姜木肃与他恩师高裔是好朋友。张廷枢父张顾行与张英是同年(康熙六年进士),张廷枢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长期在翰林院供职编修、侍读和日讲官,一直是张英的部下。据《戴名世先生年谱》,张英为张廷枢父亲顾行作墓志铭[3]437,可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错。但这次考试,方苞所取得的成绩与张英的关照无关,因方苞《祭张文端公文》云:“余幼泥古,孤行自尚。病俗流从,误矫以亢。伊余先世,与公有连。众附恐后,余避不前。”[4]468可见方苞年轻时“孤行自尚”,特立独行,不愿像其他人一样追攀高门,所谓“众附恐后,余避不前”,就是说他早年未曾攀附过张英,且没有向张英求助。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张英拜文华殿大学士,官职做到了最高品。方苞于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之后,连续参加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四十二年(1703)两次会试,都不幸落第。在此期间,张英有没有关照过方苞呢?从目前所见张英作品来看,未见他们之间有交流和往来关系。但是,从方苞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方苞与张英交往的一点点痕迹,其《祭张文端公文》云:“北试京兆,牒过礼部。公比群士,谓宜独步。”[4]468可见,方苞参加进士试时,张英是见过方苞的,且对方苞评价很高。“凡在列者,凑公称师。余独自外,接以常仪”[4]468,当时参加会试仕人,纷纷趋附,拜到张英门下,但方苞依然独行自外,“接以常仪”,对张英不作任何攀附。方苞作为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乡试解元,参加会试竟两次都未中,这应该不是他的才学问题,可能是关系运作问题。此时张英已是文华殿大学士,身居高位,从《祭张文端公文》中“凡在列者,凑公称师。余独自外,接以常仪。谓公余弃,公心以倾”[4]468来看,方苞认为张英未能给自己必要的支持和推荐,对其有不满情绪;之后两人有过面谈,“始脱文貌,喻以平生”[4]468,双方达成了深度理解。
从《祭张文端公文》中“岁在协洽,苍龙南御。公来长干,获侍旅寓”[4]469四句来看,方苞在康熙帝南巡时拜见过张英。方苞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试礼部,在这之前,张英有两次迎驾活动。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十六日康熙“以巡阅南河,省风问俗,察访吏治”[5]98,张英从桐城出发,经盱眙,到淮安府迎驾。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初九,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张英再往长干,于三月九日再次迎驾于淮安府。从方苞《祭张文端公文》中“岁在协洽”来看,方苞拜访张英应该是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
方苞《祭张文端公文》又云:“谓国得贤,如室有木。子果能驾,吾推子毂。”[4]469由此可见,张英见方苞之后,视方苞为国器,有推荐之意。方苞以母老有病推辞:“余谓公已,小人有母!衰疾相依,独身无辅。”[4]469张英了解了他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后,甚感遗憾,云:“公鉴其诚,悄然不怡。谓子固尔,我心则违。”[4]469方苞也非常感激张英的知遇之情:“感公拳拳,中如有物。”[4]469
从上文所引《祭张文端公文》来看,方苞特别提到他对张英的不攀附和他以母亲老病为由婉拒张英推荐之事,这些应该是想表明他的成名和仕途发展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跟乡贤发达无关。然而事实未必如此,三年之后,方苞还是不顾母病,参加了会试。
二、张英人脉圈对方苞仕途发展的支持和影响
1.康熙四十五年,方苞中式贡士的考官阵容与张英的关系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方苞中式贡士。榜未发,方苞闻母病,遽归侍,未得参加殿试。此事在雷钅宏《方望溪先生行状》及《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中都有记载。笔者梳理了一下是年考官阵容。知贡举王顼龄为张英同门师弟,王顼龄有《丙戌春日礼闱知贡即事呈同事诸公》记录此事。[6]卷二三王顼龄当年初到京师发展时,张英有举荐之恩。王顼龄与张英及其长子张廷瓒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之间交往密切。[7]273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这一年主考两人:“吏部侍郎李钅录予,字山公,顺天大兴人,庚戌进士。工部侍郎彭会淇,字四如,江南溧阳人,丙辰进士。”[8]96-97这一年有同考官十八人:
谕德魏学诚,字无伪,山西蔚州人,壬戌进士。谕德彭始搏,字直上,河南邓州人,戊辰进士。中允吴昺,字永年,江南全椒人,辛未进士。编修顾图河,字书宣,江南江都人,甲戌进士。编修张逸少,字天门,江南丹徒人,甲戌进士。编修赵申季,字行瞻,江南武进人,丁丑进士。编修陈至言,字山堂,浙江萧山人,丁丑进士。编修季愈,字退如,江南宝应人,庚辰进士。编修赵晋,字昼山,福建闽县人,癸未进士。检讨张元臣,字懋斋,贵州铜仁人,丁丑进士。检讨李林,字韶石,广东翁源人,丁丑进士。检讨张廷玉,字衡臣,江南桐城人,庚辰进士。户科给事中汤右曾,字西崖,浙江仁和人,戊辰进士。御史李绅文,字牧痴,河南延津人,戊辰进士。吏部郎中谢藩,字芝原,广东海阳人,甲戌进士。户部郎中闫中宽,字易庵,直隶蠡县人,己未进士。礼部郎中洗国干,字三山,广东南海人,壬戌进士。刑部郎中江鼎金,字紫九,湖广荆门人,乙丑进士。[8]417-418
是年同考官十八人中,辛未、甲戌、癸丑、丁丑科进士共八人,都是出自张英门下,外加张廷玉共九人。方苞言其房考为“顾与陈”,即顾图河和陈至言,顾是甲戌科,陈是丁丑科,都是张英门生,与张英关系都比较密切。
顾图河,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四月十三日,选授庶吉士。四月二十五日,上谕:“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教习庶吉士。”[9]781清制,一甲三名与庶吉士一起学习,是时张英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直管翰林院教育工作,顾图河自然是张英实实在在的门生。而陈至言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二甲二十一名进士,时张英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詹事府詹事。是年会试主考官是张英、熊赐履、吴琠、田雯四人。王士禛在《菀青集》序文中言陈至言:“丁丑成进士,钦选庶常。桐城相国特奏青厓(即陈至言)为知名士,竟得与选。”[10]103据王士禛所言,陈至言在康熙三十六年中二甲进士后,能够选授庶吉士,是张英力荐的结果。而中进士之后,能够入选庶常,是决定一个人仕途的大事。只有入馆选,才有翰林出身,而翰林出身几乎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梦想。它不仅是一种地位象征,而且直接关系到一些馆阁清要职位及各种主考官、学政官等衡文之职的任用。“凡是被选入翰林者,即使不能迁升文职极品,但可入直内廷,又可简放主考、学政,掌握文衡,乃名利双收之差事;且七品编、检能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平行往来,而七品知县则被戏称芝麻官,对督抚只能上手本,称卑职”[11]109,地位上差别很大。“庶吉士留馆即是翰林,不得留馆,时人亦以翰林视之”,“翰林群体实际上是一个高于进士群体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文官集团”,“翰林与翰林出身之官员”即包括曾得馆选而未留馆者,如充经筵日讲官即须上述资格,而只有进士出身者不得参与其间。[11]161正因为如此,很多进士都希望能被选上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获得翰林身份。每年庶吉士的“点定”,数量只有当年所有进士数目的三分之一左右,许多人没有机会得入馆选。陈至言作为二甲二十一名,成绩不是特别优秀,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进士总数为一百五十人[12],是年得馆选者三十四人,有一甲三名,二甲(二甲进士数原本为四十人)十三人,进士名次在陈至言前面的还有二甲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等十二人俱未入选庶吉士。[13]卷8,卷21陈至言因张英荐而入馆选,恩莫大焉。另外,陈至言之《菀青集》卷首有同学录姓氏,姚士陛、张廷瓒、张廷玉都在列;又有同门姓氏,方苞在列。《菀青集》中还有《相国桐城张夫子予告致政荣旋恭送四章》《秋日同龙眠诸子饮集》等诗,可见陈至言与张英一门关系非常密切。
从诸考官背景分析,笔者认为,这次会试对于方苞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有众多张英弟子在列,且张英次子张廷玉亲历其中。是科中式贡士,共三百十五名,方苞第四名。方苞这次取得佳绩,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是在情理之中。方苞在《祭张文端公文》中特别提到自己会试得贡士,是“由顾与陈”,且言其“实出公门”,方苞此言有两重意思:一是感谢张英弟子顾与陈的知遇提携之恩;一是表明自己与张英之间有再传弟子关系。
2.张英、方苞与李光地之间的关系
康熙四十五年(1706),方苞中式贡士之后,未来得及参加殿试,就因母亲病发而赶回金陵,李光地派人追赶。康熙五十二年(1713),方苞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当斩,李光地在康熙皇帝面前冒死进谏力推方苞、戴名世之才。彭绍升《又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云:“圣祖一日言汪霦死无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已而得释,召入南书房,公之护惜善类,启迪圣聪多此类也。”[14]卷十三方苞《安溪李相国逸事》也有相关记载:“上言自汪霦死,无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对,左右闻者无不代公股栗,而上亦不以此罪公。”[15]341
李光地如此爱护和怜惜桐城之才子,是以张英和李光地之间三十年密切关系为基础的。李光地在张英的墓表中说:“予后公三年成进士,授馆职、仕宦,出入几三十年,相知为深且厚。”[16]505张英康熙六年(1667)中式进士,因是年十月父亲病故,回家奔丧,守丧三年,康熙九年(1670)回京师,随康熙九年的进士学习,而李光地就是康熙九年进士且选授庶吉士,张英和李光地、徐乾学等人成为翰林同学。此后,张英和李光地在内廷工作几十年,朝夕面对。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英次子张廷玉请李光地为张英作墓表,证明张英和李光地交情之“深且厚”。另外,李光地让方苞为其代写了《张文端公墓表》。这说明李光地是知道方苞与张英之间关系密切的。
结合上文房考情况来考察,不管是顾图河还是陈至言、李光地,他们都是张英的老友故旧和同僚。当然,有没有具体的请托细节,因直接文献缺失,无从确证,但张英退休之后,桐城后学方苞、戴名世等都是依靠张英当年的人脉圈在发展,这种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三、张英对方苞多方面的影响
方苞中式贡士之后,虽未能参加殿试,但对张英感激于心。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方苞专程到桐城拜访张英,其中深意,外人不得而知。方苞《祭张文端公文》云:“余既南还,谒公里第。”[4]469此时,张英虽身在林泉,但心系国家天下:“公在林泉,亹亹翼翼。至忠体国,心怀宸极。”[4]469方苞拜见张英时见其状态不错,甚感欣慰:“私为世喜,公志未衰。”[4]469不料一年后,张英就与世长辞了。闻其消息,方苞痛作《祭张文端公文》,既怀念平生,又表达了故旧哀情。虽说斯人已逝,然而他对方苞仕途和思想各个方面的影响却是可以考见的。
1.张英对方苞政治仕途发展的影响
张英作为桐城先达对方苞肯定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张英当年中式进士,并长期在康熙皇帝身边工作,以其与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受世人仰目。乡贤张英的仕途成就和光环对于同乡后学方苞来说,无疑是一种榜样力量。张英的成功激励着无数桐城学子执着于仕途功名,包括方苞、戴名世等人。
其次,方苞在科举过程中,得到过张英当面指导和点拨,这在方苞的《祭张文端公文》中有清楚的描述。方苞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式贡士,名列第四,李光地对方苞的特别钟爱以及康熙皇帝对方苞的宽大处理,其中都有张英的一份功劳。
最后,张英为人处事低调谨慎的作风,对方苞有深刻影响。方苞进入朝廷之后,一改其前期的矫亢之习,像张英一样,除了一心学问之外,余事都很低调温顺。在为人处事上,以谨慎出名,这为他后期仕途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使得他由一个没入旗籍的政治重犯,到恢复汉籍,升为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
另外,张英晚年归隐双溪,方苞晚年改号“望溪老人”,表达了他对张英的景仰之情,同时也寄托了他希望自己像张英一样功成名就,以智者姿态栖心山林,获得终身的平静与安宁。
2.张英读书治学及文学观念对方苞也有一定的影响
张英生前为教育子弟不辞劳苦,写作《聪训斋语》传世,其中谈到了立身、行事、读书等方面的问题。该书不仅对张英子弟影响很大,也是同乡后学的必读书,因此对同乡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名宦之家如曾国藩等都以此为教育子弟的必读书。桐城大家子弟得其浸染者代代有人。他在《聪训斋语》提出的诸多为人处世立身之道,都成为后人奉行的准则。桐城派鼻祖方苞、姚鼐等都受到其深刻影响。如他在《聪训斋语》中提到读书的好处,开篇就讲到读书对养心养身的重要性:“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每见人栖栖皇皇,觉举动无不碍者,此必不读书之人也。”又云:“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17]3方苞也和张英一样,以读书为养心之术,曾告诫弟子沈廷芳说:“读书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当不至。’愚虽一生在忧患疾痛中,惟时时默诵诸经,亦养心卫生之术也。”[4]832
在《聪训斋语》中,张英还提到每个主体对周围山水感悟的深浅与其本身学问水平高低之间的关系:“放翁诗云:‘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故同一登临,视其人之识解学问,以为高下苦乐,不可得而强也。”[17]3方苞接受了“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的个体差异性观点,如他在《隐拙斋诗集序》中言:“孔门七十子之徒,皆异能之士。而许其可与言诗者。仅赐与商。由是言之,诗之为道,浅者得浅焉,深者得深焉”[15]302,但同时强调主体学问水平对其学习和感知能力的影响是一致的。
张英一生好吟诗,但畏于写诗之难而很少写诗,这并不影响他对诗歌有自己的看法。张英多用传统儒家诗教论诗,主张诗歌要自然吟咏真性情,但为歌者不可怨怒叫嚣,要发性情之正者。他说:
诗何为而作哉?盖蕴于吾之性情,抑扬咏叹而不能自已者耳!今之为诗者,争取新丽,夫新与丽,非诗之旨也。古人间一有之,亦自然而新,自然而丽,而无容心焉。若求新与丽而转以蔽性情之真,则不知其诗为何人作也。古之善诗者,若晋之陶,唐之李、杜、韦、白,宋之苏、陆辈,不名其集,而试其辞,则知为某作。此无他,其性情之真不可掩耳。[18]153-154
方苞也好读古人诗,他在谈诗时遵循传统的儒家诗教,认为“诗之用,主于吟咏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伦,美教化,盖古之忠臣孝子,劳人思妇,其境足发其言,其言足以感动人之善心。故先王著为教育”,而且强调诗歌要“发于性情之正”,以“冲然以和”者为美。[15]299由此可知,方苞和张英的诗学原则和立场是一致的。
另外,在文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张英认为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内在思想水平,他在《丁丑会试录序》中云:“古人以言取士,岂尽渺然无可依据?夫言者,心之声也。古者敷奏以言。”又曰:
不知言,无以知人。大约心术端纯者,则其言必正大,而无偏驳之病。识解明通者,则其言必条畅而无结塞之弊。律己恭慎者,则其言必谨饬而无叫呶之习。且先之经书,以观之义理;继之表策,以观其才识。阅者沉心静气,以与作者之精神相遇。谁谓制科之文,不可以观其人之梗概哉![16]292
在张英看来,“言为心声”“不知言,无以知人”,以文观人,是必要的,因为一种文字就是一种性情,通过文字可以了解作者的心胸、器量和境界。方苞也有类似的言论,其在《杨黄在时文序》中言:
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于世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其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汙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又必销委焉。[19]55
这是典型的文如其人说,而且方苞也明言道:“盖言本心之声。”[19]55方苞在教导士子谈到制艺时,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其《移山东州县征群士课艺文代》中云:“文者,学之枝叶。制举之文,又其近者尔。然以效圣人贤人之言,则心之精微,达于辞气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15]256所谓“则心之精微,达于辞气者”,即写作者内在的思想、道德、气性等在文章中得到表现,达到以此观人、识人的效果,该想法和张英一致。
四、结 语
统观上文可见,张英年轻时受到文学世家方氏的影响。由于生活地点不同、年龄差异,方苞早年与张英交往较少。康熙三十年(1661),方苞游太学之时开始面见张英,但因方苞性格矫亢,不喜攀附,未得到张英的关照。康熙三十八年(1669),方苞江南乡试第一,成绩优异,但两次参加会试未中,让他觉得非常不公。他认为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的乡贤张英对自己缺乏关心,对张英产生不满情绪。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十九日,张英往清江浦迎驾时,方苞专程拜访了张英。康熙四十五年(1706),方苞参加会试,得到张英人脉资源的大力支持。张英不仅对方苞仕途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在人生态度、文学思想等方面对方苞都有一定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关系,笔者认为,张英及其家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崛起是清中叶桐城派崛起的重要助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