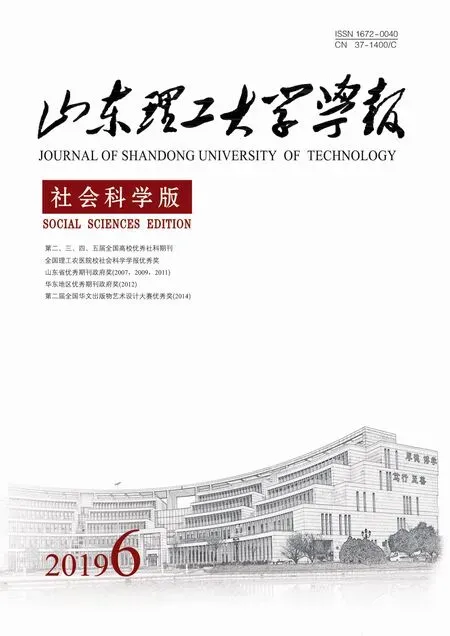刘玉栋儿童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
张 琳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刘玉栋是70后山东著名作家,他的创作质朴而深沉,扎根于齐鲁大地,深刻揭示出这片土地的变迁以及生长于斯的人们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来,刘玉栋的儿童小说《我名字叫丫头》《白雾》《泥孩子》《月亮舞台》也颇受好评。刘玉栋的儿童小说讲述了乡村环境下,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成长。这四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成长中的少年,他们的父亲或是因为去世或是因为到外地工作,在孩子需要陪伴的生活和成长中缺席了。尽管有其他人的帮助,但少年必须独自面对成长中的磨难,迅速成熟起来。在这些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是小说主线情节进展的根基和前提。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造成了作品中叙述的复杂性,使得作品众多人物中,父亲的形象更加复杂、带有更深厚的感情色彩。“父亲的缺失”将现实中的苦难、父爱的深沉、社会的变迁等重大主题深埋其中,使作品成为少年的理想飞扬和父辈的负重前行水乳交融的统一体。
一、父亲的“缺席与失去”
父亲是文学作品中重要的形象之一。而在刘玉栋的四部儿童小说中,少年主人公的父亲因不同原因在少年的生活及成长中缺席,形成了父亲形象的缺失。具体到小说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父亲因故去世,孩子失去了父亲,父亲被迫在孩子的生活、成长中永远缺席。《我的名字叫丫头》《月亮舞台》就属于这一类。这类小说从孩子的视角传奇性地讲述了父亲的去世。另一种情况是小说叙述中没有父亲的具体形象出现,只在细节中涉及到父亲的相关信息。例如《白雾》《泥孩子》中父亲是因为去外地工作而在孩子的成长中缺席。总体来说,这两类儿童小说的叙事情节中,“父亲的故事”并不是重点情节,父子之间的交流也不是表现的重点,涉及父亲的主要情节相对较少。这样的情节设计一方面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关。刘玉栋说:“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地质队员,一年到头都在野外奔波,……所以我的整个童年,父亲并不在我的生活中。后来我回顾自己的创作,发现好多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果真是缺失的。”[1]6作者把自己童年的切身体验与社会现实融合,不仅在自己的当代书写中也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写出“父亲缺失”的社会原因及给孩子成长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因为阅读者身份的变化,有意识地调整了叙事技巧,既展示儿童与父亲真实的相处状况,也书写儿童内心所意识到的父亲形象。
在这四部儿童小说的叙事中,父亲形象的缺失都与主要情节进展没有必要的联系。《泥孩子》的故事中,主要展现乡村男孩泥孩子与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生活。泥孩子只有在与爷爷、小伙伴谈话中才涉及到父母外出打工的信息。《月亮舞台》中,主要情节聚焦于胖墩儿的暑假打工经历。父亲因车祸去世之前的故事是在胖墩儿给妹妹讲的故事中出现。《白雾》写男孩冬冬的乡村生活。作品开篇就说“那一年的深秋,妈妈带着我,从城市回到一个叫白雾的村庄。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由于是地质队员常年在外工作,父亲在孩子记忆中没有清晰地印象,冬冬无法讲述父亲的详细故事。相比较而言,《我的名字叫丫头》中,父亲的故事最为详细。瘸腿父亲和他的瘸腿马的故事以及父亲的失踪得到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但在男孩丫头的记忆钩沉中,没有叙述父子之间的交流,也没有更多明显表现父子深情的情节。“瘸腿的卑微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存在感相对比较低,他于河上捕鱼收网时失踪,彻底在丫头的生活中消失。少年的成长,因父亲的缺席而少了某种束缚,也因父亲的缺席而获得了成长的催化剂。刘玉栋的儿童小说中,少年成长往往不是在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氛围下进行的,而是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被迫促成的。少年成长的温暖明媚故事之下,隐形并进的是父亲的或沉重或忧伤的故事。
《我的名字叫丫头》中,丫头的父亲是个瘸子,因为行动不便颇受村人歧视,后来得了怪病,在丫头十一岁那年的一个雨天,消失在河中。丫头坚信他的“忧伤的父亲”并没有死,而是“变成了一条大黑鲤鱼,游走了”。十一岁的少年,读懂了父亲的忧伤,他用孩子的方式解读父亲的缺失:父亲变成了鲤鱼,从家庭生活的重担下游开,从病痛中游开,从惨淡的人生中游开,游向自由的天地。这是孩子对父亲的爱的表达,是孩子希望父亲能拥有幸福人生的曲折展露。《月亮舞台》中,胖墩儿不带忧伤的讲起父亲的故事:他坐过飞机、会跳伞;他会开大卡车、勇斗歹徒;他力大无穷,像一台挖掘机;他种美丽的金色葵花;他变成巨大的鱼从水中救起儿子。在胖墩儿的心中,父亲既无所不能又温暖慈爱,他是英雄、是孩子的精神支柱。然而父亲因车祸亡故,家里负债累累,母亲被迫带着妹妹改嫁,家中只剩胖墩儿和奶奶。原本幸福的家庭骤然支离破碎,孩子只能用一个个英雄故事来远离伤痛。《白雾》中冬冬的父亲是地质队员,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陪在孩子身边,他会写信、寄东西来跟孩子沟通。冬冬一方面因父亲“正在大西北为国家找石油”而骄傲,另一方面也因同学说“他爸爸不要他和他妈妈了。他妈妈正跟吴童木的爸爸搞对象呢”而嚎啕大哭。可想而知,思念的伤痛不仅印在孩子心里,也刻在父亲心中。在《泥孩子》中,泥孩子的父母在城里打工,爷爷说“爸爸妈妈都在城里淘金子”。泥孩子在小伙伴面前引以为傲,但他也纳闷“既然河里都是金子,可爸爸妈妈为什么还非得到城里去淘金子呢?”正是因为昔日宁静纯洁的乡村逐渐遭到污染,盗伐者、盗猎者悄然而至,泥孩子的父母与大个子叔叔被迫离开乡村进城务工,泥孩子和憨牛才不得不与父母分离。父亲形象的缺失是社会变迁、人生磨难的集中表现,进而成为少年成长故事的深层动因。在刘玉栋的儿童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是小说主线情节的根基和前提。
二、儿童视角下的“父亲的缺失”
刘玉栋的儿童小说均采用儿童视角,除《泥孩子》之外,大多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不同,儿童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都有其局限性,在叙述中会存在某些空白、曲解,不能清晰地反应全部事实真相,所以儿童视角是一种限知视角。第一人称叙述是内聚焦视角,“内聚焦视角中,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2]30。刘玉栋运用儿童视角,写孩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他们眼中的外部世界,写他们眼中的父亲。内聚焦视角的运用,使儿童的内心活动表现得丰富细腻,外部世界人、事的描写则带有浓重的儿童认知特点及个人情感色彩。
小说中,孩子对所叙述的事件难以做出清晰、全面和正确的理解,他们从自己获得的材料出发描述事件、表达好恶,在充满主观色彩的叙述中展现父亲的形象。由于年龄较小,冬冬和泥孩子几乎每次都以崇拜的口吻提到父亲。冬冬以父亲“为国家找石油”而骄傲。泥孩子对憨牛说:“我爸爸是淘金子的,金子,你见过吗?哼,黄澄澄的。”他“骄傲得满面红光”。这种描述其实是孩子对父亲工作的一知半解和曲解,但他们用对父亲的崇拜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填补内心因父亲缺席带来的空洞。因叙述视角的限制,他们不能讲述远在外地的父亲的详细故事,不能提供关于父亲的更多信息,因而在《白雾》《泥孩子》这两部小说中,父亲成为一个模糊的叙事背景。但冬冬从城市来到乡村又回到城市的经历和泥孩子与爷爷奶奶乡村生活的根源均与父亲的工作直接相关,与主人公父亲年龄相近的“吴老师”“大个子叔叔”等形象也从侧面映射了“父亲”们的生活压力和人生选择。
刘玉栋的儿童小说在写父亲的特殊经历时,折中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拓展了第一人称叙述的范围,将现实情况下儿童主人公无法叙述的事情,纳入到叙述范围中来,既保证了叙述的完整,又坚持了叙述的儿童视角。就像在主人公肩头架设了一部摄影机,读者能看到的信息比现实情况下主人公能看到的更多。读者自以为看到的是全部事情的真相、是父亲的真实形象,但其实仍然被限制在主人公的视野范围内。发生在主人公视野或者理解范围之外的事情,更引人遐想与深思。叙事视角的选择造成了作品中叙述的复杂性,也使得作品众多人物中,唯有父亲的形象更加复杂、带有更深厚的感情色彩。
《月光舞台》和《我的名字叫丫头》这两部小说总体上使用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写儿童眼中的乡村生活。在涉及父亲的相关篇章时,折中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更多的信息纳入进来,更细致地描写父亲。
《月光舞台》中,胖墩儿给妹妹讲述的“爸爸的故事”均发生在胖墩儿出生至五岁之间。他将模糊的记忆、家人的讲述、自己的想象编织在一起,将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折中,模拟成年人的口吻,讲述自己心中编织的故事,塑造心中的父亲形象。“说说我周岁那年的一件事吧。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这样充满童趣的话语虽然与现实情况不尽相符,但是情感流露在讲述的字里行间,及至读者了解到胖墩儿的父亲已经去世,便更容易接受这些叙述,产生共情。这些“爸爸的故事”间隔出现,贯穿全篇,讲述了父亲去世之前,胖墩儿一家的幸福生活,与小说主线情节形成鲜明的对照,更突显少年在家庭灾难中成长的艰辛。
《我的名字叫丫头》中,叙述者丫头是一个逐渐成长中的孩子,小说开篇他的年龄只有六七岁,十一岁时他的父亲失踪了,十四岁他开始跟台阶叔卖虾酱,文章结尾,他已经是成年人了。这部小说是刘玉栋儿童小说中主人公年龄跨度最大的一部,也是男孩丫头的记忆钩沉。在叙述丫头闯祸害怕父亲责罚、父亲同意打狗队打死家里的狗这些事件时,作品运用的都是内聚焦限知视角;在叙述“瘸子父亲和滚蹄子马”故事的第六章,作品折中了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详细写事件的前因后果、写父亲的精神状态。“我父亲是个瘸子,至于我父亲的腿是怎么瘸的,别人没告诉我,我也从没有问过别人”。由于限知视角的运用,主人公不能叙述父亲腿瘸的经过。“我父亲和滚蹄子马的故事,还是发生在集体劳动时期”,这是作品要重点叙述的事件。作品在全知视角下精细地叙述了生产队买马的经过、父亲和滚蹄子马劳动、父亲与队长商量给滚蹄子马安装“鞋子”、分马肉等情景,又选择用限知视角去写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父亲的心理状态。父亲的隐忍、对马的爱惜、给马装鞋子时的自豪、分马肉时的悲伤都深埋在他的一言一行里。滚蹄子马死后,父亲“哇一声哭起来,他蹲在地里,身子一耸一耸的,像个孩子挨了谁一顿巴掌”,继而“丢了魂似的,他目光呆滞,谁都不理”,“像个罪犯似的,低着头”,分马肉时父亲“正面朝墙蹲在那里”,被母亲踢了也“拍了拍额头上的土,又重新蹲在墙根下”。父亲把瘸腿的伤痛埋在心里,得到滚蹄子马后因同病相怜而与马惺惺相惜。他可怜马也是可怜自己,他帮马装“鞋子”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希望。马死了,对父亲来说,如同是一个心爱的孩子死了,也是自己的一个希望死了。这种伤痛难以言说,所以作品采用限知视角,通过言行举止反应父亲的内心。
父亲的去世对孩子来说是难以弥合的伤痛,对家庭来说,是巨大的灾难。作品选择内聚焦限知视角来写父亲的去世,通过丫头的感受来写父亲忍耐病痛逐渐变得沉默、畏缩,写他为了家庭收益拖着病体去河上收网。“我似乎看到了父亲的背影,又似乎看到了父亲的眼睛。那疲惫的背影,那忧郁的眼睛,它们在我眼前交错不停地闪现着”。丫头竭尽全力想帮助父亲,“那年我只有十一岁,可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浑身充满力气,我心里激动着,我想我肯定能帮父亲做很多事情”。可是终究什么忙也帮不上,丫头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消失,时隔多年之后仍然懊悔为什么自己不能救父亲。这一部分内聚焦限知视角的运用使儿童与死亡拉开了一定距离,既揭示了生命消逝的残酷真相又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儿童用他们的方式来解读死亡,丫头说:“别找了,他变成一条大黑鲤鱼,游走了。”父亲消失了,但是丫头对父亲的爱不会消失。
刘玉栋的儿童小说采用儿童视角讲述故事,叙述方式符合儿童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水平,在描写父亲时又灵活调整叙事视角,让父子深情流露在字里行间,揭示出“父亲的缺失”在儿童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巨大影响。
三、父亲形象缺失的深层内涵
根据刘绪源对儿童文学母题的研究,刘玉栋的儿童小说均属于“爱的母题”下“父爱型”作品。刘绪源认为:“‘父爱型’作品指的是那些通常认为具有比较饱满的教育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3]95“它的最大特征,是‘直面人生’。它朝成人文学作品的方向大大地跨进了一步。虽然它还在根本上保持儿童文学的特点,但是同成人文学一样,它的最高审美追求,也开始转向‘揭示人生的难言的奥秘’”[3]104。刘玉栋的儿童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没有致力于为儿童创造出桃花源般的和谐环境,而是让少年主人公遭受打击、经历磨难,在克服一个个困难中逐步成长。他为儿童提供了正确认识现实社会人生的途径,也指明了依靠爱走出困境的方法,同时他能够坚持保护儿童的天真纯净和脆弱幼稚,这是难能可贵的。
刘玉栋的儿童小说中,少年主人公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父亲的缺失”。在叙述中,“父亲的缺失”有两种情况:一是父亲叙述中在场,但在事实上缺席;二是父亲事实上在场,但在叙述中缺席。这两种情况都从不同的层面反映出几十年来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对于家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父亲往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能通过工作挣到足够的钱养家,他是家庭和外部世界的最直接联系,是大多数家庭中话语权的掌握者。当代社会以来,父亲也承担越来越多的教养子女的责任。在刘玉栋儿童小说所描写的乡村环境中,父亲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七十年代农村的集体生产、地质队的工作,还是新世纪以来的进城务工、长途运输,父亲们都是工作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劳动也直接决定家里的经济状况。父亲的人生选择是基于他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并被城市化进程、环境污染等社会变化而左右,进而也影响着子辈的人生。小说中,父亲的死亡或远走都是由他们承担的养家的责任引起的,“父亲的缺失”背后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的名字叫丫头》《月亮舞台》中,父亲于叙述中在场,但在事实上缺席。在丫头和胖墩儿的叙述中,他们父亲的形象是不同的,一个是“瘸腿的卑微的忧伤的父亲”、一个是“英雄的传奇的父亲”,但他们同样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后,丫头和胖墩儿选择用浪漫的想象来抚慰失去亲人的伤痛,他们同时也接受了父亲缺席的现实,试图努力填补父亲的角色。丫头十四岁,他选择退学、织网、卖虾酱来赚钱养家;胖墩儿十一二岁,他想打工、赚钱给妹妹买书包,给奶奶买胃药。失去父亲的孩子在叙述中一再讲述父亲的故事,以父亲为榜样,逼迫自己迅速成熟,用稚嫩的双肩试图像父亲一样扛起养家的重担。然而他们内心仍然脆弱,他们需要呵护。丫头“觉得父亲是多么地爱我们。……我想父亲肯定没有死。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父亲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他嘴里叫着丫头,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丫头在孩子和成人两种身份中纠结,一边软弱一边坚强,父亲的爱支撑他完成从孩子到成人的转变。胖墩儿在梦境中迷惑于小丑想要他表演什么。他虽然有根雕的天赋,但更是一个需要呵护的脆弱的孩子,他最渴望的生活是幸福家庭中备受父母呵护的生活,然而现实却需要他像个成人一样负重前行。月亮舞台是胖墩儿的真实内心世界。孩子还是成人?儿子还是父亲?他在两种身份之间纠结选择。故事现实叙述中的温暖明朗是孩子理想中成熟的自我,梦境叙述中的压抑苦涩是孩子迷失的自我。从《我的名字到丫头》到《月亮舞台》,刘玉栋越来越关注儿童在“父亲缺失”情况下成长中的精神困惑,并且表现出保护孩子本真自我的思想。
在家庭中,孩子的养育者和成长中的引路人是父母。在刘玉栋的儿童小说中,不仅存在明显的父亲形象的缺失现象,也存在着母亲形象的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与父亲的缺失不同的是,在小说中,母亲在事实上和叙述中大多都是在场的,但是在儿童的教养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母亲的更多的作用和影响,也看不到对母亲的细致的描写。也可以说,小说把儿童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进入一个人生新阶段时父母双亲的约束力、引导力降到最低,让儿童独自进入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童话中的奇境历险在刘玉栋的儿童小说中,变成社会化冒险历程。在这段冒险中,小伙伴、邻居给予陪伴和帮助,乡村自然给予心灵的抚慰,儿童在关于自我身份认知的迷惘中,一路跌跌撞撞,找寻或者坚持保有本真的自我,最终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转变。这样的情节设计既是基于当下社会现实的,也是符合儿童文学创作规律,能够吸引儿童阅读兴趣的。
在刘玉栋眼中,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没有明确的界限,他始终怀着一颗纯朴的心、秉持一贯的严谨态度来写作儿童小说。他的儿童小说扎根于鲁北平原,融入了作者本人的个体生命体悟,既关注当代社会变迁,又写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充满童趣。刘玉栋深谙儿童文学的创作规律,精心选择叙事技巧,巧妙地处理了父亲形象的缺失问题。父亲形象的缺失既来源于作者的童年经历,又是他当代书写中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儿童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色。通过父亲形象的缺失,刘玉栋将儿童主人公推向社会冒险的极端处境,写出了父亲的缺失对儿童成长的巨大影响,表现了父子深情,揭示了重大社会问题。他的儿童小说不仅是孩子们认识社会获得教育的好读本,也是让成人阅读者回忆童年、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优秀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