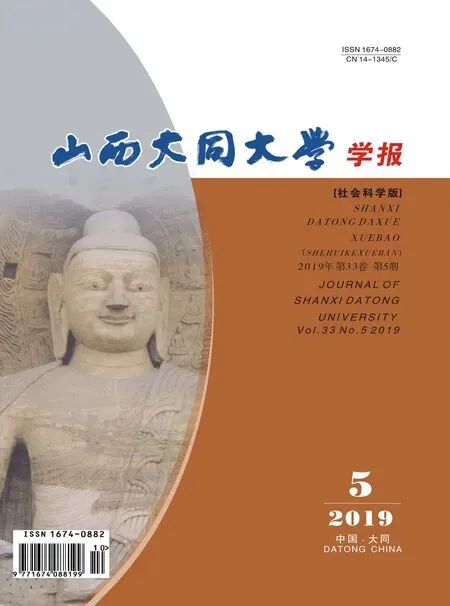萧红《黄河》的文学地理建构
郭淑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一、《黄河》素材来源
《黄河》是萧红在汉口创作的短篇小说,写于1938年 8 月 6 日,发表于 1939年 2 月 1 日《文艺阵地》(武汉)第二卷第八期,由叶君健译成英文刊登在销往南洋的《大路》画报上。
“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文化人纷纷前往武汉。萧红、萧军通过哈尔滨作家于浣非结识了蒋锡金,与蒋锡金合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 号。1938年1 月,在武汉小朝街,萧红等作家聚集在胡风周围,座谈讨论战时文艺创作。其时胡风正主持《七月》杂志,寄望于战时文学创作能够引导中国人民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他们在众多杂志中,率先发出《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战时文艺”先声。《七月》座谈会上,他们就作家在战时究竟采用什么题材和手段,作家是否上前线等现实问题展开探讨。有人认为作家与生活隔离,所以作品没有力量。萧红则明确地表示作家并没有和生活隔离,作家就在战时实际生活里。她希望抗战以来的文艺创作不要让高涨的情绪影响到脚踏实地。
1938年,萧红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处在战时逃亡路上。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战事不明朗,萧红等《七月》同人接受民族革命大学的邀请,赴山西临汾任教。1 月27 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人乘坐运载货物的列车于2 月6 日抵达临汾。然而,战事进展的速度超乎人们想象,日军很快逼进临汾。丁玲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决定转移,除了萧军坚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等其他一行人均随丁玲撤往山西运城。2 月24 日,萧红在写给高原的信中,谈起她在山西运城民大第三分校教书,2 月底将赴延安的计划。丁玲回忆第一次见到萧红时,山西还很冷。萧红与长久生活在军旅中的丁玲有明显的不同。丁玲穿着松垮的军衣,戴着军帽,早已习惯于粗犷豪放,身上的女性特质荡然无存。而萧红,“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1](P123)这一回忆显然与丁玲早年的女作家生活相关。丁玲说,“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1](P124)然而,萧红并没有去延安。
国难当头,萧红参与到抗战戏剧的集体创作中。1938年3 月初,在去往西安的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共同创作了话剧《突击》,由塞克整理后发表在1938年4 月1 日《七月》第二集第10 期上。3 月中旬,《突击》在西安公演三天七场,场场爆满,引起全城轰动。萧红等主创人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抵达西安后,萧红入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聂绀弩的《在西安》里,也讲述了萧红在西安的日子。两人在西安的正北路散步,谈起她和萧军感情的事情。萧军曾向聂绀弩交待,临汾守不住,让他们与丁玲过河去,并嘱咐聂绀弩照顾萧红。但战事正紧,交通不便,他们又困在了西安。聂绀弩回忆当时境况,“在西安过的日子太久了,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占领了风陵渡,随时有过河的可能,又经常隔河用炮轰潼关,陇海路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没有法子回武汉。”[1](P129-130)日军攻下山西河南,便向西安进攻。大炮狂轰滥炸,尽管潼关城内建筑尽毁,但强大的防御工事阻挡了日军过河。
4 月下旬,萧红回到武汉,再次入住小金龙巷。8 月上旬,搬至汉口三教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部。9 月中旬,去往重庆。
1938年1 月至4 月,在湖北武汉、山西、陕西三地之间动荡不稳定的生活节奏中,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中,萧红沉淀了一些战时故事构想。关于山西、陕西的百姓生活观察和小说素材,出现在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朦胧的期待》中,成为萧红日常生活审美化立场的一种注脚。萧红将战争中普通人的所思所想和焦虑不安的生活状态,纳入她的文学建构中。《黄河》的镜头聚焦于黄河流域人员来往频繁的渡口。千古雄关——潼关、风陵渡两个渡口,以及在此讨生活的船老板水手和参战的八路军战士,构成小说的主体背景和人物。
萧红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写入她的小说中。此前她曾在《商市街》里写过松花江,那是她对哈尔滨消夏的呈现,是一种享受夏日城市生活的基调。此后所写的《呼兰河传》,那是她对故乡的历史性思考。如今,她冷静地将黄河潼关一带的自然地理置于小说框架,以船老板阎胡子的命运诉说着古老中国的天灾人祸以及在灾难中隐含的希望和力量。
二、潼关与风陵渡
初读这个短篇小说,被萧红捕捉的独特黄河意象惊到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五千年璀璨的中华文明。王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劲壮阔,展示了黄河豪迈雄奇的景观。李白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浩荡风姿,展现出了黄河从天而降、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诗人笔下的黄河,将个人命运与黄河的雄伟壮观融为一体,使诗歌格局由此而阔大而宏富。时间走到近现代,中华民族屡遭外敌入侵遍体伤痕,在萧红心中,黄河已没有诗人浓墨重彩的壮观,也没有咆哮奔涌的动态气概,更没有直抒胸臆挥洒自如的盛唐气象。在萧红眼里,黄河只是缓慢的滞着的几乎不流动的死水一潭。对潼关黄河的照相式书写,印证了萧红拮取土地、河流的外在特征内化为对动荡时局的深切忧虑。
潼关位于陕西渭南境内,北临黄河,南踞山腰,是黄河渡口,处于秦、晋、豫三省之要冲,是进出三秦锁匙。抗战时期,潼关是运输补给和往来人员的重要通道。从潼关到对岸风陵渡,便进入山西运城地界。风陵渡处于黄河东转的拐角。作为黄河要津,风陵渡自古以来就承载了无数征战戎马的故事。潼关和风陵渡的战略地位,注定在抗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萧红的短篇小说《黄河》中便是如此。
从潼关到风陵渡,萧红重点写的自然地理景观有潼关、黄河、风陵渡,牵涉到的地名有山东、山西、关东、赵城、洪洞。季节物候是未融化掉的一片片冰排。物质景观出现了帆船、同蒲车站、席棚子饭馆、笤帚、豆粒、麦稞等。这些自然地理景观和物质物候景观,都为萧红书写战前故事,间接地书写抗日战场提供了服务。
总体而言,萧红选择潼关和风陵渡这两个带有古战场意象的地点作为叙事背景,叙述八路军战士乘民船过河追赶队伍的故事,聚焦战争的意味不言自明。小说重在突出黄河缓慢的特征。潼关段的黄河,萧红用了悲壮来形容,象征了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拐点,侵略与反侵略正是黄河悲壮的历史命运。萧红开篇就用了这样的句子,“悲壮的黄土层茫茫的顺着黄河的北岸延展下去,河水在辽远的转弯的地方完全是银白色,而在近处,它们则扭绞着旋卷着和鱼鳞一样。”[2](卷2,P51)而行进在黄河上的帆船,“一只排着一只,它们的行走特别迟缓,看上去就像停止了一样。”[2](卷2,P51)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夹带了大量泥沙。[5]河里只能看见泥沙,“常常被诅咒成泥河呀!野蛮的河,可怕的河,簇卷着而来的河,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这河本身就是一个不幸。”[2](卷2,P52)河水泛滥时对大量生命的无情吞噬,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让萧红陷入深深的忧虑。
萧红将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定在正月过后。这时候的黄河已过了结冰期,迎来了春天。“发酥的冰排流下来,互相撞击着,也像船似的,一片一片的。”[2](卷2,P52)冰排对上行船也构成一定的阻力,加重了船的前行难度。
黄河上的船,形状较为特别。“船是四方形的,如同在泥上滑行,所以运行的迟滞是有理由的。”[2](卷2,P52)萧红强调的四方形的船与冲风破浪的尖头船不同,溢出了人们所理解的造船常识。这是潼关至风陵渡黄河最具特色的水上运输工具,也是黄河人慢节奏生活的象征。
三、阎胡子与八路军战士
在一个缓慢行进的泥河上,战争来临前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气氛?萧红试图通过普通人和八路军战士的相遇,将民间对战争的猜测和八路军备战的情况揭示出来。萧红把战时特定的兵民对话带到了她的小说中。《黄河》以一个八路军战士与船老板阎胡子之间的交集,形塑了阎胡子这个普通中国人的性格和人生轨迹。在乘船渡河过程中,短暂的时间和狭小的空间都为人物关系的确立制造了难度。人物关系必须迅速搭建起来,才能有效地展开故事,达到叙事目的。萧红选择了阎胡子和八路军战士的矛盾节点来制造冲突。又由冲突的破解,牵出阎胡子所关心的战事发展。从阎胡子和水手们的立场来看,黄河上有兵船,士兵可以坐兵船,拉货的民船是没有义务带兵的。况且船处于上行,多带一个人增加船的份量,水手们会更费力气。而八路军战士有特殊的情况,由于他的妻子去世,耽误了随队伍集体出发的时间,他急于追赶队伍,不想等待兵船。意外,使得这次兵民相遇有了机会。
开船前,阎胡子下船去打酒,交待了船老板的性格特点。渡船为生的阎胡子只相信自己。年轻水手们给他打酒,要么会吞下一点钱去喝羊汤,要么会偷喝他的酒然后兑水充数。对于爱酒的阎胡子,水手都怕他,船上的水手等待不耐烦了,背后调侃他,“尿骚桶,喝尿骚,一等等到骆锅腰!”对阎胡子喝酒误船也批评一下。阎胡子船上功夫的确厉害,精通船上大小事务。对于上行船,关键的是控制重量,所以一上船,水手们告诉他有“坐闲船”的,他马上表态,“那得让他下去,多出一分力量可不是闹着玩的。”[2](卷2,P54)随后又发现水手把面粉袋放的不是地方。一袋面粉本来三十斤,放错了地方,可以费上六十斤的力量。他边嘟囔边又亲手挪动这袋面粉。
转变在于阎胡子对八路军战士的好感。他家所在地赵城是由八路军游击队保卫着。“八路上的”,他招呼着那个八路军战士,“你放下那撑杆吧!我看你不会撑,白费力气。这边来坐坐,喝一碗茶,”“你来吧,这河的水性特别,与众不同,你是白费气力,多你一个人坐船不算什么!”[2](卷2,P55)
阎胡子抓住行船的短暂时间,不停地向八路军战士打听战事进展。他对赵城是否保得住非常担心。他在赵城住了八年,孩子小是他最担心的事情。“你说那地方要紧不要紧?去年冬天太原下来之后,说是临汾也不行了……赵城也更不行啦……说是非到风陵渡不可……这时候……就有赵城的老乡去当兵的……还有一个邻居姓王的那小伙子跟着八路军游击队去当伙夫啦……八路军不就是你们这一路的吗?”[2](卷2,P55-56)阎胡子步步紧逼,像是自言自语,更是急迫地想把心中猜测和牵挂一古脑地全倒出来,讲给战士听。“可是你说……赵城要紧不要紧?俺倒没有别的牵挂,就是俺那孩子太小,带他到这河上来吧!他又太小,不能做什么……跟他娘在家吧……又怕日本兵来到杀了他。这过河逃难的整天有,俺这船就是载面粉过来,再载着难民回去……看那哭哭啼啼的老的小的……真是除了去当兵,干什么都没有心思!”[2](卷2,P56)阎胡子是黄河上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一个船老板。他磨豆腐似地翻过来掉过去地念叨赵城。他的焦虑不安反映了普通中国人的战时心态。
战时的普通中国人,只对保家卫国的军人充满信赖。在这个特殊的当口,阎胡子寄希望于八路军。因此,他不想放走八路军战士。为了打听前线消息,他在船到了风陵渡口时还将八路军战士拦下,请他一起坐在席棚里吃饭,要上碗面片汤,来上半斤锅饼,可以边吃边谈。“俺想,赵城可还离火线两三百里,许是不要紧……”“咱中国的局面怎么样?听说日本人要夺风陵渡……俺在山西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一只破船……”[2](卷2,P58)由于八路军保卫山西赵城,阎胡子就极力巴结讨好战士。而战士并不作正面回答,只说是赶路,只问他是否给赵城的家人捎个口信,其他消息一概不外露。这又让人联想到八路军战士严守纪律的形象。当然,阎胡子是山东人的急性子,八路军战士是山西人的慢性子,于是在小说中出现了十分奇怪的对话场面:倾诉与沉默。阎胡子对战争局势不断套话,把自己的底细倾囊而出,类似于进攻,而八路军战士只是简单地附和,类似于防守。这场谈话,虽然并不势均力敌,但突现了两人的不同地域性格特征。正如阎胡子所说,山东人的性格非常不习惯在山西谋生,“好比苍蝇落在针尖上,俺山东人体性粗,这山西人体性慢。”[2](卷2,P58)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决定了历史上山东人在黄河洪灾来临时,把关东认为是块福地,年年“闯关东”而不是闯山西的选择。
四、山东与山西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三百余年的移民史,也是悲壮的生存抗争史。清代由黄河造成的洪灾127年次。黄河成为山东人的心腹大患,几乎无地不灾。夏秋两季是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季节。到了20 世纪初叶至中叶,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有6年,都是由于黄河洪水泛滥所致。[3](P1-3)许多山东人携老扶幼背井离乡,逃到了关东(也即东北)谋生,谓之“闯关东”。
萧红写黄河,写的是潼关和风陵渡,是发生在陕西和山西的战前故事。可是小说主要人物却选了一个山东人阎胡子。阎胡子为什么会在山西当船老板?显然,萧红的目的并不是单独写这场战争对中国人的影响,而是写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苦难和抗争。这一点,在曾经“闯关东”的阎胡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阎胡子经历过两次逃难。这个山东汉子因为黄河发大水,逃到了关东。他的家乡在黄河边上,黄河发大水是铺天盖地、无边无际的气势。“白亮亮地,哗哗地……和野牛那么叫着……山东那黄河可不比这潼关……几百里,几十里一漫平。黄河一到潼关就没有气力啦……看这山……这大土崖子……就是它想要铺天盖地又怎能?”[2](卷2,P56)黄河水到了山东,“就像几十万大军已经到了”,阎胡子的父母被大水卷走。离开这河远一点吧,去跑关东吧,在人们的劝说下,他带着老婆去了关东。在关东他有了三间房、两三亩地,由于日军侵占了关东,建立伪满洲国,阎胡子又逃到了山西,投奔了叔叔。现在,日军又打到了山西,只积攒了一条船的阎胡子,充满了生存的焦虑。阎胡子是想过好日子并且为了生存很努力的中国人。他在水患、兵患中求生存的悲剧命运,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
尽管对于黄河所象征的古老中国的缓慢行进,对于黄河夺去无数中国人生命的病态和荒凉,萧红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然而,在小说的结尾,萧红还是给出了光明。
阎胡子让八路军战士告诉赵城的家里人,他一切都好,却还是不满足,对着往同蒲站去赶火车的八路军战士最后一次问到:“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八路军战士走回来,好像是沉思了一会,而后拍着他的肩膀说,“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2](卷 2,P59)
萧红从最基础的在黄河上讨生活的船民写起,从最简单的过好日子的普通人的信念写起,正如1938年10 月31 日,她所写的小说《朦胧的期待》结尾,李妈在梦中见到了上前线的金立之,他说“我们一定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不胜利呢,没道理!”[2](卷2,P66)在萧红写作的时候,抗战胜利还是一种希望和想像,萧红在黄河上讨生活的阎胡子身上寄托了在苦难中抗争的中国人的不屈精神。
结论
萧红将目光聚焦于抗战时期的黄河潼关风陵渡一带,对黄河的文学地理建构,改写了古代诗人赋予黄河的传统形象。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拐点,潼关和风陵渡的战略地位上升。萧红对潼关战前气氛的据实书写,印证了萧红拮取土地河流的外在特征内化为对动荡时局的深切忧虑和对于这场战争抱有的必胜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