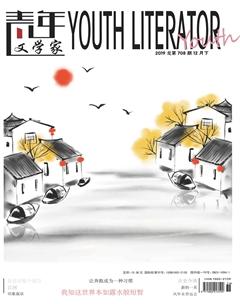谈子君形象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张馨文,南通大学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6-0-02
引言:
在《伤逝》的伊始,鲁迅先生写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整篇文章是涓生的一部忏悔录,小说完整的追忆了涓生和子君恋爱的开始到结束,令人唏嘘和感叹,涓生俨然是子君思想开化的启蒙老师,他们追求自由恋爱,却又在乌托邦式的爱情幻灭之后,子君走向灭亡。新旧碰撞,子君的灭亡是时代前进发展的必然。鲁迅一生与四个女人有着密切关系:母亲、朱安、许羡苏和许广平,与许广平相恋后,鲁迅心中依旧顾虑万千,“追求自身生的权利和爱的权利的个性主义和兼顾朱安生存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鲁迅的内宇宙中消长起伏,深广的爱和深刻的忧患交结在一起,使他心事浩茫,思绪万千。难言的欢愉和难言的痛苦终于激发了他艺术创造的灵感和冲动。”[1]《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篇爱情婚姻题材小说,篇幅短小却直击人心,表达了鲁迅先生对爱情的思考和见地,也是鲁迅先生个人的感情心路历程写照,自《伤逝》发表以来评论界就争论不休。从形式到内容,从涓生到子君的形象和内心分析,从女性意识觉醒到女性自我成长,包罗万象。批评者用不同的方法解读文本,分析子君的人物形象意义,并从子君的性格转变和命运爱情悲剧来剖析女性的当代意义,当代女性独立自强,终生学习,自我成长。
一、子君人物形象分析
阅读《伤逝》,提到子君,不少批评者将子君归为“新时代的女性”,她受过新式教育,上过新式学堂,敢于冲破家庭的束缚,在爱情上追求自己的幸福。文章中的确不难看出子君想要冲破牢笼的决心,在她跟涓生交往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父亲之后,子君能决然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子君,能让人看到想要主宰自己命运的一丝希望,这是她的言语、思想、行为和做派所表露出来的。看到自己爱着涓生那颗坚定的心后,不顾社会世俗的偏见,便自愿地选择和涓生同居,甚至在两人筹划找寻住所方面,子君坚持当掉了自己唯一的金耳环和金戒指这是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里,女子万万不能做的人生禁事,所以子君身上的“新”是的确一目了然的。
也有不少批评者认为鲁迅先生笔下的子君就是《玩偶之家》里出走的娜拉,娜拉出走的结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子君虽然逃离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却又闯进了另一个牢笼。两个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甜蜜渐渐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代替,随着时间的飞驰,涓生和子君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子君管了家务之后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是自诩是新时期进步青年的涓生所不能容忍的,他需要思想上的契合和沟通,他们在思想、文化和情趣上的分歧已越来越远。涓生丢了工作后,这个家失去了维持生计的经济来源,柴米油盐难以为继,油鸡成为口粮之后,阿随也被送走,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展现两人的矛盾: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大家争吵的线索。加以每 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涓生在日常的生活中已经嫌恶了子君,残酷的现实浇灭了子君对于生活的热情,涓生的不爱,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选择了最为体面的一条路——死亡。既不用面对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绝情话的涓生,又不愿回到和自己闹掰的胞叔、爸爸那里去。在这一点上,她又是不新的,她懦弱,她胆小,她不敢面对自己的信仰破灭。她还是那个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旧式女人。
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来看子君,她是一个集合传统和现代的思想于一体的矛盾女性形象,子君的死是对传统的否定,旧的那一套所带来的终究是灭亡。这个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走出牢笼的女性,重新回到牢笼之后,换来如此悲惨的结局。这样的“走出”和“回到”只是原地踏足,在遇到涓生前,子君养尊处优,受着新式教育,她说出的那番话,让涓生以为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的灵魂,让涓生仿佛看到了一个熊熊燃烧着自由之火的女神,子君为了爱情,与家庭斗争,甚至在组建小家时,不惜当掉了自己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这个举动与其说是因为爱情而献出自己的所有,不在乎物质付出的多少,更多的是让读者看到的是,子君的潜意识里,已经有了男女平等的启蒙意识,她开始意识到生活不该一味是男人的付出,这些都是她思想上的前进。同居之后,那个恋爱中的甜蜜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异于封建家庭中日益操劳的家庭妇女,“她终日的汗流满面,短发都黏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她开始操劳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当生活的重心回归于整日的做饭、饲鸡、喂养阿随和小官太太因为日常琐事发生口角,又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积蓄之后,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需要依靠涓生来补贴,缺少经济独立权之后,子君的精神层面也开始依赖涓生,涓生曾经给她的承诺,涓生曾经带来的“爱”,她对涓生的爱支撑着她为这个家庭付出,她心甘情愿地沉沦。她终于失去了“新生”的光芒,涓生已然成了她存在的信仰。信仰一旦崩塌,也是整个精神世界的崩塌和萎靡,子君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她感觉到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此时的子君所表露出来的正式封建传统的家族女性的通病——依靠家族、依靠男人,完全的迷失自我,在为家庭的奉献中,被岁月蹉跎的失去鲜活。
二、历史的中间物
鲁迅先生曾以“历史的中间物”来评判自己,他笔下的子君也正是如此这般的“历史中间物”,随着涓生态度的改变,从一开始的“将他的纯真热烈的爱展示给她”到后来的“他要明告她,但他没有敢”,子君的形象不断地弱化,由最初的活泼变得怯懦、猜疑、惊惧、凄惨。在五四时期强调男女交往自由、男女平等思潮的影响下,涓生和子君追求的是男女自由恋爱的模式,身为大家闺秀的子君,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此刻的她,热烈地爱着涓生,听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恋人的影响下,涓生和子君处于一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子君想要觉醒,她积极的反抗,为了心爱的人,她愿意一搏。但那时的涓生已然明白,他将雪莱的半身像指给子君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子君是还未脱尽旧思想束缚的,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新事物虽蓬勃涌现,旧事物也没有完全离开历史的舞台。
新旧交替之际,受新思想的影响,走出封建家庭,但子君毕竟還是在旧式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女子,她的思想里依旧有着不可磨灭的“从夫”思想,在她与涓生同居回归到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后,“从夫”思想愈演愈烈。在涓生狠心吐露心声之后,“她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子君不似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有着自主强烈的个性和激烈的内心活动,莎菲女士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她是完全的新思想主义的代表者,不依附于爱情,反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子君是涓生一手创造出的“历史的中间物”,是涓生带给她思想的启蒙,是涓生的承诺让她沉浸于同居生活,为他的衣食起居操劳,也是涓生感情和经济的变化,让子君变的敏感猜疑,最终走向灭亡,子君的身上杂糅了新与旧,她的这种新旧结合和巴金笔下同为历史中间物的觉新又不尽相同,觉新的新在于他思想的觉醒,他的旧归咎于家庭的压力和责任,虽然他深爱着梅,但为了父亲,为了家庭,接受了与瑞珏的联姻,为了弟弟们的幸福,他也与封建的家族抗争着,觉新之新在思想,止步于行动,子君之新昙花一现,走出又回归,行为上的一时“新”不敌思想上的止步不前。
三、女性自我成长意识
我所看到的子君,曾经为爱勇敢,奋不顾身的与家庭决裂,追求自己的幸福,又因为爱开始怀疑自己,整日惊惧,成为涓生最不喜的家庭主妇。现实的立场来看,子君只是涓生实现启蒙价值理想的牺牲品,涓生对她的爱是虚无的,是有目的的,他渴望通过年轻鲜活的子君逃离现实的虚无,一旦发现子君无法满足他的本源目的,乌托邦生活的理想破灭之后,他想着逃离。这个始乱终弃的男人没有履行他给子君的承诺,自始至终涓生所在乎的是他自己的私欲,即使《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涓生叙述完爱情的开始到结束之后的忏悔,但子君已永远地离开这个后来让她无所适从的世界,一切都晚了……不管是作为时代觉醒的新青年还是新时代的女性,子君的悲惨的结局提醒着我们时刻警醒,自我成长意识是每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所必需具备的,子君死于新生活理想的幻灭,死于启蒙的不彻底性,更死于她的止步不前,女性的自我成长意识应该是终生所坚持的。成长,既包括生理成长,也包括心理成长,我们所坚持的成长,是我们自我意识的觉醒,男人不再是女人成长的参照物,女人也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思想的成长是时刻的自省,要认识到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和价值,拥有独立的人格。正确两性关系该是应当是:感情双方依恋但不依附,对幸福爱情的向往不代表丧失自我,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是终生学习,很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之后便会降低乃至失去对自我的期待,难以确定自我角色,容易被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所影响,尤其是男人的否定,很容易导致自卑心理产生自我否定,开始紧张、焦虑和恐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二是自我事业追求,若子君在她与涓生组建的家庭中拥有一定的经济话语权,那在失去经济来源的涓生看来,他还是不能直接地说出“我已不爱你”这样绝情的话,子君的经济来源可以支撑起整个家庭的运转,也不会致使阿随被送走,子君失掉自己生活中的陪伴。当今社会的女性需谨慎“往回走”,女性要自立,提高心理承受力和社会应变力,自尊自重不妄自菲薄,合理的规制爱情和事业,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总结:
自古以来,传统女性之殇在于对家庭的依附和“从夫”思想的荼毒,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经济话语权,以夫为天,夫死,以子为天。从《伤逝》中,子君的人物形象来看,子君的灭亡除了涓生的始乱终弃之外,究其自身,死于将自己的全部交付于一个男人,神化自己心目中的爱人并将其奉为信仰,一旦遭受抛弃,没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便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输到底,作为当代女性,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女性想要在社会和家庭里获得话语权,就首先要有经济权,终生学习,从来不只是追求温饱,而是获得为自己说话的机会。我们新一代的人都在提倡男女平权,但确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注释:
[1]王排.女性文学批评:一种新的理论态度[J].当代文艺思潮,1987.(5).
参考文献:
[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J].妇女杂志,1924.10(8).
[2]曾琪.关于《伤逝》中子君形象的探讨[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3]蒋清凤.人格与爱情:子君与安娜的爱情悲剧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07).
[4]缪启昆.子君——男性主体言说下扭曲的女性形象——《伤逝》散论之三[J].职大学报,2003(01).
[5]周玉宁.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1994(02).
[6]赵红.《伤逝》中子君形象的女性话语解读[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03).
[7]于惠.女性主义视角观照下的子君的悲剧[J].德州学院学报,2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