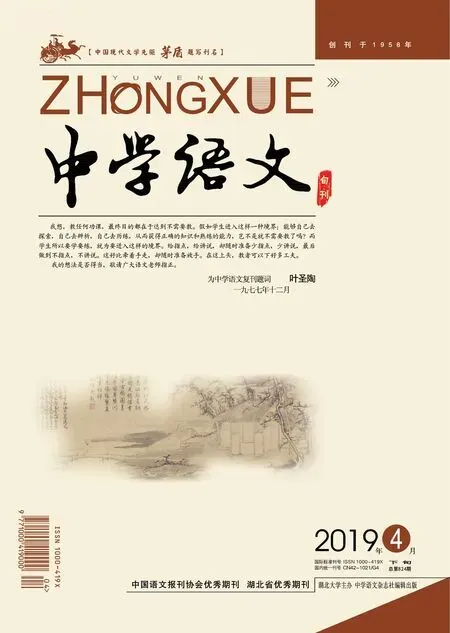精蕴 悖论 传承
——综论叶圣陶阅读教学观
李耀平
作为语文“工具论”代表的叶圣陶,其阅读教学观对当今教学、研究是否还有价值?能否给他贴上“工具论”的标签?欲答此问,须走进相关文献,重新研读叶圣陶的著作。
笔者通过研读发现,叶圣陶阅读教学观的精蕴如下:
1.积淀传统精华
叶圣陶“幼年习五经,背诵于私塾之侧,均能上口”,而后,诸子百家,诗词曲赋,无不涉及。还曾发动全家编辑《十三经索引》,他“自任断句”;又选注《荀子》《礼记》《传习录》等古籍并作绪言,由此积淀丰厚,并自然渗入其阅读教学观:“文质并重”是选编教材的首要标准;“博采众长”“温故知新”“学用结合”“举一反三”是学法观的重要内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启发诱导”是教法观的基本内容;至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激发兴趣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批判阅读思想,“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的熟读精思之论更常为其引用。总之,他对传统教育思想食而化之,酌而采之,由此根基深厚,终成一家之言。
2.汇聚时代精神
叶圣陶既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顺应清末民初重实用的语文教育潮流,又吸纳了同时代诸多语文教育家、美学家、文艺家的智慧。他强调即知即行,明显与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思想相通;他主张以文学作品涵养精神,与朱光潜“从文学作品的阅读里提高思想的境界”之观念如出一辙;鲁迅的“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反对读经等阅读观也一直为叶圣陶所阐发、提倡;胡适的“三步教学法”直接启示了叶圣陶精读指导三环节论;蔡元培的应以教白话文为主、“读书为应用”“应该教应用文”“反对逐句讲解的注入式教学”“书本不过是例子”“自主学习”等思想更是化入叶圣陶的阅读教学观。总之,如叶至善所言,叶圣陶的思想“大多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的看法”。他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熔铸了一个深邃、具鲜明时代特色的阅读教学体系。
3.主张文道统一
在阅读教学中,如何对待“文与道”,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三阶段:1919年始,“以道为主”;1938年始,“以文为主”;1942年始,“文道统一”。他明确提出“语言和思想又是二而一的东西”,并纠正自己以前观点:“无论说‘以道为主’‘以文为主’或者‘文道并重’,都是把‘道’和‘文’割裂开,既不符合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不可分割的客观实际,又不符合培养读写能力的教学实际。”因此,他力倡“语言(文)工具性”但不排斥思想性与人文性。他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二者不可分割。要真正掌握好语文工具,须致力于“训练思想”和“培养感情”。阅读教学不仅为使学生掌握语言这种工具,也为使人们“思想益正确而完善,情感益恳挚而缜密”“智赡德新”。故选文要文质兼美,讲授不能离文讲道或离道讲文。要重视文学对学生精神气质的养成、情感世界的构建、审美眼光的培养、良好人格的塑造等方面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至于阅读教学实际中强化“工具论”,将语言视为工具加以机械化训练,已远违叶圣陶本意。
可以说,其阅读教学观有容乃大,但随时代发展,局限日显。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现代化思维对古书经典的压制
他张扬“应需”大旗,要培养具有现代精神、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以应生活之需的普通公民,反对古典主义、利禄主义的科举奴化教育。具体表现为:内容上要以白话文为主,古书经籍要浅易而分量少;学法上不能如古典主义死记硬塞,注重获得真知真能,指向“致用”。
他主张荡除“古典主义”之封建思想糟粕、死记硬塞、钻训诂“牛角尖”等弊病是合理的,但因他未对此作系统阐述,也没辩证分析学古书经典的利弊得失,在实际教学中造成对古书经典的压制,几乎苗莠尽弃。其实古典主义包括读经史古文等人文教育,它对“做人”“作文”举足轻重,是学人共识。朱光潜主张看书“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要读古典。温儒敏认为“经典是我们的主食”,能真正体现人类智慧,能长远涵养我们的性情。若流连浅俗读物,不免耽搁要籍,败坏阅读胃口。“反对古典主义”承担过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在当今正视这一观念带来的诸多积弊,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古书经典,漫游于民族文化长河,与先贤大师对话,构筑精神家园,抵制“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侵袭,亦时代亟需。
2.技术化倾向对人文的消解
韩军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价值意向”。在叶圣陶阅读教学观中,他强调语言与思维结合,强调语感和审美,强调“共情”化育,强调尊重学生原初体验等,是从不同侧面贯注和强化阅读教学的人文精神。但他过于强调培养读写技能,追求教材体系的逻辑化、教学点的细密化,对教学内容的透析化、准确理解化,训练的层次化、技术化,对人文精神又有一定消解。
他的语言模式是,阅读要由大的语言单位向小的语言单位逐级解构,写作则反向逐级重构。这种观念既有刘勰“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章理论的影子,更是五四以来科学主义理性哲学的体现。它注重对文章进行“技术”分解,从语法、修辞、写作等角度“析形得义”;它抽去人的情感、个性,忽视语言往往要靠体验来内化,靠高度活跃的想象来支撑。这种解构与重构涣散了语言固有的人情、人性意向,使之成为一堆冰冷的语码。这是叶圣陶极力主张通过阅读涵养精神,却最终技术雷鸣、精神退隐的根由,因为技术让语言清晰的同时也割伤了语言的内质——流动而极具情意特征。在功利化背景下,加之师生素养有限,阅读教学不可避免地走向狂轰滥炸、抽筋剥骨,气韵灵动委顿。
3.阅读“三论”导致读写关系失衡
立足语文教育的“平民化”“实用化”,力图反拨读书旨在写作“应试”博取功名的科举教育传统,也为扭转当时把写作程度等同语文程度的倾向,他提出著名的“阅读三论”:阅读“根论”“基础论”“独立目的论”。 阅读可为写作提供知情意修养,有助于良好的文体感、语感的形成;就实际而言,读书不一定就是为了写作,有时为了求知、欣赏等。故“三论”自有其合理性,但因之对读写认知的单向度思维和对阅读的片面强调也导致读写关系的失衡。
本来,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之一,但写作所需的天赋、才情、悟性、阅历等素养非阅读尽能给予。“会读未必会写”,但“会写必然会读”,因为写作须有“读者意识”,作者要兼具读者身份对所写进行评判和检视。此外,写作能促进高质量阅读,使信息经过阅读主体选择、加工而清晰纳入原有认知结构。因此,黎锦熙主张“写作重于讲读”,胡适视写作能力为衡量语文水平的标准。叶圣陶自己也主张通过写读书笔记深化阅读,训练思维,但又过于强调“三论”特别是“阅读独立目的论”,加之张志公、吕叔湘等人的推动和广大语文教师的盲从,读写“两轮”失衡,迅速滑向“讲读”,写作沦为阅读可有可无的附庸。
“三论”本来厘清了以写作知识指导写作的误区,彰显了阅读谋生应世、传播文化等功能,但它夸大了阅读对写作的作用,是阅读教学畸形膨化、“为读而读”泛滥成灾的思想根源。
总之,在叶圣陶阅读教学观中,重涵养精神又偏重致用,重约博并举又强调“务求甚解”,重“学生主体”又主张教师“强势引导”,重“知”力“行”又偏重训练强化,重批判阅读又强调“文本中心”,重感悟积累又强调举一反三、析细讲透,重读书笔记又强调“阅读独立目的”。由于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和逻辑论证,这些悖论在实践中此消彼长而失衡、失度,阅读教学“三目标”变相、走样——理解欣赏流于浅层,学习写作高耗低效,涵养精神化为泡影,其根源在于他认知及思维方式的局限导致的阅读教学观与生俱来的缺陷。
尽管如此,这掩盖不了他阅读教学观的精深内涵、真知灼见。作为现代语文教育的主笔者,其阅读教学观不该被拔高,更不该被“颠覆”。它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时代,这些局限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印记。它作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1994年,顾黄初在号召大家学习、发展叶圣陶时也承认,叶圣陶提出观点时,“往往很少作详密的逻辑论证”,倡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多光源聚焦”研究叶圣陶。在新时期辩证重读叶圣陶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正视其中悖论,深入发掘精蕴,对我国目前课程与教学改革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也是真正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尊重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