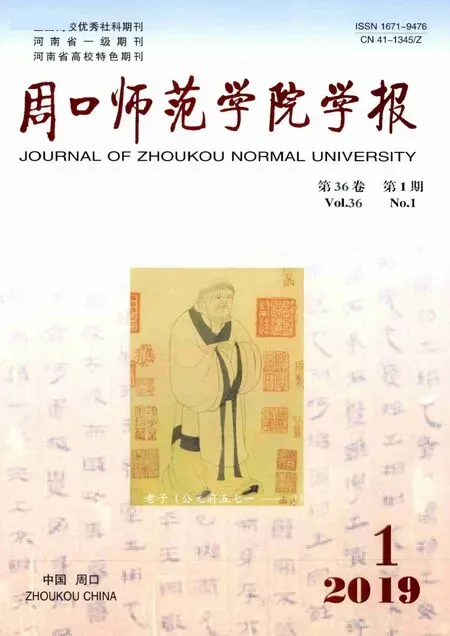君、臣、民的权力分割:韩愈的政治思想
刘真伦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分享,集权与分权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从全球化统一大市场的角度讲,现代国家的集约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上古社会;从权利让渡与权力制衡的角度讲,朕即国家的时代一去不返。现存的君主制民主国家,其皇室早已退出权力角斗场,仅仅保留了民族国家权力象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权力逐步下移分散的过程。个体的权利让渡才是公共权力得以合法存在的基础,应该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
《书·毕命》:“道洽政治,泽润生命。”孔传:“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政治道德教化的目的,就是造福百姓。立足于百姓的生存状况,考察、评判政府的行政作为,无论是平民韩愈还是官员韩愈,一以贯之,始终不变。韩愈的政治思想,就是在针对朝廷政治措置的评判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博弈的最终目的,是权力的分割。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唐,君、臣、民之间的权力分割,在君臣之间,主要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政府与百姓之间,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博弈。关于后者,笔者有另文讨论。本文分君权与相权、集权与分权、暴力与非暴力、道统与治统,讨论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
一、君权与相权
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是汉唐三省六部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而侵夺相权,是唐朝的国策,早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如此,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设置就是证据。唐初开国立制,三省长官不轻易授人,即便少量元老重臣担任此职,也都是虚衔,同中书门下三品才是职事官。这一制度的正面意义,是有利于提拔青年官员;其负面意义,则是削减相权,强化君权。唐玄宗设立翰林学士,是相权进一步弱化的信号。但玄宗时期的翰林学士还只是词臣,没有参政权,更没有决策权,看看李白就可以知道。自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翰林学士陆贽从驾幸奉天,一封罪己诏耸动天下,翰林学士的职权,才正式扩展到草诏权乃至决策权。皇帝私人秘书取代了中书省的法定权力,乃至被称为“内相”,可知位高而权重。侵夺相权,唐德宗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韩愈对德宗的批评,主要就集中在权力侵夺上。
《原道》:“君者,出令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是孔子倡导的政治观念。韩愈的提法,绝不仅仅是对孔子说法的简单重复。“君者,出令者也”,似乎有尊君的倾向。“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则是对君权的限定规范了。对韩愈的上述说法,严复《辟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此后,韩愈之说被诠释为尊君抑民、尊君仇民、尊君诛民,批判的火力一天比一天猛烈。章士钊《辟韩余论》总结严复以下的辟韩态势:“自前清末造侯官严复着论辟韩退之在思想上千年不倒之垄断地位开始动荡。以至公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韩之《原道》诛民学说,形成冰与炭之不能两存。”[1]“尊君”即是鼓吹专制独裁,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韩愈思想中有非常浓厚的“忠君”乃至“尊君”倾向,这一点恐怕无可讳言。最为今人诟病的,是他的愚忠。《潮州刺史谢上表》“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拘幽操》“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尤其令人恶心。但在家天下的封建时期,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应该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韩愈个人。除此之外,韩愈“君者,出令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的说法,至少还有四点含义值得注意:其一,对君权合法性、合理性的思考;其二,强化中央集权;其三,用社会职责规范君权;其四,为君权设定限界。
在严复之后对韩愈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中,也有少量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闿生《古文范》:“专制之世,视君王若帝天,神圣不可犯。而此文独曰:‘君者出令者也’,又曰:‘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则固具有共和之真精神,而毫不带专制时代臣下谄佞之臭味,则韩公之识实已敻绝千古矣。”[2]伦按:“君者出令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透露出韩愈对君权合法性、合理性的思考。在此之前,“君权神授”,君主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韩愈有《对禹问》一篇,柳宗元有《舜禹之事》一篇,就舜、禹传贤、传子的是非得失进行讨论。无论韩、柳本人的结论是什么,也无论这场讨论的背景是什么,问题的提出,就意味着对君权合理性以及君权合法性的质疑。当秦始皇津津乐道于“受命于天”的时候,当汉高祖洋洋自得于“吾业所就孰与仲多”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于对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韩、柳以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态度对君权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严肃的理论思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尊君”意味着强化中央集权,但集权与专制并不是同一个逻辑层面上的东西。集权、分权是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而言,专制、民主是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制衡而言。实际上,韩愈的“尊君”,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唐藩镇割据的现状而发,目的是宣扬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所谓“臣不行君之令”,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对抗中央的两河藩镇,包括此前的安禄山、史思明、仆固怀恩、李怀光以及此后的吴元济、梁崇义、陈少游、刘辟、李锜等。至于指责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是没有根据的。在韩愈的心目中,“利民”高于“利国”,已见上文;孔子高于尧舜、孟子功不在禹下,详见下文。即便是封建时期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君权,韩愈也敢于问难。所以,断言韩愈此说“完全是一种专制政策”,是“君权绝对论”,是“尊君抑民之说”[3-5],应该是一个误解。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其性质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独裁政体形成于赵宋,强化于朱明,这是史学界的共识。指责韩愈鼓吹专制独裁,是违背常识的。
“君者出令者也”,还可以看作是用社会职责来规范君权。从现代学术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人类社会职业的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无论千百年以后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劳动者与管理者的社会分工与地位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君”作为社会的最高监管者,发号施令是他的职权,也是他的责任。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最乐于接受的管理方式,是暗箱操作。口含天宪,朕即国家,何等的自由!明确君主的职责,事实上就是一种约束,一种限制,一种规范。那么在韩愈看来,君主的职责是什么?维护国家政令的统一是君主的职责。然而中唐时期,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从肃宗、代宗到德宗,但务姑息,政令不通,这算不算“失其所以为君”?维护民族文化传统是君主的职责。然而有唐一代,君主不是佞佛,就是崇道,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道统衰微不振,这算不算“失其所以为君”?寒为之衣,饥为之食,保障百姓的相生相养之道是君主的职责。然而中唐时期,军阀战乱不息,百姓流离失所,这算不算“失其所以为君”?举贤任能,除奸远佞,是君主的职责。然而中唐时期,李辅国、鱼朝恩之类阉宦势倾朝野,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韦渠牟之类聚敛之臣大行其道,而刘晏、陆贽等贤臣却难免惨死,这算不算“失其所以为君”?
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不在君主的职权范围之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具体的行政管理不在君权之内。君主正如运动场上的裁判,是不能参与场上竞争的。如果回到《原道》一文的创作年代德宗末年,就可以发现,上述对君权的限制绝非无的放矢。德宗侵夺相权,史不绝书。《子产不毁乡校颂》“有君无臣”,就是公开指责德宗“不君”。《顺宗实录》卷一:“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因缘用事。”《顺宗实录》卷四:“德宗在位久,益自揽持机柄,亲治细事,失君人大体,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职。”《旧唐书·韦渠牟传》:“陆贽免相后,上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唐代君主直接侵夺相权,武则天、唐玄宗已开其端,但规模化、制度化,应该是从德宗开始。除了亲自上阵侵夺相权之外,通过神策中尉控制军队,通过枢密使控制南衙,通过内使诸司控制百司,通过由翰林使控制翰林院,德宗的权力专制是空前的。从这一意义上讲,韩愈对君权进行规范,更值得高度重视。
君主享有“出令”的特权,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义务。韩愈在为君权设立规范的同时,也为君权设定了限界,逾越这一限界,也就是“失其所以为君”。很明显,在韩愈的思想体系中,这一限界只能是“仁义之道”。在韩愈的笔下,“失其所以为君”者,有桀、纣、周穆王、汉明帝、梁武帝以及宋、齐、梁、陈、元魏诸帝,重点则为秦皇、汉武。《杂说二》:“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这里的“纪纲”,也就是“仁义之道”。《毛颖传》谓“秦真少恩哉”,也是据此立论。《谢自然诗》:“余闻古夏后,象物知神奸。山林民可入,魍魉莫逢旃。逶迤不复振,后世恣欺谩。幽明纷杂乱,人鬼更相残。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秦皇、汉武违背了人类“自信”“知识”的理性原则,笃信鬼神,妄求长生,结果只能是“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对当代君主,韩愈虽然不敢正面指斥,却也没有轻轻放过。《顺宗实录》对德宗的昏庸贪婪一一如实记录,其书“说禁中事太切直”,“穆宗、文宗两朝累诏史官改修”,就是明确的证据。至于宪宗皇帝,其雄才大略,韩愈固然歌颂备至;但谏迎佛骨,义正词严;揭发阉宦,指斥苍天,丝毫不假辞色。
韩愈所说的“失其所以为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君”(《万章下》)。然而对于“失其所以为君”者应该如何处置,韩愈只隐晦地说了“则诛”,没有作任何具体交代。和孟子的“放桀”“伐纣”“诛一夫”“易位”“变置”相比,似乎是大有不如。不过应该注意到:孟子所在的时代是诸侯分立平等竞争的时代,韩愈所在的时代是天下一统君主专制的时代。“放”“伐”“诛”“易位”“变置”在孟子的时代是一个选择性答案,不一定直接刺激眼前的这一位君主;在韩愈的时代就是唯一的答案,其性质属于大逆不道。所以,指责韩愈“君主失职仅仅失其所以为君,可以不承担任何罪责”[6],这“仅仅”二字,未免轻率。实际上,“失其所以为君”绝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场面话,被悬置起来的潜台词具有什么样的分量,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对当事人而言,“失其所以为君”,恐怕不下于晴空霹雳、生死判决。一封《论佛骨表》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就是明证。韩愈敢于逆披龙鳞,其胆识、意义不可低估。
二、集权与分权
集权、分权,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不存在争议的,自孔子提出大一统之后,秦汉以下历代统治者奉集权为至宝,没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实际上,地方政府本来就应该享有自己的权力;二者的权力分配,本来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机制。事实上,地方政府固然免不了私下与中央讨价还价,但在台面上,却没人敢公开发出声音,更不用说在理论上理直气壮地申说阐述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拥护中央集权的声音,听不见支持地方分权的声音,韩愈也不能例外。
在中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主要表现为朝廷对藩镇尤其是两河藩镇的讨伐与放免。在朝廷内部,主张讨伐称为用兵,主张放免称为消兵;前者被视为维护大一统,后者被视为姑息;用兵的主张大多出自贵族,消兵的主张大多出自庶族;前者大多数属李党,后者大多属牛党。不过,该用兵还是消兵,因时因势,不可以一概而论。简单地视用兵为维护大一统,消兵为姑息,也是不正确的。以元和元年(806)平定西蜀刘辟而言,其实就大有可议。实际上,首先提出都领三川的并不是刘辟,而是刘辟前任韦皋。韦皋自贞元元年(785)领剑南西川节度使,镇蜀20余年,并无不臣之迹。当时以西蜀独当吐蕃、南诏数十万兵马,确实力不从心。所以韦皋请求都领三川,并非不可理解。事实上,此后南宋川陕四路时分时合,均视战场形势而定。元代建置行省,也是势所必然。从这一角度考虑,都领三川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藩镇跋扈不臣,主要集中在两河尤其是河北,川蜀并没有背叛的先例和传统。所以事发之后,大臣多主张消兵,唯杜黄裳主张用兵,其理由不在是非而在利弊,“刘辟一狂蹶书生耳,王师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旧唐书·杜黄裳传》)。用兵成功,杜黄裳的主张光耀史册,消兵的主张,在史书上就自然湮灭了。在这个问题上,韩愈因时而变,没有固执的主张。平定西蜀,他主张用兵,主要是考虑到“疆内之险,莫过蜀土”,蜀中有变,势成心腹之患。再加上“遂劫东川,遂据城阻”,刘辟展开军事行动,事情的性质就变了。都领三川可以讨价还价,攻占东川就属于反叛了。淮西一战,从元和十年(815)上《论淮西事宜状》,作《与鄂州柳公绰中丞书》《再答柳中丞书》,到元和十二年(817)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从裴度平蔡,最后到战斗结束进《平淮西碑》,韩愈都是主要的发动者、参与者。淮西的位置介于河洛、江淮之间,一旦梗阻,确为心腹大患。韩愈的用兵主张,因势因时,合情合理。
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韩愈也有过消兵的主张。元和十五年(820)秋冬之间上《黄家贼事宜状》,主张容贷羇縻,是因为主战者裴行立、阳旻“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导致“邕容两管因此凋弊,杀伤疾疫,十室九空”。长庆二年(822)宣抚镇州,是因为河北自安史乱后,长期自立,服叛无常。加上当时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南北联手,势成燎原。为打破叛镇联手对抗中央的态势,劝降镇州,势在必行。所以,韩愈主张用兵或消兵,确实是因时因势,绝无党同伐异之嫌。更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英国人从百年战争、光荣革命中学会了妥协与谈判,从而引导欧洲走上现代政治的道路。而中国人只认同大一统,只知道“平定藩镇”“平定叛乱”。从这个角度出发,韩愈主张消兵,并深入虎穴,尝试妥协、谈判,或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三、暴力与非暴力
现代政治理论体系中,不管存在多少争议,非暴力主义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派理论主张。在中国,1200年前的韩愈也有过类似的主张。
《元和圣德诗》描写刘辟与其子临刑就戮之状,残酷惨烈,后人颇多非议。或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除了金刚手段之外,韩愈也不缺乏菩萨心肠。实际上,韩愈以博爱之仁作为心性本体,以仁政爱民作为施政方略,仁爱应该是韩愈思想的主流。“为之刑以除其强梗”,其目的仍然是社会的安定、民生的安乐。除此之外,韩愈还有着明确的反暴力主张,值得今人仔细玩味。
《岐山操》:“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绪,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将土我疆。民为我战,谁使死伤?彼岐有岨,我往独处。人莫余追,无思我悲。”周人居豳,至太王古公亶父,狄人来攻。太王不忍百姓为自己而战而死而伤,主动退出,迁往岐山。不为保江山而使用暴力,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使用暴力?
《伯夷颂》:“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率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武王、周公,儒家以为大圣人;武王伐纣,孟子以为“诛一夫”。而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商纣暴虐,殷商当亡,伯夷、叔齐对此并无异议。武王、周公哀民若伤,伯夷、叔齐对之并无异议。伯夷、叔齐所反对的,是“以暴易暴”。韩愈此篇之所以“不顾人之是非”力挺伯夷、叔齐,所支持的就是这非暴力主张。这就是说,即便是打天下,即便是武王、周公这样天下公认的大圣人,讨伐天下公认的大暴君商纣,“以暴易暴”也是不行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使用暴力?
《衢州徐偃王庙碑》:“徐与秦俱出栢翳,为嬴姓。国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偾其国而沈其宗。徐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周天子穆王无道,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全篇以秦、徐对比:秦专用武胜,得以统一天下;徐专行仁义,终以失国。秦以惨烈,二世而亡,宗族灭绝;徐以仁厚,子孙繁衍,人才辈出。秦以暴虐,宗庙隳坏,社稷丧亡,祖宗不得血食;徐以善待其民,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且凿石为室以祠,世世不替。秦杰以颠,徐由逊绵;秦鬼久饥,徐有庙存。最后的结论是:“天于栢翳之绪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韩愈宁可认同“诸侯作而战伐日行”但“纪纲存焉”的“夏、殷、周”之末世,以及“不忍斗其民”而“走死失国”的徐偃王,也不认同以暴力统一天下而“纪纲亡焉”的秦始皇(《杂说》)。在藩镇割据、政令不通的中唐政治舞台上,韩愈主张大一统,要求维护中央政府的政令统一。不过,韩愈所主张的大一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纪纲”,也就是仁义之道。韩愈的非暴力主张,其理论基础就是仁义之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中,儒家主张以德服人,法家主张以力服人。韩愈的非暴力主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四、道统与治统
道统与治统,其实质是朝廷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分割。《原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道统的担当者,自周公而上,其身份为君主;自周公而下,其身份为臣下。周公本人虽然不是君主,但实际执掌政权,其身份介于君臣之间。道统担当者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道统性质与内涵的变化。“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道统的重心,在内圣与外王,亦即“道”与“教”。后人构建的道统体系,如侧重文武周公,其着眼点必在“教”;如侧重周公孔孟,其着眼点必在“道”。钱穆先生曾经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差别,其《周程朱子学脉论》云:“汉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求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历代先王祀统,早在先秦即已初步定型。《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着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自尧舜禹到商汤文武的祀统,唐初也已经确立。《旧唐书·礼仪四》:“显庆二年六月,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曰:请案《礼记·祭法》云:‘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尧舜禹汤文武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凖此,帝王合与日月同例,常加祭享。”以周、孔、孟子尤其是孟子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则为韩愈首发。韩愈构建的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下延至周、孔、孟子,有两大意义值得重视:其一,内圣与外王兼重;其二,学统与治统分立。
道统代表民族国家的法统,但君主并不是道统当然的担当者、守护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就意味着:周公以前,即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时代,道统的担当者是君主;从周公开始,下及孔子、孟子,道统的担当者不再是君主,而是士人。也就是说,体现民族文化传统的道统已经与体现现实政治权力的治统分离。
道统既然早与治统分离,那么,二者的关系又该如何呢?《处州孔子庙碑》记孔子祀典:“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由此断定“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尧舜之贤尚且不如孔子,治统岂能高于道统?相反,治统的合法性只能源于道统。说得更明白一点,道统应该高于治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二十四史多至二十四部,而中国仍然是这个中国,就是明确的证据。韩愈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来自孟子。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主张对“不君”的君主实行“易位”(《万章下》),甚而至于“诛”(《梁惠王下》),就是韩愈此说的先声。以士人作为道统的担当者,庄子的“玄圣”“素王”(《庄子·天道篇》)已开其端,汉儒则径称孔子为“素王”(《论衡·超奇篇》)。韩愈的思想上接孔、孟,与荀子专重“后王”即当代君主完全不同。
道统与治统的分离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道统的传承世世不绝,具有永恒性。对于民族国家,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不会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发生变化。其二,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后代的君主要使自己的政权具有合法性,就必须遵循民族国家的法统也就是道统。换言之,君权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合法有效[注]关于君权有限合法的思想,参见邓小军《唐代的中国文化宣言》,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4期,第62页。。其三,道统为士人提供了人格独立的依托、精神皈依的家园,在这一意义上,道统已经具有终极关怀的高度。从此以后,人不再是社会的附庸,而是社会的主人。因为他效忠的顶点,是内在的道统,而不是外在的朝廷与君主,相反,君主也必须服从道统。韩愈之所以高度推崇伯夷、徐偃王,原因就在这里。
韩愈的这一思想产生于安史之乱以后面临亡国危机的中唐时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领会得最深刻的往往是同样身处危局的末代士人。比如,文天祥在宋亡之后就面临这样的诱惑:“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最终的回答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宋史·文天祥传》)这样的忠诚,已经超越了一家一姓的局限,达到了民族国家的高度,仁义之道的高度。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不得不思考同一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近代学人中,梁济、王国维、陈寅恪,才不愧为儒学道统的担当者、守护人。士人们开始从屈原式的忠诚模式中逐步解脱出来,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将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价值置于一家一姓的政权之上,体现了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与终极关怀的时代高度。
在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内,古典政治学致力于研究政府治理的手段,描述政府运作的情况,对国家概念进行界定,并设计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现代西方政治学一方面注重对国家机构、权力、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注意考察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将政治人的行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韩愈从君、臣、民之间权力分割的角度理解中唐时期的政治文化,所涉及的君权与相权、集权与分权、暴力与非暴力、道统与治统等问题,既包含对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考察,也包含对政治人的行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的思考。其思想高度及理论价值,还需要后人认真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