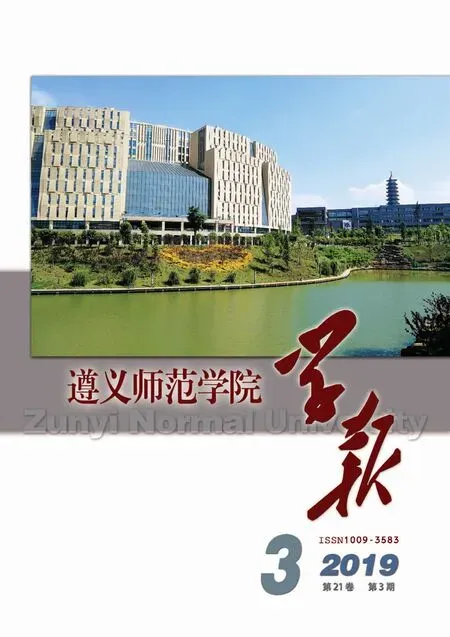“十诠”之法与冯复京诗歌创作论
丁远芳
(a.安庆广播电视大学,安徽安庆 246003;b.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冯复京(1573-1622),字嗣宗,江苏常熟人,明代后期的诗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出生文士世家的冯复京育有三子:冯舒、冯班、冯知十,其中冯舒、冯班并称“二冯先生”“海虞二冯”,是清初虞山派的代表人物。
冯复京生性倜傥洒脱,放荡不羁,钱谦益有“形容清古,风止诡越,翘身曳步,轩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1]之语称益之;一生博闻强记、勤于思考、敏于著述,其钻研著作涉及诗经、礼教、史学、小说、音乐、诗赋以及诗歌理论等多方面。现据《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艺文志》所载,整理如下:《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存,有焦竑作序,四库全书总目误为冯应京;《说诗谱》四卷,已佚;《遵制家礼》四卷,存;《明常熟先贤事略》十六卷,现存;《明右史略》三十卷,现存;《蟭螟集》十四卷,《海虞艺文目录》称毛扆汲古阁书目抄本记载有珍藏秘本;《冯氏族谱》四卷,存;《常熟县儒学志》八卷,存;《说诗补遗》八卷,存,卷末有冯舒、冯班跋,冯舒天启三年(1623)跋文谓本书成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此书系作者精心用意,以“一生目力”写成,完成后又谓“前所著尽,颇亦未尽。汉魏六朝,无所憾矣;初盛两期,自谓精确;所恨者中晚之间,立言未真耳。”临终还嘱咐子辈“不得忝则”,是冯复京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另外,冯复京现存诗赋碑文收于《海虞文徵》。
一、冯复京与“十诠”之法
冯复京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代诗学思想激荡变幻的时期,后七子尚活跃于诗坛,而公安派的影响也正逐渐扩大,诗学思潮百家争鸣。身处后七子与公安派诗学思潮争论之中,冯复京对二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多有不满,加上自身于诗学用力甚勤,治学严谨,遍观历代之诗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博综众家之学说,熔铸于心,精心用意写成了其诗学论著《说诗补遗》。作为“新一代之耳目”,冯复京感于“凡今之人,守琅琊之卮言,尊新宁之品汇,羽北海之诗纪,信济南之删选,谓子美没而天下无诗”之论,于是“历观唐人诸集”兼及汉魏六朝之作,以辨体辨格入手,“用一生目力”,从诗歌的本质、流变、审美、创作等方面详细论述,成《说诗补遗》。全书共八卷,卷一总论诗体、诗格、诗思、诗韵、诗病等方面,卷二至卷八以诗歌史的形式论按时代论述,其中卷二至卷四论唐以前之诗,卷五至卷八论唐诗。通过对历代诗歌具体分析,冯复京指出一代有一代之诗,不必法汉魏,宗盛唐,鄙薄齐梁陈隋,对前代之作,不必句字摹拟,从而否定了七子诗有定格、句字摹拟的论调。他认为唯有独创而不摹拟,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才可以动天地,感鬼神,震心魄,骇耳目。
冯复京《说诗补遗》从第五则到第三七则在辨析各体诗歌源流的基础上,对各体诗歌的创作规律也进行了总结。冯复京把诗歌的创作活动理论化地概括为十大要点,即“十诠”之法。
诗有恒体,予既备著之矣。神用之妙,可得而诠。一曰达才,二曰构意,三曰澄神,四曰会趣,五曰标韵,六曰植骨,七曰练气,八曰和声,九曰芳味,十曰藻饰。(《说诗补遗》第三八条)[2]P3841。
“十诠”之法涉及诗歌创作的多个方面:即创作主体修养的“达才”“练气”;诗歌创作构思的“构意”“澄神”;诗歌审美的“会趣”“芳味”;诗歌韵律要求的“标韵”“和声”;诗歌语言文辞要求的“植骨”“藻饰”。
二、“十诠”之法与诗歌创作
冯复京的“达才”“构意”“澄神”“会趣”“标韵”“植骨”“练气”“和声”“芳味”“藻饰”主要涉及诗歌创作的主体素质、艺术构思、诗歌声律、诗歌语言文辞以及诗歌审美风范五个方面,下文分述之:
(一)“才”“气”兼备的创作主体素质
“十诠”之法对创作主体提出“达才”和“练气”两点要求。所谓“达才”即“尽己之才”,而“达才”的基础是“有才”,惟“有才”方能“达才”,因此冯复京对创作主体的知识积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博学多闻以积“后天之才”。“练气”侧重于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培养,他所说的“气”实则孟子之“浩然正气”,自魏晋以降,诗论者对此多有论述,冯复京在此加以重新阐释。
1.“才”与“学”——博学多闻的知识储备
冯复京主张诗人应该多积累、多读书,博学多闻,以丰富的才学来矫正捻须苦吟的创作方法和粗俗鄙陋的诗风,追求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
冯复京对于当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谈学风甚为不满。《说诗补遗》第二则提到:“灵趣雄才,得自天授。精思妙诣,必以学求。然天授之奇者,不可以不学,学力之至者,未必不可以胜天也。”冯复京对当时浮游空疏学风的批判大胆而深刻,他告诫子辈们要多读书,对有疑惑的问题要自己求证,不要被已有的成见所误导:“王李李何,非知读书者,吾向为所欺,汝辈不得忝则,凡言王李者,读者其详之”。“夫博综者,文章之户牖。精釜者,人物之权衡。故弥纶折衷,当穷千古之闻见,而不可矜一察之闻见也。当求此心之是非,而不可徇前人之是非也。”冯复京晚年著述《说诗补遗》一书时常常手不释卷,还常和子辈冯舒等讨论评价历代诗人,直至去世前还研读《薛能集》,其潜心学术,用心钻研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为了能“新天下之闻见”,冯复京对历代诗歌都进行了仔细研究,不循前人之成见,真正做到了求“此心之是非”的批评原则。对历代优秀作品的学习,冯复京继承了宋代严羽的“熟参”的思想。冯复京说:“梁陈浮淫,其韵俗,中唐空踈,其韵浅,试取熟参,当自超悟。”要求诗人通过“熟参”众制,有所突破性的领悟,进而确立优秀的诗歌典范。
2.“才”与“体”——量才适体
冯复京于前文中提出将“才”与“学”结合起来,要求创作主体博闻强识,系统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同时,“达才”亦有“才”尽体用之意,即选择最为擅长之诗歌体式,将个人创作上的特点和才能融入诗歌中去:
一曰达才者,予向云凡为其体,须以某为正宗,以何为极则,此标的之大凡也。……能此体,正不必兼彼体。工我法,正不必用他法。试以古作者评之,枚李以古诗鸣,沈宋以近体著,陈思之清绮不为魏武之莽苍,杜陵之浑融,不效东山之飘逸。然而名家各擅,何必具体大成哉。[2]P7173
因各人的先天条件不同,故而后天的努力学习尤其重要。“达才”不仅要养“才”,更要“适”才。后天的学习实践中,因各人知识储备和性情涵养的差异,故而所擅长的诗歌体式不尽相同,所展现的诗歌风格也大相径庭。选择最为适合创作的“体”,亦成为“达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点上恰恰体现了冯复京细致入微之处。
3.“才”与“气”——主体精神气质培养
“练气”,即侧重于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培养。冯复京主张创作者必须要“练气”,也即是养气,他所说的“气”实则孟子之“浩然正气”。作为善于养气的创作者要“必留有余,无使困乏,主畅遂无至郁,淤循检格,无流淫放。休天钧,无伤儁逸。澄神思,无陷流俗。砺锋颖,无堕卑陬,斯可注满于喷玉之中,环周于贯珠之内矣。”[2]P7176“气”对文学评论和批评鉴赏十分重要,创作者只有培养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气势,才能尽力施展才华,创作出风格气势俱佳的作品。
(二)“意”“神”俱凝的艺术创作构思
陆机《文赋》早有构思想象特点的分析,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亦有相关论述。相对而言,冯复京对创作构思阶段的理解更加细致,即把构思阶段分为“构意”和“澄神”。冯复京所言之“构意”与历代论述大致相当:“文术万变,思路一揆。近取衿带之前,冥搜象系之外,兴来神答,则濡翰联翩。理伏景幽,则含毫渺默。”[2]P7174此处形容构意的思维特点与《文赋》、《神思》大致相同,然冯复京又有新的创见,即将“构意”分为不同层面,指出“意远者,格必高。意醇者,体必正,意壮者,气必雄。意精者,词必简”。[2]P7174而相反,“意烦则乱,意尽则贫。……意深则隐,意浮则散。”[2]P7174冯复京所言之“意”即艺术创作构思中思维想象,诗歌作品“格高”“体正”“意壮”“气雄”“词简”与艺术构思之“意”之“远”“醇”“壮”“精”密切相关,将艺术创作构意与诗歌艺术造诣紧密结合起来。
“构意”后并不立刻进行创作,要使主体的心绪进入一种不可言说的澄明之境,即“澄神”阶段:“无象可求,无方可执,造化不能秘,鬼神不能思”。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冯复京认为必须要“必澡雪灵台,涵濡学府,内不烦黩以损和,外不纆牵以萦惑。天机洞启,真宰默酬,从容于矩矱之中,邂逅于旦暮之际,庶几乎罄澄心妙万物者也。”如此之后,创作者的构思阶段才算完成,为接下来组织语言、表情达意做好准备工作。
(三)“声”“韵”相和的诗歌韵律要求
冯复京总论诗道,唯“格律、才情”二者,将诗体格律形式要求与创作主体的才情看作是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部分。
“学诗之始,先辨体式”,这种强烈的诗歌辨体意识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即谨遵诗歌体式要求:“《虞书》曰:‘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裔是而降,夏歌浩衍,商颂沈深,国风优柔,雅颂典则,有不循轨度者无有哉。”冯复京援引《尚书》之言,强调诗歌创作应循“轨度”而行,“犹制器,至圆不加于规,至方不加于矩。”冯复京对声律的要求十分严格,以声辨体,于《说诗补遗》第六四提倡“古体用古韵,惟取谐合”古体诗必须用古韵,“若拘沈约之四声,反落唐格近体,用唐韵贵在紧严,若越礼部之一字,即成宋体。”由此可见,每一种诗歌体式都在用韵上有不同的要求:古体诗、唐格近体诗、宋诗用韵的不同,若不严加辨析,一字越韵即成别体。不仅如此,各体诗歌用韵还得注意基本准则,即“用古韵不宜过奇,奇则陷于鴃舌。用唐韵不宜过巧,巧则流入诙谐。排律百韵不已,则唇吻告劳,歌行两韵则迁,则转折多踬。”
诗歌用韵,自成定式,一首诗歌“全在音节、格调,风神尽具音节中”。冯复京以为古人为诗,心中必有“金石”之音韵,具体说来又有个体、时代的差异性:
诗之有韵亦犹是耳。汉风韵藏于意表,魏制韵溢于格中,嗣宗之韵冲旷,太冲之韵孤高,渊明之韵自然,灵运之韵清远,子美之韵沉深而有味,太白之韵飘举而欲仙,王孟之韵闲淡而绝尘,高岑之韵秀令而近雅,靡不旨趣无穷,芬芳可佩,作者虽已会,众条必待斯成品矣。梁陈浮淫,其韵俗,中唐空踈,其韵浅。[2]P3843
不同时代诗人在遵循基本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之时,因时代风气以及诗人性情等个体因素不同而表现不同的风格,这是客观存在的。若片面拘泥于声律而忽视创作主体用韵的风格差异,谨奉“四声八病”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则亦不可为。显然,冯复京已经意识到“诗多拘忌”之弊,故而援引钟嵘、皎然以及本朝王世贞、胡应麟诸人“辨失”之论,认为声律之法“宜加检括”,认为诗歌创作应以“和声”为目的,不应以音律限制作者“神思”,最终达到“试取熟参,当自超悟”的境界。
(四)“植骨”“藻饰”的语言文辞要求
在诗歌语言方面,冯复京提出了“植骨”“藻饰”。“骨”,最早来自魏晋对人物的评议品鉴,后被引入诗歌批评之中,《文心雕龙·风骨》即有:“《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此处之“风”,一般指诗歌中表现出的充实、感人的情志力量,以创作主体的“意气骏爽”为前提,其基本特征是清、明;而“骨”,则意谓文章在语言表现上呈现的刚健风格。至于诗文的“藻饰”,刘勰亦有“若风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4]P1052-1064《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冯复京对于古诗的古雅质朴十分赞赏,但是在“质”与“文”的辩证分析上,他还是明确提出不可盲目追求质朴而堕于鄙陋。《说诗补遗》第一四一则云:“古诗甚质,然太羹玄酒之质,非槁木朽株之质也;古诗甚文,然云汉为章之文,非女工纂俎之文也。”鉴于初学者的特殊写作基础,冯复京告诫:“字句与其浮响倒装,不如沈实平正。与其学杜陵之苍老危仄,不如学王李之风华秀朗。与其为大历之清空文弱,不如为景龙之缛蒤丰腴。”[2]P3836
可见,冯复京吸收了刘勰对风骨和藻采的辩证认识的基础上,注重创作过程中诗歌语言要素,把“植骨”和“藻饰”并提,为的也是防止偏重其中一方面而导致失衡,最终实现其理想的诗歌范式。
(五)“趣”“味”相投的诗歌审美风范
在诗歌审美上,冯复京特别提出了“味”和“趣”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他认为优秀的诗歌必然要“会趣”、有“芳味”。这是“十诠”之法的要求,实际上,冯复京对诗歌创作实践的要求并不限于此,他还提出了“中正”“含蓄”的审美要求。
“趣”在明代诗歌审美范畴中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冯复京把“趣”和骨气神韵才力看得同等重要,他认为“趣”是诗歌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由是章句栉比,听真宰以就班;音调铿锵,循天钧而赴节。骨气神韵,趣味才力,则主张旋运於章句音调之中,以赞成厥美者焉。”[2]P7163冯复京强调的“趣”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诗歌审美的方面:“盖诗以道性情,性情所向,涉则成趣。上溯汉魏,下迄盛唐,善鸣诸家,莫不以兴趣为主。”[2]P7175冯复京认为“趣”的生成来源乃是“性情”,“趣”是情感注入的产物,是性情的呈现,属于主体层面的范畴,是审美修养和审美追求的产物。《说诗补遗》第二云:“灵趣雄才,得自天授。精思妙诣,必以学求。然天授之奇者,不可以不学,学力之至者,未必不可以胜天也。”第七三则又道:“非沉思曲换,去故就新,天趣横生,高唱郁起,而可以成家者,未之有也。”可见,“趣”是审美主体的天赋,是主体天赋生机灵动的体现,而“灵趣”则具有自然天成、不可强求、生机灵动的特质。因此,生机、灵机、天真直露乃得趣之要。
冯复京将“芳”的嗅觉感受与“味”觉感受联系在一起,提出“芳味”说:“氤氲郁烈,嗅之触鼻者芳也;醰粹丰腴,尝之隽永者味也。然辟芷幽兰,岂曰不芳,太羹玄酒,岂曰无味,又芳而无味,则山泽之癯瘦,味而不芳,则河朔之羶肥矣。”要求诗歌既能呈现出浓烈芬芳的嗅觉美感又要给人以丰腴隽永的味觉美感,在诗歌审美层面上将各种感官的深层体验直接纳入诗歌的品阅之中。一首诗歌的内蕴千姿百态,理趣韵致也是变化万千,但好的诗歌必须要有内在的活力生趣、情理韵致。冯复京所说的“芳味”正是诗歌内在的活力生趣、情理韵致的审美风范。
三、结语
冯复京的“达才”“构意”“澄神”“会趣”“标韵”“植骨”“练气”“和声”“芳味”“藻饰”之诗歌创作“十诠”之法,是其诗学理论著作《说诗补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复京在系统地梳理汉魏六朝以及唐代诗歌发展流变史的基础上,饱读历代诗歌,以辨析诗歌体格入手,从诗歌本质论、流变论、审美论、创作论等方面建构诗学理论,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十诠”之法。
“十诠”之法虽为诗歌创作而论,然其举要则涉及诗歌创作的主体素质、艺术构思、诗歌声律、诗歌语言文辞以及诗歌审美风范等多个方面:诗歌创作主体应该多积累、多读书,博学多闻,以丰富的才学来矫正捻须苦吟的创作方法和粗俗鄙陋的诗风,还应“量才适体”以各人之知识储备和性情涵养的差异选择最为擅长的诗歌体式,同时亦要培养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气势,创作出风格气势俱佳的作品;在艺术创作构思上,注重“构意”和“澄神”,使主体的心绪进入一种不可言说的澄明之境,为接下来组织语言、表情达意做好准备工作;在诗歌声韵要求上,一方面严格要求创作者遵循诗歌韵律法则,同时亦注重诗歌用韵的各体和时代差异性,要求不应以音律限制作者“神思”,应当“试取熟参,当自超悟”;在诗歌语言方面,冯复京吸收了刘勰对风骨和藻采的理论观点,注重创作过程中诗歌语言要素,把“植骨”和“藻饰”;而在诗歌品读审美接受上,冯复京以“会趣”“芳味”论之,要求诗歌既要呈现浓烈芬芳的嗅觉美感又要给人以丰腴隽永的味觉美感,在诗歌审美层面上将各种感官的深层体验直接纳入诗歌的品阅之中,“趣”“味”执着,正是冯复京追求的自然天成与内在的活力生趣、情理韵致相统一的诗歌审美风范。
就一般文人而言,其创作自觉地将个体生命价值与外在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5],作为一介布衣文士,冯复京一生仕途坎坷。然其出生文学世家,一生博闻强记、勤于思考、敏于著述,其学术视野相对开阔。冯复京主要活动于明代万历年间,其诗学思想受七子派影响较深,但是冯复京能够做到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冯复京在认识到了七子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不足的基础上,严厉批评其遗风流韵种种弊端,并积极探索,在前人优秀创作传统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批评,提出诗歌创作的“十诠”之法。“十诠”之法,是冯复京诗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明代诗学理论史不可忽视的一环,对梳理明代诗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