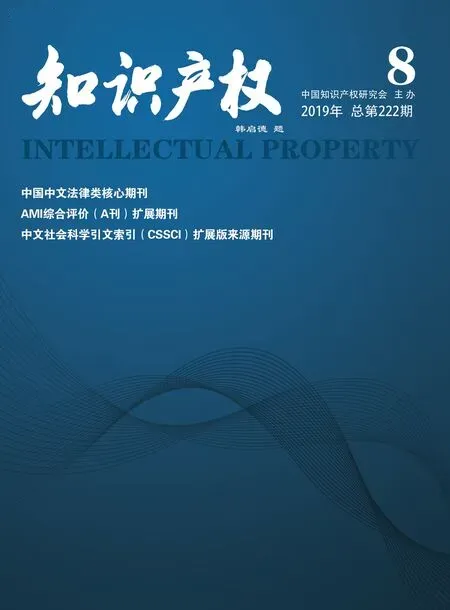知识产权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余 俊
内容提要: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被卷入了世界现代性的历史大潮,由此开启了我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法制现代性转型的艰难历程,即推动我国传统社会向着以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的现代社会变迁,推动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固有法统完成现代性法权制度及其义理价值的塑造。这就决定了作为非中华固有之制的知识产权法制,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基本同步,它从一开始就被现代性的表达与实践裹挟其中。在知识引进的大潮下,知识产权在观念启蒙、概念传播和制度移植等方面完成了文化基层建构,其目的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撑,自上而下地把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植入中国社会,以创设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新的生产、生活和法治秩序,从而演绎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生动实践。
引 言
一百七十余年前,“破门而入”的西方人,触发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李鸿章:《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国被迫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轨道。由此决定了,一百七十余年来,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最根本的是一个现代性建构的艰难历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以现代性核心价值(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等)为支撑,以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等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历史性巨变。②金观涛著:《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6-25 页。这一转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局部到整体,涉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等方方面面,但千言万语,不外乎一个中国现代性秩序的建构与塑造。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经济在最近四十余年突然爆发,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经济的持续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自然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是一个跨越三个世纪,而至今尚未完成的方案。
知识产权制度是现代秩序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财产制度之一,是现代国家最基础的法权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义理价值体系之一。知识产权与现代性之间可谓玄黄不辨、水乳不分。虽然,关于现代性的起源问题,涌现了无数真知灼见,关于知识产权的历史探索,也不乏大量著述论点。但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围绕知识产权,聚焦中国历史,追根溯源二者最初联系的研究,仍是一个有待发掘并精耕细作的领域。鉴此,本文希望回到中国与现代性相遇的最初原点,沿循知识产权进入中国的内在逻辑,尝试揭明二者之间的隐秘勾连,冀能还原历史与秩序的本来面貌。
一、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传统法制的变革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签订城下之盟。从此,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现代性的历史大潮,中国社会被推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发展轨道,成为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如果说,在明清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思想一直处在自我完足的状态中,那么,在明清以来,中国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它思想与学术的‘自给自足’,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已经融入了世界思想与学术的知识背景中,或者说,世界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已经不由分说地进入了中国,而那个‘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而只是‘万国’格局中的‘清国’。”③葛兆光:《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载《读书》1999 年第4 期,第85-89 页。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也不能按照固有的节奏和方式前进。“破门而入”的西方人,打碎了延绵数千载的“中央之国”的盲目与自大,也改变了围绕这个“中国中心观”而绘制的世界图景,触发了“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④严复:《论世变之亟》,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 页。的千古“世变”。
这一“世变”,已不再是旧时的王朝更替,也不同于所谓的“华夷之辨”,而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强力冲撞下所面临的剧变与质变。“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而此一雪耻图强运动,分析到最后,则是一追求国家‘权力’与‘财富’的运动。”⑤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8- 9 页。
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与感召下,晚清的政治与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变法求强”应是当时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12 页。“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⑦严复:《救亡决论》,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40 页、第50 页。“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⑧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597 页。传统的“农本商末”的治国方针难以为继,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转移国策,应是必然之举。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向现代转型,已成历史大势。于是,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中西会通”,由表及里,以器入道,在不断探索发展路径的过程中,自觉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缓缓地向着现代社会变迁。
甲午战败,使精英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与法律传统必须改变。“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⑨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93 页。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自1840 年以来迄今所见的第一篇倡言中国应研究法学的论作”,参见李贵连:《中国近现代法学的百年历程》,载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7 页。要想构建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传统法制亟需完成“中国之现代性的法权制度及其义理价值的塑造”。⑩高全喜、张伟、田飞龙著:《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27-28 页。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二、知识产权话语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性的耦合
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⑪刘春田:《知识产权制度与中国的现代性》,载《法制日报》2012 年6 月6 日第9 版。知识产权法律以制度文明为支点,以私人利益为杠杆,成为现代国家最基础的法权制度之一。知识产权法价值以人类创造天性为本源,以市场经济秩序为依托,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义理价值体系之一。知识产权与现代文明之间可谓玄黄不辨、水乳不分。由此注定,在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法制同步向现代转型的大局驱动下,在清末有识之士发起的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中,知识产权法制凭着自身的独特优势自然就成了转移国策、改造法统的一个理想选择,也决定了知识产权与“老大帝国”的首次相遇便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话语体系。
1859年秋,洪仁玕在中国第一份现代化方案《资政新篇》中提出,“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若天国兴此技,……国内可保无虞,外国可通和好,利莫大焉。”专利制度自国人首次提出便进入了现代化的语境。1873年3月,郑观应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倡导:“如朝廷有示体恤商贾,任天下之人自造轮船,尤能制一奇巧之物,于国家有益者,则赏其顶戴,限其自造多少年数……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⑫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53 页。1892年,薛福成在日记中主张:“今中国务本之道,约有数端……如有能制新奇便用之物,给予凭单,优予赏赐,准独享利息若干年。”⑬薛福成著:《筹洋刍议——薛福成集》,徐素华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14 页。1898年6月,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列举了创新对欧美诸国致富致强的重要意义,并“乞下明诏奖励工艺,导以日新,令部臣议奖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寻发新地,启发新俗者”,以“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⑭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90 页。“保无虞”(内政)、“通和好”(外交)、“国家有益”“富民之道”“务本之道”“举国移风”,这些事关国家发展战略和现代转型的话语体系从一开始就把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表达卷入其中,使知识产权观念在中国的首次出现便与国策转移、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融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洪仁玕、郑观应、薛福成和康有为等早期先进之士对知识产权属性的把握还局限于政府所赏赐的一项特许公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解还停留在依靠官方的行政手段,对知识产权作用的认识还止步于器物文明,那么,汪康年、严复、孙宝瑄、江宝珩及陶保霖等人的论述则更加深入地揭示了知识产权作为制度文明的内在魅力,其认识不仅更为接近知识产权的制度本原,也更加契合知识产权的现代性特征。1896年12月,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先后发表《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商战论》,他在前文中提出,“今日之务,宜筹商人能自行之法,各业能自振之方……宜定专利之法,使创造者不致有徒费之虞。……苟行之数年,未有不见富庶之效者也。”⑮[清]汪康年著:《汪康年文集》(上册),汪林茂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29-30 页。他在后文中认为,“商之所利,货物美,资本轻,程途捷,行销广,四者而已。……不行激劝之法,不定专利之条,不严冒牌之禁,则货物不能美。”⑯[清]汪康年著:《汪康年文集》(上册),汪林茂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33 页。在此,他不仅开创性地将著作权法(“激劝之法”)、专利法(“专利之条”)、商标法(“冒牌之禁”)联系为一体,而且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使“商人自行”“各业自振”“使商人便利,使商人有权”⑰[清]汪康年著:《汪康年文集》(上册),汪林茂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34 页。,深刻地揭示了知识产权法的市场本位的属性。
1899年3月20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翻译刊登了发表于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的《论布版权制度于支那》一文,文中强调:“支那改良之策,其中最急者在以经世实用之智识,供给四万万人也。……盖版权制度者,供给智识之原动力所借以保护者也。”⑱《论布版权制度于支那》,载《清议报》1899 年第13 期。1902年,严复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书信中不仅强调著作权兴废与国家强弱贫富和国民文野愚智的关联,而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细数著作权对于创造者的重要意义:“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夫其国既借新著新译之书,而享先觉先知与夫输入文明之公利矣,则亦何忍没其劳苦,而夺版权之微酬乎?盖天下报施之不平,无逾此者。……今夫国之强弱贫富,纯视其民之文野愚智为转移,则甚矣版权废兴,非细故也。”⑲严复:《与张百熙书二封》,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577-578 页。1903年,孙宝瑄在日记中对清末以奖励为基础的专利制度提出了批评:“我国欲鼓励其民,每以给奖或赐匾额示宠异,不知皆虚名也。虚名之不足动人久矣,必如西国之许人专利,而后足发人之歆羡心也。”⑳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679 页。1908年,江宝珩(笔名侠庵)在其创办的《农工商报》发表《论专利与工艺发达之关系》㉑侠庵:《论专利与工艺发达之关系》,载《农工商报》1908 年第30 期。,毫不讳忌地从人的自私贪婪本性出发,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即治国之善法”,因此建议制定西洋专利之法,以满足“创造者之贪心”和“大众之贪心”。在起草著作权律的过程中,陶保霖在文章中围绕著作权法与出版法的异同,详解著作权的概念、性质、历史与正当性,指出“(著作权)非由政府之审查认定而生,乃因著作之事实而生。……为完全之财产权矣。……著作权法纯属保护个人私权者。”㉒陶保霖:《论著作权法出版法急宜编订颁行》,载《教育杂志》1910 年第4 期。此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也曾为清末著作权立法不惜笔墨,他在由其主编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版权通例》《版权之关系》㉓[美]林乐知译,范祎述:《版权通例》,载《万国公报》第177 卷(1903 年);《版权之关系》,载《万国公报》第183 卷(1904 年)。两文,强调:“版权者,所以报著书之苦心,亦与产业无异也”,“彼著书者、印书者自有之权利,谓之版权,而国家因以保护之”,在极力宣扬著作权“私权”本质的同时,林氏有意将之与产业相提并论,其所采用的修辞和表达与中国当时改变国策和改造法统的历史情境是完全吻合的。
不难看出,与洪仁玕等人相比,汪康年等精英不仅同样表达了知识产权对于国家强弱贫富的战略意义,而且十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制对于“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在法律制度上为清末发展国策的转移确立了理论支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话语表达上开始重视知识产权法制对于维护创造者个人利益的重要价值。这对于改造中国不合时宜的固有法统,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着以个人权利等核心的价值观为支撑的现代社会的变迁,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的、深远的历史影响。质言之,他们的认识更加贴近知识产权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隐秘勾连,也更为契合知识产权输入近代中国的历史隐喻,知识产权法制和学术与现代中国转型的语境从此愈加难以分离。
三、知识引进与知识产权话语的基础性建构
十六世纪以降,虽然西洋人,特别是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并不断输入近代西方文化,甚至专门推介了知识产权制度。例如,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于1857年6月发表于《六合丛谈》的《格物穷理论》一文就特别介绍了西方的专利制度,“西国凡悟得新理者,君长必旌异之,造新器者,令独擅其益,禁人不得仿造,以夺其利。”“望中国亦仿此为之。上为之倡,下亦必乐从,如此十年,而国不富强者,无是理也。”㉔韦廉臣:《格物穷理论》,载《六合丛谈》影印本1 卷6 号,第604-606 页。另据本文考证,《格物穷理论》也是最早涉及专利制度的中文文献,比学界通常视为乃“中国第一篇用文字形式表述专利制度文献”的《资政新篇》早两年有余。但当时的清政府却以抚慰朝贡国的心态款接他们,并无吸取西洋知识之意。因而,彼时西洋学术中虽有新字新语,但于我国却未有显著影响。
甲午战败,朝野震惊。“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㉕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 页。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强盛国力的事实对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和启示,如康有为在1897年12月上书时所言:“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己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㉖张之洞著:《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李忠兴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16 页。要学西方,先学日本,渐成上下共识。日本“天时、地度、国体、宗教、民情,皆与我为近……今之言改政者,莫不胎范于日本之制”。㉗《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第1 卷),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载泽序。在法律领域,从法规订立到法学教育,从术语体系到制度内容,都开始全面模仿学习日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张:“将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则欲取欧美之法典而尽译之,无论译者之难其人,且其书汗牛充栋,亦译不胜译。日本则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国也,译和文又非若西文之难也。”㉘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新译法规大全序》,载沈家本撰:《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242 页。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侵入我国。㉙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著:《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8-119 页。
1900年左右,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㉚此书初版已不可得,有学者根据相关史料推定出,本书约初版于1899 年5、6 月至1900 年11 月间,系在日本印刷,刊成后亦传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参见石云艳:《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载《南开语言学刊》2005 年第1 期,第205-213 页。在日本出版。该书搜集整理了近200个日语外来词,并在每个词汇后附加了简要说明,其中介绍了“商标”(点牌)㉛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梦花庐氏增刊,第38 页。和“发明”(创造之事,又小儿聪明)㉜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梦花庐氏增刊,第75 页。,从而最早把“商标”和“发明”等词汇输入了汉语体系。1901年,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社㉝1900 年成立于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译书机构。有关该社的详细介绍,参见[日]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217-221 页。在东京出版了井上毅著、章宗祥翻译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㉞此文也可参见《译书汇编》1901 年第8 期,第21-43 页。一书单行本,文中在介绍法国赋予外国人的私权类型时,提到外国人可以享有“著作之版权及让与权”㉟井上毅著:《各国国民公私权考》,章宗祥译,译书汇编社1901 年版,第9 页。“发明之专利权”㊱同注释㉟。,外国人在法国的,所有工商业之建造物的“制造标记(即牌号)㊲括号中为原文译者所加译注,下同。当时的译者们在翻译日文著作时,习惯在一些国人比较陌生的词汇后添加注释,以便利于读者理解。译书汇编社甚至曾刊出“难于索解之处,读者尽可致函本编同人”的通告。”可以与法国人的“标记”获得同样保护;㊳同注释㉟。在论及各国对于外国人权利的限制时,提到“著述及美术之特许(即专利权)与商标(即牌号)之保护”㊴同注释㉟,第12 页。都不得属于外国人,除非各国之间签有互惠条约或者加入了法国等11国缔结的“工业权之条约”。㊵同注释㊴ 。这标志着“著作”“版权”“发明”“专利权”“标记”“特许”“商标”“工业权”等语词开始以法律术语的形式进入国人视野。1907—1909年间,《日本法政词解》《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法规解字》《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及《法律名辞通释》㊶朱树森等编:《日本法政词解》,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1907 年印刷;钱恂、董鸿祎编:《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法规解字》,商务印书馆1907 年版;[日]田边庆弥著:《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清]王我臧译,商务印书馆1909 年版;刘天佑编:《法律名辞通释》,绅班法政学堂1908 年版。等法律辞书在中国相继出版或发行。它们不仅把“著作权”“版权”“商标”“特许”“意匠”“智能权”等作为法律概念收入其中,而且第一次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作了解释。此外,当时还从日本输入了诸多知识产权法律绕不开但非专有的基本概念,如服务、表现、请求、支配、市场、执行、侵害、申请、停止、文学、艺术、法律、权利、规则、故意、劳动、思想、美术、传播、独占、原则、义务、法定、科学、人格、管理、交易、脚本、专卖、信号、侵犯、商业、商品、出版及登记等。㊷参见高名凯、刘正埮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版,第82-99 页。上述著作把“权利”和“义务”也视为由日语引进,但据学者考证,1864 年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卷一中已有“权利”“义务”之译语,日本人正是从该书中取来了这两个用语。这一点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承认。参见[日]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上述术语中有一些属于古代汉语原有但日本人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文学、艺术 、思想等),有一些属于日本人以汉字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如传播、独占、出版等)后再被引入中国。
法律名词是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因素的社会生活予以简化的概念性工具。在法律名词的背后,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近代中国输入这些日语新词,与其说是对语言的照搬,毋宁说是对语言背后所蕴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模仿。它们的引进,不仅为知识产权观念启蒙、知识普及以及知识产权法制与学术体系的创建构设了一个法律概念平台,而且通过这些名词的流通与传播,为知识产权学术研究的社会化、建制化发展以及知识产权文明秩序的生长、衍生和拓展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㊸联书店1983 年版,第283 页。。
四、知识产权法制初创与现代性的中国实践
经过诸多朝野、中外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上谕中说:“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并且明确指出:要学“西学之本源”,“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㊹王汎森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版,第184 页。从而拉开了清末新政、改造法统的帷幕,老大帝国正式转入了与世界同步、向现代转型的改革轨道。1903年4月,清廷又颁发谕旨:“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㊺[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5013 页。正式实行重商主义国策,数千年的重农抑商一变而为振兴工商。
无论是新政改革,还是国策转移,都离不开法制保障。为此,清政府又先后颁行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898年)、《商标注册试办章程》(1904年)、《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等现代法律规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制体系,改变了数千年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固有法统,为构建现代文明秩序提供了法律支援。从表面上看,知识产权法制的初创与清末新政改革的实行,在时间上“恰好”存在重叠,但这绝非历史的惊人巧合,而是知识产权自身的制度禀赋所决定的必然逻辑。知识产权秩序本能地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知识产权制度本能地属于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成。传统中国要步入现代文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这是现代化规律的力量,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也是制度文明的力量。也正是基于此,《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的目的在于“智民富国”㊻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是属于“保商之政”㊼《商部奏拟定商标注册试办折》。,《大清著作权律》则旨在“保障权利”。㊽《民政部为拟定著作权律清单请旨交议事奏折》。
清末新政中所创建起来的现代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一方面是属于晚清法制变革的有机组成,另一方面,又是作为振兴实业的重要举措,被清政府赋予了引领工商发展的历史重任。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从发展国策上改变我国延续千年的“以农立国”的基本方针,从法律传统上改造“漠视个人权利”的固有思想,从意识形态上力革“耻言贸易”“耻于言利”“忽略私权”的惯常积习,从而“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㊾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载《东方杂志》1912 年第7 期。,最终把我国引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兴起,充分彰显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生动实践,即通过对域外知识的自觉引进,并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撑,把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植入中国社会,以创设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发展方式,不同于中国固有法律传统的新的生产、生活和法治秩序,以促使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由持续千年的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转向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性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改造国情,求强致富,建构现代文明的目标。
结 语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在中国的起源,是以“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㊿薛福成著:《筹洋刍议——薛福成集》,徐素华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8 页。这一千古变局为背景,以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法制的同步现代转型为驱动,在一批受到西方先进文明激励的清末政治与知识精英的推动下自觉发生的。它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法制体系,是以建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为宗旨,以域外既存的制度体系为模板,不断照搬、移植和模仿的产物。这是一种知识引进上的自觉,也是一种识时务之举,更为知识产权启蒙,乃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51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7 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所引入的现代的立法理念、系统的术语体系、丰厚的理论基础、成熟的文本体例,不仅为知识产权经济、法治和学术秩序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奠定了资源基础,而且也为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重建知识产权法制提供了知识储备。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52《管子·形势》。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表达与实践,也是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工业文明之道”的普世性特征与共通性原则不断嵌入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过程与结果。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有自身的特殊国情、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即便已经融入全球现代性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也必须寻找一种有差异的现代性的存在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必定在某一层面具有普遍的规律性与同一性,但其在不同国情和文化情景中的表现和实现却必然会受到地方性知识的制约,必定会彰显从本土性资源承继而来的文明的基因与历史的胎记,它在地方所呈现的制度与理论的应然体系也必定是本土化的、差异性的。为此,还需要立足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实践本身演化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反思并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发展并自觉维护具有中国性格的知识产权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