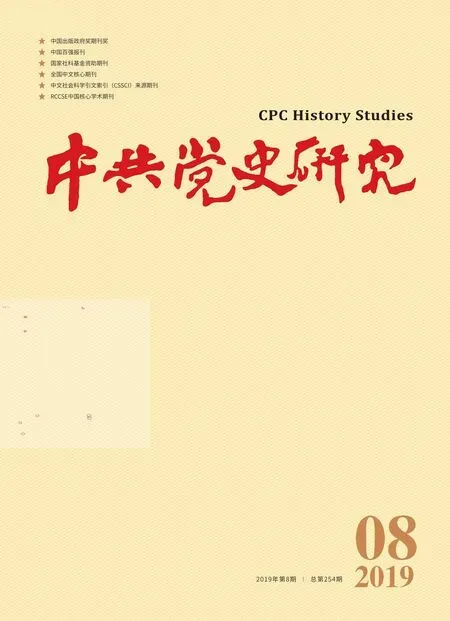五四时期的民族情感与反日运动的展开
马 建 标
五四运动之后,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曾写了一首小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1)《周恩来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0页。这首诗很典型地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学生的烈士意识,正是这种爱国精神鼓舞着“五四”学生走向街头,发表反日救亡演说,呼吁国人抵制日货。在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期间,周恩来也与众多的青年学生一样,满腔热情地参加爱国运动。他的这首歌颂“壮烈死亡”的小诗却是“五四”青年特有的精神、情感、意志与心灵的综合体现,这种情感因素也是理解中共早期成员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2)与国民党相比,中共更擅长从事“情感动员的革命工作”,这种情感动员传统的养成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五四时期的运动经历及其丰富的情感特质有关。参见〔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7—121页。。如果忽略他们所处时代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无法理解五四时期反日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血书”“断指”“自杀”等极端行为,而这种烈士精神所渲染的“民族情感”正是五四时期反日运动得以持续和扩大的原始力量(3)关于五四运动后自杀现象与爱国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刘长林:《仪式与意义:1919—1928年间为自杀殉国者举办的追悼会》,《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作为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集体性的民族抗争,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涉及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人员之众、行为之激烈在北京政府时期都是鲜有其匹的。根据日本东京商业会议所做的调查结果,中国的反日运动造成日本直接商业损失多达1500余万元。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曾屡次向北京政府抗议,要求取缔排日运动,如同“水上之画字”,结果都是徒劳一场(4)《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57-01-01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日运动期间,发起者往往会借助烈士形象的宣传来激励中国人的民族情感,通过这种民族情感来激发消极保守的商人阶层参加反日运动。五四时期,由这种烈士精神所渲染的民族情感在反日运动中的动员作用,时至今日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烈士精神作为一种极端的民族情感形态,将个体情怀与民族情感融合在一起,符合五四时期民族救亡的时代需要,并对其后的革命动员具有垂范意义(5)关于情感动员的研究,参见James M.Jasper,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James M.Jasper,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vol.13, no.3, Sep., 1998, pp.397-424。。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问题时,一般用“反帝爱国运动”称呼之(6)高莹莹:《反日运动在山东:基于五四时期驻鲁基督教青年会及英美人士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这种语义含混的说法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五四时期的“反帝运动”是针对所有列强的,实际上五四时期的“反帝对象”主要是日本。虽然五四时期的“反帝对象”仅限于日本,但它无疑是现代中国反帝运动的新起点。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烈士精神”及其激发的民族情感在五四反日运动中是如何加以运用的,这种“情感动员”在民族动员中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五四”之前的“烈士精神”与民族运动
在近代历史上,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烈士形象,首推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壮烈殉国的谭嗣同。谭嗣同“以身殉国”的故事以及由此彰显的“烈士精神”,超越了狭隘的英雄主义层面并上升到国家主义高度。正如张灏所言,谭嗣同的“烈士精神震撼了一个时代,同时也为早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型”(7)《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此种烈士精神也是激励无数有志青年投身反清革命的精神动力。烈士精神饱含忧国忧民的革命情怀,强调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烈士内心渴望“对灵魂的升脱和精神的不灭”(8)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在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汪精卫受此烈士精神的感染,在1910年春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行刺未遂而身陷牢狱,但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狱中感怀诗,反而更使其成为一代青年的革命偶像(9)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所代表的烈士精神对凝聚时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精神的激励又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恰如时人所言:“有了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殉国,便有武昌首义的成功,所以想到民国成功的根源,便不能忘却七十二烈士奋斗牺牲的伟迹。我们饮水思源对于七十二烈士的丰功伟烈,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实足为吾民族吐气,增吾族无上之光荣。”(10)朱公振编:《本国纪念日史》,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45—46页。在十余年的清末历史进程中,从戊戌变法烈士谭嗣同到辛亥年间七十二烈士,他们为民族国家的创建而勇于牺牲的烈士精神渐次成为驱使集体革命行动的重要情感力量。辛亥革命元勋章太炎特别称赞“烈士精神”的感召力在革命动员中的作用,认为革命党人的“舍生忘死精神”感动了天下,“四方之人感其至诚,覆清之声,洋溢中外”(11)《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7页。。陈天华就是这样一位感动天下的革命烈士。1905年12月7日,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激励中国学生“共讲爱国”,其《绝命辞》写道“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于次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12)《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5页。。陈天华蹈海而死,是否直接受到谭嗣同的影响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为国牺牲的勇气进一步发扬了烈士精神。曾与陈天华一同赴日留学的杨昌济就是谭嗣同的崇拜者(13)参见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陈独秀也是烈士精神的推崇者,他认为:“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1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2页。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必须靠“少数之少数”的先觉者与启蒙者(15)〔日〕近藤邦康著,丁晓强等译:《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这种启蒙者的孤独感与责任感更加凸显了烈士精神的可贵。陈独秀时常怀念先他而去的几位烈士亡友,以坚定他继续启蒙国人的意志与决心,“赵(声)、杨(毓麟)、吴(樾)、陈(天华)不惜自戕以励薄俗,恐国人已忘其教训,即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矣”(16)陈独秀:《双枰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
从陈独秀及其同辈友人陈天华、吴樾、赵声等所发扬的烈士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谭嗣同烈士精神在清末民初的代际延续。同样,以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对烈士精神的推崇与认同也很明显。当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之时,因为杨昌济的提倡而研读谭嗣同《仁学》和船山学说(17)李锐:《早年毛泽东》,第45页。。杨昌济先后留学日本和英国十年,研习教育与哲学,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18)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在其直接影响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一师学生在他们的文字著述中时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19)李锐:《早年毛泽东》,第44—45页。。谭嗣同的烈士精神多少带有一些侠义色彩,其精神不死和灵魂不灭的英雄气概与一战爆发之后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族精神。
在1915年抵制日本“二十一条”的运动中,烈士精神得到提倡,借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1915年5月中旬,成都学生界在致全国各报馆的信中写道:“国家当风雨飘摇之时,而人民犹在醉生梦死之中,欲唤醒之,以与共济时艰,则又诸公之黑血是望。”(20)《成都学界之激昂》,《申报》1915年6月2日。烈士精神是知识信仰与个体情感的混合体,因此烈士精神的信奉者一般是那些拥有良好教育的社会群体。自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运动以后,烈士精神被逐渐阐释为一种“效忠国家”的精神,而为国牺牲个体生命也受到社会舆论的鼓励。此时中国社会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加剧了青年人内心的苦闷,特别是青年人的自杀现象被赋予反抗社会压迫的意义。陈独秀就认为“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所以才自杀”(21)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因思想的冲突而自杀,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因而具有了烈士殉节的意味。如果说清末民初的烈士精神是为了探索生命的终极价值,那么五四时期的烈士精神则被赋予反抗社会压迫和外御其侮的新的时代内涵。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鲜血”已经成为烈士精神的“象征物”,并与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22)进入民国以后,欧美国家用红色纪念先烈的方式对中国产生影响,红色具有为革命献身的意义。参见李若晴:《烈士精神与革命记忆:20世纪诗画中的红棉意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在对外抗争运动中,“断指血书”成为一种广受社会崇拜的英雄主义行为。1918年5月20日晚,留日学生归国代表李达、龚德柏、王希天等与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会议,抗议中日共同军事结盟,会场中不少同学悲愤痛哭(23)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8—179页。。同日夜,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湖北籍学生张传琦闻中日交涉已经签字,割破手指并血书“亡国条件非取消,不能达到目的,勿限于五分钟热度”等字,在京城高校广为宣传。5月21日,该校的另一位学生夏秀峰也断指血书“请愿书一件”。(24)《大学生对于新交涉之请愿详记》,《时报》1918年5月25日。从1915年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运动到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结盟运动,断指、血书、坠城、投河等不怕死的壮烈事迹经常见诸媒体报道,以此来唤醒中国,鼓动民众的反日情绪。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知识阶层的普及,民族主义所强调的群体意识进一步赋予烈士精神以崇高的地位,并将个体的生命价值与救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弘扬烈士精神,这一价值判断的思想预设是民族主义理应高于一切,“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一个外来民族合力推进的扩张。为动员全民族的集体力量,必须使它的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处在一个危急关头,并因而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25)〔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中国学生为了唤醒民众并使其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以及中国面临的危机,他们甘愿用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来唤醒民众,以烈士精神来召唤国人的爱国激情。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国民大学全体学生在《敬告邦人书》中呼吁:“当国家存亡之际,正吾人死生之关”,“尤须各激爱国天良,虽杀身成仁而不悔;质言之,即不要钱、不怕死而已”(26)《北京国民大学全体学生敬告邦人书》,《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在五四运动期间,烈士精神所彰显的情感力量与民族主义信仰结合在一起,成为支配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源泉。
二、 “塑造烈士”与反日动员
经过清末民初的历史积淀,烈士精神已经成为“五四”学生的集体意识。在此种社会心理状态下,烈士事迹自然地成为媒体热衷报道的议题,而大众媒体的宣传进一步扩大了烈士形象的传播。烈士形象的塑造与社会传播,一般是通过在公开场所举行烈士追悼会,讲述烈士的爱国故事,并经过报纸的报道,形成全国共享的新闻事件。在此过程中,烈士追悼会具有制造民族情感气场、形成民族情感共同体的作用(27)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策源地,“五四”学生烈士形象的塑造也与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缘。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即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年仅18岁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上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28)《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4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50页。像这样用“鲜血书写爱国标语”的事例,在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中不胜枚举。如1919年5月7日,济南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耻纪念大会”。当日上午10点,大约3万人参加此次大会,关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情况以及北京学生受爱国心的驱使痛打“卖国贼”的故事在人群中广为传播。在此次大会上,一位名叫张兴山的演讲者甚至咬破手指,血书“良心救国”四个大字。(29)“An extra of the Ta Tung Jih Pao of the 7th May 1919,” May 8, 1919, 893.00/3165,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资料, Roll 22, 893.00/3141-3275。不过,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自觉意识与广大民众对民族国家观念的隔膜,成为“五四”学生发动大规模反日运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五四”学生要想扩大反日运动的社会基础,就必须使一般民众意识到当前的国家危机。只有这样,普通民众的民族情绪才能调动起来,大规模的反日运动才有可能实现。
在五四运动期间,有两名青年学生被塑造成著名的烈士:一是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二是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二人被塑造成烈士,各有其独特的缘由。二人之死对于推动中国各地区反日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郭钦光被塑造成烈士,既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也是清末民初以来烈士精神逐渐被中国社会认同的一个必然结果。关于郭钦光的生平,时人记载:“郭钦光字步程,年三十一岁。广东文昌人也。家贫,父兄早殁。幼善任击,迭为人报不平。乡党皆器重而资助之。迄游学京师,备极勤勉,少事寡言。惟谈及国事,则慷慨激昂,捶胸顿足,有不灭国贼,死不休之慨。自月之四日,北京学界有游街大会之举,君踊跃前驱,追击国贼。闻同学被捕者多,忿不可奈。呕血数升,翌晨即送往法国医院调治,竟以怨恨不起。当其弥留时,有告以章宗祥已毙者,乃仰天笑曰:国贼已亡,吾死无憾矣。遂瞑目无言。溘然长逝。”(30)《天津公园之学生大聚会》,《时报》1919年5月15日。
不独郭钦光的死被塑造成壮烈之举,甚至其早年历史也被描绘成是爱国的。6月14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在追悼郭钦光大会上说:“郭烈士于袁氏帝制时代,即大声疾呼,以冀唤醒同胞之觉悟。昔因国事痛心,居处时常抱抑郁愤恨之声,每现于颜色,以致身躯多病。”(31)《南京学生追悼郭钦光等大会情形》,《五四运动在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然而,郭钦光的真实形象并非如宣传的那样。实际上,郭钦光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北大学生,他之所以被塑造成全国景仰的烈士,主要是一种现实的策略选择,“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32)《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9页。。简言之,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情感动员,郭钦光被塑造成烈士,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策略选择。
因地理之便,天津学生界较早地举行郭钦光追悼会,对郭钦光的纪念活动继而在全国展开。5月10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发出通函,邀请天津各校学生于5月11日在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内为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当日下午,郭钦光追悼会如期举行。此类活动的意图正在于讴歌郭钦光救国的壮烈事迹,渲染其烈士形象。如南开、成美两学校全体学生赠送的一副挽联写道:填胸义愤拼一死,以挽危亡,宗泽大呼,英雄泪尽;瞋目悲歌舍此身,何足轻重,荆卿高唱,壮士不还。当然,天津学生界举行的郭钦光追悼大会,并非单纯为了表彰郭钦光的“烈士精神”,更主要的是借此鼓动人心,为推行更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作舆论准备。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布的郭钦光追悼会通知,即指明其开会意图是“借以征求伟论,醒救同胞也”(33)《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追悼郭钦光》,《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页。。天津中等学校举行的郭钦光追悼大会,也是由各校校长演说,并“讨论关于青岛外交问题一切进行办法,及推举代表晋京参与会议情形,以资取决”(34)《中等各学校联合举行追悼郭钦光大会》,《五四运动在天津》,第15页。。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学生界追悼郭钦光的活动,得到顺直省议会的有力支持。顺直省议会发起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5月12日,天津著名绅士孙仲英提议“北京学生郭钦光爱国之举竟致殒命,拟由天津教育界同人每人先捐资一文,他界听其自由,以资做一纪念品而垂永久,可谓轻而易举”,众皆赞成(35)《顺直省议会发起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五四运动在天津》,第20页。。郭钦光被塑造成烈士形象,是学生界推动反日运动的一个策略选择,是为了警醒国人,更是为了克服中国人固有的缺点如“五分钟热度”等(36)《顺直省议会发起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五四运动在天津》,第18—19页。。郭钦光追悼会的举行基本上是在当地反日运动走向高潮的前夕,这也说明当地社会精英是在选择恰当的时机举行烈士追悼大会。5月3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会议,筹备追悼郭钦光大会,得到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支持(37)《上海学联筹备追悼郭钦光大会》,《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在对郭钦光烈士形象的塑造上,参与者往往会引用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历史故事来激励人心,如有人把郭钦光与宋代太学生陈东的爱国事迹相比附,上海女子中学挽联是“谁令伯仁至此;其视陈东何如”,等等(38)《追悼郭钦光大会纪事》,《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76页。。郭钦光的烈士形象塑造,确实具有一定的精神感染力量。上海静安寺路汇芳照相馆免费洗印并放大郭钦光的遗像,以示“该馆对于郭烈士钦服之意”(39)《上海学联筹备追悼郭钦光大会》,《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73页。。5月31日,上海大小商店皆为郭钦光下半旗志哀,其中河南路、南京路、法大马路一带尤为整齐(40)《追悼郭钦光大会》,《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78页。。根据《申报》数据库的统计,从1919年5月到7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山东、南京、武汉、沈阳等地都为郭钦光举行过追悼会。
正如郭钦光的烈士形象是基于一种宣传策略的需要,武汉学生李鸿儒也被描述成一位为国牺牲的模范。五四运动爆发后,李鸿儒立即投入爱国运动。6月初,李鸿儒在劝业场演讲时,遭保安队殴打致伤。6月16日,李鸿儒在往南阳途中,忽闻中华大学学生胡宗灿伤重不治,不禁悲愤填膺,遂跳水自杀,其遗书写道:“鄙人救国无状,徒存所耻,尚望学界同人,各抱爱国之忱,誓达目的为止。”(41)《学生忧愤投河》,《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18日。在宣传李鸿儒的爱国事迹方面,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18日,恽代英为武汉学生联合会写作追悼李鸿儒启事。同时,恽代英联络其他社会团体,计划在6月22日为李鸿儒等人的追悼会召开筹备会。(42)《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564、565页。7月1日,恽代英又改写李鸿儒的传略,发表在7月10日的《汉口中西报》上。恽代英之所以热心宣传李鸿儒的烈士事迹,积极筹备李鸿儒等人的追悼大会,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其舍己殉国的精神,更主要的是一种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一方面开展反日运动如抵制日货等,另一方面反对北京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安福系。在五四运动期间,抵制日货与反对安福系是恽代英的两大政治斗争目标。7月1日,恽代英在改写李鸿儒传略的同时,又写作《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名片有国货可用了》《日货国货辨认法》等文。这些文章标题表明恽代英是把反日与反对亲日派作为重要的斗争目标的,而为李鸿儒等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则是达到上述目标的重要宣传手段。
烈士追悼会作为各界力量参与的大型群众集会,需要动用大量社会资源,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才能完成。因此,追悼会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联合的结果。除武汉教育界的恽代英之外,汉口和记蛋厂的买办商人以及汉口辅德中学的创办者刘子敬也是烈士追悼会的重要筹备者。刘子敬亦是即将成立的湖北各界联合会发起人之一。从恽代英的日记中,可知恽代英主要负责李鸿儒等烈士的追悼会启事及其生平传略的文字宣传工作,至于追悼会的具体筹备、联络等事宜,恽代英很少参与,如其所言:“五烈士追悼会,从上数星期闹起,至今日下午四时尚无布置,而定期明日开会。”(43)《恽代英日记》,第571页。实际上,刘子敬主持的辅德中学为追悼会筹备工作做了较为妥善的布置。当恽代英7月2日晚赶到辅德中学时,惊闻“(追悼会)已布置有头绪矣。大异!”半信半疑的恽代英到追悼会会场视察后,方信以为实。(44)《恽代英日记》,第571页。
7月3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汉口红十字会、武昌律师公会等18个团体,不顾湖北当局的反对与阻挠,在汉口大智门外联合举行李鸿儒等烈士追悼会。是日,有1000余人参加追悼会,武汉律师代表施洋宣读祭文,发表演说道:“殉国五学生此次牺牲性命,价值较之黄兴、蔡锷为高尚。黄蔡两君对内关系,五君捐躯对外关系,所谓外患亟于内讧,诸君因追悼而来,五君未达之志,尚望同人继续进行,以竟全功。”(45)《追悼殉国学生参观记》,《汉口新闻报》1919年7月4日。同日,武汉三镇街上悬挂白旗,以示追悼之意。有一家商店门前贴的挽联,上书“君为国死,我为君哭”。此次学生烈士追悼会是武汉地区自五四运动以来社会各团体的首次联合行动,推动了湖北各界联合会的成立(46)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将烈士的牺牲意义放置在“对外关系”层面上,就是强调他们的死亡是“为国牺牲”的,这种认识表达了追悼会的组织者希望将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压迫的“屈辱感”转化为民族的抗争精神,进而构建一个拥有共同“耻辱经历”的“情感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柯银汉(Edwin S.Cunningham)也注意到此次烈士追悼大会,他在给美国驻京公使芮恩施的报告中写道:“7月3日,武汉学生举行反日游行,有一个学生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死亡,他是跳河自杀,被淹死的。”武汉学生还希望柯银汉能够支持他们的反日游行。一位姓宋的武汉学生代表特意来到美国驻汉口领事馆,希望学生游行队伍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天访问领事馆,游行路线是经过俄国领事馆,再到美国领事馆交流,这是因为“学生们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但俄国领事拒绝了中国学生游行队伍经过其领馆所在地的请求”。事实上,武汉学生对美国的崇拜之情并非特例。比如,上海学生联合会在给武汉学生联合会的电文中写道:“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美国是我们的朋友,此次反日运动得到了美方的支持,我们向美国人民表示感谢。”(47)“Wuhan Cities’Students Association,” July 7, 1919, 893.00/3205,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资料, Roll 22, 893.00/3141-3275。
中国人对美国的这种好感,已经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恐慌。为了纾解中国人的反日心理,日本在华媒体甚至打出“种族主义的旗号”,借以离间中美友谊。1919年8月12日,芮恩施公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汇报说厦门当地的一份日本报纸发表题为《反日运动:给黄种人兄弟的忠告》的时评,其中写道:“青岛问题已经引起中日两国的严重误解,但事实上日本会将青岛归还中国的。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产生的真正原因是白种人在挑拨离间。他们要离间黄种人的内部关系,以确保白种人在东亚的利益。”(48)“Racial Propaganda by the Japanese Press,” August 12, 1919, 893.00/3185,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资料, Roll 22, 893.00/3141-3275。芮恩施在这份报告里,还提醒美国国务院重视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种族主义宣传。中国的反日运动越是激烈,越能削弱日本在华影响力,反过来更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发展。但就那时的中国民族精英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种族竞争,而是如何凝聚中华民族自身的团结,以抵御外侮。
三、 反日运动的开展
烈士追悼会以及烈士形象的塑造,是民族精英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观念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反日运动本身就是民族救亡的重要举措。无论“救亡”还是“启蒙”依然是局限在“五四”精英世界里的话题,而为反日运动所塑造的烈士形象则是沟通精英世界与普通民众的重要纽带。五四时期救亡性的反日运动正好碰上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使得此次反日运动兼具“民族救亡”和“爱国主义”启蒙的双重性。(49)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文史哲》2019年第3期。在全国范围的反日运动展开之前,时人已经注意到反日运动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特别是学生界,上海《时报》记者戈公振就指出:“青岛问题发生,上等社会之人已知之,而深虑之。中下社会之人,则否,或知之而以为风马牛不相及,此种现象至堪扼腕。今京沪学生均有演讲团之组织,乘此机会,可以造成舆论之基础,而收举国一致之效果,愿主持其事者,幸勿以空言而忽之。”(50)公振:《演讲团》,《时报》1919年5月16日。
事实上,京津地区率先发起的反日运动确实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并直接带动其他地方排日风潮的兴起。1919年5月8日,济南美国总领事毕克福德(Geo F.Bickford)致信美国驻京公使芮恩施,提及:“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反日运动所造成的麻烦,并担心济南的学生以及其他爱国民众也会采取同样的反日行动,故而济南官方在昨天出动一部分警力驻扎在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附近,以便维持秩序。济南的日本领事馆代理领事显得惊慌失措,他甚至请求英国领事禁止中国游行队伍进入领事馆所在区域。当然,英国领事无权这样做。”(51)“Geo F.Bickford to Paul S.Reinsch,” May 8, 1919, 893.00/3165,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资料, Roll 22, 893.00/3141-3275。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也就是纪念日本在1915年5月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一天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故而也是倡议抵制日货的绝佳时机。一份号召在5月7日抵制日货的传单这样写道:“日本既占据我满洲,今又欲强夺我山东,如此看来,日本真不是我中国的友邦了。我中国人民无论士农工商,应从民国八年五月七号起,齐心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银行钞票。若各人有日本钞票,应去兑现,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看完请再交他人。”(52)《收内务部函》(1919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2-01-004。
在各地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过程中,举行烈士追悼会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以天津为例,通过郭钦光追悼大会的召开,天津学、教、商、绅各界成立了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5月14日,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议决把反对亲日派“卖国贼”列为主要斗争目标,议定“此次联合会之目的,非达争回青岛、惩办国贼之目的誓不罢休”。(53)《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议决事件五项》,《五四运动在天津》,第21页。天津何家庄国民学校学生组织了游行团,“每至大街小巷间,且进且唤,欲使人人尽知国耻,共起御侮”,“对于抵制日货一事,尤为猛烈进行”(54)《何家庄国民学校纪念国耻并组织游行团》,《五四运动在天津》,第17页。。烈士追悼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商界的爱国行为,不少商界人士为学生的牺牲精神所感染,投入反日爱国运动之中。
实践证明,令人壮怀激烈的民族情感总是比理性的爱国主义更能发挥舆论动员的效果。5月24日,济南女师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表示“吾辈怯弱女子,别无救国之能力,唯有抱定一种决心,提倡家庭一种永久抵制日货,以为消极对待办法”,每逢演说至沉痛处,全场学生无不落泪,且有放声大哭者,“一时悲惨之状,楮墨几难形容”(55)《济南女师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在这种充满民族悲情的氛围下,山东的反日运动高潮迭起。5月24日,青州绅商学各界召开国民大会,青州第一中学学生杨某登台演说,当场咬断手指,血书“赤心报国身死志存”。演说毕,由各界公推调查员20余人,分赴城厢各商号调查日货。各学校学生则排队赴街巷游行演说,以促国民之醒悟。(56)《山东各地召开国民大会》,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56—257页。学生是反日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山东表现得尤为明显。据山东省省长公署职员李贡知在5月20日记载:“省城各学校联合抵制日货甚力,学校用品中之属于日货者悉焚毁之,有买日货者共罚之,各界亦颇感动。”(57)李贡知:《旅济随笔》(1919年5月20日),胡汶本、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386页。
由于山东问题是引发“五四”反日运动的导火索,因此山东省会济南的学生在反日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激烈。根据济南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陶德满(Lawrence Todnem)的报告,基督教青年会在济南所属的学校共有3385名学生,只有不到10%的学生来校读书,其余90%的学生都在从事抵制日货运动(58)Annual Report Letter of Lawrence Todnem, Associate Secretary,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Tsinanfu, Shantung,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30, 1919, Annual Reports and Annual Report Letter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in China 1919, volume 3,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1919,pp.5-6.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藏, Local Identifer:YMCA-Forsec-00729。。1919年6月15日,美国国际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驻华代表T.M.加特里尔(T.M.Gatrell)在给纽约公司总部F.M.狄尔文(F.M.Dearing)的报告中指出:“差不多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里,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学校的学生都举行了罢课行动。抵制日货在有组织地进行着,并已经引起日本政府的抗议,这让北京政府的处境很尴尬。”这份报告还说:“学生反日运动在迅速蔓延,一些大城市里的商人也开始罢市,政府与抗议者的冲突时有发生。”(59)“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to Breckinridge,” July 15, 1919, 893.00/3184,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资料, Roll 22, 893.00/3141-3275。就全国而言,学生界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从北京政府查禁反日运动的一份电稿内容中可略知其大概。6月4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向各省发布密电说:“近闻各地排日风潮,鼓荡甚广,亟应先事预防。兹查学界宣言及所标旗帜,有指斥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暨其他侮辱字样,实与国际平时称谓原则背驰,既恐惹起交涉,且恐转滋误会,关系甚巨,应请责成地方官厅,如有前项情事,应即严行禁阻,毋得任意指斥,以慎邦交,而维秩序。”(60)《内务部严禁反日运动电稿》(1919年6月4日),《五四运动在江苏》,第119—120页。
学生界视日本为“敌国”,以此启蒙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天津学联代表谌志笃回忆说:“四十年前,同学们不知道什么叫‘群众路线’,也不知道什么叫‘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学习’,仅是‘唤醒同胞,一致救国’。当时,学联特设讲演科,专负对市民宣传之责……他们带领宣传队队员经常在街头、宣讲所和公共场所作通俗演讲,或深入家庭宣传,‘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以动员广大群众。”(61)谌志笃:《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01页。通过宣传日本的“敌国”形象来激励中国人的爱国心,这种事情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宣传策略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引发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纠纷。在上海的反日宣传中,就出现了中国人“侮辱日本天皇影像”的举动。由于日本人把“天皇”视为国家的神圣象征,所以旅沪日本侨民集体游行,向中国政府抗议。还有传言说“中日恶感激动,日本全国六千万人群思牺牲对华”。为平息旅沪日侨的愤怒,中国外交部特派上海交涉员杨士晟亲自会晤日本驻沪领事,妥商消弭方法。(62)《收国务院交抄致经略使等电,排日事》(1919年6月20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0-01-003。根据日本方面报告,天津日本租界也发生中国人侮辱日本天皇形象的事情。6月21日,在天津日本租界的“大和公园”树上发现“挂有二寸大小的人形玩具,腹部写有日本皇帝字样”(63)《国务院交抄天津曹省长电》(1919年7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2-02-008。。此外,汕头、宁波、沙市、重庆等地都出现了“侮辱天皇影像”的类似行为。在日本政府的抗议下,1919年7月5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禁止侮辱日皇举动”(64)《国务院发各省电》(1919年7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2-02-010。。
民族主义的普遍信仰使得反日运动具有了某种情感正义,而掌握民族主义话语权的青年学生则借此分享了原本属于政府的市场监督权力。5月18日上午,杭州学生界为郭钦光开过追悼会之后,下午就将缴获的日货付之一炬。在焚毁日货时,杭州学生代表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焚毁日货的初衷自然是为了警醒国民,如亲历此事的浙江第一师范学生陈范予所言:“思此番行动,有影响于国民不少。夫人真非木石,苟稍有血心,经此而犹购日货者未之有也,童孩之脑中输入‘仇日’二字尤深云云。”(65)〔日〕坂井洋史整理:《陈范予日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94页。在如此激烈的反日风潮之下,一些日本在华商人的营业活动受到冲击。5月21日午后3时,一位名叫“政二金次郎”的日本商人用船只载运货物到常州武进县销售时,当地居民“借口外交关系,向该日人诘问,一时人声淆杂”。武进知县姚知事恐怕“滋生事端,派警备队前往船埠保护”,并劝告这名日商立即离开常州。(66)《收苏州交涉员代电:日人游历被袭击事》(1919年6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2-006。在湖北沙市,日本三轮洋行的门面玻璃于5月26日晚8时被愤怒的中国人用石块、棍棒等工具击毁,日本货物遭到毁坏(67)《代理总长会晤日本小幡公使问答》(1919年5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2-001。。在湖南常德,排日风潮也很激烈,当地群众集会上甚至有军人发表反日演说,学生出面阻止客人搭乘日本商船(68)《收国务院交抄至各省电》(1919年6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2-004;《代理总长会晤日本小幡公使问答》(1919年5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2-001。。
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商业势力在华独占鳌头,故而抵制日货是打击日本势力的有力手段,也是“当时全国学生们的一致要求”(69)李云鹤等:《五四与安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02页。。学生界将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结合在一起。浙江第一师范学生傅彬然说:“反对日本侵略,向市民宣传用国货,不用日本货之类的爱国活动,当时多数学校都有。”(70)傅彬然:《五四前后》,《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43页。在抵制日货过程中,学生界甚至垄断商品交易的行政权,试图对商品流通进行额外管制。这种情形在中国各地抵制日货过程中比较普遍,如5月2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要求各商店不卖日货”,并规定罢课后还要进行“宣讲、发传单、调查日货”等事项,上海两家大公司先施、永安在此压力下宣布于22日起“不卖日货”,其他行业也大体“均以抵制日货为宗旨”(71)《学生联合会开会纪事》,《申报》1919年5月22日;《先施永安公司实行不卖日货》,《申报》1919年5月21日。。
当时,中国各地学生界已经充分意识到,要想使抵制日货运动获得显著成效,必须联合各界共同行动才行,成立专门的日货调查组织是抵制日货运动的有效办法。如天津各界联合会就成立了“日货调查部”,随时调查华商与日商有无交易事情发生。一旦查出交易记录,天津各界联合会调查部将对涉事商人开设罚金。此外,调查部还负责印刷抵制日货传单,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商人对于天津各界联合会的抵制日货传单也不敢公然抗拒,因为他们误以为抵制日货行动得到了政府的默许。所以天津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的外交抗议。(72)《施履本参事会晤日本船津辰一郎总领事问答》(1919年8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0-01-009。即使地方政府没有默许抵制日货运动的进行,但是一些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因受到反日情绪的感染而不去干涉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5月30日,日本驻江苏领事大和久义郎在给中国外交部特派苏州交涉员杨士晟的信中说:“日商东亚公司在苏州火车站前的仁丹广告牌等均被破坏,以及苏州市内各处所设立的仁丹广告牌无不破损……而最怪者,警官现视暴举,毫无干涉。”(73)《收苏州交涉员代电:苏省拆毁日商广告事》(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2-013。
抵制日货的关键是要得到商界的支持,而商界的态度又取决于商会的立场,因此商会是学生界争取的重要对象。事实上,许多商人从内心深处是不赞成抵制日货运动的,这一点学生界亦有很清醒的认识(74)李云鹤等:《五四与安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02页。。仅以苏州为例,即可看出商界对于抵制日货的真实心态。据东吴大学学生会调查,苏州“外间商家多有假‘拍卖日货、以期净尽’之名,行暗中担任销售日货之实”(75)《东吴大学学生会会长为商家借拍卖之名暗销日货事致苏州总商会函》(1919年5月29日),马敏、祖苏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12—1919》第2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5页。。原因很简单,作为商人,他们的核心利益就是要谋利。由于市面上日货充斥,商人们完全可以趁机谋取大利,如果一旦赞成抵制日货,首先就要检查日货,焚毁所存日货与禁止日货进口。如此一来,商人的当前经济利益及其日后的营业必将大受损失。学生界主张抵制日货,主要是出于一种爱国的理想,况且抵制日货不会损害学生界自身的利益。
学生界要争取商人及其他各界的支持,就需要进行民族情感的动员,激发社会各界人士的良心,“让他们也能够仇视日本”(76)李云鹤等:《五四与安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03页。。在这方面,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6月10日,天津罢市以后,次日又有商人公然开市。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质问商会董事说,“日前大会全体公民一致表示:‘誓死救国’并要求商界一致行动立即罢市。昨天罢市情况良好,何以今天竟无故开市?”当时有一商董,问马骏是何许人,天津有无财产?马骏说:“本人是吉林人,天津固无财产,我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一死以谢同胞。”马骏说完挺身以头撞柱,幸而旁边有人把他抱住。据刘清扬回忆说:“经过马骏这样青年不惜牺牲生命以救国的决心,竟感动了多数的董事,又决议从十二日起,再继续罢市。”(77)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26页。以马骏为代表的天津学生在抵制日货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为国牺牲精神”也引起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饶斌森(Arthure G.Robinson)的注意。1919年9月1日,饶斌森在写给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总部的信中谈道:“天津学生的抵制日货运动是非常值得关注。在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中,天津学生发挥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可以确信的是,天津学生的反日运动真的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民族意识。此次爱国运动将不会结束,并将一直持续到他们把中国的内敌和外敌都清除掉为止。”(78)Sixth Annual Letter of A.G.Robinson, Year 1919, Tientsin, China, Sept.1, 1919, Annual Reports and Annual Report Letter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in China 1919, volume 3, p.16.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1919.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Kautz Family YMCA.
但是,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被学生界的爱国真情所打动。在多数情况下,商人是拒绝抵制日货的,特别对于那些中小商人阶层而言,作为小本经营者,家庭生计很容易遭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经常以暴力手段逼迫商人罢市、抵制日货。故而,许多小商人对抵制日货叫苦连天,但他们的苦衷很难被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所理解。在学生看来,这些只知道“叫苦”的小商人“缺乏国家观念”,“在国耻之下尚考虑自己的安危”,如此下去,“将有亡国之危险”(79)《3情報送付ノ件/3済南青年会幹事トッドネムノ民主主義ニ関スル演説其他》,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青島民政部政況報告並雑報第一巻,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 Ref.B03041662900。。
学生与商人往往因抵制日货问题而发生流血冲突,并引发政府的干预(80)李云鹤等:《五四与安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03页。。在学生看来,抵制和检查日货则是“最激动人心的”,也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壮举。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衍回忆说:“学联会的主要工作,除出打电报、发宣言,援助北京学生的义举之外,最激动人心的,是抵制和搜查日货。首先是各校学生分别组成了小队到贩卖日货的商店去劝告,后来就把检查到的日本货到西湖边上的公众运动场去烧掉。”(81)夏衍:《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30页。无论是抵制日货还是提倡国货,背后体现的是对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身份意识的觉醒。一份由恽代英起草的抵制日货传单这样写道:“国一天不亡,我们一天不做奴隶,日本人总不能餍足。”(82)《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学生是此次反日运动的前锋,但因年轻气盛,爱国心切,在抵制日货问题上往往不顾及商人的尊严与利益,导致双方冲突不断。比如,天津学生团对那些与日本商人有交易的中国商人经常“任意搜查其账簿,如发现有日货交易事情,就会对商人有种种胁迫举动”,甚至还将“与日商贸易的华商载上人力车,以旗面写明该人姓名与日商交易字样,游街示众”(83)《次长陈箓会晤日本小幡使问答:天津学生团排日事》(1919年7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0-01-005。。再如,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芳泽到山东调查反日运动情况时,对学生在反日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产生很大困惑:“以未成年之学生而得无上之行政权,政府乃置若罔闻,此不解者一。探政府当局者之内意,似乎皆不赞成学生之举动,然又指导戒饬之,其意安在,此不解者二。国家主权之代表人原系一国之政府,而竟令学生代替政府处置一切,是于事实上中国主权代表者,不为政府而为未成年之学生,此不解者三。”(84)《收山东交涉员函》(1919年8月12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1-060。然而,由学生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其致命的弱点——不体谅商人利益的得失,故而抵制日货运动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反日运动基于爱国的初衷,因而具有正当性,即使北京政府面临日本政府的抗议也不能贸然取缔反日运动。一旦政府不能及时阻止反日群众的集会活动,蔓延全国的反日运动就会出现失控的可能。
学生界领导的反日运动还有一个政治目标,那就是反对北京政府的亲日派。学生界如何从反日转向反对中国政府内部的亲日派,五四运动亲历者杨振声对这种斗争矛头的转换有很好的解释:“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当时的当权军阀段祺瑞是亲日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85)杨振声:《回忆五四》,《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61—262页。为了逼迫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等人下台,许多城市举行了“三罢”运动,即罢市、罢课与罢工。在此次“三罢”运动中,青年学生表现得最为激进。但对商人而言,长期的罢市必然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根据日本的情报调查,在6月14日,受罢市影响的数十名济南商人聚集在济南城内的福德会馆,声称“罢市虽对大商家并无影响, 但小本经营的店铺、商人实际已吃不消。青岛问题事关外交, 不属国内事务, 仅靠国民运动断难解决。尤其今日大局已定, 此事应当交由政府处理,而且开业后依然可以继续种种提倡国货之办法”,于是他们决定在6月15日开业(86)《2情報送付ノ件/2帰還苦力ト済南基督青年会及帰還苦力ノ罷業決議》,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青島民政部政況報告並雑報第一巻,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 Ref.B03041661900。。就这样,山东的“三罢”运动从5月23日开始到6月15日结束,前后历经24天(87)《2情報送付ノ件/3各界ノ罷業中止ニ関スル会議ト各商店ノ開業》,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青島民政部政況報告並雑報第一巻,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 Ref.B03041662000。。
学生界起初的反日运动,在对外方面主要表现为“抵制日货”“收回青岛”,在对内方面主要表现为“惩办曹章陆三位卖国贼”,即所谓的亲日派,这一阶段是“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爱国反帝运动”(88)夏衍:《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30页。。1919年6月初上海举行“三罢”以后,工人、店员、商人等其他阶层也参与进来,进一步促使反日运动扩大化。面对社会各界的联合压力,徐世昌总统不得不将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北京政府对游行学生的逮捕行动,增加了其他各界对爱国学生的同情。1919年6月13日,山东工商联合会致电大总统徐世昌以及北京政府,宣告“济南全体罢市的理由”,同时提出“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没收其财产”等项要求。(89)《收山东工商联合会电》(1919年6月13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1-01-001。
虽然学生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与商人时而发生冲突,但在对日关系上,学生界的反日宣传还颇具灵活性。具体言之,“五四”学生在宣传反日时,为了争取日本民众的支持,特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爱好和平人士进行了区分,他们声称反对的只是与中国为敌的日本侵略派,并不反对爱好和平的日本普通人民。日本黎明会领袖吉野作造对此有深刻认识,他在致中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排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平民主义的日本。”全国学生联合会对吉野作造的上述评论也深表赞同,在给日本黎明会的信中写道:“博士(吉野作造)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关于反日运动的目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自称:“吾侪运动之目的,一则表显人民之心理,鸣历来秘密外交之不当,以促敝国政府之反省。一则表示国民之能力,借经济上之打击,以促贵国人士对于贵国政府之决心。”(90)《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11页。1919年6月,吉野作造曾经计划以日本黎明会的名义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负责组织学界领袖访问日本,以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的理解,只因当时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之际,如果中国学生领袖访日容易被外界视为“已被日方收买”,故而访日计划被搁置起来,一直到1920年5月才由北大教授高一涵率领北大学生团访问日本。(91)黄自进:《吉野作造在五四时期的对华文化交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第505—529页。
然而,学生动员民众参加反日运动时,更多的是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的“敌国”来描绘和宣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王拱璧的《东游挥汗录》一书以绘声绘色的笔法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敌国。该书在记叙1919年留日学生在日本的“五七”巷战一节中写道:“日人之所以日甚一日,毫无忌惮者,良因青岛到手,东亚主人之资格已备,对于心目中之奴隶牛马臣妾而鞭打之,以行使主人之职权。”(92)王拱璧:《东游挥汗录》,《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87页。同样,恽代英在1919年5月撰写的《呼吁青岛》传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此虽“挑拨感情语”,亦是警醒国人、提倡国货的一种不得已办法(93)《恽代英日记》,第544页。。
如果只有满腔热血的民众,却没有领袖的提倡与组织,反日运动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特征,重要表现就是各地烈士追悼会的筹备与举行。这些追悼会的次第举办以及烈士形象的塑造,毫无疑问都是绅、商、学等地方力量共同促进的结果。以武汉为例,恽代英就认识到,要扩大反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力,就必须突破学生界的小圈子,遂主动与“商界、律师公会、教育会、省议会以及新闻媒体等联络,酝酿实行民众大联合”(94)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第143页。。7月10日,武汉学生联合会通告各团体,建议组织各界联合会,通告说:“为今之计,唯有各界联合组成一各界联合会,庶可共谋远大。以民意为前提,作外交之后盾,急起直追,自不难一呼而集。”(95)《学联通电各团体》,《汉口新闻报》1919年7月12日。7月12日,湖北各团体召开各界联合会筹备会议。8月13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向湖北省军民两署递交呈文,请求准予立案。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名义的各界联合会,其动机亦如湖北各界联合会所云:“现外患迭起,内乱未息,非联合各界之真正实力而为一伟大实力,集合各界之真正民意而为一健全民意,又何克以缓内而对外。”(96)《各界联合会呈请立案文稿》,《汉口新闻报》1919年8月21日。这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社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思想产物。当时,远在巴黎的外交官王正廷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民族主义主导一切的全民政治时代。他说:“中华民族正在缓慢地觉醒。中国终将重返先进文明国家行列,重享昔日的荣光。”(97)“China’s Case For The World: Interview With C.T.Wa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September 6, 1919, p.633.
四、结 语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死难者举行追悼会,自有其特殊的用意,就是通过追悼会这种集体纪念活动来宣扬“精忠报国”的牺牲精神,树立“大公无私”的爱国者形象,从而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达到团结一致抵制日本、挽救国权的目的。追悼会具有道德宣扬和政治教育的功能,既是为了纪念死者,更是为了“面向未来”,即用死者的牺牲精神来激发国人的仇日情绪,旨在挽救民族危机。如戈公振所言:“郭钦光死矣,追悼之何益?故昨日之会,乃为后死者勉耳。夫救国非郭君一人之责,而郭君毅然为之,以至于死,则其蓄志之坚久可知。今全国学生为国奔走,其目的与郭君同。倘群以郭君之志为志,则水滴石穿,何求不得一死,岂足数哉。”(98)公振:《时评三:追悼郭钦光》,《时报》1919年6月1日。这种反日情绪所表现出来的冲击力,甚至让远在东京的日本首相原敬也感受到了。1919年5月14日,原敬接待了刚从上海返日的寺尾亨,后者告诉他,“中国现在的排日风潮非常兴盛,令亲日派无能为力”(99)〔日〕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8卷,东京乾元社,1950年,第214页。。
在抵制日货、反对亲日派的过程中,一般中国人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意义。“五四”学生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吹鼓手。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民族精英的鼓吹,“大众自身事实上并不曾产生民族主义的花果;要等到宣传之风把民族主义的种子由一些特殊个人和阶级间吹散过来的时候,这种花果才会产生”(100)〔美〕海斯著,帕米尔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过程,“五四”学生则在反日运动中充当“唤醒者”。他们对此使命有明确的认识,如五四运动亲历者邓颖超说:“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101)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71页。
在推动五四反日运动的开展上,基督教青年会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9月30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John S.Burgess)在给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总部的报告中称赞道:“北京学生在5月4日火烧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是爱国举动。北京学生每天都在街头发表,制造公众舆论,这些爱国举动都是由于山东问题引起的。”(102)Annual Report Letter of J.S.Burgess, Student Secretary,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Peking,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30, 1919, Annual Reports and Annual Report Letter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in China 1919, volume 2, p.3.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1919.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与此同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狄尔耐(Eugene A.Turner)也同样认为:“学生界的反日运动是爱国性质的,他们正在肩负起改变自身与国家面貌的伟大使命。”(103)Annual Report, E.A.Turner, Shanghai,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30, 1919,Annual Reports and Annual Reports Letter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in China 1919, volume 1, Part I.National Reports, p.1.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1919.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在此之前,日本首相原敬也从来访的台湾人郭春秧那里了解到,在中国的基督教徒是“真正需要注意的势力”(104)〔日〕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8卷,第214页。。像基督教青年会这种具有欧美国际背景的跨国组织在五四反日运动中所扮演的幕后推动者角色,在过去常被忽略,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的英美籍教师对于反日思想的传播可谓不遗余力,值得进一步研究(105)《收驻日本使馆函》(1921年3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33-114-01-001。。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在各地的开展,除了充当前锋的青年学生之外,那些隐居幕后的省议会、教育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商界领袖也就是时人所言的绅、商、学以及英美在华组织等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后世研究者对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将能作出更为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