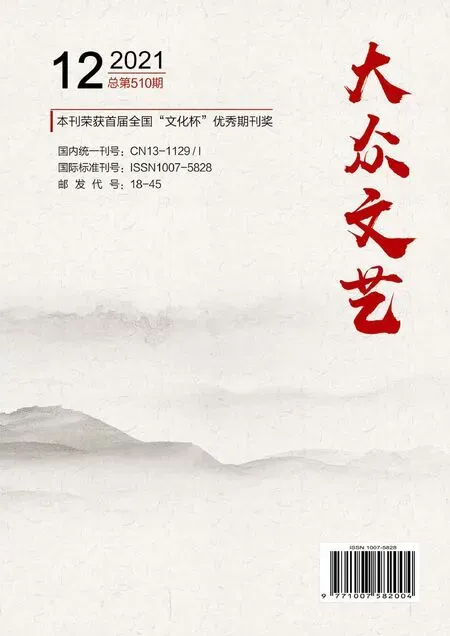石黑一雄《上海孤儿》的创伤书写
(杭州师范大学 310000)
石黑一雄的作品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以此激发了学界学者的研究兴趣。相比其他作品,国内外学者对《上海孤儿》的研究相对稀疏,其研究主题多聚焦于移民身份与族裔身份的构建问题,探究其作品中的英国性和日本性;其研究角度多着眼于叙事方式、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多个视角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主人公碎片记忆、不可靠叙述的叙事形式进行分析,探讨作者如何述说难以言表的创伤经历。回忆是《上海孤儿》的主要叙述形式,整部作品是主人公班克斯回忆往事的心路历程。在追忆过程中,班克斯经历了年幼时父母失踪所造成的家庭创伤、双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漂泊不定的文化创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产生的战争创伤,表现了其面对往事困境的痛苦心境。
创伤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弗洛伊德、贾内等学者对“创伤”的研究逐步推动了“创伤理论”的发展。到了20世纪末,创伤研究逐至繁荣。继弗洛伊德与贾内之后,众多现代创伤研究者对创伤这一概念陆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凯西·卡鲁斯在她的经典著作《无主的经验:创伤、叙述和历史》一书中对创伤的定义是:“在突发事件或灾难性事件面前,个体原有的经验被覆盖,而受创者对这些事件本身通常表现出延迟,以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的现象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反应”。她认为创伤可能是单次的突发性事件造成的,也可能是长期时间积累下来的压倒性时间所造成。比起创伤事件本身,卡鲁斯更关注创伤所造成的后果。此外,朱迪斯·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把不同的受创者群体,如战争受创者、强奸受害者、自然灾害受创者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记忆对创伤个体的影响,揭示了创伤对个体毁灭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突破了性别的界限,全面阐述了创伤概念和本质和复原的过程。创伤经历所带来的,不仅是对肉体与精神上的冲击,也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从而造成了个体行为的重演、记忆冷藏,以及叙事上的障碍。
一、创伤与记忆
创伤的经历会使受创者产生扭曲的心理,试图改变自我记忆和自我认识。创伤造成个体精神上的障碍与麻木,使受创者长期处于精神障碍的状态,以至于使其产生了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有别于普通记忆,“缺乏语言的叙述和已经,而是由生动形象的感觉和意象编码而成”(赫曼,38),通常会以视觉或者听觉的非语言形式反复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当有情景与受创者受害时的情景相似时,受创者会不禁想起当初受害的场景,随之而来的便是创伤的记忆。创伤经历的记忆是痛苦之源,这些记忆通常以幻觉或噩梦的碎片化的方式反复出现。受创者无法控制创伤所带来的影响,反复出现的创伤场景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力感使受创者无法同普通人一般正常生活。因此,受创者会下意识地排斥这些痛苦的记忆,在回忆时通过否认事实和编造想象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慰,仿佛创伤那一刻永远停留在自己的回忆与想象中,从不会受时间的影响和推移。
在《上海孤儿》中,幼时失去父母的创伤导致班克斯有意地逃避事实,并长期处于意识混沌的状态之中。石黑一雄的叙述巧妙地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使读者从一开始就深陷班克斯所勾勒的探寻父母失踪案的迷宫之中。班克斯的回忆之旅由七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的定位。看似合理并具逻辑性的故事发展,实际上,班克斯模糊不堪的记忆与他试图述说的回忆存在着一种张力。当受创者听到别人讲述相似的经历或在现实中看到与受害时相似的场景时,他会不禁想起当初受害的场景并与现实里的场景混淆。尽管是一件十分微小的事情,也可能勾起受创者痛苦的回忆,也就是说,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和场景对于受创者来说都是危险的。面对童年时的创伤经历,班克斯的内心处于渴望述说又不敢面对的矛盾状态。因此,整个故事的叙述就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来回摆动。日夜有父母和保姆的悉心照料,与邻居日本朋友哲的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在班克斯九岁时的一场突然变故中宣告结束。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面对父母失踪的事实,班克斯毫无心理准备。事情的突发在他的内心留下了阴影和创伤。为了摆脱孤儿的身份,班克斯幻想成为一个大侦探家,努力追寻父母的下落。然而,由于创伤记忆的压制,班克斯在回忆的过程中出现了幻象,模糊了现实与幻觉的界限。为了躲避创伤带来的痛苦,他过度依恋童年的记忆,依然认为父母被绑架后关在一所老房子里,误以为在战场上见到的日本士兵就是他的童年邻居玩伴哲。正是童年所受的创伤带来的伤痛才迫使班克斯将那部分记忆永远地留在了过去。由上述例子可见,班克斯的叙述不断被他的回忆所打断,现在的叙事与过去的回忆相互交织,体现了创伤记忆闪回、碎片化的特点。
对于班克斯创伤记忆的扭曲与模糊,在石黑一雄屡次提到视线被遮挡的问题中也有所体现。在抵达上海时班克斯叙述道, “这里人似乎抓住一切机会刻意挡住别人的视线”,这令他非常恼火;在舞会中,班克斯走出电梯还没来得及看一眼铺往舞厅的豪华地毯,他的视野便被英国领事馆管事的肥硕身躯挡住;班克斯想看地毯两旁的华人门卫的视线也被别人遮挡。可见,班克斯的视线屡次被遮蔽,使他无法看清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此外,班克斯对于自我记忆的可靠性进行了反复的验证。“我记得自己可是完全融入了英国的校园生活......记得到校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许多男生站着说话时喜欢摆一种姿势......我清楚记得当天我就把这套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那天说了些什么我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吃完东西后......”;“泛上脑海的第二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不过记得却不很清楚。”;“恰恰相反,当时的情景我历历在目”。可见,一些描写回忆的词汇如“我记得”、“我清楚记得”、“记得却不很清楚”、“历历在目”不断地重复交错,前后无意产生一种自我矛盾,表现了班克斯作为创伤受害者记忆的混乱。创伤记忆的不断地重演,而班克斯作为当事人却毫无意识。
二、创伤与不可靠叙述
创伤受害者在回忆与讲述创伤经历的时候往往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一方面极力逃避与否认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噩梦般的创伤记忆,一方面又想大声述说自己所经历的痛苦。这种矛盾心理使得受创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讲述创伤经历时会犹豫不决,甚至有时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们的感受。可见,创伤受害者的叙述通常带有主观意识,其叙述也往往是一些被打碎的记忆的残片。因此,由于创伤受害者矛盾心理的介入,其所讲述的创伤经历的真实性就有可能降低。
不可靠叙述分为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两种方法。学者韦恩·布斯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 , 一种针对故事事实 ,另一种则涉及价值判断。詹姆斯·费伦进一步发展了布斯的理论,增加了第三种类型“知识/感知轴”。这正是石黑一雄小说中,不可靠叙述所强调的意识层面:主人公一方面尝试希望通过讲述与回忆来减轻内心的痛苦,一方面在叙述和回忆的过程中他们又有意识地企图逃避和否认真相。这般矛盾心理导致了他们的叙述摇摆不定、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特点。
由于无法摆脱和控制创伤所带来的痛苦,班克斯不断否认和逃避他所遭受的创伤事件,试图塑造一个强大的如英雄一般的自己来摆脱自身的困境。故事的开头,作者在班克斯的回忆中提到,学生时代的班克斯以怪人、性格孤僻怪异闻名。结束回忆回归现实的班克斯对此大吃一惊又迷惑不解。在他的印象中,孤独又可怜的孩子不可能是他。可见,班克斯回忆的真实性并不成立,他是一个孤僻怪人的事实不可否认。同样地,上校认为变成孤儿的班克斯是一个沉默寡言、软弱无助的小孩,对任何微小的事都显得畏畏缩缩,郁郁寡欢。班克斯的姑母也认为他时刻都忧心忡忡。可见,失去父母之后,班克斯变得脆弱、敏感,创伤使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也随之改变。然而,面对他们对自己的评价,班克斯显得不快,甚至恼火。“根据我的回忆,我清楚记得自己很快便随遇而安,适应了生活中的变故。我分明记得,那次海上旅行我一点都不伤心,相反,船上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令我兴奋不已”。“事实是,我一点也不像围在我身边的那些大人们心理所想的那么沮丧难过”。在班克斯的自我回忆和认知中,成为孤儿后的他适应能力很强并且能从痛苦中迅速恢复。这一坚强的自我形象与他人记忆中孤独、脆弱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班克斯所塑造的自己不过是为了缓解伤痛而掩饰真实自我的表现。因此,在创伤受害者回忆创伤经历时往往会为了掩盖伤痛而对事实予以否认与逃避,他们的叙述是不可靠的。石黑一雄正是利用了创伤受害者极力回避与想要面对的矛盾心理,将虚与实刻画地惟妙惟肖。自始至终,班克斯都用十分确信的口吻回忆与讲述探寻失踪父母的故事,努力追寻并维持他内心深处的“真实世界”。然而,当一切真实与假设被瓦解,他最终发现事实的真相与他自我认知里的“真实”大相庭径,而他努力塑造的坚强自我在面对现实的冲击时显得苍白无力。在经历了幻灭之后,班克斯最终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开始接受自己的孤儿身份。这种接受恰从侧面反映了其创伤的愈合。
三、结语
《上海孤儿》中的不可靠叙述聚焦于创伤个体的内心世界,石黑一雄立体地呈现了主人公遭受创伤的各个阶段,巧妙地将受创者欲言又止、进退两难的困境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经历痛失双亲的创伤事件后,班克斯在回忆与讲述时却是充满自信,语气平静,这体现了创伤受害者既渴望述说又逃避痛苦事实的矛盾心理,而恰是这般矛盾心理导致了他们的叙述摇摆不定、模糊不清、自相矛盾,呈现出其创伤叙述中的不连贯、碎片化和跳跃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