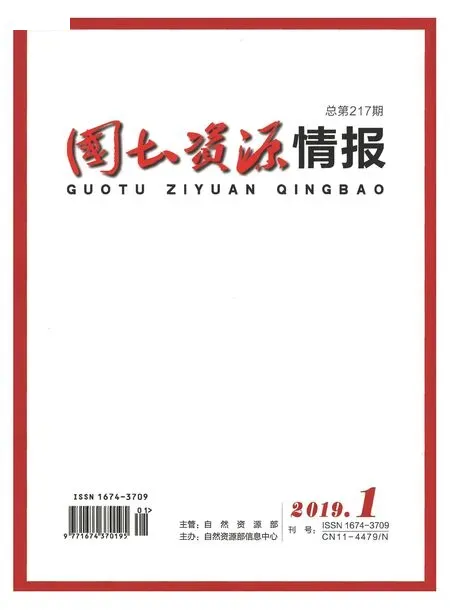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地矿业管理经验与启示
姜杉钰,余星涤
(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北京 100035)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物种丰富,是世界上自然环境最为优美的国家之一。为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海洋公园等多种保护地的方式实现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形成了较为全面和完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矿业大国,被誉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铁、铝、金、铜、钴、煤炭等多种矿产的储量位居世界前列,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澳大利亚政府本着“不给地球留疤痕”的矿业发展要求,为兼顾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尤其在自然保护地矿业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自然保护地的矿业管理是世界性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是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优先的新形势下,如何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研究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地矿业管理经验,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保护地矿业权的处置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现状和管理特点,分析了保护地矿业管理政策和相关法律,进而剖析和总结了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地矿业管理的经验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保护地矿业管理提出了建议。
1 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地现状和管理特点
1.1 自然保护地现状
澳大利亚陆地面积为768万km2,海岸线近37000km,陆上共有50多个类别的保护地、共计10000余处,保护地总面积超过140万km2,接近该国陆地面积的20%[1],近海地带为保护生物礁等也设立有海洋公园等保护地。从类别上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区域保护区、本土保护区和保护公园这5类保护地占据了保护地总面积的90%左右,其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区域保护区和保护公园是澳大利亚各级政府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本土保护区则是为保护原住民居住地自然和文化资源设立的一种特殊保护地[2]。总体来看,澳大利亚保护地的类别多、分类细,体现了保护目标的多样性特征。
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于20世纪90年代逐步建立和完善,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地体系具有较好的对应性。根据保护地的性质、目标等内容,可将澳大利亚的各类保护地划分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体系的6个层级中[1],即Ia严格自然保护区、Ib荒野区、II国家公园、III自然遗迹保护区、IV生活环境/物种管理地区、V陆地海洋保护景观和VI资源管理保护区。其中保护相对严格的I—IV类保护地(以保护自然和文化价值为主)的面积约占保护地总面积的50%左右,而V—VI类保护地(以游憩和休闲为主)则占据另外的50%[3]。
1.2 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由西澳大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北领地和首都特区共同组成,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的土地分为国家土地、私人土地和原住民土地,不同土地上的保护地由不同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具体来看,国家土地上的公共保护地实行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分级管理体制。在联邦政府层面,负责自然保护地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是能源与环境部,该部代表联邦政府管理6个国家公园、27个海洋保护地和3个植物园,澳大利亚国家公园董事会、国家环境保护理事会等非官方组织也协助联邦政府制定保护地政策和管理标准,开展相关实地活动。与联邦政府相比,州一级政府在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中起到更主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均设有自然保护主管机构,如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管理局、昆士兰州环境保护局、西澳大利亚州保护和土地管理局等,其职能包括投入保护地建设和运营经费、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对保护地进行系统管理等。原住民和私人土地上的自然保护地,如本土保护区和私人保护区等,通过政府和原住民及私人协议建立,同样被纳入国家保护地体系,受到国家保护地体系的资助,但其管理主要由原住民和私人,或者委托澳大利亚灌木丛遗产基金会、自然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完成。由于澳大利亚70%以上的土地为私人和原住民所有,为实现生态保护的完整性,联邦和州、领地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私人建立和管理保护地,这也成为澳大利亚未来保护地建立和管理的重要趋势。澳大利亚的保护地管理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样化、多方参与”的特点,有利于缓解区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有利于协调政府-私人-原住民之间的管理冲突[4]。
2 自然保护地矿业政策和法律特点
据统计,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中约50%与矿石有关,矿业生产总值占GDP的7%左右。矿业的蓬勃发展曾一度造成生态环境和地质遗迹的严重破坏。例如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地区就曾因铁矿石开采,破坏了世界上范围最广、意义最重大的旧石器时代石刻艺术画廊,这种破坏直到Murujuga国家公园建立后才得到有效控制[5]。随着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和矿业发展的矛盾冲突成为困扰澳大利亚政府的难点问题之一,其中关于是否在卡卡杜国家公园周边进行加比卢卡铀矿开采的问题就曾引发了北领地原住民、联邦及州政府以及多家企业和社会组织长达近20年的争执[6]。为了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和矿业发展,澳大利亚各方经历了长期的努力和探索,不断深化和细化联邦和州、领地的相关政策,逐步提高矿业和环境等相关领域法律法规之间的适应性和协调性,目前已形成比较成熟的自然保护地矿业政策和法律体系。
2.1 保护地矿业政策
客观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也深知矿山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对地表植被、地下水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造成破坏,但又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矿业发展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陆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较高,但保护地的矿业政策却较为宽松,特殊问题和矛盾的处理也十分弹性化。
研究表明[3,7],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等级,澳大利亚有超过一半面积的陆上自然保护地是允许进行矿业活动的,其他原则上禁止矿业活动的保护地中也保留了矿业进入的弹性准则。例如昆士兰州的284个IUCN III—VI级保护区(不包含自然保护区)中的173个就曾批准过矿产勘探许可证,379个自然保护区中有149个存在共273个矿产勘探许可证,其中186个勘探许可证是在保护区设立之后颁发的[8]。据保守估计,澳大利亚严格意义上不允许矿业活动的保护地面积仅占保护地总面积的25%左右,占国土面积的5%左右,与IUCN关于禁止矿业活动的保护区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的建议十分接近了[3]。
矿山企业若考虑在禁止矿业活动的保护地内进行矿业活动,则需要预先向经联邦或州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相关负责人审议环境评估、资源潜力等材料后,方可获得矿业许可,联邦或州政府主管部门也有权拒绝申请[7],如澳大利亚联邦地质调查局曾向西澳大利亚州政府提出过费兹杰拉德河国家公园(Fitzgerald River National Park)的矿产资源勘探申请,但遭到了拒绝[9]。在允许矿业活动的保护地内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时,政府对矿山企业和地勘单位提出了很高的环境监测标准和土地复垦要求。在企业获得矿业许可之前,矿业和环保部门会严格审查勘查开采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矿业公司还必须缴纳矿山复垦抵押金以保证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在勘查和开采过程中,矿业公司需要依据“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不断完成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合理处理生产排污;矿业活动结束后,有关部门还会按照标准严格审查环境治理情况,对环境治理突出的矿业公司给予一定的表彰[10],如西澳大利亚州每年向环保工作最出色的公司颁发金壁虎奖。
2.2 保护地矿业相关法律法规
澳大利亚联邦和州均具有立法权,形成了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依法管理和处理相关矛盾冲突提供了必要的保证。《1999年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法》是澳大利亚联邦管理保护地矿业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法律,它继承了《1974年环境保护法》的主体内容,规定了保护地内矿业活动的准入条件、矿山环境评估以及复垦要求等内容。1996年出台的《澳大利亚矿山环境管理规范》也是涉及保护地矿业发展的重要法规,其中将年度公共环境报告编写规定为矿山企业的一项基本义务。
各州和领地根据实际情况也在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管理方面进行了立法,涉及了保护地矿业管理的相关内容条款。例如,昆士兰州的《2008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该州《1992年自然保护法》中划分的国家公园、森林储备区、湿热带遗产保护区、沿海大堡礁保护区以及海洋公园等A类环境敏感区不允许进行矿业活动;在自然荒野区、世界遗产管理区、生态系统濒危区、文化遗迹保护区等可以进行矿业活动,但矿业活动开展前需要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产生争端时通过协商或者仲裁机构进行裁决[11,12]。西澳大利亚州的《1978年矿业法》规定:一是在国家公园、保护公园、州森林保护区等A级保护地内的矿业权授予,需要征得州议会批准,其他自然保护地内进行矿业活动需征得州环保部长同意;二是保护地内开展的矿业活动需按规范程序进行,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也应达到相应要求,对于违规操作或环境破坏严重的矿山企业,政府有权进行处罚或收回矿业权[9]。南澳大利亚州《1992年荒野保护法》规定,荒野保护地存在允许采矿和禁止采矿两个部分,其中两种情况下允许采矿,一是设立之前已经授予的采矿权,政府需要向采矿者发布保护地设立的声明,并要求其开采过程中不得破坏环境,否则依法有权终止采矿活动;二是保护地设立以后,采矿者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可以获得采矿权,但需承诺在开采过程中不得破坏周边环境[13,14]。
3 自然保护地矿业管理经验和典型案例分析
3.1 允许战略性矿产在保护地内的矿业活动,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
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给予石油、天然气、铀矿等战略性矿产在保护地内及周边的勘探开发空间,但是对矿山环境监测治理和土地复垦向来十分重视。1983年西澳大利亚州曾允许在卡里吉尼国家公园(Karijini National Park)进行战略性和稀缺高价值矿产的勘探开发活动[9]。为保证铀矿的供应,澳大利亚北领地卡卡杜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 所环绕的世界第二大铀矿山——兰杰铀矿(Ranger mine)也一直被允许开发生产,但政府要求矿山作业时要严格把关邻近Magela湿地和Alligator河流域的核污染监测,企业为此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污染监测技术的研发[15,16]。同样,为了保证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允许在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地的生态核心区(生态脆弱或保护价值极高的地区)以外部分进行油气勘探开发,但石油公司必须进行严格环境管理和评估程序,同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监测油气勘探对近海环境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最大的天然气开发项目——西北大陆架天然气项目在环境管理方面的支出就超过了750万美元[17]。
3.2 调整保护地等级,协调保护地和矿业权边界和位置
澳大利亚矿业发展的历史悠久,而自然保护地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完全建立起来,这导致很多矿山企业在保护地设立之前就已经持续生产了很多年。为了合理解决新建保护地和已有矿业权之间的位置冲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取了调整保护地等级和协调边界位置的方式予以解决。
以西澳大利亚州为例,自1971年开始,该州环保局开展了拟建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位置和范围的核查评估工作。结果显示,拟建的936个保护地中有454个涉及了123个矿业或石油勘查开采权益,通过调整保护地边界和降低保护地等级,最后只剩8个矿业权还位于保护地内,大大减少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了弥补避让矿业权造成的保护地质量和面积的损失,西澳大利亚州政府还将原先拟建的672个无矿产资源潜力的B级和C级保护地升级为A级保护地[9],避免了未来可能存在的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
3.3 鼓励矿业权人自愿缩减边界或者完全退出保护地
对于禁止矿业活动的保护地,经边界调整无法避让的矿业权,州政府大多数会鼓励矿业权人自愿缩减矿业权边界或者退出。2014 年,西澳大利亚州设立的金伯利国家公园涉及了力拓集团和美铝公司的5亿t铝土矿储量和14个采矿租约。出于树立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和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有限等原因,2015年,力拓集团和美铝公司主动放弃了新矿山的开发计划,同时同意支付约75万澳元用于复垦[7]。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为鼓励矿业权人和矿山企业主动同政府联系,协商解决保护地和矿山重叠问题,提出矿业权人可在任何时间自愿削减和放弃国家公园和地区公园内的矿权地,如果能在变更前提出自动放弃矿业权,政府部门将考虑授予该矿权人持有其他类似矿业权一个放弃假期(relinquishment holiday)[18]。
3.4 矿业权强制征收并给予补偿
上文已述,澳大利亚在自然保护地划界定级时已考虑到矿业发展的相关问题,而且大多数保护地内也并不完全禁止矿业活动,因此自然保护地矿业权强制退出的情况并不多见。尽管如此,由于在环境保护要求较高的保护区内严禁采矿,因此征收之事也时有发生。澳大利亚通过司法裁决及立法规定,自然保护地的主管部门或更高层次政府有权对自然保护地内的矿业权进行征收。
昆士兰州所辖的弗雷萨岛大部分属于森林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早期因保护地管理体制不健全,昆士兰钛矿有限公司和DM矿业公司等陆续在保护地内建立起金红石、锆石和钛铁矿等矿区,引起了一些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后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审议和论证后,决定仅保留该岛面积的10%作为采矿区,其他位置禁止采矿,已有的矿山企业全部退出和关停,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受到影响的两家矿业公司赔款450万澳元,还为失业人员提供了100万澳元的补偿[19]。
3.5 依法处理矛盾和纠纷
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处理矿业权和保护地冲突提供了法律保证,在政府、企业、个人的相关利益无法协调时,法律途径成为澳大利亚解决保护地矿业冲突的重要手段。2001年,必和必拓公司因不满当时澳大利亚州环境和遗产部拒绝该公司在金门山国家公园(Gammon Ranges National Park)内采矿权的延期申请,将其告上法庭,南澳大利亚州最高法院受理了该案。法庭经过权衡南澳大利亚州《1971年采矿法》和《1972年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法(SA)》的相关条款后认为,澳大利亚环境和遗产部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必和必拓公司无权在金门山国家公园获得采矿权延期[20]。
4 对我国的启示
4.1 建立完善保护地体系
澳大利亚的保护地建设始于1866年,在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历程中,联邦和各州政府协调解决了各级管理混乱、空间重叠和保护标准不同以及各方利益冲突等问题,最终形成了标准统一、协调管理、相对完善的保护地体系。同澳大利亚相比,我国保护地建设起步较晚,目前仍面临着保护目标模糊、机构责任不清、空间布局交叉重叠等问题,建立完善保护地体系是完善保护地矿业管理的前提条件。建议借鉴IUCN的保护层级和目标,优化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框架下的自然保护地管理和监管体制,形成多方参与的综合性规划。
4.2 实行保护地矿业权差别化管理
考虑到实际国情,澳大利亚对保护地内的矿业权实施了严格监管前提下的适度弹性管理政策,多措并举协调生态保护和矿业发展之间的冲突和问题。与澳大利亚十分相似,我国也是兼具优美生态环境和丰富矿产资源的大国,如何在生态保护的同时谋求矿业的平稳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鉴于澳大利亚的经验,我国可综合考虑不同保护地层级和目标、不同矿种的战略定位、不同开发方式的环境扰动等因素,实行矿业权的差别化管理。具体而言,一是针对无法避免严重环境破坏的矿业活动,应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采用调整边界、鼓励资源退出和强制退出的多种方式,避免各方利益的直接冲突,强制退出应给予相应补偿。二是研究制定保护地内矿业权差别化准入标准,在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允许保护地内非核心生态功能区(如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油气、铀矿等能源和战略性矿产的勘探和开采活动,以保证国家资源安全,在矿业活动的同时,加强全过程的环境影响评估和监测;三是地热、矿泉水等对环境影响十分有限的流体矿产,可考虑在允许人类活动级别的保护地内开采,以便更好地开发旅游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环境保护。
4.3 完善配套法律法规
澳大利亚的联邦和各州关于保护地和矿业权的各类法律为保护地矿业权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撑。相比之下,我国仅有一部《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了保护地内禁止的相关活动,《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仅笼统地涉及了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等约束性条款,法律层面缺乏生态保护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管理层面缺乏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导致保护地涉及的矿业权管理无法可依,差别化管理政策难以落地。
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一是出台保护地管理相关法律,明确保护地内矿业活动的准入条件、矿山环境评估以及复垦等要求,为保护地矿业权管理提供法律支撑;二是建议修改完善《矿产资源法》,体现生态保护的原则,加强与保护地相关法律和制度的衔接;三是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未出台之前,可以由省级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法规政策或地方规范性文件,明确生态保护、矿业权管理部门与矿山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