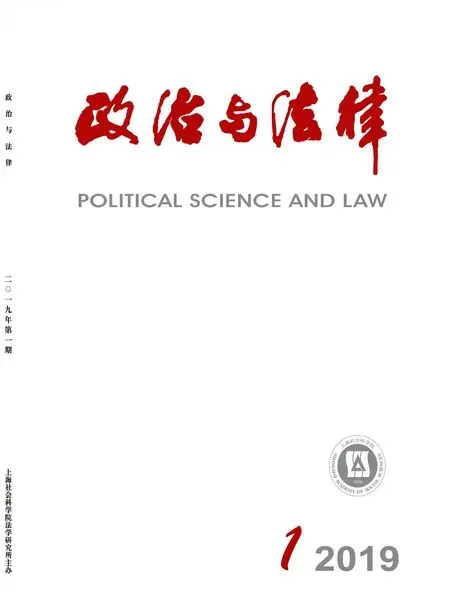“法律解释权”行使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陈金钊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上海200042)
法谚有云:“法无解释不得适用。”由此可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实际上拥有着“法律解释权”(以下简称:“解释权”)。①笔者对“解释权”和法律解释的理解主要是从法律方法论或者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的。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体制将解释权定性为国家机关对法律条文进行抽象性解释的权力,至于具体纠纷中的法律解释则以法律适用的名义展开,“解释权”成了“法律适用权”的组成部分,但恰恰是这种具体纠纷中法律适用者(执法者、司法者)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权”才是法律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权”。为了避免歧义,笔者于本文中以加引号而表示特定含义的“解释权”与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的解释权相区分。“解释权”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解释权”行使的宪法性和原则性规制。这一宪法原则的落实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解释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思维方法的支持。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制定“法律解释法”,另一方面也需要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法律价值和法律方法来限制“解释权”的任意行使。“解释权”不仅需要依文义解释的方法依法开展,还需要把人权价值融入其中。否则“解释权”的任意行使将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难以落实。“解释权”的行使是一种思维活动,无法完全通过行为规则来约束。因此,对“解释权”的规制就需要由法律思维规则来完成。笔者于本文中主要论述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引入价值指引,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研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解释权”的行使过程中如何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①
一、“解释权”行使中人权价值的缺失
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表明了我国推进“人权保障”的信心与决心。自此之后,在宏观立法层面,“人权保障”的国家要求和宪法义务得到了认同。然而,在司法、执法等微观层面,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缺乏价值指引、有效监督和规则约束的“解释权”,有时会偏离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会因为忽视人权等价值而导致对法律的机械运用。更有甚者,披着“解释权”的外衣所进行的权力寻租还会对公民的具体人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解释权”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流失在了“解释权”的行使过程之中。这种情况决定了研究者需要及时探寻应对方法。
(一)文义解释的绝对性需要加以限制,人权价值需要融入司法、执法
在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存在“解释权”是正常的,同时,“解释权”的行使需要多种方法的运用。然而,在依法办事经过多年的宣传后,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认为依法办事就是在思维决策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办事,因而把文义解释当成了唯一的解释方法。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曾出现过,人们称那个时代为严格法治时代。在那个历史时期文义解释成了黄金解释规则,然而随着单一文义解释方法的弊端逐步呈现,体系解释规则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对价值、目的的强调,使得文义解释的绝对地位逐渐被“文义解释优先”所替代。“文义解释优先”意味着在法律运用过程中,需要首先使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同时还需要将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法律价值纳入解释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近些年我国一些有争议的案件中的法律解释,诸如“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展现的都是对法律的死抠字眼式的理解和解释。虽然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础性方法,对保障法律意义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将法律规定及其文义解释绝对化。“解释权”的行使不仅需要依凭文义解释的方法,还需要人权价值的释放以及体系解释的运用。
法律解释具有“规范机能”,②所谓法律解释的规范机能指的是,“理解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决定判决的基准或社会生活中一般行动的准则”。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法律解释的结论会经由法律适用环节对诉讼或纠纷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要满足“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解释权”的审慎行使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解释权”运行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注意到人权价值的指引,也不重视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方法的意义。某些解释结论不仅令普通民众大为诧异,也足以令法律职业共同体感到不安。这些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产生的解释结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人权价值的指引以及没有对法律进行体系性解释。
“火车不是机动车”的解释结论因“高荣梅诉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以下简称:“高案”)、③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行再提字第003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宁行终字第155号行政判决书和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2005)白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书。“张萍诉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而进入人们的视野。④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行终字第121号行政判决书。实际上关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依法”判断,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绝非个案。在“高案”中,吕明英(高荣梅之女)因下班穿越铁道回家时被货运列车撞伤致死,高荣梅向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时被该局告知吕明英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称火车不属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在随后提起的两审行政诉讼程序中,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可了这一解释结论。直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指出须从工伤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解释相关争点时,一、二审判决和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才最终被撤销。
“玩具枪也是枪”这一解释结论由于“赵春华案”的迅速传播而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同时,“王国其案”“刘大蔚案”也作为类案引发了广泛争议。在“王国其案”中,⑤参见《男子出售20支仿真枪坐牢四年,申请67万元国家赔偿》,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6-04/21/c_128915911.htm,2018年7月30日访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刑一复字第54号刑事判决书。王国其原系来广州打工的河北省邯郸市农民,以在广州一德路卖玩具为生,2009年10月,王国其却因涉嫌枪支犯罪被捕。2010年5月,王国其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随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维持原判结束了二审程序。虽然在2012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并将王国其的刑期由10年减为4年,但涉案罪名仍未改变。2014年12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出撤诉被裁定获准,当王国其向法官询问是否会再次被起诉时,法官称其应向检察院咨询。带着困惑的王国其因不满来源不明的撤诉裁定,随后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该人民法院撤销了该裁定,并发回重审。2016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才向王国其送达了不起诉决定书,最终认定“王国其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
法律的应用就是法律解释。仅仅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可能会产生错误。缺乏人权价值约束的“解释权”可能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假如“解释权”的行使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工伤保险是职工的社会救济权利,他可能就注意到这种权利的人权属性,就会从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从宽解释,而不是死抠机动车的概念,也就不会“依法”得出“火车不是机动车”的结论。⑥其实,相关立法把机动车撞伤作为工伤标准,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只有被机动车撞伤才是工伤,减少了上下班途中职工获得救济的机会,实际上是对权利的“克减”。体现人权保障的规定应该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意外伤害,达到严重的程度可认定为工伤”。假如“解释权”的行使者能从被告人权保护的角度思考法律的意义,也就不会产生“玩具枪是不是枪”的争议。“法治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不是仅仅服务于建立和维护法律秩序,还是为了达成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这一事业的达成以确认人的尊严为条件,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目的。”⑦李桂林:《实质法治——法治的必然选择》,《法学》2018年第7期。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的是对良法善治的追求,然而只关注法律规定,“解释权”的行使者却走向了良法善治的对立面。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不仅需要文义解释,还需要体系解释,尤其是人权价值的指引。
(二)“有权解释”不等于可以机械运用法律
马克瓦德(OdoMarguard)曾这样追问过解释的意义:“解释学是一门艺术,即从文本中得到其中没有的东西。问题在于:既然有了文本,还要解释干什么?”⑧转引自[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这是对法律解释必要性的追问,表达的是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其深层含义是对过度解释的批评。然而,法律离开解释必定无法实施。正是因为有了法律文本的存在,才有了关于法律解释的学问。文本是法律解释的对象,文本的一般性、抽象性以及意义的流动性为解释留下了很多空间。按照保罗·利科的说法,“文本就是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⑨[法]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文本是立法者用法律语言所固定下来的法律规范。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一般性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具有天然的缝隙,需要通过解释予以弥补。关于“有了文本为什么还需要解释”的追问,其实不是对解释必要性的否定,而只是对法律意义固定性的捍卫,所指向的问题是过度解释所带来的解释困境,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运用不需要解释。法律只能在解释中运用,但法律解释有多种方法,文义解释只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法治反对解释”仅仅意味着人们对清晰的法律只需要在认定意义上的解释。法律意义的整体性以及解释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指引和体系解释的必要性。
从“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这样的类案中可以发现,“解释权”行使者解释时不具备体系思维能力,在解释有关概念术语时,既不考虑人权等价值,也不考虑法律的体系因素,只是以死抠字眼式的方式解释法律条文用语。如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的机动车概念去解释工伤保险事故用语,而不管法律是否与案件具有相关性。对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罪中的“枪支”的解释,只考虑法律用语的意义,而没有思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体系要素。可以说,在法律运用或法律解释过程中,对法律价值、目的的遗忘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失,助长了机械执法和司法的方式的蔓延。笔者对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一般人看来都会认为是荒谬的解释结论反而在司法实践中持续发生呢?原因之一就是权力的张扬,它致使一些人认为,只要有“解释权”,能够找到决策的所谓“法律依据”,其判断就是正确的,只要“依法办事”,符合文义的要求,体系解释的方法就可以不使用,人权价值、法律目的就可以不考虑。
“解释权”如何行使是法治建设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们需要意识到,任何法律运用都不是单一法律方法的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价值引导的除弊解释等构成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一方面,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权力,“解释权”的行使无疑必须符合规范性的要求,即恪守法律的含义,根据具体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行使者以合乎立法目的、合乎人权保障的方式推进法律解释活动,死抠字眼式的执法和司法的方式,除了带来“解释权”对人权价值的伤害之外,更会对形式法治的声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的确有些人认为,机械司法、执法是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机械司法并不是形式法治的必然结果,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运用形式法治方法”。⑩陈金钊:《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形式法治并不是忽视实质价值因素,而是为了避免陷入过度的价值纷争。形式法治的核心是强调“在法律适用的形式平等和法律制度的安定性之下,人们可以有依据地规划其未来的生活,从而使得人类生活变得可以预期和可以控制,社会秩序和安全感由此得以形成”。①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形式法治的理论抱负绝不是为了机械的适用法律,而是为了在方法上促成法治。机械执法司法的形成与形式法治无关。特别是中国的机械司法和执法者,内心往往缺乏法律方法的意识。很多人之所以机械执法司法,除了缺乏法律思维和科学的法律方法指导,更多的是在回避法律适用的理性论证义务,以“合法”为幌子逃避社会对法律适用的追问和责难,用貌似“合法”的思维来掩盖不讲理的行为,或用“法律依据”掩护“解释权”的简单粗暴行使。法律解释必须排除死抠字眼式的执法和司法,需要坚持价值引领和其他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否则,类似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的解释结论还会重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失落在“解释权”的行使中,也会一再发生。
(三)“解释权”不能沦为权力寻租的合法外衣
朱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论及农村地区法律规避的合理性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论断:“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②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笔者认为,在这些成本中,借着“解释权”进行权力寻租也是相关权利主体在寻求法律救济时不得不面临的情况。更有甚者,还存在以“解释”的名义帮助不法当事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情形。这样的执法和司法当然无助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的落实。
由于事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行为”主要是思维活动,与一般的违法行为不一样,“解释行为”是以有权解释机关的面目出现的。正是因为有权做出解释活动,所以很多忽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行为”首先体现在错误的思维之中。这种纯粹的思维活动,由于不是具体的“违法行为”,就存在取证难、认定难、制裁难的问题,并进一步导致了法律责任、法律惩处的灰色地带的出现。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在执法领域,还是在司法领域,权力寻租多出现在“解释权”行使的这些灰色地带。违法犯罪会受到惩处,这是“解释权”行使者都心知肚明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警钟长鸣,特别是终身责任制的实施,使得这一领域的贪腐有所减少。然而,很多人也已经看清,“解释权”的行使这种思维过程既可以扩张法律的意义,又可限缩法律的意义,而上下左右、扩张伸缩的解释,对案件处理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很多牵涉到公民权利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也存在着可办可不办的空间,这就出现了“依法刁难”问题,③参见陈金钊、吴冬兴:《正视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方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拿到好处就办,拿不到好处就不办”成了极少数人的工作信条。“政府的权力在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严重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取消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万能的政府更加任性,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这与人权保障的要求相悖,与人本政府建设的要求相悖。”④吴传毅:《由人权保障原则看人本政府的构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利用“解释”进行寻租就以这种“合法”的形式展开,而利用“解释权”寻租一旦背离了法治的要求,就可能产生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因为司法、执法的很多方面都与公民的基本人权息息相关。
考察上述现象之后人们就不难理解,近些年来争夺“解释权”的现象为什么会蔓延,为什么若干“简政放权”的后果就是放掉的权力借着“解释权”的名义实现了权力的复归。其根本原因就是很多此类的“解释权”的行使空间成了权力寻租的场所。由于“解释权”是法律运行中的必要权力,“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貌似合法的寻租机会。以解释之名曲解法律、利用法律、玩弄法律的行为,多是以守法的名义所进行的活动,而以有权解释之名进行的解释性思维活动,又很难在“行为”上断定是否违法。所以,对那些在思维上不明显的权力寻租,就很难靠对行为的制裁来解决。相对于行政、司法领域赤裸裸的徇私枉法行为,隐性的、借着“解释权”进行寻租的权力行使方式对“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诉求造成了更加深远的不利影响。
二、为何“人权保障”会在“解释权”行使中流逝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即使人权价值、理念、制度等具有相同的表述,基于机制、体制、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和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人权价值和制度的具体落实仍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当中国接受外来的人权观念(概念)以后,理论研究者必须进行主动的解释。然而,主动解释也不是任意的解释,而是需要接受法律价值和制度规范的约束。在当代中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宪法原则,需要将其贯彻于对具体执法和司法案件的解释过程之中。人权价值、理念、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与人们对人权价值和制度的认同程度、解释方式的运用有密切关联。这样看来,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之所以会在某些“解释权”的行使过程中难以彰显,从实践的层面看,是因为执法和司法过程缺乏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法律解释规则的支撑;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看,是因为立足“解释权”的“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的研究相当不够;从制度的层面看,是因为作为国家权力的“解释权”游离在制度之外。
(一)法律解释实践中缺乏“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有效的解释规准(Valid canon)反映了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求法官在适用它们时进行价值判断”。⑤William N.Eskridge,Jr.,The New Textualism and Normative Canons,Colum.L.Rev.531,552(2013).在对美国制定法解释的研究中,就有一种基于描述进路的法解释研究。法学家们尝试从理论的角度,对活跃在制定法裁判实践中的各种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法律解释规则,进行理论上的识别和区分,详细分析实践中不同的解释规则背后所体现的各种实质价值因素,并试图以“解释性普通法”“解释的一般法”“解释性推定”为视角对其进行定性。⑥See Gluck,Abbe R.,The Federal Common Law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Erie for the Age of Statutes,William&Mary Law Rev,753(2013).See William Baude&Stephen E.Sachs,the Law of Interpretation,130 Harvard Law Rev,1136(2017).这些研究所共同反馈的信息就是,在制定法的解释实践中,具有拘束效力的法律解释规则对法律条款和法律价值的落实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可以转化为自觉的解释行为。“法律要想实现统治,就必须付诸实施。但是当法律被实施时,不是法律而是其实施者在进行统治。为了让法律的实施者遵循法律的意旨,他们就必须不仅要服从法律,而且要服从更强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可能是非以法律形式呈现的。”⑦Richard Stith,Securing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Interpretive Pluralism:An Argument From Comparative Law,35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401(2008).“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价值诉求和宪法原则的落实,要求“解释权”的行使者在行使这项权利的过程中受到相应的法律解释规则的约束。这一解释规则就是“人权保障”的解释规则。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法律解释实践中,系统性的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法律解释规则并未得到彰显,各种以管理为导向,以方便权力行使和规避行政义务、司法义务为导向的解释理念却颇有市场。偏离“人权保障”要求的文义解释,有可能引起对法律的滥用、误用和错用。现实中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对意义模糊、矛盾的法律含义的解释上,而且已经蔓延到很多法律条文规定明确之处。在“火车不是机动车”这种解释类案中,由省级审判机构做出了“应当从工伤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解释相关争点”的表示后才使解释问题最终定论;在“玩具枪也是枪”这样的解释类案中,甚至使得当事人经受牢狱之灾,导致国家赔偿。这些偏离人权保障要求的“解释权”的误用和滥用现象,既对涉案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已然损害了良法善治的声誉。
(二)对“尊重人权”研究不足,助长了法律解释中的价值遗忘
我国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以后,研究者围绕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展开了多方面研究,使其成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热点问题。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之后,笔者认识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需要体制、机制、规范等,还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话语权体系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和解释方法。从现状来看,学者们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方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很少有立足“解释权”角度的研究。人权入宪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但人权的落实,不仅需要宪法的规定,还需要具体法律的保障,需要把人权落实到司法、执法活动之中。特别是尊重人权的实现与解释活动或者说“解释权”的行使联系密切,这就需要将人权价值、制度融入解释方法。以往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制度的完善,而对实际存在的“解释权”以及对解释过程的规制研究不足,出现了立足“解释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研究的缺失。
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就保障来说,有立法的制度保障、执法落实和司法救济的保障。然而,对于尊重人权来说,如果没有思维方式或解释方法的支持,有可能成为法律名义上的道德要求。笔者在“中国知网”(截至2018年1月)中以“人权保障”为“篇名”进行搜索,有1948篇文章;以“人权保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文章2769篇;以“保障人权”为“篇名”进行搜索,有3176篇文章;以“尊重人权”为“篇名”进行检索仅有356篇文章,以“尊重人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仅有16篇文章。在对这些论文进行研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虽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在内容上有交叉,但通过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到,人们对“人权保障”或“保障人权”的研究比较重视,而对“尊重人权”的研究不够重视。之所以对人权保障研究较多,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较多,而尊重人权需要在解释、论证的过程中完成,它主要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对文化心理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为持久的关注。其二,人权保障有很多具体的措施,主要是制度保障、机制体制保障、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对损害的救济、人权保障行动计划、人权保障评估等。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其问题意识、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比较容易凸现。尊重人权的问题没有保障人权的问题多,其问题意识也不是那么明确。其三,尊重人权是一种主观心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属于综合性的基础研究。人们无法仅仅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确定什么是“尊重”人权,以及不尊重人权该如何进行处置。笔者认为,在“解释权”行使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权,以人权的名义进行解释,是落实人权价值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尊重人权是文明社会的理性思维方式,以人权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具有批判与反思、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功能。
需要看到,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尊重人权,才有可能保障人权。虽然宪法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仅仅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所有的国家行为都是由人(即那些有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做出行为的人)来完成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意味着立法者应该创设人权保障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修改、废除那些不尊重人权的制度和规范。执法者、司法者不仅要恪守尊重保障人权的法律规范,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价值的实现。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保障有多种方式。将人权价值制度化、法律化是立法途径。立法者创设保障人权的法律以后,执法和司法同样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主要路径。要在司法、执法过程中较为全面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必须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第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权保障的研究很多,相比较而言,行政法、社会法等关于人权保障的研究较少。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人权观念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但是由于机制、体制、文化传统等原因,对人权中的社会权等还没有充分的认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常常被称为‘社会权’,是人权发展到20世纪后增加的主要内容。它指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充分发展个体生产和生活能力的保障和良好个体精神人格和社会人格的权利。一般包括个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和获得社会保障权等。”⑧龚向和:《社会权的概念》,《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笔者发现,人们虽然对人权、社会权、劳动权等有旺盛的需求,执法过程中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部分工作人员法律运用过程中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人权,在解释社会权、劳动权的时候,往往是死抠字眼,机械执法。
第三,对人权尊重、保障的主体、行为和制度研究较多,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或实现方法的研究较少。现有的人权保障研究可分为行为、主体和制度三种。应该说,这种研究已经很全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缺乏对“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其主体研究包括对罪犯、犯罪嫌疑人、儿童、艾滋病患者、弱势群体、妇女、农民工、劳动者、未成年人、卖淫嫖娼者、吸毒者、农村人口等主体的人权保障研究。其行为研究包括对民事裁判、刑事诉讼、逮捕、刑法裁量、法律监督、战争、司法、刑事和解、侦查环节、刑罚、立法、反恐、强制执行、违宪审查、公安行政执法、风险防控、维稳、国家治理等行为中人权保障的探讨。其制度研究主要是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制度建设的角度论述人权保障。在这三类研究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章主要涉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原则、标准、思想、机制、体制、模式等“本体”问题,也有一部分文章把“人权保障”作为视野、视域,展开对其他问题的研究。
虽然各学科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都会牵涉到“解释权”的问题,但对此问题却只有少数学者从司法角度展开过研究,对行政执法和社会法解释的研究不多见。这说明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没有深入到思维方式或方法论层面。在现有的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只有少数学者从解释学、“解释权”的角度研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只有大约5篇文章直接涉及法律解释方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例如,林来梵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增设,可誉为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点睛之笔。它标志着现行宪法首次用一个概括性条款确认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不仅在法解释学上具有丰富的意涵,而且在规范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⑨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在宪法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表明了我国全面解决人权问题的信心和决心,但还需要正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方法,即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如何贯彻人权制度、理念和精神这一问题。人权的实现需要通过有权解释来理顺权力与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⑩罗豪才:《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人权》2009年第6期。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保障人权的实现。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入宪,但还需要解释主体发自内心地接受人权价值体系,将人权价值体系融入对法律的体系思维之中。
(三)“解释权”游离于制度之外
“解释权”原本是指解释主体阐明法律意义的权力。有权主体享有对模糊、矛盾法律规定甚至法律空白的意义释明权。权力的行使直接决定法律的范围、明确法律的意义。因此,人权价值、制度的实现程度与法律解释存在着很大关联。一般来说,司法、执法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执法、司法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国外法学对法律解释非常重视,因为法律如何解释对人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很多国家都制定了规范法律解释的法律。在中国,与现代法治相匹配的法律思维模式还没有定型,法学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宏观权力的研究,而对涉及人权保障等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实际上,对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不仅需要其他法律制度的配套支持,还需要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解释法予以保障。
从国家机关的分类来看,国家权力的行使有多种形式,如立法、执法、司法、监察等,“解释权”是与这些国家权力相伴随的一种权力。目前,我国在《立法法》中对法律解释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认为其属于法律的“废、立、改、释”之中的释法性权力。对司法和执法领域的法律解释,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具体法律适用过程中有司法解释的权力,行政机关只有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有解释的权力。从制度上看,很难找到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的规定。然而,实际上法律解释权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法律规定的一般性解释,这种解释也可以称为机关的规范性解释,另一种是对法律规定在具体个案中的解释。我国没有统一的法律解释法,只有零星的有关法律解释的规定,因此,对法律规范的一般性解释存在着随意解释的现象,同时,现有制度对个案中存在的“解释权”却视而不见,缺少相应的规则和程序。这样,个案“解释权”在很多情形下就成了制度外的权力。
把“解释权”置于法律制度之外,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任何权力都应该是制度内的权力,从总体上看,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的途径。就制度建设来说,目前迫切需要制定“法律解释法”,不然就很难把执法、司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法律解释权”纳入制度可约束的范围。质言之,“解释权”的行使需要制定法的规制。并且,制定“法律解释法”也是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需要。这一原则是一种责任或义务性规定,明确了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或义务主体。国家机关在行使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权力时,应该遵守这项义务或履行该项责任。任何权力都不能是绝对的权力,都必须有责任或义务与之匹配。国家权力也不是绝对的权力,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所有法律解释者的责任或义务,因而需要加以制度化。“法律解释法”一方面需要对解释主体资格加以规制,另一方面还需要设定解释的原则、规范和程序。
三、如何在“解释权”的行使中“尊重和保障人权”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解释权”的行使过程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取消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解释权”。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的尝试已被法律发展史证明为不可行,同时,“行政权所处理的事务覆盖面极为宽广,且行政机关数量远远多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就决定了行政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内容广泛、数量众多、层次繁复、形式多样”。①魏胜强:《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评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司法、执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取消实际存在的“解释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制定“法律解释法”,对“解释权”行使进行法律规制,但在“法律解释法”出台以前,应尝试从法律方法或者法律思维规则的角度制约“解释权”,强化对“解释权”行使的法律价值、人权观念的阐发。
(一)全面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国家”,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社会组织等,这些机关、组织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对人权尊重和保障的责任,需要体现于对人权尊重的思维过程。在法律思维过程中,“规范性解释是我国法治生活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解释权则是启动和证成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享有解释权的执法机构就其管辖范围内的文本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范性解释,并将其作为在规制垄断行为、处理具体案件时实质上的规范依据”。②金善明:《论反垄断法解释权的规制》,《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然而,在当前我国的司法、执法活动中,还有一些相关工作人员没有正确理解“尊重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意蕴。要做到正确理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需要人们认识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既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原则中的核心原则,那就意味着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或者说义务主体。具体地说,各类国家机关如立法者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等均包括在内。在法律运用和解释的过程中,“国家的义务首先是尊重人权”,③同前注⑨,林来梵、季彦敏文。“强调人权就是强化国家的责任”。④参见前注④,吴传毅文。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种义务,意味着在其进入法律解释环节之后,就指明了思维必须尊重和捍卫人权的解释方向,应该把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原则落实到思维过程之中。因此,“尊重”进入法律解释领域后,“法解释学就不得不赋予它具有实质性的法律内涵,从而避免虽然宪法规定了‘尊重人权’,但流于空洞化”。⑤同前注⑨,林来梵、季彦敏文。“尊重”不是单纯的心理状态,而是需要代表国家行为的主体接受人权价值的约束。
第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除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社会组织。只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最重要的主体,不仅自己要带头尊重和保障人权,还要督促社会组织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概念和人权的实现是充满矛盾的关系,需要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调整解决。”⑥韩大元:《国家人权保护义务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功能》,《法学论坛》2005年第6期。这就意味着不仅国家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社会组织、经济主体等也负有同样的使命。“人类有智慧解决在各种社会资源中发现、完善有利于人类自我发展的各种有效途径。”⑦同上注,韩大元文。人权不完全等同于可能包含个人特征的“个人权”。人权是指人人都能满足的基本需求,是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是要求他人、社会、国家等把自己当成人看待的权利。法治的核心就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权。然而,法治对人权的保护不是简单的规则之治。⑧参见陈忠林:《自由、人权、法治》,《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同时,人权保护需要其他规范与之匹配。因为人权观念和价值体现在各种法律之中,仅仅靠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并不足以保障人权,还需要各个部门法的积极配合。只有各个部门法都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才能使这一原则不至于落空。要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思维方法,就应当规制“解释权”滥用法治话语权和构建相应的法律思维模式。
第三,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正确理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运用法律方法,否则随意解释就会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不仅需要,而且可以通过法律方法进入执法、司法过程,主要方法就是运用人权保障的原则对人们的思维过程进行价值评价,对行为的合宪、合法性进行规范认定。这样,人权保障原则可以作为认定主观过错的考量要件,也可以作为合宪性解释的依据。⑨参见张豪:《民事裁判中人权保障》,《北方法学》2007年第2期。需要在探索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基础上,将人权原则导入法律解释的规则体系。侵蚀人权的“解释权”行使活动,现在还没有办法获得救济。因而,目前首先需要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涉及公民权利的法律进行正确、恰当、合法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恰恰需要法律方法的介入。
(二)塑造规制“解释权”滥用的人权话语权
在我国,法律解释权由国家机关拥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有审判解释权,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有解释权。目前我国还没有在制度上授予作为个体的国家工作人员解释法律的权力,但实际上授予机关的解释权,需要由个人以机关的名义行使。从“解释权”的来源看,解释权有两种:一是来自法律规定(授权)的解释权,二是来自话语权建构的“解释权”。“话语权即受制于多维的言说空间。角色关系的多重性为个人话语权提供了选择的余地,也决定了话语权的多重界定。言语交际的双向性、动态性使话语权既包括话语言说权,也包括话语解释权。两套话语权系统既密切关联,又各自相对独立。将话语权放置于多维言说空间中考察,既是对话语行使权力的界定,又是对话语表达策略及交际界面的审视。”⑩祝敏青:《多维空间的话语权》,《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影响力意义上“解释权”就是话语权。要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必须塑造人权话语,建构人权话语体系,以影响关涉人权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方式。
“福柯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是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其中最深刻的含义也正是需要我们在迷宫般的物化丛林中,用话语来构造出一片天空。”①张一兵:《〈回到福柯〉:穿越断裂的思想丛林》,《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31日。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十分注意运用政治话语构建话语权,然后用政治话语权将人们的思维、行为引导至政治家所期待的方向。如今,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做法得以提倡。这就需要塑造法治话语,用法治话语引导“解释权”的行使。法治话语就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用法治言辞构造法治天空,用法治影响人们的思维走向。法治话语体系包含人权话语,因为人权构成了法律、法治的基本价值。如果在法治话语中没有人权观念,法律解释就可能偏离人权制度和价值。自由、平等、民主以及人权保障均属于法治价值,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如果不顾及人权保障价值就会招致人们的批评,这体现了人权作为话语的“权力”。
目前人权话语对法治思维的影响还不够。因为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在价值追求上特别重视“秩序”。“秩序”具有压倒其他价值的分量。为达到“秩序”就必须非常重视权力的管理功能。很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最后一条,都不忘记加上“解释权”的归属。然而,在行使“解释权”的时候,却不是把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习惯于在方便管理的意义上行使“解释权”。需要意识到,权威不能仅仅因权力而获得,还应该因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拥有。权威不能代替平等的解释、自由的论证以及对正义的探寻。这就牵涉到是通过实质解释还是形式解释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如果因为权威而没有了平等解释、自由论证,行政相对人、纠纷当事人就可能不仅会失去表达意见的机会,而且其人权还可能受到伤害。
(三)构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模式
在法律规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中国的法治建设遇到了“解释”的困境或陷阱。可以说,“解释权”的正负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从正面功能来看,“解释权”于其中发挥着双层功能。其一是启动法律解释操作的依据。法律解释是有权解释,攸关执法判案之合法性与妥适性,因而须依法据理地开展。唯享有“解释权”的执法主体方有资格启动法律解释并依此执法判案。其二是合理解释的法律保障。“法律解释旨在明确文本规范中的概念内涵和法律意义,但执法机构时常基于自身执法需要而作出扩大或缩小解释,甚至越权或滥权解释,超越了法律解释的边界。”②同前注②,金善明文。从负面功能来看,“解释权”可能导致法律文本规制作用的下降,甚至还可能导致借解释之名曲解法律、漠视法律,模糊规范本身的内容,偏离规范价值的取向。
那么,如何走出解释可能带来法律意义的混乱或者偏离价值的困境呢?对此,有两种方法非常重要。一是使法律价值介入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例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二是加强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然而,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够,还需要塑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模式的塑造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某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在法律运用过程中遗忘人权价值,就是因为在其现有的思维模式中缺少价值要素,而只是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是最“保险”的,即使出现不良后果,那也是法律规定有问题。可见,在依法办事的同时,还需要秉持对法律的开放姿态,注意将价值因素引入到法律思维模式之中。
有人认为,在中国人权的解释和人权保障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这一模式的构成基础包括:(1)在形成方式上,坚持阶段性与演进性的统一;(2)在路径选择上,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3)在结构内容上,坚持稳定性与包容性的统一;(4)在评判标准上,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主要内容是: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结合;基本人权和首要人权的统筹;权利和义务对等;人权与公权的平衡;法治与德治的兼顾;人权与主权的协调;国内与国际合作并行。③参见熊万鹏:《论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人权》2012年第6期。笔者认为,这种人权解释或保障统一论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已经被很多人接受。这是建立在以辩证法为核心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统一”,对全面、正确认识人权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统一”,其实只涉及对人权保障和解释问题的认知,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于人权保障来说,还需要在认识论基础上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要找到解决人权保障问题的方法论就需要透彻分析对人权的解释以及“解释权”。进一步而言,“解释权”的运用需要结合法律解释学上的体系解释方法。在“解释权”的运用过程中,需要将有关人权的法律规定、价值与社会情势等作为解释要素,在诸要素间寻求一致性。作为话语权的“解释权”,实际上是在认识论基础上,通过“解释权”的行使找到解决纠纷的方法。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实现,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认识论,还需要可以保障实施的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解释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解释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对话语权制高点的抢夺。其争夺方式之一就是建构思维模式。“解释权是话语权(discourse power)的核心;话语权是一种借助事实、解释、观点等信息对人的意识和行动产生影响、支配作用的能力,是权力的一种特殊表现。”④王一鸣:《科学发现的解释权及其寻租问题》,《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12期。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等理论都丰富了话语权的内涵。有必要建构一个思维模式,来保障话语权的实现。就话语权的实现途径或方法而言,话语权包括选择权、解释权、传播权等;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更多的是拥有话语权的解释者,在解释的时候就确立了价值和规则。在西方人的法律思维模式中,始终有自然法与实在法、法与法律的区分,但这种区分仅仅具有相对意义。西方法学家在强调法律重要性的同时,大多也没有忘记高于实在法的自然法,没有忘记人权价值对法律解释的指导意义。虽然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有法文化的特征因素而不能照搬,但其对价值层面的重视态度仍是值得参考的。
(四)形成“人权保障”的法律解释规则
这些年来,人权实现的保障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现了由价值体系到制度的演变。然而,需要注意到,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现有的制度、价值认知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在制度难以有重大变化的时候,先应该提升实现人权保障的方法,否则,人权保障有可能流于形式。因而,需要注意从价值、制度、机制、体制到实现方法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人权实现机制。有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法律解释规则或规范不属于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的实证法律规范,对法官或法律适用者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即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必须遵守它们。”⑤王夏昊:《论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性质及功能》,《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然而,法律解释规则是对千百年来法律实践的概括总结,是法律人思维的规律。这些法律思维规则虽然不是行为规范,但确实是正确思维的指南。法律思维规则“属于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人都承认和接受的规准或规范,是法律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人所必须掌握的一种内在技艺。因此,特定法秩序的法律人在法律决定证成或法律推理中遵守或适用它们,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知识品格,是一种理性理由,而且遵守或适用它们是特定法秩序的法律人之间‘约定俗成的’”。⑥同上注,王夏昊文。对司法和执法实践研究而得出的法律思维规则,是法律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对正确行使“法律解释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律思维规则包括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论辩、法律修辞规则等。“解释权”的行使虽然最终结果表现为行为决策中对法律意义的释明行为,但这一过程却主要是思维活动。思维活动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很难被作为行为方式加以监督。在思维过程中,价值导向、理解能力、情景因素等对解释结果的影响都很大。法律解释规则在有些著述中也称为法律解释的准则。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思维判断中出现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现象。然而,这种正常的现象在法律运用的一些场合就可能会衍生出不正常的现象,进而影响法治秩序或者权利保障。执法、司法过程中的不同理解,对法律后果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对“解释权”的行使进行思维和行为的双重限制。法律解释需要有思维原则和规则的指导。“解释权”的行使应该受到法律思维规则的约束。只有在思维过程中接受人权价值、法律规定和法律思维规则的约束,才能实现法治秩序和公平、正义、自由等人权价值。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原则或规则。“在法治社会中,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⑦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前线》2001年第5期。不仅需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认知融入“解释权”行使之中,还需要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具化为法律解释规则,甚至是优先规则。人权保障规则的优先性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可以为执法、司法活动提供解释规则。“优先”的原因来自于宪法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适用于立法活动、司法活动、执法活动、社会法解释活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宪法的精义,也是对法律解释活动的方法论要求。进行法律解释需要以人权保障为价值追求,尊重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本着有利于弱势群体,有利于人权供给等标准,对法律规定进行恰当解释,进而将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四、结 论
既然解释是法律意义的衍生方式,那么“解释权”的行使就应成为“人权保障”的实现手段。“解释权”的行使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违背,缘于解释过程中对人权的忽视,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位,“解释权”行使中“人权保障”缺失造成解释权的滥用。在我国“法律解释法”没有出台以前,需要通过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来明确法律解释规则,以便用思维规则、人权价值引领来规制“解释权”,从而保障法律的全面正确实施。应当在全面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基础上,塑造规制“解释权”滥用的法治话语权,构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模式,形成“人权保障”的法律解释规则,由此逐步开启从“解释权”入手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落实于执法、司法之中的进程。
——以《警察法》的修改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