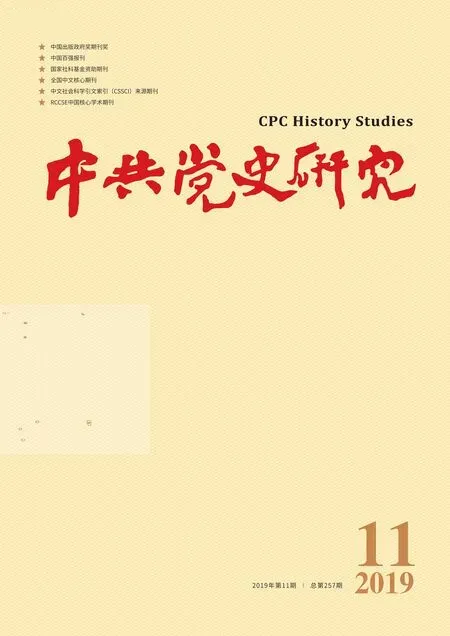早期《新青年》杂志中的德国想象
毛明超
一、引 论
1915年,因反袁遭通缉而流亡日本的陈独秀潜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于9月15日在上海群益书店发行第一期,自次年9月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称这部“天下第一刊”在思想上引领了新文化运动进而影响了五四运动,实不为过。自发刊之日起,《青年杂志》即取法语“青年”(La Jeunesse)一词为题名;在创刊号中,陈独秀更撰写《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认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等“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1)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陈独秀曾于求是学堂修习法语,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也曾节译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陈作“薛纽伯”)的鸿篇《现代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contemporaine)。参与五四运动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曾留法,而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更总结道,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18、19世纪法国民主思想和自由主义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思想。‘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往往流露出法国浪漫主义的痕迹”(2)〔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第37页。。由此,考察《新青年》杂志中对法国思想的接受似乎更显得顺理成章。
然而,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已经可见撰稿人对德国之兴趣要远胜法国。由李亦民编译、刊载于第一卷第一号末的《世界说苑》,介绍的并非法国,而是德国的政治社会与风俗国情,共分《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二)》《柏林之宫殿》《柏林之情景》《德意志之国民性》《德国之交通机关》《柏林之公园及娱乐场》《柏林之除夕》《德人关于决斗之取缔》《德意志之军人》共九节。在第一卷第二号末尾,李亦民又增补《德国之社会党》《柏林之战捷纪念塔》等两节,继续向读者介绍德国。(3)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因此,考察早期《新青年》中的德国形象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同样重要的问题了。
在既有研究中,对于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形象的建构,已有若干探讨。德国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与史通文(Andreas Steen)在关于中德关系的史料论集中指出:“长久以来,中国的德国形象都带有认同与敬佩的烙印。对于众多知识分子而言,军事成就、德国统一、普鲁士崛起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立宪专制君主制都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榜样。”(4)Mechthild Leutner and Andreas Steen (ed.),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11—1927. Vom Kolonialismuszur“Gleichberechtigung”Eine Quellensammlung,Berlin:Akademie Verlag,2006, p.496.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崛起以及由此得出的对中国之模范作用是德国形象在华理想化的根源。德国学者费路(Roland Felber)则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中的德国形象,突出了保守派与革新派对德国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不同解读(5)Roland Felber,“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in der Zeit des Vierten Mai,”Berliner China-Hefte,Vol.17(1999)pp.27—40;〔德〕费路著,赵进中译:《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与中国“五四”时期民主的呼声》,郝斌等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62—1381页。。赵兵则从整体上勾勒了新文化运动中德国形象的变迁,尤其是从一战时期军国主义与强权主义之滥觞到战后挽救“德意志精神”的尝试(6)赵兵:《欧战前后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德意志精神”及其转向》,《德国研究》2017年第1期。遗憾的是,该文作者并未对“德意志精神”的内涵作出任何阐释。。本文则试图在上述研究尚未及之处,以1915年至1919年5月间所出版的前六卷《新青年》为考察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相关史料,探索前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德国的历史、政治、哲学与文学中寻找重塑现代中国的路径与指导。不过必须指出的是,20世纪早期学人对外国思想的接受难称系统,倒颇有“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风范,更多的是以目的为导向,挑选能够“实用”的若干观念,而非纯粹介绍学理。输入中国的各式主义,与其说是理论或思想体系,不如说是“价值评判模式和意识形态旗帜”,以至于出现思想上的杂糅造作,一如周作人所调侃的那样:“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一框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7)方维规:《何谓启蒙?哪一种文化?——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而作》,《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6期。故此,本文不谈“形象”只谈“想象”,不过谈“想象”并非为了从学理上纠偏,而是撷取《新青年》中所呈现的德国元素,以勾勒“五四”之前知识界思想全景中的一隅。
二、早期《新青年》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趣
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界对德国军国主义十分景仰,是学界的共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完成统一且经济迅速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对致力于自强的一代中国官员是一个鼓舞”,因此中国对德国之钦慕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最为具体”(8)〔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页。。19世纪70年代,王韬所编译的《普法战纪》便已引起晚清政界与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而对于洋务运动而言,军事之“器”的层面显然最符合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天津武备学堂之建立、张之洞成立“自强军”、胡燏芬与袁世凯所组“定武军”于天津小站练兵,均是师法德国在军事层面的具体体现(9)〔美〕费正清、邓嗣禹著,陈少卿译:《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266—267页。。梁启超同样将德国作为一个“新造之邦”竟能“摧奥仆法,伟然雄视于欧洲”之原因归结于“尚武”,尤其是俾斯麦“铁血之主义”(10)梁启超:《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而两次世界大战间德国重整军备、快速崛起,又再次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提供了成功范例。《青年杂志》发行初期正值一战,对战局的关注也自然使得对德国的兴趣首先集中于军事层面。
例如,李亦民在《世界说苑》栏目中,首先描绘了德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军人崇拜。他在介绍德皇威廉二世时,尤其突出其对军人的厚爱,“德人中最受皇帝优遇者,惟军人、学者与实业家”,威廉二世“尝当众演说曰:‘统一德意志帝国者,非国会之多数党,乃朕所厚赖之军人’”(11)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而在《德意志之军人》一节中,他又描述德国社会“视军人也,如吾国之视士人。吾国夙以士为四民之首。举国上下,交相崇拜……德人之视军人,亦大率类是”(12)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这幅图景并无夸大之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德国的浩劫》中写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治下的普鲁士陆军,“造就了一种令人瞩目而深入的军国主义。它影响了整个民间生活”,而在德意志统一、第二帝国建立的年代,军国主义因其强力与功绩更受追捧,“一个普鲁士的中尉在人间走动着就像一个年轻的神”(13)〔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何兆武译:《德国的浩劫》,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18页。。于是,一种狭隘的普鲁士主义便深入国家行政机构与社会生活之中,导致视野急剧萎缩,一切文化追求与道德标杆都被简化为军事纪律,而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最终导致了纳粹夺权的灾难。
但在民初知识分子的眼里,对军人的尊敬恰是德意志社会“军国主义”的体现,也正是德国在一战初期所向披靡的原因:“德意志之社会,功利主义、军国主义之社会也……欧战方起之初,多有以是疑德国军人不堪苦战者。而今日之经验,乃适得其反。盖重其人,则人知自重,军心固结,自有足以胜人者在也。”(14)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在第二号中,李亦民又专门介绍今坐落于柏林蒂尔加滕公园中心的“战捷纪念塔”(Siegessäule),以表德国三次统一战争之军功。在第一卷第四号中,陈独秀好友、后率部参加“讨袁”和北伐的潘赞化,以“潘赞”为笔名撰文《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并将之描绘为“武士中之武士,护国之神,世人赞之曰普鲁士魂之结晶”。潘赞化详尽描述了兴登堡在东线的军事指挥艺术,特别是其受命于危难却力挽狂澜并取得“端严堡之大捷”(即1914年东线的坦能堡大捷)的经历,并总结指出:“故德人崇拜兴登堡元帅,视德皇加甚云。”(15)潘赞:《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而李亦民则在第一卷第六号撰文介绍一战期间指挥德奥部队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奥古斯特·封·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强调其“已往之勋绩,实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者”,更称颂马肯森在战事中所展现出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精神,“况乎躬冒矢石、万死不顾一生之精神,尤非常人所能望哉”(16)李亦民:《德意志骁将麦刚森将军》,《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为了彰显二人军功,《青年杂志》为这两篇传略配了插图,其中第一卷第四号所刊兴登堡的照片占满一页篇幅,展现的是他在1914年夏末谋划坦能堡战役的形象。早期《新青年》撰稿人对德国军事与兵家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势,更加深了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神往。陈独秀虽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仍对“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有所保留(17)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但他在杂志第二年开篇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俨然认定德意志帝国行军势如破竹,必能取得一战之胜利,进而导致欧洲政局之剧变:“欧洲战争,延及世界,胜负之数,日渐明了。德人所失,去青岛及南非洲、太平洋殖民地外,寸地无损。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二京,轨轴相接。德虽悉锐南征,而俄之于东,英法之于西,仅保残喘,莫越雷池……审此,一九一六年欧洲之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新受此次战争之洗礼,必有剧变,大异于前,一九一六年,固欧洲人所珍重视之者也。”(18)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
难以想象,一份以法语为外文名的杂志之主笔竟如此花费笔墨,宣扬德军在一战中的胜利。而刘叔雅(即刘文典)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刊载的《军国主义》一文中,更是毫无遮掩地为“天下莫强焉”的德意志帝国摇旗呐喊:“开战以来,一战而灭比利时,再战而破法兰西,三战而蹶露西亚,处四战之地,抗天下之师,而能战胜攻取,亟摧敌国……其丰功伟烈,真书契以来所未有也。”(19)刘叔雅:《军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由此,德意志军国主义再次被神化,甚至竟达到影响战与和的地步。《青年杂志》于1915年12月刊录的《国内大事记·引入协约问题》,记载英法俄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驱逐德国在华之一切势力”,但记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人今方醉心于德国军国主义”,故而舆论对加入协约国一事,仍然以拒绝为多。
三、军国主义与青年教育
如若借用“体用”之争的话语,则可发现早期《新青年》撰稿人所关注的并非战舰、火器及练兵之法等器物之“用”,而是希望以西方思潮尤其是德意志军国主义式的尚武、好胜与牺牲精神来革新中国文化之“体”。他们并未著文介绍德国军队的组织架构,也较少在意一战在军事科技领域里的革新(20)仅有刘叔雅在《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一文中提及德国的人造橡胶、毒气等;蔡元培在《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一文中提及“克虏伯炮”及发达的铁路交通网等。但二人并未着墨描写新式武器的构造或其在战场上的实际功用,而是强调“科学”在整体上对战争与存亡的决定性影响,并借此宣传科学精神,要求青年研习科学。,更对德国政治体制不感兴趣。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早期《新青年》杂志关注更多的是军国主义对于个体精神与民族个性层面的影响,并欲借此重塑中国青年。
《德国青年团》一文便是这一意图的最佳体现。作者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在拿破仑战争后重新崛起,在统一后不失锐气,根本原因恰在于“全国上下,从事青年教育益力”。这种青年教育并非单纯的文化或军事训练,而是培养军国主义的牺牲精神。在作者看来,正是这种牺牲精神,造就了德国之强盛,“实际德国之强,不在军容之盛;由于国家之基础巩固,举国人民,复能贯彻青年德意志主义,尽其所有智力能力财力,以供国家牺牲。有此精神,乃有今日之战绩,饮水思源,谓非青年社会教育之赐不得也”。(21)谢鸿:《德国青年团》,《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而贯彻实行这一理念的,便是文章所介绍的“青年德意志团”。与当时的中国一样,一战前的德国也出现了一股“青年崇拜”(Jugendkult)热潮,尤其以走出城市、漫游德意志乡土的“候鸟运动”(Wandervogel-Bewegung)为代表。但是,这种原本意欲在社会转型期反对传统价值、拒绝工业文明与现存政治社会结构的青年运动,却被德国军国主义所利用,以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化旗帜下宣扬尚武与牺牲精神。谢鸿所记的“青年德意志团”,正是1911年由普鲁士陆军元帅科尔玛·封·德·戈尔茨男爵(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号召成立的“青年德意志联盟”(Jungdeutschland-Bund),而到1914年,“青年德意志联盟”已兼并了“候鸟运动”,发展至约有75万余成员(22)曹卫东编:《德国青年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22页。,其目的除了对成员进行半军事化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成有坚强体力与强毅精神之健全国民,所谓德意魂是也”(23)谢鸿:《德国青年团》,《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因此,《青年杂志》明显欲以“青年德意志团”的成功为典范,提倡效仿德国青年军事教育之宗旨,并非以其为榜样操练军队,而是将之理解为青年的道德教育,磨炼青年之心性与意志,以军国主义方式培养其坚毅忠勇、不畏牺牲的精神。由此可见,早期《新青年》之所以推崇德国军国主义,除了惊叹于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初期的破竹之势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更新中国的民族性,进而塑造出真正的“新青年”。
这一目标与陈独秀的观点完全吻合。陈独秀强调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者尖锐对立,更是造成双方于当今世界之不同处境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言下之意便是要求青年摆脱“恶斗死宁忍辱”的“东洋民族性”,转而塑造“恶侮辱宁斗死”的“西洋民族性”。(24)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刘叔雅更直接写道:“好战者美德也,爱和平者罪恶也。欧洲人以德人为最好战,故德意志在欧洲为最强……世界诸民族中,吾诸华民族最爱和平,故中国亦最弱。此迷梦若不速醒,亡国灭种之祸必无可逃。”故而经历一战的中国青年应当从“和平迷梦”中幡然醒悟,“人人以并吞四海为志,席卷八荒为心,改造诸华为世界最好战之民族”。(25)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一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回顾德军胜势后所告诫新一代青年的那样:“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26)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
四、青年教育与尼采哲学
以德国之军国主义塑造新青年的目标,与《青年杂志》宣扬个人自主与精神解放之初衷有着紧密关联。青年之所以要处于“征服”地位,正是为了摆脱从属地位、摒弃“奴隶道德”,与束缚个性的儒教纲常一刀两断,从而生成“独立自主之人格”(27)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质言之,在早期《新青年》的撰稿人看来,中国的道统不过是束缚个性的枷锁,为求革新与救亡,必须以主体性的力量将之彻底击碎,而秉持“以个人意志为尊”之信条的日耳曼民族为个人独立提供了最佳的路径参照。李亦民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即强调指出:“日耳曼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故富于独立自尊之心,而为我之心强盛。主张自己权利,不肯丝毫放过,亦为诸族之冠。”(28)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于是乎,军国主义所奉行的尚武与斗争精神恰恰坚定了个人与传统决裂的意志。在此之外,突出个体意志、强调反传统的尼采哲学则成为早期《新青年》撰稿人所关注的另一德国要素。
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向青年“谨陈六义”,第一条便是要求青年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个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正是在塑造独立自主之新青年的语境中,陈独秀引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贵族道德”与“奴隶道德”之二分,将古代中国的道德规范(如“忠孝节义”)与“盛世”之梦(如“轻刑薄赋”)贬为“奴隶之道德”与“奴隶之幸福”,而将“有独立心而勇敢者”称为“贵族道德”,进而要求青年以此争“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29)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贵族道德”又译“主人道德”(Herren-Moral),其与“奴隶道德”(Sklaven-Moral)之二分,出自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在尼采看来,“主人道德”是指由“主人”(或“人类的高尚种类”)以自身为标杆“创作价值”,而“奴隶道德”则是那些“受压迫”与“不自由”者所持的“有用性的道德”,即将一切有助于他忍受“此在(Dasein)压力”的情感与手段视为善(30)〔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赵千帆译:《善恶的彼岸》,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2—266页。。自然,陈独秀在这里化用了尼采的哲学,与其说指出了两种道德体系的对立,不如说强调了“贵族”与“奴隶”的对立;而在他的语境中,所谓“贵族”并不必然身居社会高位,但必有不满足于轻徭薄赋之迷梦的独立与自由精神。这样,陈独秀就将尼采的道德批判引入了“思想启蒙”与“人格独立”的范畴中,使之成为新青年之人生观的指引。在《人生真义》一文中,陈独秀写道:“又像那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31)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陈独秀在分析了种种不同的人生观后,将个人追求幸福视为人生的唯一要义,而将社会道德律令视为次生的规范性原则,“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显然,尼采哲学的引入为他的这一论断提供了理论基础。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便已开始着手介绍尼采哲学,特别是其中摧毁一切偶像崇拜的精神。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论及“精神的三种变形”,以狮子“我意愿”的个人意志挑战巨龙“你应当”的社会道德规范,通过批判和破坏“给自己创造自由,也包括一种对义务的神圣否定”(32)〔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32页。。这正与新文化运动要和文化传统决裂而追求个人解放的宗旨相契合。斯洛伐克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指出,中国的“青年革命者”之所以对尼采哲学充满兴趣,恰恰是因为尼采破坏神话与偶像,振聋发聩地高呼“重估一切价值”(Umwertung aller Werte),与《新青年》的宗旨不谋而合(33)关于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可参考马立安·高利克的论文《尼采在中国(1918—1925)》《尼采在中国(1902—2000)》等。参见〔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著,刘燕编:《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55—252页。。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一文便是明证(34)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乐黛云曾总结道,“五四”前后人们心中的尼采形象“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35)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尽管这一阐释与尼采之本意不尽相同,尤其没有顾及尼采的哲学实际上是对基督教伦理学的清算,但对尼采哲学的化用确实促进了五四时期不受礼法约束的“贵族式”个人主义之兴盛(36)关于“尼采式的贵族自由主义”,参见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31—33页。。同时,尼采哲学所蕴含的批判与解构之方法从构成上实可类比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也因此成为“五四”前后“新思潮”的代表。在后五四时代的第一期《新青年》(即第七卷第一号)中,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潮”概括为“评判的态度”,即尼采“重估价值”的彻底的批判姿态:“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3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在胡适看来,尼采哲学所带有的批判态度恰恰从形式上定义了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决裂的内核,因此,对尼采哲学的推崇也构成了德国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推崇军国主义之基础
早期《新青年》对于德国军国主义与尼采哲学的介绍,首先带有鲜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是“竞存争生”的必然要求。自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介绍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后,社会达尔文主义便逐渐盛行于中国(38)关于达尔文主义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接受,参见〔美〕浦嘉珉著,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关于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探讨,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外,高一涵曾对斯宾塞有所介绍。参见高一涵:《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在英语世界之外,德国生物胚胎学家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也是社会进化论的积极提倡者(39)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收入杂文集《坟》)一文中,便概述了赫克尔(鲁迅译“黑格尔”)的“种族发生学”(Phylogenie)在进化论体系中的地位。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马君武也在《新青年》中连续撰文介绍赫克尔的哲学体系。参见马君武:《赫克尔之一元哲学》,《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赫克尔之一元哲学(续前号)》,《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赫克尔之一元哲学(续前号)》,《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 ;《赫克尔之一元哲学(续前号)》,《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所谓“种族发生学”,即将达尔文原本适用于同一种属内的个体进化论运用于物种及人种之上,将不同物种理解为优胜劣汰的进化产物。。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运用于国家或民族间的斗争,认定不同人种间完全处于竞争状态,而世界历史的兴衰正是人种进化的体现。在这一视角下,人类社会处于“人皆为他人之豺狼”的无政府状态与零和博弈,各人或各民族为生存故必须互相争斗,否则便会按“弱肉强食”的生物学逻辑落入任人鱼肉的地步,作为弱者而被“淘汰”,剥夺其生存权利。因此,要求青年向在一战初期战无不克的德国看齐,实际上便是要求在生存斗争中诉诸强力,不至于在其中败下阵来。
刘叔雅在《青年杂志》发表的《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一文就将叔本华哲学的核心归纳为 “求生意志”,并将世界纷争均归因为“世之相残相杀无有穷期,究其所求,唯在生存”(40)刘叔雅:《叔本华自我意志说》,《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自然,叔本华本人认为意志所造成的冲动将成为人类存在的痛苦之源,因而其哲学倾向于虚无主义,但刘叔雅已清晰地意识到,叔本华的求生意志说“一变而为尼采超人主义,再变为今日德意志军国主义”,实际上是后二者在思想上的渊源。在《军国主义》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论述道:“然则以何因缘而道军国主义,曰以求生意志故(Wille zum Leben),盖众生由求生意志而生,互争其所需之空间、时间、物质,而竞存争生之事遂起……求生意志乃世界之本原,竞存争生实进化之中心。国家者,求生意志所构成。军国主义者,竞存争生之极致也……国于今之世界,苟欲守此疆域保我子孙黎民,舍军国主义无他道。生于今之世,苟欲免为他人之臣虏,舍持军国主义无他法。”(41)刘叔雅:《军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因此,军国主义被置于“保国保种”的逻辑中而具备了必然性与必要性:既然生存为民族与国家的第一要务,而在国际社会中盛行的是丛林法则,各方之间只有竞争而无合作,那么以军事强力捍卫自身的生存权利与空间,就成为在此“竞存争生”环境下幸存的不二法门。而作为“军国主义之产地”以至于“天下莫强焉”的德意志,便因此再次成为了“吾国之镜”。
除了“竞存争生”的逻辑之外,普鲁士崛起的历史也为借鉴德意志军国主义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刘叔雅还勾勒了初经拿破仑战争的德国在19世纪早期的困境,尤其以文学化的笔法描绘了1807年夏普鲁士与俄国在拿破仑大军之铁蹄下被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刘作“谛尔西特”)的历史:“然试一稽史乘,一世纪以前,其贫弱衰微殆有甚于今日之中国……拿破仑之雄师劲卒驰骋于其国中,逐之极北之地,路易兹后北面长跪,以乞哀于拿破仑前,而终不能邀战胜者之垂怜,饮泣吞声以为谛尔西特城下之盟,丧其版图人口之半,偿金一万三千万佛郎,限制常备军,数不得逾四万二千人,遵奉其无理之条例。其耻辱,痛苦,损失,十倍甲午庚子之和约。”(42)刘叔雅:《军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路易兹后”即1807年代表普鲁士在和谈中与拿破仑周旋的王后路易丝(Luise von Preußen)。德国学者明克勒在对德国政治神话的研究中,指出王后路易丝在提尔西特卑躬屈膝、受辱于人前的历史,在普鲁士反拿破仑的话语体系中经过加工,成为普鲁士屈辱的象征与崛起的动力。路易丝在提尔西特的屈辱正是普鲁士的屈辱,但她作为女性,在大敌当前之时竟能忍辱负重,又激起人民的抵抗精神,使得提尔西特成为“普鲁士政治的转折点”。1813年著名的铁十字勋章(Das eiserne Kreuz)之设立,也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希望以此纪念早逝的亡妻路易丝:设立勋章的日期被定为王后的生日3月10日,而第一枚勋章则于7月19日追授于路易丝王后。参见〔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李维、范鸿译:《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0—268页。在此述及“路易兹后”,与“十倍甲午庚子之和约”内在逻辑一致,即以屈辱刺激民族觉醒。根据1807年7月7日、9日法国分别与俄国和普鲁士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Frieden von Tilsit),普鲁士应将科特布斯割与同法国联盟的萨克森王国;将易北河以西的大部分领土割与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作为普法间的战略缓冲区,并由拿破仑幼弟热罗姆·波拿巴(Jérme Bonaparte)任国王;将第二、三次瓜分波兰时所占的领土让于新成立的华沙大公国;允许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成为受法国保护的共和国;同时裁撤军备,加入法国对英国实施的“大陆封锁”。而7月12日普法于柯尼斯堡签订的补充条约规定普鲁士须支付1.5亿法郎战争赔款,在赔款缴清前由法国在其领土驻军。《提尔西特和约》导致普鲁士分崩离析,所辖人口从近千万骤减至493万,军队仅余4万,种种割地赔款之屈辱条件,委实可与“甲午庚子”相比。(43)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而“谛尔西特城下之盟”“十倍甲午庚子之和约”一说,既是为了突出当年普鲁士之积弱困顿,与此时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进而突出军国主义在救亡图存中的无限潜能。同时,“甲午庚子”之耻旧事重提,必然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作者显然是为了以此切肤之痛警醒国人不能寄希望于乞怜外敌以求苟安于一隅而自保,而应当以普鲁士为范例,奉军国主义为圭臬,因为德国“统一复兴所以若是之神速者无他,军国主义而已……军国主义者,德意志强盛之总因”。而这种争强好斗、不甘人后的军国主义并非仅限于政治与军事层面,可同样作用于实业与思想界,作者列举史学家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刘作“特莱谛开”)、教育学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刘作“鲍诤”)、哲学家欧肯(Rudolf Eucken,刘作“倭根”)及文学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人言论,论证“思想家文人持军国主义,故摛藻振翰以发扬民族之精神,启迪国民之思想”。(44)刘叔雅:《军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在调和军国主义与德意志文化这一点上,刘叔雅与其所引众名人并无二致。正是特莱奇克、欧肯、豪普特曼和赫克尔等人在共同签署的《告文明世界书》(亦称“九十三人宣言”)中宣称:“军国主义诞生于德意志文化,其使命就在于保护德意志文化。”(45)黄燎宇:《当纳雄奈尔的歌声响彻德意志大地——〈告文明世界书〉述评》,《北大德国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六、对军国主义与尼采哲学的批判
然而世界历史已然证明,军国主义与尼采哲学在积极的破坏性之外,更具有非常危险的一面。当为己所用时,尼采哲学作为解构传统的利器、军国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自然具有积极意义。但若是一味强调个人意愿而罔顾他者的正当权利,便会走向极端的自私自利:原本约束个体行为的道德伦理既然已被破除殆尽,个体意志的宣泄便不再具有强制性限制,若是在此基础上复又践行“权力意志”与“弱肉强食”的逻辑,则会将“唯我独尊”视为强者理所应当的地位,走上沙文主义道路。尤其是本已高擎军国主义大旗的德意志帝国,若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尼采哲学作为其世界政策的原则运用于其他民族,为一己之昌盛而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则贫弱的中国恐怕难免“劣汰”之命运。《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一文就记录了1917年初刚刚赴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德意志帝国“军国民主义”之威胁以及其背后尼采哲学渊源的冷静观察:“在昔学者曾发明世界进化之理,惟所持之论,均未能精详,故宗之者甚鲜。迨至尼塞(德国大文学家)复发明强存弱亡之理,以世界之上,须强者吞灭弱者……故现在德国主张进化论,有强存弱亡、自然淘汰之语……故此次战争活动,影响于今世界甚剧。如德国能得优胜,必以帝国主义支配今世界。”(46)记者:《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政学会欢迎会之演说)》,《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而在3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一号中,蔡元培又来信对所载文字做了校订,将上段引文修正为:“自尼采以此义为世界进化之唯一条件,而悬为道德之标准,于是竞强汰弱之义大行,而产出德国之军国主义。”他不仅揭示了尼采学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而与军国主义的关联,更指出此类思潮之交媾将会导致德国以帝国主义威胁世界。字里行间,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实已透露出对尼采哲学与军国主义之泛滥的担忧。
即便是宣扬军国主义的旗手刘叔雅也注意到,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傲慢之上的“黄祸论”,恰恰盛行于他非常推崇的德国,而“倡此说者以德皇维廉二世为最力”(47)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的确,威廉二世正是所谓《黄祸图》的始作俑者(48)《黄祸图》是画家赫尔曼·科纳克弗斯(Hermann Knackfuß)于1895年根据威廉二世的草图所创作的油画,题名《欧洲各族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Völker Europas, wahrt eure heiligste Güter!),后由威廉二世赠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画中,化身七位女性形象的欧洲各国聚拢在十字架的光芒之下,大天使米迦勒执剑居中,左手指向海对岸的威胁——一尊乘着巨龙的佛祖。《黄祸图》刻意建构了基督教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并煽动欧洲国家以武力应对。不久后的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事变”使得欧洲内部的武力联合成为现实。。德国汉学家余凯思指出,隐藏在“黄祸论”之种族主义范畴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恐惧,即对东亚工业化、军事化与廉价劳动力竞争的恐惧(49)〔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229页。。这种掺杂着种族主义歧视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普遍的军国主义文化相混杂,便会导致诉诸极端暴力的倾向,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弗尔布鲁克所评论的那样:“这些暴行,以及不排除‘灭绝’‘劣等’民族的可能性的心态,有其长远影响,是德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暴行的一个背景。”(50)〔英〕玛丽·弗尔布鲁克著,卿文辉译:《德国史:1918—20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而更让人瞠目的是,诸如欧肯、赫克尔等德国科哲大家竟也坚持种族优劣之分。在《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一文中,刘叔雅写道:“记者所最惊心动魄者,则倭根(R.Eucken)、赫克尔(E.Haeckel)二氏痛斥英人之宣言书……当欧洲大战之初起也,倭根与赫克尔共撰一文,宣告天下,责英人以条顿民族之尊,不应使黄色人种,加入战争。又谓俄人为半东洋半野蛮之民族,英人不当与之联盟以残同种……俄国为半东洋,即为半野蛮,此虽敌国丑诋之辞,然其贱视吾东洋贱亲吾黄种亦可概见。呜呼!硕学大师之所见如此,其军人政治家尚复视东洋人为人类耶?”(51)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此处所谓“宣言书”应当是欧肯与赫克尔于1914年8月19日发表于德国诸多大报的《宣言》(Erklärung)一文。文章虽未提到“黄种”,但指责英国犯下“不可磨灭之耻罪”,因为“英国竟为了一个斯拉夫、半亚洲的势力,与日耳曼民族作对;它不仅与野蛮更与道德败坏并肩作战”(52)Rudolf Eucken and Ernst Haeckel,“Erklärung”,Jenaer Volksblatt,August 20th.1914.。德意志帝国种族优劣观之根深蒂固,《新青年》撰稿人已很清楚。刘叔雅告诫青年,既然“黄白人种不两立”,则更应正视德国的威胁:“吾青年当知德人之不即能灭吾种类,特以事势不许耳,他日飞艇东来,则彼以一师之众,数月之间,可以尽歼吾四万万人而有余。”(53)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而陈独秀更是在《对德外交》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白皙人种之视吾族,犹人类之视犬马。德意志人过用其狭隘之爱国心,尤属目无余子。”因此,当北洋政府仍因对德宣战与否摇摆不定以至于陷入“府院之争”,更演出了一出张勋复辟的闹剧之时,陈独秀坚定对德主战,除“服公理不服强权”的口号外,也是因为苟且求和,必为秉“弱肉强食”信条之德意志人所不齿,“否则虽日日长跪于其前,彼世界最重强权且勇武可敬之德意志人,必不容吾不战而屈苟安忍辱之懦夫栖息于人类”。(54)陈独秀:《对德外交》,《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实际上,《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就发表了译自《伦敦自由旬报》的《血与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更发表译文《协约国与普鲁士政治理想之对抗——美国韦罗贝博士在国际研究社之演说》,均着力批判普鲁士军国主义(55)汝非译:《血与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陈达材:《协约国与普鲁士政治理想之对抗——美国韦罗贝博士在国际研究社之演说》,《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在一战行将结束之时,德意志帝国的侵略主义已全然暴露无遗。在陈独秀看来,在一战这场“主义”的战争中,先前所借镜的德国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绝对化,已完全成为君主主义与侵略主义的代表,因而构成了对积弱民族的威胁,“使德意志完全胜利也,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其势益炽,其运命将复存续百年或数十年未可知也。此物存续期间,弱者必无路以幸存”(56)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正是在“反帝反侵略”的对德总纲下,胡适、蔡元培等人在《新青年》上集中批判了德意志军国主义及尼采哲学。胡适批驳德国狭隘的国家主义与“强权即公理说”,并将其思想渊源回溯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在胡适看来,“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Ü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残人之种,非所恤也……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弱肉强食’是也”(57)胡适:《藏晖室札记(续前号)》,《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胡适所引的“德意志国歌”即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封·法勒斯雷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于1841年所作的《德意志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以约瑟夫·海顿所作的《天佑吾皇弗朗茨》(Gott erhalte Franz den Kaiser)为曲调,在一战时广为传唱。实际上,在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并没有正式的国歌。直到1922年,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才将《德意志之歌》定为国歌。霍夫曼·封·法勒斯雷本的原诗共三段,胡适与其后蔡元培所引即为第一段前两句“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Über alles in der Welt”,但因为前两段宣扬“德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沙文主义,在二战后即遭禁止,现在的德国仅取第三段作为国歌。。
在胡适所引的《德意志之歌》中,强权思维的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此种观念认定满足一己之欲求为生存之唯一准则,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宗旨奉行极端个人主义,视伦理道德等人际行为准则与社会约束为无物,而这恰是尼采哲学之弊端。对此,胡适看得非常清楚。他明确指出,正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与“超人说”将达尔文主义极端化、绝对化,以“生存”之名消解道德与文明,并否认弱者的存在价值:“强权主义(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为德人尼采(Nietzsche)。达尔文之天演学说,以‘竞存’为进化公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其说已含一最危险之分子……至于尼采则大异矣,其说亦以竞争生存为本。而其言曰,人生之目的,不独在于生存,而在于得权力而上人(The Will to Power)。人类之目的,在于造成一种‘超人’社会(Superman/Übermensch)。超人者,强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残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噍类。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谓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所以捍卫弱者,不令为强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贼也……自尼采之说出,而世界乃有无道德之伦理学说。尼氏为近代文豪,其笔力雄健无敌,以无敌之笔锋,发骇世之危言,宜其倾倒一世。然其遗毒乃不胜言矣,文人之笔可畏也。”(58)胡适:《藏晖室札记(续前号)》,《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则刊发了蔡元培临近一战结束之时所作的反思性文章《欧战与哲学》。他认为,欧战乃哲学或主义之战,而德国的政策所体现的正是“尼采(Nietzsche)的强权主义”。与胡适一样,蔡元培也清晰地指出尼采之理论“在乎汰弱留强”,赋予强者以无底线的权力,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现,这种对强者与威权的盲从又与军国主义的纪律性与等级体系相契合。因此,蔡元培总结说:“他(尼采)的世界观,所以完全是个意志,又完全是个向着威权的意志。所以他说:‘没有法律。没有秩序。’他的主义是贵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为德国贵族的政府所利用,实作军国主义。又大唱‘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sche über alles),就是超人的主义……条约就是废纸,便是没有法律的主义。统观战争时代的德国政策,几乎没有不与尼氏学说相应的。”(59)蔡元培:《欧战与哲学》,《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
与胡适一样,通过引用《德意志之歌》,蔡元培令人信服地指出德国军国主义的社会学和哲学背景,指出借用叔本华之意志概念的尼采哲学与“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相交媾,将一己或一国之私利绝对化,将他人置于从属性的次要地位,而原本用来解构道统的批判性则成为消弭一切社会规范的破坏性。蔡元培通过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阐明,在所有强制性约束缺位的情况下,军国主义得以打着尼采哲学的旗号,以“竞存争生”之名行侵略吞并之实。而同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陶履恭则更直接地指出:“军国主义是一个荒谬的理想,因为那理想里头已经含着失败的种子,因为那理想否认生命和生命的价值。”(60)陶履恭:《军国主义》,《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由此可见,不论是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具有反传统之积极作用的尼采哲学,还是曾作为榜样备受关注与推崇的德意志军国主义,已彻底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批判与鞭笞的对象。
七、从军国主义到社会革命
但是,对德意志军国主义与尼采哲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德国本身的拒斥。一战既已被解读为“主义”的战争,按国家集团划分敌我便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以政治理念区别阵营。击败德意志军国主义与侵略主义的并非协约国军事力量,而是劳工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想新潮在德国引发的政治革命。诚如陈独秀所言,欧战之终结“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61)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于是,《新青年》中便出现了双重的德国形象:一边是德意志军国主义,另一边是萌芽于德国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从创刊之初就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例如,李亦民专门介绍“德国之社会党”,指出其“未尝有容许君主之意”,在德皇面前不行礼,以突出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纲领,更详细记载社民党在俾斯麦的种种镇压下未曾屈服,在帝国议会中所占席位更从1878年的9席增至1912年的110席,一跃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62)李亦民:《世界说苑》,《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文章塑造了社民党在政治高压下所取得的成功,以此凸显其百折不挠的坚韧,更使之成为政党运动的标杆。
而在文学领域,《新青年》所提倡的是正视人间疾苦的自然主义。除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外,德国著名剧作家、诺奖得主格哈特·豪普特曼亦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值得注意的是,引介外国文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学革命”,对文学中所揭露出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普及与政治教育的方式。典型案例便是《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所载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介绍了豪普特曼(胡作“郝卜特曼”)的名作《织工》(DieWeber)。胡适将全剧主题概括为“贫富之不均”,坦承“其写织工之贫况,真足令人泪下”,而第四幕中织工起义又觉“读之令人大快”。剧中描写织工“围主者之家,主者狼狈脱去,遂毁其宅”,仿佛是五四期间学生火烧曹宅的文学预演,而第五幕则更以“工党”革命胜利作为结尾。胡适总结道:“‘贫富之不均,人实为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时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群力之可以制资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罢工之举,铤而走险,为救亡计,岂得已哉。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耶!”(63)胡适:《藏晖室札记(续前号)》,《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换言之,胡适已经注意到贫富差距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人类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因此可以通过社会变革破除之。更重要的是,胡适意识到在两个独立的阶级——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对立,工人可通过联合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以罢工或革命改变遭压迫与剥削的现状。尽管坚持改良主义的胡适认为罢工是“铤而走险”的不得已之举,但通过他的介绍,豪普特曼的自然主义戏剧所蕴含的社会革命潜能得以展露于《新青年》读者眼前。无怪乎陈独秀指出:“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64)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新青年》开始更加关注德国可能出现的社会革命。第三卷第三号的《国外大事记》以《德国政潮之萌动》为题,介绍当年3月德国社民党借预算案机会,“于大呼叛逆声中宣言德意志之共和实不可免”,强逼德皇进行宪法改革(65)《国外大事记·德国政潮之萌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待到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威廉二世于11月9日被迫退位,社民党的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与独立社民党中的激进派“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分别于当日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与“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短短几个月后,“斯巴达克团”起义便惨遭镇压,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遇害,但从总体上看,德国社会主义成功终结了德意志军国主义与君主专制。因此,李大钊总结道:“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这件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66)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
在这篇《BOLSHEVISM的胜利》中,李大钊勾勒了两个德国的形象:一是早前颇受推崇、现今一败涂地的德意志军国主义,二是代表世界新潮流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奉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说,“五四”前夕的《新青年》仍愿以德国为借镜,只是所师法的对象改变成了另一种德国思潮——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即“马克思主义专号”便是最典型之代表。该号刊载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引论,包括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上半部分。李大钊在文中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学说,并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著作中转译了《共产党宣言》选段,借此积极宣扬劳工联合和社会革命,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67)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由此号开始,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实践的主要发生地苏俄便日渐成为《新青年》所关注的焦点。自1920年第八卷起,《新青年》成为新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机关刊物,该卷各号均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多摘译美国杂志《苏俄》(SovietRussia)的文章;而彼时刚刚镇压了左派的“斯巴达克团”起义与右派的卡普政变(Kapp-Putsch)、正百废待兴的魏玛共和国,终于逐渐淡出了《新青年》的视野(68)自1919年末陈独秀远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分裂后,对于德国较为详尽的介绍只有张慰慈以《最近德国政治变迁》为题的两篇文章,梳理了自一战结束至1920年的德国议会、政党、社会政治与革命的情况。参见张慰慈:《最近德国政治变迁》,《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续第4期)》,《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