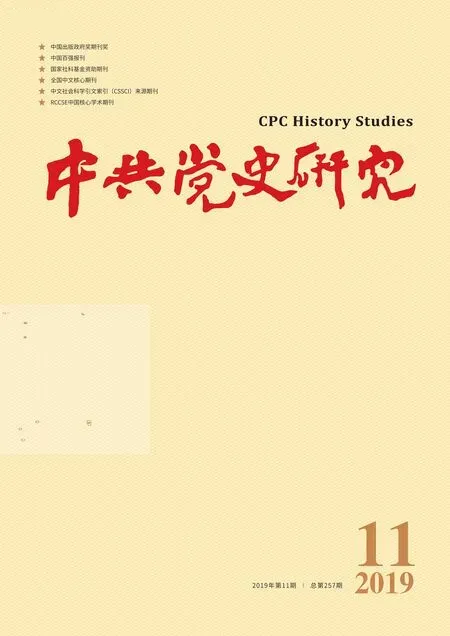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
李里峰
近十年来,“新革命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他学科的部分学者亦参与其间,学术影响越来越大,而学界对其内涵和价值尚未达成共识。鉴于此,笔者拟在简要回顾学界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就“新革命史”的概念和方法略作辨析,以就教于方家(1)本文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革命史研究的创新问题,仅围绕“新革命史”概念本身进行梳理和辨析。。
最早提出“新革命史”概念且阐述最详、倡导最力的学者,当属李金铮教授。他于2010年发表《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首次明确提出“新革命史”概念,主张以“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等作为继续推动和创新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2)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此后,他又陆续发表多篇论文,不断阐发和扩充对“新革命史”的学术见解。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新革命史”作出如下界定:“所谓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同时,他还将“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六点:“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3)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王奇生、应星等学者对“新革命史”的提法表示认可,并就其含义和特征作出较系统的阐述。王奇生在对20世纪中国革命进行宏观分析时指出,“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和走向大致呈现三种趋势: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话语、逻辑和价值,不再直接用作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思想,而是成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将革命相关各方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以再现其复杂多元、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在描述历史过程的“求真”基础上进一步“求解”,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和政治文化(4)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和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应星则从社会学研究逐步转向革命史研究,认为“新革命史”理念的一大重要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即追问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性结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结构和气质如何与中国传统文明、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发生互动,又如何影响中国的革命实践(5)应星:《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论题,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察其渊源,观其流变”,深入理解中共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历史效果(6)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
一些学者没有全面讨论“新革命史”的内涵,但亦从不同角度理解和接受这一理念,并用来指导具体学术研究。张济顺将“新革命史”的兴起理解为“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个方面,认为它对研究20世纪50 年代的上海历史具有启发意义,使之呈现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碰撞和交汇的复杂面相(7)张济顺:《新革命史与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董丽敏指出,“新革命史”对中共革命的理解具有“撑大”和“拉长”的特征,前者是指引入经济史、社会史或其他资源以弥补以往的政治史范式,后者是指把中共革命纳入共和革命、国民革命、阶级革命乃至更长的历史脉络之中(8)董丽敏:《从延安到共和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常利兵认为,“新革命史”就是要把革命放回历史现场,把革命还给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新革命史”研究需要把握革命与政治、革命与社会及其变迁、革命与文化、革命与观念等四个方面的问题(9)常利兵:《“告别革命”论与重提革命史——兼论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 年第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0—51页。。唐小兵将“新革命史”概括为新材料的挖掘、新“问题意识”的提出、新方法和理论的引入、新研究典范的初步确立等,并提出从思想文化史、社会文化史两方面持续推动“新革命史”研究的具体设想(10)唐小兵:《“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代雅洁和杨豪梳理了新世纪以来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认为这些成果从革命事件(从上层到下层)、革命动员(从宏观到微观)、革命政策(从表达到实践)、革命组织(从静态到动态)、革命政治文化(从遮蔽到显现)、革命主体(从阶级到群体)等六个方面,体现了“新革命史”研究的学术路径(11)代雅洁、杨豪:《“新革命史”路径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满永从革命中的“新人”塑造出发,通过梳理身体视角下的革命史研究以及土地改革中身体政治实践的讨论,强调身体政治可为“新革命史”提供启示,进而“迈向实践的历史研究”(12)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贺文乐从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角度理解“新革命史”,以此探讨中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整合过程(13)贺文乐:《新革命史视野下“组织起来”之考察——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历史教学》2016年第2期。。
有的学术评论和综述文章也用“新革命史”之说来概括评述对象的学术价值,如游海华为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所写的书评,认为该书“从新革命史的视角,以制度选择、社会变革与民众互动为主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深度解读,拓展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讨论空间”(14)游海华:《新革命史视野下的中国苏维埃运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肖文明梳理海外汉学研究相关成果,认为“新革命史”的历史叙述重新引发了学界对新中国前30年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15)肖文明:《超越集权主义模式:关于“前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海外中国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等等。此外,2016年和2017年,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先后举办两届以“新革命史”为名的学术工作坊(16)彭晗:《第二届“新革命史工作坊”会议综述》,《近代史学刊》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9—257页。;2018年召开的山东革命根据地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作者亦称之为“新革命史”视野下的“再出发”(17)张学强:《“新革命史”视野下山东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再出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
杨奎松、黄道炫等在革命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影响很大的学者,似乎没有明确使用“新革命史”的概念表述,亦未专门阐述其理念和方法,但他们的学术主张与“新革命史”理念高度契合,其研究成果也常常被视为“新革命史”的代表和典范。此外,曹树基由明清史转向当代中国史研究后,提出“新党史”概念,主张在方法和资料上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科学化水平,尤其强调采用科学的分析工具去解读海量史料(18)曹树基、刘诗古:《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齐慕实等国外学者也有“新党史”的呼吁,主张拓宽视野,把党史、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有机结合起来,利用翔实的地方档案材料研究中共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历史进程(19)〔加〕齐慕实著,翟亚柳译:《革命:作为历史话题的重要性》,《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0期。。
“新革命史”概念问世后,已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和采纳,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吴重庆等学者一方面肯定“新革命史”在理念和方法上的创新尝试及其对革命丰富性细节的挖掘与呈现,一方面又认为其“仍固守于对国家—社会关系此消彼长的认知模型上,封闭于以代理人、受害者、庇护关系等概念构筑而成的历史理解中”。他强调对革命的“同情和共感”,呼吁将中共革命置于文明史视野下,通过剖析儒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贯通改革开放40 年、新中国成立70 年和中华文明2000年的历史进程。(20)吴重庆、柏奕旻:《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文化纵横》2019年第1期。陈红民承认革命史研究取得了创新性进展并表示赞赏,却认为没有必要冠以“新革命史”之名,并列举了若干理由。尽管如此,他又向“新革命史”理念提出几点建议以“帮助其完善”,如注重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贯通,注重党在城市的发展,借鉴政治学和新闻学等学科的方法,借鉴民国史的研究成果等。针对这些批评意见,李金铮撰文一一解释和回应,对“新革命史”理念作出了进一步阐述(21)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上述关于“新革命史”的论述,内容丰富,说法各异,但不难发现共同特征或相似之处。“新革命史”究竟新在何处?结合学界既有表述,笔者认为,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22)需要说明的是,“新革命史”之说既是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也是对未来走向的展望。因此,许多被视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论著,其实早在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即已问世。
其一,旨趣:回归学术的革命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近现代史曾经被简化为革命史,一度存在将革命理论等同于研究革命史的理念、将革命者与革命史研究者的角色相混淆、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简单化等问题(23)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历史学者一度对革命史失去了兴趣。而“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正是要将革命史从神话与魔化、“唯革命化”与“去革命化”的极端状态中摆脱出来,使之重新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24)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被视为“新革命史”研究的典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该书在充分占有和细致解读史料的基础上,把回归学术、再现历史场景的旨趣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一篇书评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史的旧有书写更多的是结果导向的宣传和论断,距真实的历史有相当的距离”,而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尽可能从原初的历史出发,摆脱历史研究中最容易陷入的结果导向陷阱,以探寻历史的本真”(25)周祖文、金敏:《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其二,范畴:多元融汇的革命史。按照历史学次级领域的常见划分方式,革命无疑属于政治史的研究对象,而“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恰恰是要超越纯粹政治的范畴,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去探讨中国革命,呈现其丰富多元的复杂面相。李金铮长期从事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他的“新革命史”理念首先意味着革命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结合,他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以中共民间借贷政策的演变为例,探讨中共革命政策与民间传统的互动关系(26)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注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更为“新革命史”倡导者所一致认可。美国学者傅礼门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常被提及的代表作之一。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则被视为从社会文化视角对革命史进行新探索的成功范例,书中关于革命政治文化的分析尤其令人拍案叫绝。不过,也有学者发出过“重提政治史”的呼声,因为政治在近代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支配力和重要性,“革命”则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社会史可以弥补传统政治史的缺陷,却难以替代政治史在跨区域意义上的整合作用(27)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历史研究》2004 年第4 期。。既要跳出纯粹政治史的研究视角,又不能抽离革命最核心的“政治”特质,对“新革命史”研究者是一个挑战。
其三,层次:上下整合的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大多侧重宏观描述,往往具有重上层而轻下层、重中央而轻地方、重精英而轻民众的倾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共革命是一场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地方革命”(28)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1006.,其最终成功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贺康玲、韦思蒂、纪保宁、古德曼、吴应銧等国外学者基于不同时段、地域和视角,对中共和农民在地方场景中的互动作了精彩描述,使西方的中共革命研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术转型(29)参见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68期,2010年6月,第143—180页。。同样,“新革命史”的倡导者也把中共革命的地方实践、不同区域和层级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作为推动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利用大量基层材料细致体察革命的发生过程和历史场景,从微观互动论视角揭示革命的运行机制,成为许多学者青睐的研究路径。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一书,就是因为凸显了普通民众在革命进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而被李金铮一再列为“新革命史”的代表作。
其四,时间:前后贯通的革命史。20世纪中国发生过前后相继的数次革命,“新革命史”主要是针对中共革命而言的,尤其是1949年前中共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革命(尽管李金铮一再强调“新革命史”的理念也可适用于其他革命)。但是为了更准确和深入地理解中共革命,恰恰需要将其放到“中国革命”乃至革命之前和之后的长程历史脉络中去考察。王奇生对此作过脍炙人口的精彩论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累积繁衍、升级递进三大效应,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一直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30)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不过,虽然“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无不赞同贯通中共革命的不同阶段、贯通中共革命与其他革命、贯通革命时期与革命前后的学术主张,但因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路径依赖所限,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史论著极为罕见。美国学者裴宜理的几部代表作如《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等,倒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将中共革命置入长时段加以考察的学术理念。
其五,空间:全球视野的革命史。“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指出,传统革命史研究只是就中共革命谈中共革命,忽略了中共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关系、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革命之异同,从而难以看到中共革命的特色及其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因此,“新革命史”需要借鉴全球史视野,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边界,强调相互之间的联系、互动和比较。(31)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既要比较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革命之异同,又要探讨不同国家革命之间的影响和互动关系;既要揭示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的影响,又要体察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对自身独立性的追求。如应星所说,“新革命史”研究需要相对深入地理解西方现代性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努力打通中共革命的国际源头与国内根基(32)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在这方面,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等都是学界公认的重要著作。
其六,方法:学科交叉的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的视野比较狭窄、方法比较单一,“新革命史”则要广泛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学科领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考察。前述傅礼门等人关于中共革命与乡村变迁的经典著作,便充分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三位合作者也分别来自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裴宜理关于华北农民抗争和上海工人政治的研究,算得上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的研究方法以及诸如“文化置位”“文化操控”等核心概念,显然来自西方学界盛行的“文化研究”。应星、孟庆延等学者探讨中共组织网络、红军领导机构、查田运动、阶级划分等问题的系列论文,体现了将社会学“问题意识”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学术自觉。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以人类学方法刻画中共革命中的国家形构过程,探讨作为革命象征的“星火”与代表民间传统的“香火”之间的互动关系。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等著作,将革命史研究与文学、文化、歌曲、绘画、建筑、城市规划、庆典游行等元素熔于一炉,对中共政治文化史作出了生动诠释。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则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角度切入中国当代史,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想当然地根据字面意思,把“新革命史”简单地理解为传统革命史的对立面。从“新革命史”倡导者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这一学术理念实际上具有“重提”革命史和“重写”革命史的双重意味:前者是为了回应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和革命史研究被边缘化的状况,后者则是要在学术研究的视野、方法、风格等方面突破传统革命史的局限性。李金铮最早提出“新革命史”,便是建立在对“告别革命论”和反对革命史研究提出批评、对“中共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与问题”进行反思这两个前提之上,而前者显得更为直接和重要(33)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传统革命史观(固化的革命史)→现代化史观(被边缘的革命史)→重提革命史(与“告别革命论”对话)→重写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对话)的演变过程,它和传统革命史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关系。
从笔者所归纳的上述含义来看,“新革命史”主要体现为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在把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共革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革命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等方面,“新革命史”和传统革命史并无实质性区别。“革命”和“革命史”概念的意涵都相对比较明确,传统革命史和“新革命史”的立场、观点不同,视角、方法有别,其对革命本身的界定则是大体相似或至少可以沟通的。李金铮、王奇生等人所阐述的“新革命史”理念,诸如高度强调学术化建设,诸如返回历史场景,诸如常识、常情、常理,诸如革命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诸如在求真的基础上求解,诸如拓展革命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创新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但在笔者看来,并未突破“革命史”(无论新的还是旧的)本身的范畴、前提和预设,也并不具备“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意义。可以比较一下。近百年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范式转移:一次是20世纪上半期传统政治史的衰落和社会史的兴起,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挑战和削弱了社会史的中心地位。在这里,作为“史”之修饰词的“政治”“社会”“文化”,都具有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视角的双重意涵: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政治史侧重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社会史侧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社会生活,文化史侧重思想观念和文化教育;在研究路径的意义上,政治史意味着权力、支配和反抗的视角,社会史意味着结构、关系和下层的视角,(新)文化史意味着观念、象征和意义的视角。(34)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学海》2018年第3期。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同时呈现改变研究对象和转换研究路径的双重意义,从而构成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移。而革命史之所谓“革命”,尽管有各不相同的定义,在学术研究中却只能作为描述和分析的对象存在,其本身并不具备研究路径或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新革命史”也就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范式转移”。
行文至此,不妨回到那场关于“新革命史”之说是否必要的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是革命史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体现了重提革命史和重写革命史的双重取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描述革命史研究新进展的意义上)和学术价值(在引领革命史研究新方向的意义上)。但是也不必夸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提出“新革命史”当然有助于激发革命史研究者的创新意识,没有这一提法似乎也并不妨碍历史学界在方法、资料、视角、观点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笔者推测,许多被视为“新革命史”代表人物的知名学者并未采用这一概念,或许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新革命史”的学术理念,而多少有不愿将其变成一个固化和封闭概念的因素在里面。
在汉语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来表达新事物与旧事物之关系。例如“除旧布新”,新旧之间是二元对立的,布新须以除旧为前提;例如“新陈代谢”,新旧交替的过程很复杂,往往呈现新旧杂糅的状态,但是最终旧事物会被新事物所取代;例如“推陈出新”,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推出更好的新事物;例如“开拓创新”,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突破常规,尝试新事物、新方法。“新革命史”之“新”,首先意味着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开拓创新,也具有学术观点上推陈出新、新陈代谢的意义,但不应该把“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理解为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的二元对立关系。如有论者所说,“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之间并非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关系(35)代雅洁、杨豪:《“新革命史”路径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新革命史”概念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令人赞赏,但在笔者看来,没有必要(事实上也很难)给“新革命史”作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定义,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创新、开放、多元的学术理念,以推动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