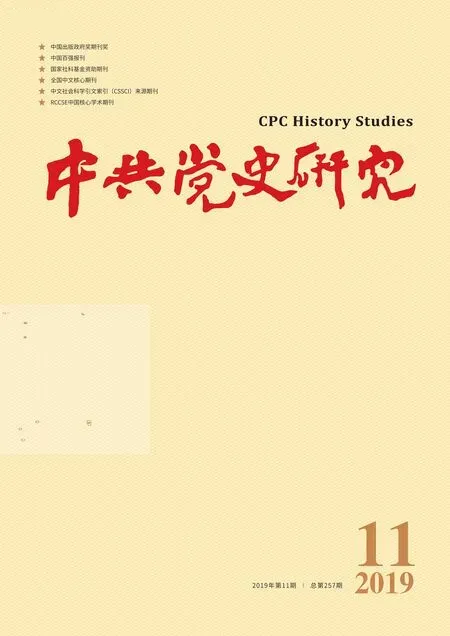知识分子视野下的“新革命史”研究*
唐小兵
近些年来,“新革命史”成为历史学界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这种研究注重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等不同视角,通过搜集、整理与解读档案、文集、报刊、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多元史料来重构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图景,在“问题意识”、理论假设、学术路径和解释框架等方面都取得较大突破,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王奇生、杨奎松、黄道炫、张济顺、裴宜理、石川祯浩等教授的研究著作和专题论文。这种“新革命史”的学术潮流不仅对于史学界内部重新认识和阐释20世纪中国革命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溢出了史学界,对于文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在发挥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可以说,“新革命史”正在形成一种新颖而有生命力的研究范式。
在“新革命史”的学术脉动之中,从知识分子的视角重审20世纪中国革命是一股特别值得重视的潮流。这一视角对于知识分子研究本身的深化和革命史研究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知识分子研究注重的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既有意识又有行动的个体,关切的往往是知识人的政治、生活与观念,而“新革命史”关注的往往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逻辑与机制,二者的结合自然会产生相得益彰的学术效果。
中国革命尤其共产主义革命恰恰是某种历史规律的“例外”,依照陈旭麓的名言,中国的近代化并不是如朱维铮所言的“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1)《陈旭麓文集》第5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09页。,可以说是伴随着一系列外敌入侵之屈辱记忆的被动近代化过程。正因如此,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结构并未滋长发育到与其时引入中国的思想潮流相匹配的程度,反而是先知先觉的士大夫和后来的新式知识人利用西方思想理论、按照各种蓝图来试图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乃至后来的革命历程中就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基本上是两代知识分子领导的。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2)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
知识分子视野的引入,对于拓展和深化“新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历史的正当性、道德的正当性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这三种正当性的建构都与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密切关系。共产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多次尝试后的抉择,是后五四时代大部分中小知识青年在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潮流中的自觉选择,这彰显了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为无产阶级和底层庶民进行的社会革命,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安源罢工就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响亮口号,这说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解救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道德正当性。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与动员依托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一整套社会理论学说,因此也具有意识形态维度的正当性。从这三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进而言之,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双重面孔,而神圣性源于超越对于一己私利之追逐,来源于对深受政治、经济和精神压迫的民众的同情与解放的冲动,这种神圣性更多的是在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得以彰显。
知识分子视野引入“新革命史”研究之后,大大拓展了“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围与学术路径,深化了“新革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丰富了整个革命史研究的议题范畴。在传统的革命史研究中,与工农阶级相比较,知识分子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中,又偏向于对农村根据地革命的研究,因为“农村包围城市”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道路的经典论述。知识分子视野引入革命史研究以后,有助于破解此前单向度的历史目的论式的论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复杂性尤其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革命普遍性模式的特殊性就能够得到一定凸显。可以说,知识分子视野是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维度之一。
首先,知识分子视野有利于增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理论性的重视。这种理论性不但包括革命理论从西方或日本进入中国的传播、翻译和接受过程,也包括这种革命理论是如何被本土的革命领袖和理论工作者进行再阐释的。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可以说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也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地利);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3)〔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在这样一种在地化和本土化的历史脉络中,研究者才能理解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革命思想观念的历史建构是如何完成的。源自西方的革命经典理论与具体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张力与对话,催生出共产党人自觉追寻具有中国独特性的一套革命思想的精神动力,而对这一过程的历史性回溯与清理,无疑有助于理解“五四”启蒙观念、苏俄外来理论学说与根据地革命形成的思想体系之间的长期冲突与磨合过程。正是在这样一种视野中,艾思奇、柳湜、胡绳、胡乔木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本土论述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才变得可以理解,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纳入知识分子的理论视角才能得到完整理解,毕竟“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对于思想、价值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的解释,它加强了新文化运动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与制度在当代中国无效的理论表述。新的出发点以跨历史的诉求来拒斥中国传统,这比起以源于西方价值的名义对于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式的攻击,要显得更为合理和更具确定性——通过辩论传统的史实性(historicity),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得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成为多余”(4)〔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其次,知识分子视野有利于彰显和理解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城市的重要性。此前,一谈到中国革命,习惯化地认为这是一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乡村革命,是乡村包围城市、边缘颠覆中心的阶级革命。因此,挖掘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元素,就成为论证中国革命具有本土性乃至民族性、中国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尊重历史事实,我们会发现中国革命的起源与发展其实与城市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小组是在北京和上海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上海成立的。近代中国的城市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提供了新式学校、各种社团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而这些传播新思潮的公共空间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不具备的。或许正因为此,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多是成长于城镇的知识分子。城市为革命知识人的成长和交往提供了全新的空间,比如租界、学校、电影院、咖啡馆、书店、报馆、亭子间等共同塑造了知识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情感方式。当我们把“城市性”这个因素带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阐释中来,很多新的历史研究论域就被打开了,比如城市的国际性与区域性问题,尤其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都市与东京、欧美城市之间的左翼思想和人员流动,城市与周边乃至乡村之间的思想、书籍、信息和人员的流动与互动,长期扎根乡村的中共入城以后与城市的运作模式、管理方式乃至精神气质之间的融合问题,等等。在这方面,最新的研究如高峥《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1949—195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便涉及这个问题。从更早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叶文心笔下的施存统在金华、杭州与上海这几座城市之间的穿越,萧邦奇笔下的沈定一在衙前、杭州与上海之间的奔走,等等。回溯传统革命史的已有论述,在很大意义上,晚清民国所形成的城市性被简化为资产阶级文化的象征,而在这些城市里寄身活动的知识人也就成为具有“原罪”的阶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南北问题、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中心与边缘、国统区与解放区等问题,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脉动里成为长久困扰其进程的重大议题。
再次,知识分子视野有利于在一个更为纵深和广阔的脉络里理解这个阶层在中国革命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在此前的不少革命史书写里,知识分子总是作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中的“毛”而存在,是一种被严重低估了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历史存在。事实上,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员、宣传与组织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可以说是一场由先知先觉并且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革命,是以新思潮、新理论、新观念等革命理论掀动中国社会的革命。就此而言,无论怎样评估知识阶层的作用都不为过。王奇生曾有一个判断:“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5)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第10页。张灏也曾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在1895年以后,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宇宙观开始解体,在知识分子里产生普遍的精神失落与思想迷惘。在惶惶的文化解体过程中,他们急需一种新的个人与群体生命的方向感、文化认同与精神的归属感。到了五四时代,这种精神失落已经变得很普遍,形成一种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五四健将罗家伦用‘回旋时代’来描写当时他们所面对天旋地转的精神世界,最能凸显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震撼。”(6)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77期,2012年9月,第15页。在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双重危机之中,知识分子既是这种危机最敏锐的感知者和直接的见证人,也是最努力试图改变中国危机状况的社会精英,革命就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方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角色、处境与功能的研究,就成为“新革命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动员而言,中共在乡土中国对农民等底层民众的动员,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乡村小学教师。乡村的地方文化精英和小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理论的“二传手”,他们成为联结城市革命精英与乡村普罗大众的最佳中介。按照刘昶的说法,这群人是中国革命的“普罗米修斯”(7)参见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71页。;最近应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指出了这一面相(8)参见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209—222页。。《中国青年》曾发文指出:“中国的小学教员,在客观上至少也应当是国民党左派的群众,阶级认识更清楚的进步分子应当毫不畏惧地站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旗之下。他们应当是社会各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连锁’;他们应当是农民运动的最适宜的人才;他们应当是乡村文化运动中心的力量;他们应当是散布革命种子在各地建筑革命势力的先锋!小学教员在社会的地位,一面可以与绅士、商家、地主相接近,同时也可与农民工人相接近。他与资产阶级利害的冲突没有工农的明显,而他的一点师长的威信,又可获得封建观念未消灭的乡村人民的相当敬意。农民对于小学教员的尊敬信仰,更不用说,所以小学教员如果以民族的利益来号召,必然能在乡村中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而无疑。这种联合战线的建立,对于民族、对于工农,对于小学教员本身,都有绝对的利益。但是如果除去这介于中间的小学教员与学生做连锁,这个联合战线时时都有破裂的危机。”(9)砍石:《怎样做小学教师》,《中国青年》第138期,1926年10月。在城市里,无论发动工人参加罢工还是吸纳中小知识青年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乃至共产主义革命,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如裴宜理研究安源这座小城的罢工政治,就敏锐地注意到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是如何充分利用基层社会尊重读书人这一文化传统来进行“文化置位”的。可以说,离开了知识分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就宣传而言,中共自20年代一诞生就一枝独秀,在意识形态竞逐的场域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与一批卓越的宣传家比如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彭述之以及后来的胡乔木、邓拓等发挥的历史作用密不可分,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从知识分子的视野切入,重新审视20年代中共与国民党尤其是中国青年党的理论竞争和思想激辩——其实质是争夺被政治化的进步青年——就可以为打开这个影响中国至深且远的“1920年代”提供最有效的历史路径,比如在《中国青年》《向导》等期刊上进行的中共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的大论战。就组织而言,中共从一产生就深受苏俄组织体制之影响,后来又派出刘少奇、蔡和森、李立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而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更是逐步锤炼其组织的严密性与灵活性。相对于国民政府党政系统的二元化倾向及其带来的组织系统的分散(10)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中共在纯化组织队伍和灌注革命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这些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群体在其间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后,知识分子视野有利于拓宽“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径以及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一提到革命史研究,习以为常的学术路径是政治史、社会史等研究方法,预设的往往是政党如何动员和组织民众,对于1949年后的当代史研究也经常是预设了一些基本问题,如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伸展到基层社会和地域社会的或不同地域社会和文化对于革命政治的差异化应对。但若将知识分子视野引入,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将能由此及彼、由表入里,精神史、心灵史和思想史等学术路径都可以逐步导入。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中共与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关系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革命按经典定义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但事实上不得不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小资产阶级和没落士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理论预设与革命的实际运作之间存在一种无法消解的悖论。正因如此,在40年代的延安,党的刊物就曾提出“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这一看上去似乎矛盾的命题(11)《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共产党人》第1卷第3期,1939年12月1日。。事实上,若从共产主义革命的长程和特征来看则丝毫不让人费解,前者表征着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意图,而后者是在实际的革命过程里觉得必须提升工农的文化水准才能有效开展工作。正是知识分子的参与,带来了这场革命的丰富面相,也给这场革命带来了一种天然的崇高性与超越性,更赋予这场革命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复杂内涵。
知识分子视野的引入使得“新革命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丰富,而中共革命与知识分子尤其是边缘知识分子的深刻而复杂的关系也在“新革命史”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得到更有力的揭示。有学者指出:“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12)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这些在社会流动中居于边缘的知识群体,相当一部分因为理想主义的感召、民族主义的刺激和现实生活的困顿而投身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的革命之中。边缘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中的位置、处境、角色与命运,赋予了这场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特质与底色,比如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群众性与阶级性、革命在城市里对中小知识青年的动员和吸纳等,而这恰恰是“新革命史”研究值得进一步去探寻和挖掘的学术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