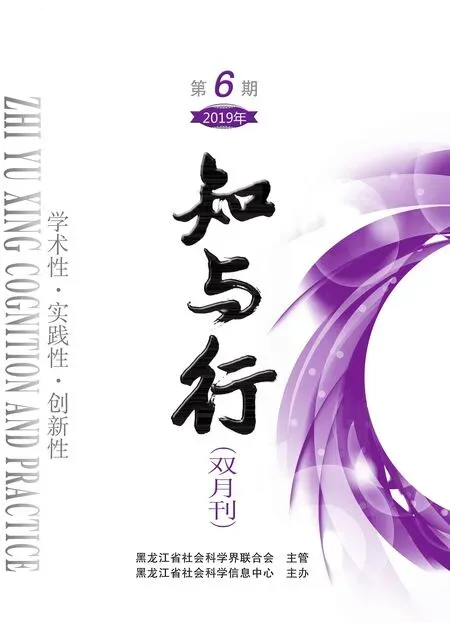灵知精神是时代的精华还是糟粕?
——以沃格林与阿甘本的理论为切入点
林海璇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与列奥·施特劳斯从历史大家着手勾勒西方政治哲学史不同,德国政治学家沃格林从诸如爱尔维修、达朗贝尔、巴枯宁等小人物身上寻找现代性危机的症候,进而断认: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灵知主义的存在,就如同德里达认为共产主义是幽灵般的存在一样,它从不寓居于某一主义之中而亘古不变。如果沃格林的现代性诊断是合理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断:现代性危机的产生实质上也与灵知主义的丧失有关?马克思认为哲学是时代的精华,那么灵知精神究竟是时代精华还是糟粕?
一、灵知主义与生命政治的缘起与分歧
沃格林从早期自身经验中体察到“极权主义的革命成为人们看待现代文明之展开的透镜”[1]3。这种从现代性最极端和最隐晦的场域透视着现代文明发展总体性的做法,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吉乔奥·阿甘本的理论视角不谋而合。两人在同一起点上走向了不同的岔路,沃格林选择了灵知主义作为现代性危机的“消毒剂”,即他更侧重于挖掘纯粹的宗教精神,灵知精神更是基督教精神的精华所在;阿甘本则是从“身体哲学”方面入手,集中于《亵神》《潜能》等散文,甚至是使他扬名学界的“神圣人”系列,其架构也是围绕“赤裸生命”而展开。“赤裸生命”的理论原型是罗马法中的“受谴者”,但在他唯一一部纪实性档案记录作品《奥斯维辛的现代性残余》中,我们可以找到“赤裸生命”最原初的现实形象——纳粹集中营中的“活死人”。由此可见,沃格林基于极权主义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是其理论渊源,在之后的作品中,我们鲜少再见到他回归这一敏感性历史问题的探讨,而是全部围绕“灵知主义”在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等不同领域中的渗透性影响。
灵知主义的式微与生命政治的崛起、兴衰之间体现的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症候。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形成的“欲望塑性生产”、人被物欲化与工具化,产生的两个后果,一个是人的精神陷入空虚与贫乏,纯粹追求智慧的灵知精神无论在哪一个主义之中都是难以生存的,因为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思维逻辑背道而驰;另一个是人的去政治化,人的去政治化是哈贝马斯预断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直接结果:现代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诱大众投身科技事业,从而不问政治事务,产生出“非政治化”的政治真空状态。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人主体陷落的实质表现,然而灵知主义旨在拯救现代人灵魂,重塑现代人精神生命;而这正好抵牾与应治生命政治对人的身心的全面性摧残。从这个意义上说,灵知精神是时代的精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在经历了神启——人启之后,人在现代性中重新迷失自我,这时让“基督教精神”重新归位,是对西方精神世界、伦理道德的塌方的根本性的思想救赎。
二、沃格林与阿甘本对神圣性的不同解读
沃格林与阿甘本对“神圣性”有不同的解读,在沃格林看来“灵知主义”的“神圣性”必须是与有正义的灵魂的相结合,会产生改造救赎世界的作用,若与邪恶反动的灵魂相结合,对世界而言就是一种毁灭。沃格林的理解范式符合大众对“神圣性”的积极理解。而在阿甘本看来,只有在生命政治下重新审视“神圣性”才能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对“神圣”与“卑污”的颠倒,看似“神圣”的普世价值、人权理论,实则是最为空洞无力的“人权陷阱”之所在,是体现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之本质所在。相较之下,阿甘本对“神圣性”的异质化解读,为其打开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批判的现实路径,而沃格林,则在哲学形而上的范畴中,囿于并止于“理论批判”。
(一)灵知主义的“神圣性”
面对后启蒙时代人的工具化和价值理性的陷落,自由主义的旁观姿态,为极权主义势力开展变态的意识形态工程提供契机。正如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它先于肉体在精神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通过向民众普及政治观念,实现意识形态霸权。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掌舵者,通过自我神圣化,成为世俗的上帝,拥有民众绝对的信仰崇拜。这种神圣化操作,最终形成弗洛姆心理学分析中的“法西斯主义人格”。独裁者进一步将个人人格赋予国家,从自我神圣化进一步发展到他我神圣化,从而形成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人格”。据灵知主义者看来,灵魂具有灵性,并不代表这灵魂就是正义的,它也有可能是邪恶的、反动的。所以沃格林才会说:“当这些灵魂(真正具有灵性的灵魂)的无可置疑的深邃被错误导向人的启示时,只会加剧破坏的力度。”[2]3希特勒深受尼采“意志论”的影响,其自传体《我的奋斗》中,将个人意志进一步发展成操纵国家命运的权力意志,极端鼓吹个人奋斗精神拥有可以创造和摧毁一切的力量。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凯撒主义大国情节,这些都成为法西斯主义在精神层面上对人的本质进行全面性改造的意识形态手段。这是比纯粹的政治革命更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革命,不过这种思想革命被邪恶的具有灵性的个别灵魂导向了灾难的深渊。
灵知主义的“神圣性”,只有被具有正义的、有灵性的灵魂所把握和知觉时,才能发挥它所独有的世俗化的宗教创造力。如果说独裁者作为邪恶的灵魂从一开始就试图混淆“神启”和“人启”的根本异质性(这从法西斯独裁者用个人意志完全取代上帝意志可以看出,他们的野心不只是成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不仅仅满足于代理上帝管理人间事物,而是要彻底取代上帝,成为权威与权力的统一体;而一般国家主权者依然恪守对神灵的敬畏,遵循通过“神启”达致“人启”的过程),那么正义的灵魂从一开始就会将两者截然对立,并且会将“神启”转化为“人启”,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蕴含的灵知精神。
撇开经济决定论不谈,那些将马克思理解为弥赛亚式的人物的思想家,是否都捕捉到其核心所在呢?革命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但是将革命展现为一种“革命性启示”的,马克思是第一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地位无须赘述,但很少人去质疑,这种新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告别了旧唯物主义,是因为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人的空场。可是马克思也未曾明言他与唯心主义,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彻底决裂。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藕断丝连的地方,就在于展开思想革命,对人进行革命性启示。谈到德国古典哲学,我们不能因为它纯粹思辨的无显示性的革命行动力的致命缺陷,就连带否认它在意识形态上巨大的革命潜力。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对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认知就十分具有“灵知性”,“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3]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意识形态上的观念革命,启示并催生了马克思具有现实性的实践革命,柯尔施将其视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
但是,沃格林对马克思进行的弥赛亚式解读也是存在缺陷的。我们肯定马克思具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认为这种科学主义并不是孔德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而是倾向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的灵知主义。马克思早期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兄弟的批判,并不是简单地指向纯粹宗教批判,更准确来说,他批判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二分,是对宗教世俗化与世俗宗教化这一德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批判。他的批判指向内隐了多个维度,既包括对当时德国民族意识觉醒远远落后于法国的焦虑,也是对当时宗教精神的萎靡不振的失望,认为应该有一种全新的革命精神取而代之,从而达到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目的。以基督教精神在西方以及犹太人传统中的正统性地位来说,与其说用一种外来的“舶来品”来取代腐朽化的宗教精神,倒不如说,宗教精神本身通过内部的自我革新,重新焕发革命力,一种全新的基督教精神为西方世界所接纳的可能性,远远要大于毫无根基的外来思想。可以说,灵知精神是基督教精神的精华所在,沃格林将马克思弥赛亚体认为一种“革命末世论”是不恰当的。灵知精神正是剔除了基督教精神中消极被动的认命,等待救赎,或者无所作为,这显然与革命内在的抗争性是相悖的,它所保留下来的是,对人自我拯救的积极行动的肯定,对人实现从无意识向有意识的历史性存在的转变、从自在到自为的更高级别的精神解放的肯定。因此,马克思主义带有弥赛亚色彩,在于它内在性地承继了被其自身批判扬弃的灵知精神,不应该将灵知精神与宗教精神混为一谈,在何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弥赛亚主义,也绝不会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的前提下演说的。
(二)生命政治的“神圣性”
“神圣性”是阿甘本展开生命政治批判的基本架构。但在阿甘本的语境下,与我们所理解的语汇发生了形式与内容的倒错:“神圣人”恰恰不是意指最具神圣性,而是最卑污和最低贱的代名词。“神圣化”也不是由凡入圣、超凡入圣的过程,不是入天堂,而是下地狱,成为非人的存在。“神圣性”使得生命直接弃置于暴力之下,成为被主权者肆意征用、捕获、控制的对象。“赤裸生命”就是这样一种通过“神圣化”操作而成为“神圣人”。神圣的躯壳下是污浊的内在,这就是“神圣人”(或称之为“赤裸生命”)遭到弃置的原因。而如果从沃格林的灵知主义来看,这种肉体的摧残直接导致了精神上的枯萎,这从历史上集中营中囚徒的生存状况可窥知。阿甘本解读的生命政治下的“生命”具有双重性:一是人的自然生命,二是人的政治生命,唯独缺失了精神生命的维度。对于人肉体生命的沦陷而导致“赤裸生命”的生存状态,阿甘本也确实提出了自己的救赎方案:用“形式生命”对抗“赤裸生命”。何谓“形式生命”?在《至高的贫困》中,他谈及未来共同体中人们重返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是“生命不可分离之形式”,从而使得回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善好的生活”成为可能。虽然阿甘本未曾摆脱“人是政治性动物”的思考路径,对于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生活与幸福的、有质量的生活之间进行的直接关联全盘接受,但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关注到个体性生活中的人通过生活方式达到对精神生活的调节与提高的作用,这从他谈到人的天赋只有在共同体的生活之中、在与他人共处的共同生活中才得以可能。并将这种共同体的凝聚力归于拥有唯一一个共同的心灵与灵魂。实则在这个时候,阿甘本已经在他的生命政治批判中展露出“灵知主义”倾向。因此,他一方面主张人的重新政治化,同时却也提倡一种清心寡欲、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但此时他还未完全转向对思想、精神的关注。直到在后面出版的《无目的的政治手段》中,阿甘本直接将“形式生命”等同于“思想力量”,“思想即形式生命,它是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这种生命的密不可分性——生命在理论中、同样程度的也在身体过程和习惯方式的物质性中呈现的这种密不可分性——生命在哪儿,哪儿就有思想”。[4]将思想赋予“形式生命”这一核心概念,表明阿甘本已经从不自知的探索转向了明确的救赎方案,唯有思想精神的救赎才有可能抵牾生命政治。
可以说,阿甘本“神圣人”系列中的所有意象本质上都是非神圣性的存在,以神圣之名命名卑污之物,以一种反讽的手段揭示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对人肉体上的直接性摧残,导致精神上的健全与发展更不可能。现代“神圣人”还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潜在地可能成为“赤裸生命”。阿甘本这一惊悚的政治预言有何依据?人权话语的虚假性是阿甘本在多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人权宣言,在阿甘本看来就是一个虚假的人权陷阱。但是,仅仅是主权者设下陷阱就可以制造出“赤裸生命”吗?恐怕未必。换言之,阿氏之从主权者愚民的权威视角去解读人民沦为“赤裸生命”的必然性,反观历史上在集中营中的“赤裸生命”,他们之所以行尸走肉,在于灵魂受到摆布,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灵魂,更谈不上拥有灵知。而现代性社会缘何还会重蹈历史悲剧呢?我们排除掉难民、移民等特殊人权主体不谈,就普通公民而言,为何连捍卫自身基本的权利,甚至是生命权也丧失了?根本而言,是西方民主制度下,公民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丧失,尤其对基督教精神中灵知精神的体悟能力的丧失。所以阿甘本仅仅从公民的去政治化这一后果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还只能算是触及皮肉的批判,真正伤筋动骨的甚至不是西方伦理道德的全面塌方,因为这还只是表现之一。只有基督精神,或准确称为灵知精神的彻底丧失,才会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面临毁灭性危机。
三、灵知精神是时代的精华
阿甘本在生命政治批判视野下,从哲学高度上将“灵知主义”荟萃为“灵知精神”来把握,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升华的过程,不仅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而且契合马克思对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的理论判断。阿甘本将“灵知精神”升华到哲学高度与哲学立场,其理论逻辑是: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并从中诊断其根源是灵知精神的缺乏;为了应治这一危机,从灵知精神的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作为社会交往的灵知精神,如何通过语言与交往行为展现出来;最后提出灵知精神的未来希冀,成为复兴共产主义的精神导向。
(一)交往行动的指导原则:灵知精神具有流动性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种宗教精神成为时代的精华是否缺乏科学性呢?当然这里我们仅限于探讨西方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灵知精神,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灵知精神,脱胎于宗教,却不留宗教迷信、神秘主义的痕迹。这从柏拉图将哲学誉为“爱智慧”就可见一斑。沃格林认为,灵知精神作为精神救赎的方案,必须具有流动性,它不能囿于基督教传统中,它需要求助于所有与宗教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才得以“溢出”。这也是为何在沃格林的作品中,他总是试图从不同流派的不同思想家身上寻觅具有独特性的“灵知精神”。他的理论阐述也是基于一种“灵知精神”,关注每一个思想家思想建构背后的“智慧”,格外重视作为个体的生命流程中的经历对其思想的塑形作用。因为灵知精神的核心在于个体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在于对自身命运中的因果性的通达彻悟外化为行为,就是一种人际交往关系。人际交往关系是否和谐,在于是否达到主体通性。交往关系是一种对象性活动,这决定了人对自身命运因果性的掌握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通过他人来达到。因此哈贝马斯在《劳动和相互作用》中,就以黑格尔对基督教精神的论述为例,表面上看,不明命运因果性的人会破坏伦理的总体性,即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但实际上,不明因果性的人会使得自身陷入被排斥的境地:“长期忍受被排挤和被隔绝在生活之外的痛苦,直到他在异己者的镇压下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在远离异己的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异化。”[5]纳粹集中营里的“活死人”现象,就是在强行暴力下脱离了与正常世界的交往联系,在营中经历了由肉体向心灵的逐步沦陷。他们是丧失灵知精神的极端代表。
哈贝马斯把在黑格尔纯粹观念上的主体间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具体的语言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以语言为媒介,也是一种将内在智慧与灵性外化的直接而有效的途径。灵知精神作为时代的精华,不能被桎梏于自我沉思,而是要外溢出自身,借主体建立对象性关系的契机表现自己的实际存在。所以人们常常会说,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在修养,贵族与暴发户的鲜明对比就是这么而来的。要言之,灵知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走出宗教、哲学等传统意识形态藩篱,并借助语言等多种表现形式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关联,这是灵知精神潜移默化地世俗化过程。
(二)现代危机的产生根源:灵知精神的丧失
现代性危机的产生是信仰危机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在西方都逐渐成为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用以标榜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砝码。宗教确实是走入西方寻常百姓家,他们周日依然要去教堂做礼拜,他们睡前依然会在床前放置一本《圣经》。但是我们也见到,在西方“景观社会”“消费社会”等新型社会形态之下,一切行为都失去了本真意义,要么沦为纯粹的物欲行为,其代表就是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要么就是为了意义而意义,徒有虚表,例如,圣诞节成为购物狂欢节,人们更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过消费来放纵自己,谁又愿意如苦行僧般静心省思呢?万圣节成了装神弄鬼的游戏,谁又还记得表达生者与死者平等的这样一种愿景?
灵知精神的丧失,不仅仅是一种集中现象,它已经裂变为一种普遍现象,现代人层出不穷的拜物教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还是伊居·德波的景观拜物教,人一直是以匍匐的姿态转移着朝拜的不同对象,当人对自己所造出来的“物”顶礼膜拜的时候,这种异化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可以这么说,现代社会衍生出的诸多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国家合法性危机等等,本质上都是灵知精神丧失的症候。这并不令人诧异,因为同理而论,如果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夜之间从地球上彻底消失,那么次日醒来的中国人就真的成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无家可归”之人了。灵知精神,从狭义上说,就是西方世界精神文明的根基与命脉。而出现形形色色的危机,现代国家如果只是像修补匠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抑或者是如庸医一般讳疾忌医,治标不治本,怕伤筋动骨,可能就有陷入全面瘫痪的风险。从广义上说,灵知精神滥觞于西方,但随着世界交往进程的演进,共产主义的幽灵都能够从欧洲上空远洋而来,灵知精神又有何不可?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包容性和内化力十分强大的文明国度,有多少“舶来品”成了“中国特色”,反倒是其本祖本源被历史所遗忘。共产主义是否中国化不是在此讨论的重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共产主义确实在中国扎根了,并且相比于越南、老挝以及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的更加稳定。其根本分歧在于,我们不仅塑造了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外在形象,而且发展改造了共产主义的合理内核: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就是虚无缥缈的,因为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教科书式的教条化理解,则是掏空了作为“灵魂”内核的“灵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的智慧精华都被抛弃了,留下的都是无用的渣滓。
(三)共产主义的复兴:灵知精神的重生
灵知精神被边缘化的现状,与几百年前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生存境遇惊人的相似。为何作为时代精华的东西的发展都命运多舛呢?相比于灵知精神,共产主义如今已经取得一定的世界认同感,甚至被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作为一种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改良制度选择。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与灵知精神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前者的成功复兴,必然为后者的重生提供契机。在基督教社会前景堪虞的情况下,与其在厘清宗派斗争与信仰分歧之间耗费精力,倒不如暂且悬置“基督教”这一空壳,我们又何妨以共产主义为灵知精神“道成肉身”的现世的载体,试图重新盘活灵知精神呢?沃格林在实证主义者孔德的思想中挖掘出历史哲学发展的“灵知式”特征,虽然孔德并未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联,但从孔德的解决路径设计来看,却无意之间内在勾连了马克思强调历史进程中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孔德看到并试图调和的历史无意识过程和历史意义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将历史意义归于人类思想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进过程。马克思虽然不完全承认这种带有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发展史”,但意识的演进过程内嵌于马克思诸多理论之中:在早期异化理论中,马克思在探讨劳动异化的问题中,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是最深层次的异化,其他三种异化都是其外在性表征。因此,对于当时处于异化状态的劳动者来说,如何才能摆脱身体上的压迫和精神上的摧残呢?单单从无意识的麻木状态被触觉到受压迫的有意识状态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意识到并且进一步深化这种知觉,深入到对异化根本原因的探索中,找到其根源在于类本质的异化,才有可能真正摆脱异化的桎梏。甚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卢卡奇首肯的是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作用。实证主义者孔德给马克思宝贵的灵知精神财富就是一种人的启示,他的精神统一的“心灵理论”以及为之奋斗的世俗宗教的目标,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对精神维度的构建和社会维度的构建不谋而合。灵知精神实然蛰居于共产主义之中,也许开始只是为了寻求以避难之所,但当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将传统的宗教、哲学都消灭之后,灵知精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或许才能大白天下。
灵知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华,除了具有流动性,还具有包容性。它哪里仅仅满足于一个孔德呢?它完全有足够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那些被历史一棍子打死的思想家中挖掘出思想宝藏。巴枯宁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撒旦思想”“神秘主义”“虚无主义”等标签似乎一直存在。但在一片思想荒芜中顽强存活的革命理论,无形间启迪了马克思去寻找历史革命力量的代理人,马克思最终找到了“人民群众”,巴枯宁却囿于“贫苦阶级”,但不可否认,马克思确实受到巴枯宁“心灵是革命的本质”的理论影响:如果没有革命情感、激情等因素,那么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和国家政治学说就冷酷到与“独裁主义”理论别无二致了。同样,马克思在谢林“内在的回归”中找到了“自由与必然”,甚至在费尔巴哈那里也能从中寻觅出一点人类本质学以及宗教世俗化的启示。
灵知精神在马克思这里找到新的栖息之所,这种脱胎于宗教却能极强适应带有科学性的理论载体,源于这两种理论之间具有“同宗同源”的历史亲缘性。很多人会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弥赛亚主义,但马克思个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能够使得他彻底摆脱宗教思想吗?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反问之,如果英雄没有出处,他又何以为了摆脱自身不愿承认的出处与之进行自我批判?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早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学的批判,都是在与一个个分裂的“自我”进行自我斗争。沃格林试图还原所有形形色色思想家中宝贵的“灵知成分”,而阿甘本在触及这个问题时更倾向于将其外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生命形式,无论如何,这两位当代前沿思想家都为我们思考“灵知主义”打开了全新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