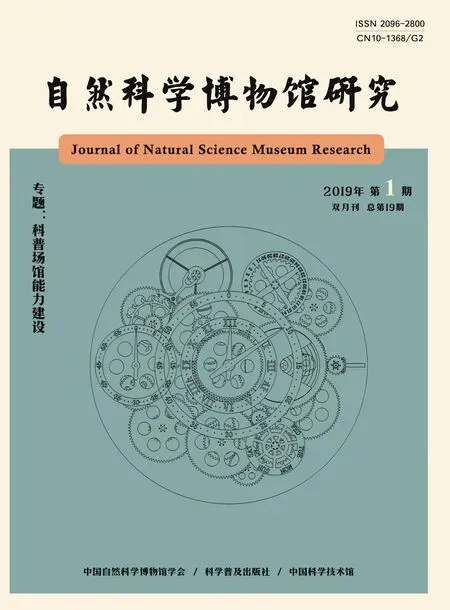“参与式博物馆”之 “参与”的理论与模式
—— 《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书评
费 扬
一、关于本书
(一)作者简介
妮娜·西蒙 (Nina Simon),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现任美国圣克鲁兹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长、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其在社交技术、游戏、参与式设计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曾为世界各地上百家博物馆与文化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与参与式项目设计。此外,她不但运营着网站 “博物馆2.0”,该网站与全球多家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文化机构合作,开展了多项教育项目与观众参与式展览;而且,她常常在Ted等平台上向博物馆界及公众传播参与式博物馆的理念。她于2012年被美国博物馆协会授予 “南希·汉克斯”奖,且被 《史密森尼协会会刊》誉为 “博物馆的远见者”。
(二)本书背景
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源于博物馆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乔治·E·海因尝试将 “建构主义”②建构主义最先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者基于原有经验建构知识的过程,源于社会文化中的互动。引入博物馆中的学习与教育,其认为:“观众是可以在博物馆学习的,人们在博物馆内的经历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用自己的心去感知自我、感知世界。”[1]这种强调通过观众自身的探索去获取新的知识与见解的学习模式与学习行为是本书的理论支柱。在妮娜笔下,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剧院等文化机构不再是以往庄严肃穆的 “神殿”,而是需要观众通过参与分享经验与见解的 “大众论坛”。因此,她将这些参与式机构定义为: “观众能围绕其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2]而涉及传播学范畴,“参与式博物馆”的提法可溯源到 “参与式文化”一词。美国传媒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将 “参与式文化”定义为:“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的障碍相对较少;十分鼓励创作以及向他人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合作指导,将丰富的经验传授给新手;参与其中的成员认可自身的贡献;成员彼此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交联系 (至少他们关心别人对其作品的看法)。”[3]可见, “参与式文化”的内涵在于人们通过分享、交流与合作成为文化的参与者与贡献者,妮娜将之引入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机构,意在强调观众不仅仅是博物馆的参观者与内容的消费者,其可以通过自身参与、与他人交流甚至是与馆方合作的方式,成为博物馆内容的贡献者,从而最大化提升博物馆展览的传播效益。
此外,本书的副标题 “迈入博物馆2.0时代”中的 “博物馆 2.0”一词脱胎于 “Web 2.0”,Web 2.0指互联网传播互动中的一种新型模式,“它比其前身Web 1.0更具动态性与交互性,允许用户访问网站的内容并生成更多的内容”。[4]而妮娜将其引入博物馆领域,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关于博物馆情境学习、认知体验等相关的理论,构建起关于 “博物馆2.0”的蓝图。她希冀的 “博物馆2.0”时代中,博物馆不再高高在上地作为内容的生产者,观众拥有更多自主表达的权力,他们将与博物馆一道,成为知识的传播者与产出者。
二、关于参与的理论
(一)从 “我”开始
作者认为建立参与机制的第一步在于确立以观众为中心的原则,“以观众为中心的第一步不是思考机构或其项目可以提供什么,而是找出谁才是有兴趣的观众;什么样的体验、信息和策略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2]为此,博物馆需要转变运营态度,不单单考虑博物馆能提供什么,而是思考观众需要什么?在此,作者引入“拉取式 (Pull Media)内容”①互联网术语,指用户主动在网络上检索信息。的概念,强调观众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应扮演主动搜集信息的角色,自主筛选信息的前提是需要博物馆将每一个观众视作独立的个体,尊重观众的个性,合理利用观众的个人资料。此处,作者介绍了 “library Thing”②国内与其类似的网站可参考豆瓣 “读书”板块,详情请登录:https://book.douban.com/。网站的例子,读者可以在该网站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型图书馆,读者通过在个人资料中添加阅读过的书籍资料,该网站便会生成类似于图书馆的书单,向观众推荐类似的书目。将此方法移植到博物馆中,馆方需要通过前期搜集观众资料,了解观众的个性与彼此间的差异。例如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短期展览 “英雄”,观众在参观前都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测测自己最像八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神怪中的哪一个;测试结束后,馆方会为观众派发记录有英雄相关信息的卡片,观众可以在了解个性的同时进行主动参观。测试通过信息过滤的方式为观众的后续参与铺平了道路,使观众迈出了进馆参与的第一步。
(二)从 “我”到 “我们”
除了探讨个人行为的参与,作者基于 “Web 2.0”理论,试着将 “我”引申到 “我们”,将文化机构的个性化转为社交化,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互动,从而增强体验感。集体性的参与体验要求各位观众经过彼此的互动形成网络后,促使观众之间进行社交,每位观众都能真正参与进来,获得丰富的参与感与体验感。然而虽然有的观众带着社交的目的进入博物馆,但并非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喜欢与他人密切交流,或是跟其他观众组队,而不给自己留下一点私人空间。因此 “卓有成效的从 ‘我’到 ‘我们’式体验会协调好个人行为和个人喜好,从而产生一种既有效又有趣的集体价值。技术专家常把这称为 ‘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2]这种集体智慧产生的前提即在于博物馆设计一个能让每位观众都参与其中的社交平台,这一平台首先需要博物馆以及各个文化机构明确其设计的展览或者项目要取得什么目的,观众间应采取何种互动方式?在此基础上,这一平台 “需要以观众和机构是否获得有用的成果来衡量社交平台的功效,而不是单纯地为了采集数据,这样设计出的社交平台才能反映出馆方及各文化机构所期待的参与价值。”[2]例如书中提到的由美国未来研究所发起的 “科技大畅想”项目,该项目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供玩家相互间进行对话的游戏,但吸引了众多玩家集思广益,进行头脑风暴。它预设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未来进入太空跟现在上网一样方便,你打算做什么?”玩家不可以给出笼统折中的答案,他们要么往好的方面想象,要么往坏的方面想象,然后将所给的答案展示出来。每位玩家都可以在网站给出的索引卡片中挑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行回复,这样玩家可以回复任何人的卡片,而自己的卡片又可以被任何人回复,由玩家间的互动浇灌的问题树逐渐生出枝丫,最终在讨论网里长成参天大树。未来研究所通过 “科技大畅想”搭建的社交平台,以问答的形式连接起了每一个陌生的玩家,玩家在平台上畅所欲言,分享各自的知识。这个平台也很好地体现了未来研究所 “帮助人们对未来作出更好的、更有见地的决策”的理念。
(三)设计社交实物
博物馆在搭建好社交平台,吸引参与的观众相互取得关联后,另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便是博物馆内的实物,即藏品以及那些帮助藏品进行阐释的辅助展品。妮娜在本书中提倡的社交实物并不一定是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精美文物,“而是看它能不能激发观众间的交流,能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社交体验。它们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即个性化、话题性、刺激性与关联性。”[2]这些实物需要能够嵌入博物馆营造的社交情境中,它们往往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以及想要互动的欲望。例如,博物馆中常见的关联性实物,它们多以互动装置的形式出现,观众需要通过彼此间的合作来解决馆方给出的问题或是通过互动参与达到某一效果,实现博物馆展览的传播效益。
此外,也有学者探索了运用真实生命体创建真实自然环境的多感官参与的可行性。他们从美国植物园的实例出发,探索植物与观众之间产生的社交联系。“沉浸式自然体验能够让观众们在植物园中全身心地体验植物;漫步在花园中,嗅闻、观察、触碰植物,增加的交互式展览和项目还能丰富观众的体验。”[5]这些植物园通过多感官参与的平台,人们 (尤其是孩童)可以在室内或室外探索各种各样的植物,通过一张庞大的参与网,汇聚起人与植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联。这一具有生命实体的展项也丰富了社交实物的内涵,为建构不同类型的参与式博物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三、建构参与的模式
(一)四种参与模式
本书中除了有关参与的理论外,妮娜对于参与式博物馆的实际操作也进行了相关探索。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促进中心发起的 “公众参与科研项目”(简称PPSR)将公众参与科研的方式分为三大类,即贡献型、合作型与共同创造型。该分类根据公众参与科研的程度划分,从贡献型到共同创造型表明公众参与科研的程度逐级递增。而妮娜在PPSR项目分类的基础上,为观众参与博物馆活动增设了第四种模式——招待型。“招待型项目就是馆方将其部分设施和资源移交给公共团体或一般观众,帮助他们开发、实施并展示自己的项目。招待型项目最大限度地减少馆方的干预,让参与者自己使用机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2]贡献型参与模式,观众虽然可以参与博物馆活动,但主导权与控制权掌握在馆方手中,博物馆中随处可见的留言板便是观众贡献的常见项目;合作型参与模式,馆方虽然邀请观众参与到有关项目的制作中,但主导权仍然由博物馆掌控;而共同创造型参与模式,观众与馆方合作的同时兼顾二者间的双重需要,与合作型相比较,在共同创造型参与模式中馆方赋予观众更多的权力,合作完成的项目也由馆方与观众共享;招待型参与模式,观众的权力达到最大化,观众能通过自身掌握的参与技巧自由使用文化机构,从而为机构带来一定的创造性收益。台湾学者刘婉珍也介绍了温哥华美术馆 “开放式创作坊”这一招待型参与模式的意义与影响。“开放式创作坊是一个以观众为中心的实务操作学习场域,观众可随时自由进出,自己选择创作坊中的材料进行创作。观众不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也是一个进行社会互动的场域。场域中常出现儿童引导父母及祖父母尝试新媒体,以及祖父母示范如何用针编织,画面动人。”[6]从贡献型模式到招待型模式,不仅意味着博物馆与各文化机构权力的下放,也意味着观众参与的方式与程度也在逐渐深入。观众与博物馆可以处于同等地位,馆方不干预原则下的观众参与不但展示了博物馆亲切的一面,而且观众的大胆尝试可以为博物馆后续的运营建设带来更多有益的思考。
(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在探讨参与的原则、理论、具体实施项目后,还需要思考如何使参与式项目可持续发展。“参与式项目只有和馆内文化相一致的时候才能获得成功。不管它与馆方的使命有多么深的联系或是其理念有多么新颖,它必须要让工作人员觉得操作起来方便,这样他们才会全心全意地接受它。参与式文化需要对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关切予以教导、支持和回应。”[2]参与,首先需要让工作人员参与进来,“当博物馆决定与观众建立联系时,双向沟通与对话的机制是首要考虑的,这意味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必须被纳入到整体思考中。”[7]博物馆在应对观众参与的同时,不能全然不顾工作人员的诉求与利益。工作人员内部群体可以对参与式项目进行先期试验,通过自身的参与,思考该项目有何改进之处,然后再引导观众进行参与,取得更好的效果。再者,馆方需要改变态度与馆内文化,馆方需要适当性地放权,与观众建立平等且友好的关系,多鼓励馆方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听取观众的意见和想法,给予观众更多信任。参与的长效发展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博物馆与各文化机构在运营阶段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需要将 ‘博物馆就是论坛’的宗旨贯彻到底,同时鼓励观众营造自由的参与空间,鼓励工作人员大胆创新,启用参与式项目,融汇新的沟通技巧。”[2]
四、相关思考
本书的编排体例既逻辑严密又简洁明朗,妮娜从参与的原则出发,论述了参与如何由从“我”为中心过渡到 “我们”的社交化倾向,并归纳了四种参与模式,最后对参与的长效实施进行了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一再强调的 “参与式博物馆”并非是一种特定的博物馆类型,而是一种博物馆乃至各大文化机构的设计理念,妮娜期望通过参与式理念的探索,使得更多的博物馆与文化机构加入参与式项目的尝试,共同促进文化机构迈入 “博物馆2.0时代”。
本书提供了许多颇为出彩的案列,它们代表着各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在践行“参与式理念”的有益尝试。这些案列既包含了许多生动的博物馆展览项目,也不乏一些具有启迪意味的线上游戏,它们一起被妮娜嵌进了“博物馆2.0”的理论与实践之网中。作为理论思考的先行者,本书作者妮娜·西蒙建构了有关参与的前期思路,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可以在 “参与式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后续的观众研究,探讨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应该如何参与,以期与妮娜的 “参与式理念”建构起更为细致的 “参与式系统”。
然而,将 “参与式博物馆”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博物馆界,而不考虑实际的建设与运营成本,自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有关 “参与式理念”却可以为我们所用,如书中提到的社交实物。我国博物馆可以思考如何设计契合博物馆社交情境的实物,它们可以激起观众的兴趣、引起观众间的对话,甚至可以引发观众的好奇与惊讶,这样博物馆在社交实物层面就不仅仅停留在一些令人逐渐乏味单调的互动装置上。再如我国近年来新兴的民俗类博物馆与非遗类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展览对象通常是物质实体背后的动态展示过程,例如龙泉窑青瓷的制作工艺、某个民族的传统歌谣等等,对于此类“非物质”的展览对象,观众通常需要上手操作,并通过现场的体验来感受它们的魅力。因此,引入 “参与式理念”便大有裨益。如妮娜提到的参与模式中的招待型,博物馆可以在规划好参与成本,做好前期准备后,“大胆放手”让观众自己在创作坊中随心所欲地创作,体验传统技艺的制作流程。有经验的观众可以向新到访的观众示范相关操作的细节。观众自己制作的成品也可以成为展览的组成部分。
本书作者所希冀的 “参与式博物馆”是在参与式系统中运行的有机整体,馆方多以亲民的形象出现,他们提倡的馆内文化鼓励观众自由参与,而博物馆中的工作人员也多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可以让观众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参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交活动,分享智识经历,并为博物馆生产展览内容,相应地博物馆也能在观众间的对话以及观众与馆方的对话中提升传播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