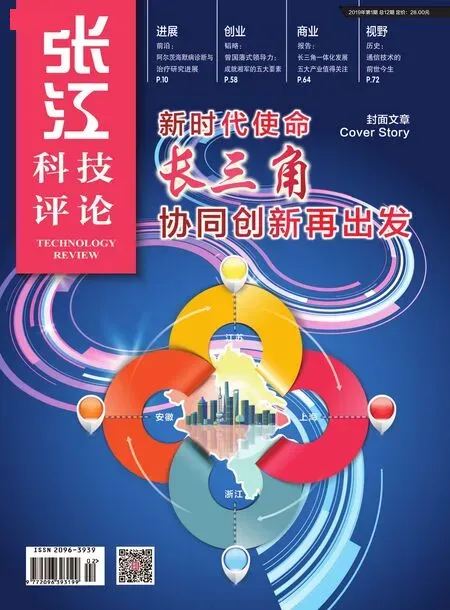我国新药研发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 文/陈凯先
我国新药研发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方面利好因素在逐渐形成。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我国的创新药物研发逐步接近或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0世纪中期,以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生命科学进入了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时代。20世纪末期,基因组学研究、基因组测序技术和功能研究的发展,形成了生命科学的“第二次革命”。现在,生命科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 “汇聚”,生命科学不再是单独的、界限分明的学科,而是一个跟物理学、信息科学、工程学等很多学科互相交融、汇合发展的学科。
学科的交叉和汇聚拓展了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的空间,技术研究和开发应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创新的周期也大大缩短。由于技术创造、商业模式和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创新模式越来越显现出网络化、全球化的特点,加速推动产业变革的步伐。
新药研发的前沿动向
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肿瘤免疫疗法、生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生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药物研究的不断进步。
基因编辑技术在清除艾滋病病毒(HIV)、阻止癌细胞生长、治疗亨廷顿舞蹈病、治愈遗传性肝脏疾病等方面开始展现出重要的前景。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有效地用于构建模式动物、研究疾病机理;也可以对蛋白编码结构域进行突变、筛选和发现药物作用的新靶标,而一个新的药物靶标的发现往往可能导致一系列新药的出现。
另一个重要动向就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T)研究的进展。CAR-T技术通过对人体T细胞进行体外修饰,嵌合进肿瘤表面抗原的受体,使得T细胞能够定向识别肿瘤细胞。经过修饰的T细胞经扩增后被重新回输到患者体内,能够长期发挥监控、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CAR-T技术在血液肿瘤治疗中有显著的临床疗效,世界上第一个接受CAR-T治疗的患者是一个名叫艾米丽·怀特黑德(Emily Whitehead)的小女孩,她5岁时被诊断出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各种治疗方法都无法遏制她体内的癌细胞,生命垂危之际,她接受了CAR-T治疗。经历了短暂的危险期后,她居然神奇地康复了,一直到现在,她依然很健康。此后,很多大制药公司纷纷进入CAR-T研发的行列,我国也积极地跟进。2017年对CAR-T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也可以说是CAR-T突破的元年,当年的8月和10月先后有两种CAR-T药物被批准上市。目前,CAR-T治疗的价格非常昂贵,大约需要50万美元。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药物价格将会逐渐地降低,将来能够成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治疗方法。当然,目前这样的治疗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进行不断的研究。
现在,生命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的特点就是汇聚。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发展动向是癌症免疫疗法。继2013年《科学》(Science)杂志将癌症免疫疗法评为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后,癌症免疫疗法成为2018年研究最热门的生物技术之一。PD-1/PD-L1药物在黑色素瘤、肺癌、尿道上皮癌等一些特定的癌种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开创该研究领域的科学家荣获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除此之外,生物大数据、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3D打印技术制药等也都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些技术在药物发现、筛选、设计、合成等领域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新药研发的进展和成果
我国的新药研发,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特别是在国家宏观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的药物研发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8年,我国实施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目的是针对恶性肿瘤等10类重大疾病来研制疗效好、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的药品,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构筑国家药物创新技术体系。重大专项的实施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
●重大品种研发成果显著
新药研发取得显著成效,逾百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有30多个是一类新药,获批上市的创新药物数量是专项实施前20多年的7倍。同时,项目对200多种临床急需的药物品种进行了技术改造,药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专项支持的部分创新药和首仿药已陆续进入不同省份的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物目录。
埃克替尼是我国研发的首个肿瘤靶向治疗药物,于2011年获批上市,在我国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物市场销售额上已超过进口药,患者治疗费用显著下降。
2014年,创新药物西达本胺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口服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药物。与国际上已上市的同类药物相比,西达本胺不仅使患者生存期得到延长,而且价格也只有同类药物的1/10。
另一个创新药物阿帕替尼于2014年12月获得CFDA的批准上市。阿帕替尼是全球第一个在晚期胃癌中被证实安全有效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也是目前晚期胃癌靶向药物中唯一的口服制剂,它可显著延长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时间。
通过重大专项的推动,我国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大大加强,解决了过去很多临床急需药品空缺的难题,为保障临床医疗和应急需求做出了贡献。
除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之外,后续还有很多药物正在临床研究或上市审批中,其中有一些是我国的原创新药,非常值得期待。
●创新体系的建设
新药研究离不开创新性技术平台体系的建设。在重大专项组织推动下,我国新药研究平台体系建设在综合性大平台、单元性平台(包括GLP安全性研究评价平台、GCP新药临床研究平台等)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国家化合物样品库等资源型平台和企业研发平台建设也卓有成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等单位承担多项重要研究和应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我国的11家GLP创新体系通过了28项国际认证,已基本与国际接轨。GCP平台积极服务药物创新,牵头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我国药物创新体系门类渐趋完整,布局和整体实力都达到了一定水平。
●中药现代化
我国在中药新药的研发、重大品种的培育、创新体系的建设、中药国际化的推动、中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绩和重要进展。
●药物研究和产业的国际化
国产药物在获得国际市场准入、国际成果转让、境外投资、国际认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一批国产药物制剂通过国际认证,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巿场;国内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国际转让逐步增速,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对于我国产业转型,增强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
●推动医药产业加速发展
目前,我国医药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位。医药产业的结构有了很大提升。主营收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这些企业快速成为行业骨干。
新阶段、新要求和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药产业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药物研究主要是仿制国外的药物,缺乏系统性的创新能力。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为模仿创新阶段,我国的药物创新技术平台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研发成功。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处在由模仿创新走向原始创新的转变期。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长,我国新药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将逐步实现新的历史转变,从“跟跑”逐步向“并跑”和某些方面“领跑”跨越。
新的药物研究技术和方法正在不断孕育新的变革和突破。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物理、化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学科与新药研究的交叉和融合不断加强,深刻地改变着药物研究的面貌,推动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从科技发展进步的历史来看,新药创制总是在第一时间吸收和应用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的最新知识、方法和技术,多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总是有力促进药物研究高新技术变革。
我国的新药研制的格局也正在发生变化。我国药物的研究体系主要由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组成。过去,企业的研发能力非常薄弱,大学、研究机构把研发的新药转让给企业,企业承担中试放大和规模产业化的任务。现在,这样的局面已开始变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步增强,一些优秀企业基本具备“me too,me better”模仿式创新的能力,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新药研制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我国企业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还非常少,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是最低的。
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开始有所改变,企业的研发投入近年来在逐步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医药研发的创新成果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创新项目与资本融合加快。2015年,和记黄埔制药、百济神州先后向美国证交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IPO)申请,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2017年9月,再鼎医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资本市场的介入对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长,我国新药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将实现新的历史转变,从“跟跑”向“并跑”和某些方面“领跑”跨越。
对于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这样的形势下,医药行业的未来应如何发展?
第一,调整和完善我国药物创新体系各组成部分在新阶段的定位和任务。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一批企业逐渐建立和增强了自身科技力量和研究经验,一批生物医药创新企业蓬勃发展,逐步具备了开展规范化的新药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能力。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和改变我国药物研究的格局,科研机构和大学对自己承担的责任和定位应该有所调整,要更加重视“同类第一(First in Class)”的新药研发,更加重视前瞻性、战略性的新方法、新技术、新策略的研究,从跟企业并排竞争到引领企业创新方向。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主动对接科技前沿的突破,开拓新药研究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原始性的创新和核心技术,是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前沿的基础研究,不仅孕育着新药发明的突破口,也不断更新药物的研发理念,创造医药产业的新形式、新业态。
第三,加强多学科、多种技术方法的交汇融合、综合集成。学科交叉、技术集成已经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药学领域,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转化显著加快。药物化学、药理学、信息科学、技术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多学科综合集成的趋势不断增强。
第四,重视天然和合成小分子的挖掘和研究。在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快速发展、中药复方综合作用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小分子药物的发展也应受到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小分子药物不仅依然占据医药市场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是在研和待批的新药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药物,小分子药物依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医药领域已经形成和实施了“三步走”的创新发展设想:首先初步建立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和雏形,为创新发展奠定基础;随后再继续努力,在国际新药研发“第二方阵”中争取逐步走到前列;最后再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进入跨越发展阶段,争取在国际先进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当前正处在实现“三步走”发展设想的关键阶段。
我国的新药研发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如改革评审制度、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新药研发的平台正在不断完善;生物医药成为风险投资的热点,各方面利好在逐渐形成。
展望2020年以后的“十四五”规划,国家将继续有力推动生物医药领域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发展:自主研发的药物能够更多满足人民健康的需要,产生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新药产品,形成大型医药企业,推动生物医药向支柱型产业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