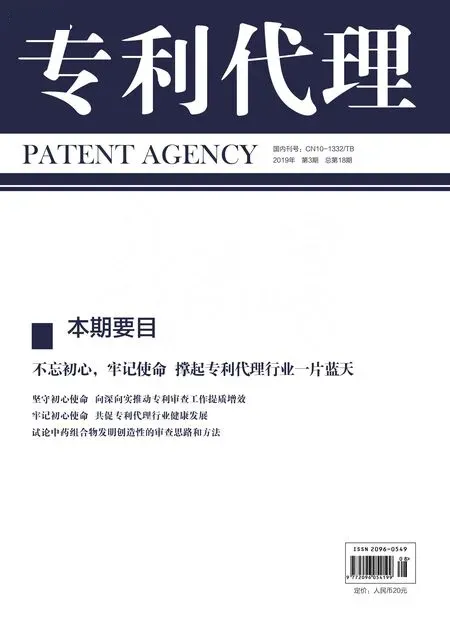专利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归属研究*
罗贵斌 孙一中
一、专利权转让的内涵与诉权的可转让性
(一)传统诉权转让与请求权相关理论互动对专利诉权的启发
2015 年《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118 条提出“非依法律规定,不得禁止或者限制民事权利客体的流通以及利用”,①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2015-04-19)[2019-05-05].https://www.chinalaw.org.cn/Column/Column_View.aspx?ColumnID=81&InfoID=14364.但最终的《民法总则》并未采用这一表达,这隐约表现出立法部门在对权利的处分自由空间上相对谨慎,尤其在现有法律对物权之外的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转让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未进一步区分具体的权利内容与转让条件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相关请求权转让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观点并不统一。请求权是权利人要求相对方作出一定行为的权利,而诉权则作是“公民要求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权利”②黄忠顺.再论诉讼实施权的基本界定[J].法学家,2018(1):68-82.,二者实际上都是因基础性权利被侵犯而分别基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产生,请求权和诉权的转让存在一致性。米伦布鲁赫认为“仅具有独立意义的债权得成为债权让与的标的物,不仅包括物权之诉也包括具有限制效力的债权。”③Vgl.Mühlenbruch.DieLehre von der Cession der Forderungsrechte,3.Aufl,Greifswald:Mauritius,1836,S.245,转引自:冯洁语.论法律行为对处分的限制——历史阐释与适用范围的教义学反思[J].法学家,2017(6):31-32.诸如抚养、人身损害赔偿等由于权利本身的不可让与性以及应收账款债权等基于当事人约定等原因无法转让的债权则难以产生法律上的债权变更效力,而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本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因此专利侵权损害请求权及其诉权能否让与的关键在于该请求权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限制或者有无合同行为对请求权的转让带来障碍。
(二)专利权的人身属性对诉权转让的影响
专利权与传统的物权相比,在纯粹的财产属性之外,由于权利保护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智力成果,与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一样,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财产性利益具有可流转性,但基于人身属性产生的利益在转让过程中则有着诸多现实障碍。原专利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实体性权利义务的转移则带来相应请求权的转移,专利权转让的内涵决定了与之一并流转之诉权的基础是财产利益请求权还是人格利益请求权。对专利权的人身属性内涵界定应是回答基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起诉权能否转让的理论基础,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应当以具体的实体权利为基础,王利明主张将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分离④王利明.论人格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J].中国法学,2018(1):1-20.,基于这一主张,专利权的转让可以分解成为人格权与财产权两个独立权利的转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系财产权,人格权请求权的基础即是专利人格权。关于专利人格权,尽管我国现有法律中并未明确这种表达,但从《专利法》第17 条⑤《专利法》第17 条规定:“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权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和《巴黎公约》的相关规定⑥《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s amended on September 28,1979) (Official translation)》Article 4ter:“The invent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mentioned as such in the patent”。来看,专利人格权或者人身权是存在的。由此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专利权与著作权一样,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是否意味着能够自由转让的仅仅是专利权的财产性利益?笔者认为,专利权的人身属性对专利权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转让并不会造成障碍,但对于专利权的人格请求权则可能带来障碍,专利权人身属性的存在是由于研发团队在研发过程中注入了大量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人身要素,但这种属性是由发明人带来的,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s amended on September 28,1979) (Official translation)》Article 4ter:“The invent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mentioned as such in the patent”。因此,专利转让过程中的发明人的署名等权利实际上并不能转移。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转让实践中实际上也已经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在2019 年前,专利申请权的转让可以连同发明人一并进行变更,但从2019 年开始,无论是专利申请权(授权未缴费下证的专利)的转让还是专利权的转让,发明人信息则不能再进行变更,因此专利权的人身属性并不影响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对应诉权的可转让性。
二、专利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归属司法实践
对专利转让前的诉权归属认定,主要存在转让双方对转让前诉权归属有明确意思表示和无意思表示两种情形。基于诉权的私权属性,无论当事人通过约定明确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由原专利权人拥有还是受让人拥有,实务中普遍认可这种约定效力;而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普遍推定原专利权人继续拥有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而受让人则不享有该诉权。
(一)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效力优先
第一种是在专利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转让前的诉权由受让人享有的,法院倾向于支持受让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如在孔玮与安达泰星公司专利侵权纠纷⑧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604 号。中,孔玮作为原告,也是涉案专利的受让人,法院以公证的合同中的约定为依据,认可了受让人针对自授权公告之日起至转让之前的侵权行为的诉权。同样,在深圳市粤美笔业有限公司、郑明娟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⑨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终923 号。一案中,法院认为原专利权人深圳市捷讯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将涉案专利转让给郑明娟,并于2014 年3 月12 日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深圳市捷讯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明确声明在登记日前或登记日后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诉权和获得赔偿的权利均归属郑明娟,因此,郑明娟依法拥有主张侵权责任的诉讼权利,郑明娟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这两个案件中法院均认为受让人可以依当事人意思通过合同约定或者原专利权人声明的方式取得对转让前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更有甚者,在武汉科兰诉美投实特公司专利侵权⑩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民终244 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武汉科兰公司(专利独占许可被许可人)与韩相姬(专利权人)在涉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第16 条中已明确约定,武汉科兰公司可以作为涉案专利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就侵权行为单独向法院起诉,同时针对涉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之前的侵权行为,武汉科兰公司也可以单独向法院起诉。另外,韩相姬出具《授权书》的时间虽然晚于涉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时间,但该授权书并未明确排除武汉科兰公司的合同权利,故武汉科兰公司主体适格,这实质上认可了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对许可前已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诉权,举重以明轻,专利转让合同中若明确约定将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的起诉权让与受让人,该约定应当是有效的。因此,该案充分表明法院对包括对转让前后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诉权能否转让方面的态度是肯定的。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余杰法官在其网文中也肯定了通过约定将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及诉权转让给受让人的合法性⑪余杰.专利转让后谁享有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EB/OL].(2016-05-30)[2019-07-10].https://mp.weixin.qq.com/s/EyOEm9i69CdTDtL0aEmSGA。但是对于无明确约定情况下,其认为由于转让前诉权已经产生,诉权不因专利权转让而推定为由受让人享有。这种主张与前述观点相较,更加周全,实务操作性更强,肯定了合同约定诉权转让的同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对专利权转让之内容并不当然包含诉权的观点。而实践中的专利转让存在大量的约定不明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专利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应当由原专利权享有还是由受让人享有,需要进一步对专利权转让之标的的内容进行解释。
(二)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推定由原专利权人享有对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
第二种情况下,对于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专利受让人是否有权对转让之前的侵权行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在实务层面存在内部冲突。一方面,如果认定有权起诉,则该主张往往也需要原专利权人的参与才能实现,因为在实践中法院需要查明被控侵权人实施专利的行为是否有法律或者合同依据,尤其是如果被控侵权人主张其在转让之前即已获得了原专利权人的授权,固然受让人可以原专利权人在转让时未充分披露专利许可等信息向其主张违约,但专利受让人的侵权损害赔偿主张实际上已然落空;即使法院查明后,系原专利权人在转让后对该被控侵权人的许可,专利受让人对被控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能否成立依然需要对专利转让合同进行审查后才能确定。另一方面,如果认定受让人有权起诉,但实际上在转让之前,专利的实体权利和起诉权均是由原专利权人所持有的,转让之后,侵权行为发生之时的专利实体权并未因为转让行为而由受让人持有,否则就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某专利权存在并列的两个权利人,甚至出现实体权与起诉权并非由同一权利人持有,这与传统的诉权理论不符。另一种解释是专利转让后,受让人获得的是对受让前该专利权的期待利益。
尽管在实践层面,专利转让当事人之间并未明确约定转让前的诉权归属情况下存在诸多困境,不同法院在实践中均倾向于支持原专利权人享有针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在张士华与博山真空设备实业公司、沧县鸿翔医用包装有限公司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⑫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民终276 号。中,二审法院认为张士华将涉案专利转让给石家庄陆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行为,只导致此后涉案专利权人发生变更,但并不能限制此前专利权人享有的权利,故张士华就涉案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于法有据。这里实际上是认为专利转让前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归属于原专利权人,从该案判决书看,法院并未对原专利权人的转让合同约定并未作出审查,对原专利权人就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推定,但即使被告有证据证明原专利权人已经将转让前的专利诉权转让给了受让人,能否得出原权利人无权就转让前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结论也是有待考究,因为专利转让实质上仅仅是发生在原权利人与受让人内部之间,尤其是关于转让前的诉权转让约定能否成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被告)抗辩的依据并无法律规定,尽管专利转让公告产生公示效力及于第三人,但并无法律依据表明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尤其关于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约定的效力也会及于第三人。而在高燕青诉星达文体厂、远泰经营部专利侵权纠纷一案⑬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终1009 号。中,法院则进一步明确了当转让合同无明确约定时,受让人无权就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该案法院以高燕青作为专利受让人在无法举证证明其有权就受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而驳回其起诉。
三、专利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归属认定现实困境
一方面,专利权转让作为一种私权处分行为,同时受到《专利法》与《合同法》的规制;另一方面专利权及相关诉权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公法属性,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的流转应当既要考虑专利权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权利负担带来的风险,又要兼顾专利诉讼管辖和时效规则等现有法的适用空间。司法实践中多不认可专利受让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的诉权,这种实务上的做法并未解决专利权和相关诉权的多重属性带来的现实困境。
(一)原权利人享有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的模式存在请求权基础缺失、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等问题
1.原专利权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拥有诉权违反诚信原则
专利受让人受让专利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专利权相关技术实施权和排他权,实现技术垄断,但若原专利权人在转让后仍然保留对转让前侵权行为的诉权,而受让人无权起诉受让前的侵权行为,在实践中容易因原权利人在专利权转让前对外作出的许可甚至是事后补充的许可等原因对受让人的专利权实现带来障碍,容易使专利受让人的权利期待落空,这与诚信原则相悖。
2.原专利权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拥有诉权缺乏请求权基础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转让实际上将相关的诉权一并转让给了受让人,但这种诉权的转让并不当然意味着受让人可以对转让之前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如果在专利权转让后,受让人发现在转让前存在专利侵权行为,针对转让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但在转让前该损害已经发生,受让人对该侵权行为产生的不利后果是否具有直接利益关系并非确定无疑;而若由原专利权在转让后继续享有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实施权,则会出现转让不充分或者非真正转让的结论,原权利人将专利权为基础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均一并转给了受让人,其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既已丧失,即使赋予其诉权,却因脱离了该实体性权利已无实际意义。
3.原专利权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拥有诉权导致专利诉讼结构混乱
如果侵权损害行为一直从受让前开始延续至受让后,事实上既对原专利权人的利益造成了现实的损害,又对受让人的权益造成了现实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原专利权人由于不再拥有对转让后的侵权行为之诉权,因此仅能够就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且无法主张被控侵权人停止继续侵权,而受让人则既可以主张停止继续侵权,又可对转让后的侵权行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但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就出现了一个侵权行为同一时间被多个权利人追责,存在重复诉讼、诉权结构混乱的现实难题。
(二)受让人享有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的模式下,存在诉讼时效和管辖规则混乱、与权利公示公信原则相悖等问题
1.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将增加公众权利负担,有违公示公信原则
专利权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法律在保护权利人对技术方案的垄断利益的同时也作出了一定限制,这些限制的目的是对社会公众利益加以保护,具体的是通过公开专利权人的技术方案增加社会技术福利,社会公众可以了解到这些技术的内容,并且从权利的登记信息进一步了解到权利的归属,进而对自己的商业行为的侵权风险以及可能向谁承担责任可以确定的评估,对非专利权人而言,这是一种可期待的信赖利益。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站在公法的角度提出,该模式下某侵权人需要面对的被诉侵权风险来源由一个变成了两个或者多个,即使专利信息的公开内容中可以获悉权利人信息,但进行专利权变更登记和公告的事项是专利权的转让这一民事行为,并不是专利权转让合同本身,⑭尹新天.中国专利法详解缩编版[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86.因此在无法获悉转让约定内容本身的情况下,公众或者某潜在侵权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会侵权、侵犯谁的专利权的可预见性很低,这有违专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
2.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对时效规则适用带来挑战
专利侵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点是以权利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侵权行为之日,而“法律上规定诉讼时效,其目的是要使已经发生的事实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⑮尹新天.中国专利法详解缩编版[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95.,如果由原专利权人享有诉权,时效期间会更早结束,而专利权的转让可能由于受让人对于转让前的侵权行为获悉的时间迟于原专利权人,可能导致原本已经超过原专利权人起诉时效的侵权行为再次落入专利受让人对该行为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这会使得时效制度价值落空。
3.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使得诉讼管辖更加复杂
受让人享有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的模式下,专利侵权诉讼管辖的复杂性来源于对“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认定。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将原告所在地直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新专利法司法解释精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56.但在具体的侵权案件中,原告所在地往往就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这种情况下,原专利权人与专利受让人所处不同地域,就会带来侵权之诉的地域管辖可能从原专利权人所在地扩张到专利受让人所在地。
四、困境突破
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归属认定需在现有的制度和理论框架内结合我国国情,以有助于专利价值和各方期待利益的实现为分配原则。基于此,在当事人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推定由专利受让人享有专利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这与国际通行做法相符,也符合中国专利事业的基本国情。
(一)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并无理论障碍
1.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与我国诉权理论相符
按照德国法,诉讼实施权与当事人适格泾渭分明,前者属于诉的合法性要件,后者为诉的正当性要件⑰黄忠顺.再论诉讼实施权的基本界定[J].法学家,2018(1):68-82,193。转引自[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李大雪译.德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86-287.,如果将转让前的诉权由原权利人享有,则会出现原专利权人不拥有实体权利却但具有诉权,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诉权二元说相矛盾。因此应当推定受让人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再审查是否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诉权转让及诉讼利益归属,至于合同的约定效力在转让双方之间发生效力外是否由于未公示产生效力而无法及于被告则在后续审查中查明。美国《专利法》第281 条规定:“专利权人应通过民事诉讼对于侵犯其专利的行为获得救济”。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专利转让的不可分原则,实际上就是认可了将转让前后的所有权利一并转让给了受让人,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权利的稳定性,保障公众的期待利益。此外,有观点认为当侵权行为在转让之前就已经结束,受让人的损失并非现实发生的,根据民事诉讼对诉的要件规定,如果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存在实际的损害后果,受让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就没有实际的意义。笔者认为受让前的侵权行为一方面对原专利权人的利益造成了现实的损害,这种损害对应着受让人对损害赔偿的期待利益,受让人有权基于该期待利益就受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另一方面可以推定原专利权人已将其针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并转让给了受让人,因此由受让人享有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理论上并无障碍。
2.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并未增加社会整体的权利负担
笔者认为,首先,即使赋予专利受让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之诉权,实际上并不会增加公众利益负担,就某侵权行为人而言,在专利转让前行为已经结束,但如未被原专利权人追责,其需要承担责任的风险依然存在,仅仅是原告由原专利权人变成专利受让人;其次,对于针对被控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的延长问题,可以通过被告举证手段予以解决,只是因为被控侵权人能否举证原权利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否就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信息进行充分交流以进行时效抗辩会使得案情相对会更加复杂,但并不会对现行时效规定适用带来障碍。
(二)受让人对专利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享有诉权有利于专利价值与各方期待利益的实现
1.由原权利人享有转让前侵权行为之诉权可能引发诚信和信任危机
在私法领域,诉权转让的有效性系基于当事人之间对于自己私权利处分的自由,专利权作为一种私权利,权利人有权将专利权相关实体利益转让给受让人,这种实体利益既包括现实的专利实施利益又包括对过去已经发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之期待利益,由此受让人能够相应的获得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之诉的权利,现实中如由于合同未明确约定而剥夺受让人的诉权,则会强化原权利人的不诚信动机,增加社会成本。明确专利受让人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之诉权,与诚实信用原则相符,也有利于解决由于专利转让带来的前后权利人分别向侵权行为人重复索赔以及由于权利信息获取障碍带来的期待利益受损等问题。
2.专利权转让是专利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受让人享有诉权有助于转让的成交
从权利人的角度看,权利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实施专利技术或者许可他人实施并获取收益,也可通过转让收取专利转让费的方式实现专利的价值,明确受让人的诉权范围,可以提高受让人的购买意愿,提高专利权转让的议价空间;就权利本身的价值而言,明确诉权的归属会提高权利的流动性,有利于专利权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赋予受让人更加完整的诉权,更加符合国情需要
1.有利于统一司法标准,化解各方利益冲突
实践中,各地法院普遍的做法是直接驳回受让人对转让前侵权行为的起诉或者要求受让人补充原权利人同意起诉的证明,这无疑会增加诉讼成本。明确专利权受让人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之诉权将有利于统一地方法院对侵权纠纷案件的受理标准,化解了专利受让人作为权利人在个案诉讼中为主张权利而不得不向原权利人寻求书面声明或者授权的矛盾,同时也有利于涉案专利的后续维护及管理,使各方权利稳定性和可期待性进一步明确,实现收益权与管理权的统一。⑱专利转让后由受让人投入人财物进行年费缴纳、无效应对等管理工作,如果由原权利人继续拥有诉权,则会出现原权利人从受让人的后续管理行为中享受利益的情况,对专利受让人不公平。
2.营造良好的专利运营氛围,助力专利运用价值本位的回归
中国当前的主要目标是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型,重转化重运用是我国当前专利政策的重要导向,也是专利制度的初衷,明确专利诉权归属,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专利运用与维权保护氛围,助力专利运用价值本位的回归,提高市场主体的创新热情,真正鼓励发明创造的效果。
——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20号判决切入
——以受让人权益保护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