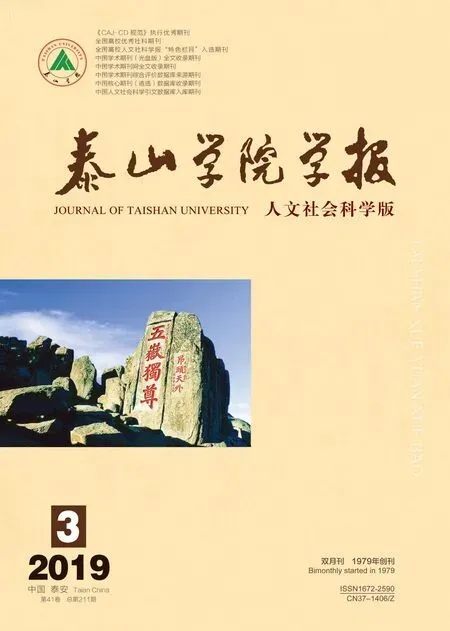“素养”内涵的知识论界说
仲建维,王燕红
(1.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邹城实验中学 山东 邹城 273500)
对“素养”的定义较难驾驭,但是对“素养”内涵的把握无疑是有关“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e)”的讨论中最基础的部分,缺此则有关核心素养的讨论恰如无根的浮萍,恐难以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有鉴于此,本文聚焦在“素养”概念上,主要从知识论的视角或知识分类的角度来着力解析其内涵。
一、欧盟理解“素养”内涵的知识分类视角
当前关于核心素养的讨论主要参考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的相关研究,本文也不例外,主要关注的是欧盟理解素养内涵的知识分类视角。这里先约略介绍一下经合组织对素养内涵的定义,这种介绍会作为一种思想背景穿插在后面的相关分析之中。
经合组织在1997年就启动了“素养的界定和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简称DeSeCo)”的研究项目。在该项目早期的一份研究文献中就指出难以给素养概念下一个完全客观的定义,因而“DeSeCo秉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概念取向,用或多或少是明确的、合情推理的和科学上可接受的这样的标准来限定素养的运用”[1],相应地,它确定了两项限定标准:素养比知识和技能(skill)更为广泛;素养是学习得来的。后一项标准不做讨论,单就前一项标准而言,它在高度限定性的意义上相应区分了素养、知识、技能的不同内涵:“素养概念是指满足高度复杂的需求的能力(ability),其意味着一套复杂的行动体系;知识这一术语指的是通过学习、调查、观察或经验而获得的事实或观念,指的是被理解的大量信息;技能一词指的是一个人运用相对容易的知识来执行相对简单的任务的能力(ability)”[2]。
后来在其正式的政策文本《素养的定义和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战略文件)》(以下简称《战略文件》)中,DeSeCo给素养下的定义是“一种素养被定义为满足需求或成功地执行一项任务的能力,它包括认知的和非认知的维度”[3]。这一定义简短但却包含了界定素养内涵的两种视角:外在视角和内在视角。素养是一种体现在外在行动(满足需求或执行任务)中的能力,这种外在视角的定义似乎融合了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立场:它把个体面对的个人和社会需求置于中心(forefront),强调素养之满足需求的功能和功能性操作过程;它认为素养不是独立于行动的,而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并得以被观察到的。这种外在功能主义的视角具有优先性,不过它“需要由一种把素养概念化为内在的心理结构的方式加以补充”[4],即是说,还要有一种内在结构分析的视角,不过这种内在视角只是一种“补充”。从内在分析视角来看,素养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认知的和非认知的维度,更具体言之包括相互协作的“认知和实践技能、知识[包括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动机、价值取向、态度、情感和其它社会及行为的元素”[5]。
在上述内在分析中,提到知识包括默会知识的知识,已经涉及到了知识分类的问题,不过《战略文件》中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欧盟则是明确地从知识分类视角切入来讨论素养的内涵,这主要体现在其2002年的一份文本《核心素养:普通义务教育中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以下简称《概念》)之中。
《概念》文本中列出了几种知识分类。第一种知识分类是know-what和know-how的区分,know-what指的是事实性的知识或信息,know-how指的是操作性的知识或技能。第二种知识分类是know-what、know-why、know-how和know-who之间的区分,know-what指的是能够容易传递的事实性的、可被符号化的知识,know-why指的是科学理解及科学对人类的影响,know-how指的是能够执行某种任务的能力,know-who是知道谁拥有必须的know-what、know-why、know-how。第三种知识分类是符号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的区分,符号化知识能够用语言或符号来表征、储存和交流,这种知识可以从其拥有者中分离出来并被其他个体或组织储存和分享,而默会知识则是和其拥有者紧密关联、不容易传递的个人知识,其能使个体选择、解释和发展符号化知识并付之以有意义的运用。基于这些知识分类,《概念》考察了知识社会的知识状况,要而言之,在知识社会中,创造、分配和接触储存性的事实知识愈来愈快捷,人们记住这些知识的需要在下降,“相反,他们需要合适的工具来选择、处理和运用所需要的知识来应对变化的职业、休闲和家庭模式,这就解释了教育中重视发展素养而不是教授事实性知识的日益增长的倾向”[6],文本又引用哲学家M.Canto-Sperber和J-P.Dupuy的看法说“这些素养超越了与学科相关的知识,是由know-how而不是know-that的形态构成的”[7]。
不过《概念》文本没有进一步从义理上来解释这些知识分类及其与素养内涵的精致关系。实际上,把知识分为know-what、know-why、know-how和know-who,这是由学者Lundvall和Johnson提出的一种知识分类框架,后来它被引入到了经合组织1996年的著名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报告简单介绍了这些不同知识的定义并进而认为:“知识是一个比信息宽泛得多的概念,信息一般来说是指知识的‘know-that’和‘know-why’部分……其它类型的知识——特别是know-how和knowwho——更多是默会知识,它们更难以符号化和测量’”[8]。这四种知识的区分是在经济学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它的思想基础是当代哲学的知识分类观。其中know-what和know-how这两个概念在源头上来自于英国分析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的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之分。经合组织把这四种知识区分又与默会知识这一概念联系起来,这自然令人想到匈牙利裔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的区分。经合组织运用这些知识分类概念以及欧盟基于这些知识分类来讨论核心素养问题,都代表着这些源出于哲学的知识分类观已经跨出了学术的范畴,成为像经合组织和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知识分类观的哲学例解
为求在义理上对上述知识分类有更深入的把握,接下来我们追溯到赖尔和波兰尼的知识分类观。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相对于英文explicit knowledge和tacit knowledge的中文翻译“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已比较固定,所以接下来本文会继续运用这一对中文翻译术语,而对knowing that和knowing的翻译则多样,例如翻译为“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么做”、“知道那个事实”和“知道怎样做”以及“所知”和“会知”等,因此这里不取中文翻译,而是使用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这一对英文术语。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些知识分类,我们借用分析杜威曾经引用过的一个例子[9]:苏格兰的一个制造商从英国以高薪聘请了一个能以调配出鲜艳的色彩闻名的染印工人,希望这个工人把他的这种技术教给其他工人。这个染印工人到来了,可是,他用以配置染料的方法(这是他染出鲜艳色彩的秘诀)是用手去掂估染料的重量,而通常的方法是用秤去称染料的重量。制造商要求这个工人把他用手掂估染料的方法改变为用秤衡量的方法,以便把他的这种特殊配料方法的一般原则确定下来。可是,这个工人发现他自己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因而不能把他自己的这种技巧教给其他人……
这个例子首先很容易让人想到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区分。苏格兰制造商基于希望能够把英国工人的高超技能或技艺传授给其他工人的教育意图而试图获得一种能够容易表达和传递的客观性规则,即明确知识,因此他要求这个工人把其用手掂估染料重量的操作方式转换为用秤来秤量的方式,因为秤量的方式更容易转化为一种用言语来讲述的操作规则,而用手掂估的方式默会性太强,无法转化为一般规则,但这位工人拥有的怎样操作的知识不但无法用言语规则来陈述,而且只能用用手掂估这种实践操作方式来表达,它甚至无法转化为用秤来衡量的实践表达方式。
上述案例分析基本已点明了默会知识的特征:默会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这种知识之表达的难度依赖于默会的强度,不过通常来说它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或者说无法用言语充分来表达的,但不是说它不能表达,实践行动即是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默会知识的存在不限于上述案例中所说的情形,如果变换一下案例,即假设这位工人的高超技能是由于他学习和运用某种操作规则的结果,则还是有一些导致他技艺如此之高的个人原因是他自己本身无法说清的,那是他自己说不清甚至意识不到的某种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实质上就是默会知识。他可以把规则和一些实践体会告诉他人,但是有些部分是他只能靠操作行动来演示的,甚至有些部分是他无法演示出来的。至于规则,则可能当他技艺熟练到极致时,他摆脱了对规则的有意识思考,更甚者他自己对这些规则已经说不清楚了,这时候,这些规则或者明确知识的部分实际上已经转化为默会知识的状态。
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之分与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之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解释的,因此上述案例也可以置换成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的区分,制造商希望获得的工作原则属于knowing that,而工人的高超技艺体现的知道如何做但不能言明的知识属于knowing how。赖尔的这种知识区分背后有一种思想意图,即瓦解源自笛卡尔的理智主义观念。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人体是一架有形的机器,而人心如同幽灵一般无形而静谧,因此可比喻为“机器中的幽灵”。心灵平时寓居在身体里,像一个发动机一样主宰着身体,但它本身可以离开身体独立存在。理智主义者继承了这种幽灵观,认为一项行动包括着双重活动,即先有内心里进行的理论思考活动,后有这种内心活动支配的身体活动。相应地,他们把knowing how还原为knowing that,认为knowing how就是知道如何做事的规则,身体行动只是这种独特的knowing that的实践呈现方式,这样knowing how本质上还是一种特殊的knowing that。
但是赖尔的knowing how概念绝不是上述唯理智者理解的knowing how。在赖尔那里,有一对与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的区分相应的概念,即理智(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大致说来,理智活动主要是理论思维活动,而智力是可以用“精明的”、“机智的”以及“愚蠢的”等心理谓词来描述的东西。与把knowing how还原为knowing that一样,理智主义者把智力还原为理智,即认为人有智力地做事就是首先在内心从事了一项理论性的思考活动。但赖尔反对这种还原,在他那里,智力本质上是一种能力,而能力是一种行为方式,即假如具备了某种条件,则一个人就会倾向于和能够按照某种方式做出行动,能力必须体现在行动中。对Knowing how的理解必须结合智力、能力概念,就此郁振华教授把knowing how翻译为体现了智力的“能力之知”[10],而理智主义者通过把know-ing how还原为knowing that,就否定了knowing how是一种能力的性质。
另外赖尔列举了两种实践情形以说明knowing how的存在以及knowing how不能还原为knowing that:首先,“有许多种类的行为都显示了智力,但它们的规则并没有明确表述出来”[11],上述案例中英国工人用手掂估染料重量的技术行为典型地属于这类行为;其次,“若仍然假定,我为了合理地行动,就必须首先细考之所以要这样行动的理由,那么我怎样去把这个理由合适地用于我的行动将要遇到的特定情况呢?因为,这个理由或箴言必定是具有某种一般性的命题。它不可能含有各种详细的说明,来适合于各种特定事态的每一个细节”[12],也就是说,在一般规则及其运用的情境之间有一个难以言明的智力运用空间,人掌握了规则却依然有可能会聪明或愚蠢地做事情。
无论knowing that还是默会知识概念,都意味着“我们频繁地以没有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知识为基础,来思考、感知、评价和行动”[13]。我们平常的知识意识局限于knowing that和明确知识,但波兰尼本人则赋予默会知识以优先性,他说“默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植根于默会知识”[14],同样,赖尔实际上也是认为人类的行动主要是由knowing how来主导的。
三、基于知识分类视角对素养内涵的扩展性解释
上述对知识分类的哲学例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素养内涵的理解,当前的研究中广泛存在着对素养与知识和能力等之间关系的讨论,接下来的讨论将聚焦于这些关系。但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知识、能力等概念的,换言之,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使用上并不一致,素养概念与这些概念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对这些概念的辨析来展开的。
(一)素养与知识的关系
素养不等于知识,这是国内讨论核心素养的学者普遍所持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但其合理性是建立在对知识的常规理解之上的。DeSeCo在说素养比知识和技能的含义更广时,它同时对知识做了限定性的理解,即把知识界定为事实、观念,或者概而言之是信息。我们平常对知识的理解就限定在这层含义上。基于这种知识概念,素养确实不同于知识,因为从性质上来说,素养是用来规定和描述人的,而知识只是培养素养的载体,而从内在构成上来说,素养不只包括知识,还包括其它诸多要素。但如果我们的知识意识发生改变,即认识到我们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知识,则素养与知识的关系就不能再这样简单地加以理解。
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是一种个体拥有的并主要是在行动中表达的知识,这就意味着,这种知识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那种作为培养素养的载体和工具的外在客观知识,它已经体现为素养,因为它本质上已经是一种能力之知。另外,欧盟在《概念》文本中概括几种知识分类时,是在“从知识到素养”这一标题下展开的。从这一标题中自然地会得出素养高于知识或素养超越知识的推论,甚至最糟糕的情况是可能会导致轻视知识还是重视知识的论争。但是,如果从知识分类的视角切入,这一标题只是意味着教育中知识意识的转向,即侧重强调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而不只是注重教授事实性知识或信息,推而言之,这一标题并非意味着要从轻视知识和超越知识的意义上谈论素养,而是要从知识性质的变化和转向上来谈论素养。由此分析可以论断,在素养概念框架下,基于知识在内涵和外延上发生的变化,知识相对于素养的地位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甚至可以说知识占据了素养的核心。
从素养与知识的关系中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素养与学科的关系问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学科核心素养”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学校中的知识毕竟主要还是以学科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所以,素养的培养需要沉降到学科层面来讨论,也因此,“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在教育改革中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视。但石鸥教授认为“核心素养不能说成是学科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容易产生歧义。核心素养指向人本身,唯有人,才可以用素质与涵养——素养——及其程度或水平来衡量。核心素养不能衡量或修饰学科。学科可以达成某些核心素养,但它不等于核心素养”[15]。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它指出了素养的目的属性与学科相对于素养培养的载体属性或工具属性的区分,两者在概念范畴类型上是不同的,因为范畴类型不同,所以可以用知识来修饰学科,但不能用核心素养来修饰学科,学科里不包含核心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核心素养”概念是不成立的。不过,欧盟实际上已经有“与学科相关的素养(subject-related competencies)”和“独立于学科的素养(subject-independent)”或“横向素养(transversal competencies)”之分[16]。欧盟确立的八项核心素养中,“使用母语交流的素养”、“使用外语交流的素养”、“数学素养和基本的科学和技术素养”以及“数字素养”等明显主要是由某门具体的学科来体现的,因此是“与学科相关的素养”。其实“学科核心素养”这个概念表达的就是“与学科相关的素养”的意思,它的意思并不是说学科里面有核心素养,而是指某种核心素养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某种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已属于同一种概念范畴,就此而言,说“核心素养不能说成是学科核心素养”,可从范畴大小而不是类型上重新理解为核心素养。除了包括学科核心素养外,还包括其它素养,但是“学科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本身是可用的。
“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除了意味着可以在学科范畴内培养素养外,还更意味着要基于素养的内涵来发展一种新的学科意识。《概念》文本中还认为:“在教育背景下,符号化或明确知识主要是由学科知识来代表的”[17]。“学科核心素养”不是意味着要完全瓦解这一种学科知识地图,学校教育确实承担着传授大量用言语和符号来表达的明确知识和knowing that的任务,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知识的学习与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的有机统一关系,即明确知识的学习的质量依赖于人拥有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的程度,同时,明确知识的掌握很大程度上指向于促进人拥有的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的提高。
(二)素养与能力的关系
素养与能力的关系是有关素养的讨论中另一个被重点关注的问题。蔡清田教授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他认为“‘素养’比‘能力’更适用于当今社会,顺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将过去传统所惯用的‘能力’升级转型为‘素养’”[18]。但问题是,蔡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能力这个概念的呢?
联系DeSeCo对素养和技能的区分来看。DeSeCo把素养界定为满足高度复杂的需求的能力(ability),把技能界定为一个人运用相对容易的知识来执行相对简单的任务的能力(ability)。对素养和技能内涵的这种高度限定性定义是否有过度限定性之嫌在此置而不论,这里关注的是,很明显,无论素养还是技能都是用“能力(ability)”来加以规定的,即是说素养的本质就是能力,而能力要在行动中加以发挥和表现,DeSeCo概括了三种核心素养:互动地使用工具;自主行动;在社会异质团体中互动。这些表述核心素养的语句鲜明地体现了表达能力的意思,每种表述的前面都隐含着一个词汇“能够”。当用能力来规定素养时,这种能力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功能性的整体,它不是素养的下位构成单位,也不存在素养和能力相比谁重要谁次要的问题,并且能力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单位与知识、态度并置比较。
而蔡先生所使用的能力概念是一个能够同知识、态度等要素并置比较的构成性单位,相应地,他的素养概念是从构成上强调了能力的局限性并主要强调态度作为一个构成要素的关键性,即他所言,素养意味着“不只重视知识,也重视能力,更强调态度,可纠正过去重知识、能力而忽略态度的教育缺失”[19]。可以把态度要素广义地扩充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当素养概念强调这些要素的时候,它主要是在教育目的观上强调了知识和能力之外的第三维度,即道德维度。我国出台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中把学生核心素养定义为“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其实就通过强调“必备品格”而凸显教育的这一维度,以体现“立德树人”的宗旨。这种理解素养和核心素养内涵的思考方式已经与经合组织和欧盟有一定的差异,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展开分析。
这里我们依据赖尔对智力行为的分析来进一步讨论素养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上面所讲的knowing how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之知的观点并联系“素养主要是由knowhow构成的”这种说法,则素养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不过,赖尔主要关注的是智力行为,智力本质上是一种能力,而能力是一种行为方式,因此,智力行为是一种体现了特定行为方式的行为,但反过来说,不是所有能力都是体现智力的。如果某个人偶然做出了某种外部行为,明显这种行为不是出自某种行为方式,因此这种行为不体现能力,更不体现智力。动物能够在强化物的刺激下做出重复的机械动作,表现体现为一种行为方式,但这种行为方式主要依赖的是动物的生理能力,并且其高度依赖强化物,而且往往不能在变换了的情境中表现出来,因此很难说它是一种智力行为。体现为一种智力性行为方式的行为当然有重复性,但它更有灵活性,即是说,它不局限于在一个单一的任务情境中机械地表现,而是能够超越单一情境,能在变换了的不同任务情境中灵活地表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依据单一行为来判断行为方式。就此而言,如果两个人做出了某种同样的行为,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认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只有考察他们在变换了的不同任务情境中的复合行为表现,我们才能判断其行为方式的异同。
赖尔对智力行为的说明可以置换成对基于素养的行为的说明,就此可以概括地说,素养本身是一种能力,但不是所有的能力都体现为素养,只有那种体现出能够应付复杂的或变换的任务情境的能力才可称之为素养。
四、结语
杜威曾经比较了学校产生之前和学校产生之后的知识和教育的不同状况。概括而言,前学校的教育知识虽然较为低级,但它“至少是付诸实践的”[21],是能够为生活结构所吸收的知识,因而是有生机的,而学校教育或正规教育是伴随着符号化的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诞生的,当然这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危险也如影随形,即教育“和通过语言符号即文字传递学问等同起来”[22],这种学校知识因为和实践及社会相隔离而往往不能被个体的经验与生活所吸收,因而变得抽象、死板和无活力。杜威的这种考察也可借由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以及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区分来加以说明。在前学校阶段,符号系统不发达,因此这时候的教育知识自然主要是knowing how或默会知识,相应地青少年的学习主要是靠实践参与中的模仿等方式进行的而不是符号化学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相应地,用来储存知识的符号越来越发达,这些都在根本上塑造了人们的知识意识,即越来越把知识理解为就是用符号储存的事实和观念,即越来越重视用各种符号表达的knowing that和明确知识。学校机构就成了这种知识的代理人,它被赋予了直接传授这些储存性知识的使命,相应地,学习就变成了符号化学习。
无论杜威对学校起源的考察还是knowing that与knowing how的区分以及明确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区分,都是和讨论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关系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的。杜威的考察揭示了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隔离的历史根源,并基于其一以贯之的反对二元论和主张有机统一的哲学精神来讨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有机统一关系。同样,基于上述知识区分来考察的素养概念,意味着以培养核心素养为指向的教育改革,其基本主题也是破除教育中存在的以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隔离为中心的各种二元现象,并倡导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机统一。我们的世界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用言语和符号来表达的明确知识和knowing that及默会知识,作为一种能力的knowing how和作为一种理解力的默会知识在学习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就只能停留在原始层次或低层次,同时,我们的knowing how和默会能力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我们对knowing that和明确知识的学习,这就是knowing that与knowing how和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
同时,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这些新的知识论概念,通过强调与行动的关联而体现了当代知识观的一种新转向,即强调知识的实践维度和过程维度,素养概念内含了对knowing how和默会知识的侧重强调,自然带有一种强调要从实践维度和过程维度关注知识教学和学习的教育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