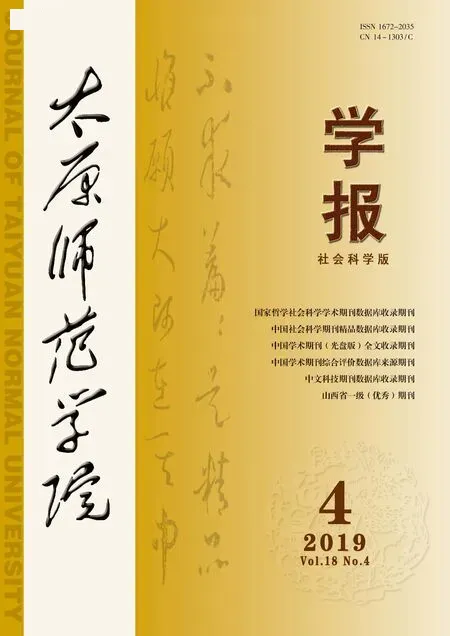从死亡独白看品特对莎士比亚的继承和创新
——“跨越地平线”与“生存还是毁灭”的比较分析
崔彦飞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毋庸置疑,死亡是文学作品书写的永恒主题之一。当代戏剧文学巨匠哈罗德·品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同样不乏死亡主题。品特的早期作品《房间》以赖利突然被殴致死而结尾,《哑巴侍者》中枪手格斯和本与死亡同舞,《温室》中作为代码的个体死亡与上层管理阶层的阴谋死亡形成张力。品特中晚期的一些作品许多地方也呈现出一种死亡的气氛,譬如《无人之境》和《归于尘土》中有对亡者的集体回忆,《送行酒》则充满着对迫害者死亡的恫吓,《家庭之声》在最后竟出奇地让死者加入了生者的对话。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死亡常常是一种形而上思索的对象,比如《哈姆雷特》中的“生存还是毁灭”,虽然现在常被认为是表达选择的习语,但是它在剧中最原始的意义则是对死亡本质的追问。戏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中,麦克白在对生者讽刺的同时对死亡发出了叹息:“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行,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1]178除此以外,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殉情、裘利斯·凯撒之死等都是莎士比亚表现死亡的范例。“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分别出自品特的戏剧《月光》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是两段死亡独白。本文通过分析这两段独白相似的叙述结构、现实意蕴及其所折射出的不同的时代主题,认为品特的创作不仅有对前辈莎士比亚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这种继承和创新是与品特在青年时代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表演分不开的。
一、“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的叙述结构
“跨越地平线”是《月光》剧中安迪的一段独白,虽然它同“生存还是毁灭”相比还不被众人所熟悉,更谈不上经典,但是,随着品特剧作研究的不断发展,这段独白的人文价值必将为读者所重视。“跨越地平线”是安迪卧病在床,回忆自己的一生,面对失去女儿,又遭儿子背离时所发出的独白,读来让人感觉意味深长,安迪面对死亡时的无奈、焦灼和疑虑跃然纸上:
贝尔:死亡是你新的地平线。
安迪:也许吧。也许吧。但重要的问题是,当我死的时候或者死去之后,我是否会跨越过这条地平线呢?也许我根本就跨越不过这条地平线。也许我就正好卡在这条地平线上。在哪一种情况下,我能够跨越过去看它呢?我能够看到那一边吗?或者这条地平线是无限延伸的?那边的天气怎么样?究竟是阴雨连绵还是晴间多云?或者是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还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你也许会说你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你也许是对的。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那里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因为如果那里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的话,那么进入让人感到疲乏无力的迷雾的那一点究竟是什么呢?一定有个孔洞。唯一的问题是,我无法找到它。要是我能找到它该多好,我就会爬进去,去见见那个正在往回走的我自己。就像你正在照镜子,却看见里面有个陌生人,于是惊恐地发出尖叫一样。(1)此处主要采用华明译文,引用时略有改动,见哈罗德·品特《归于尘土》,译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2]271-272
“生存还是毁灭”这段独白出自于《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是哈姆雷特从鬼魂嘴里得知自己父亲被叔父毒死之后,踌躇、犹疑的一段心灵写照。现实残酷,幽灵又不可知,“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这一种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他的力量;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领到沉沦的路上”。[3]312-313正是这种内心的怀疑和残酷现实的交织,激发了善于思考的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死亡独白的经典: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一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俊杰大才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3]315-316
“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这两段独白都有对死亡的隐喻。“跨越地平线”是走向死亡的委婉说法,“生存还是毁灭”中则是死亡如眠的类比。虽然这两段死亡独白从细节内容上来说并不相同,但是从叙述结构上来看却十分相似,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提出问题—死亡的隐喻—隐喻的延续—解决问题的思索。
“跨越地平线”首先提出问题:“当我死的时候或者死去之后,我是否会跨越过这条地平线呢?”当然问题本身就蕴含着死亡犹如“跨越地平线”这样一个隐喻,地平线两岸即为生死两界,颇有康德式此岸和彼岸的意义,面临着可知和不可知的存在。面对“跨越地平线”似的死亡,安迪疑窦丛生,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我是否会跨越过这条地平线呢?也许我根本就跨越不过这条地平线。也许我就正好卡在这条地平线上。”他无法确定什么,只能对“跨越地平线”这一死亡的隐喻进行推演:“在哪一种情况下,我能够跨越过去看它呢?我能够看到那一边吗?或者这条地平线是无限延伸的?那边的天气怎么样?究竟是阴雨连绵还是晴间多云?或者是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还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纷至沓来的疑问累积叠加,使人头晕目眩,但又引发人们去思索如何解决问题。由于思索本身涉及种种概念的考虑,因此安迪又以贝尔的口吻嘲笑自己,承认自己的无知,“你也许会说你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你也许是对的”,但这并不影响安迪对所提问题的思索或者力图解决的意愿:“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那里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因为如果那里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的话,那么进入让人感到疲乏无力的迷雾的那一点究竟是什么呢?一定有个孔洞。”正是在对这种让人丧失生命的“孔洞”的寻找中,死亡的问题在思索中不断延宕,“唯一的问题是,我无法找到它。要是我能找到它该多好,我就会爬进去,去见见那个正在往回走的我自己”,因此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意图似乎也只能是一种奢望。进一步来讲,死亡如果是个“孔洞”,可以让人在生与死之间往来,那么这正像“你正在照镜子,却看见里面有个陌生人”一样,让人“惊恐地发出尖叫”,因为在安迪看来,一个人从来无法认识自我,就像无法在生与死之间去感知死亡一样,于是剩下的只能是对问题的延宕、犹疑和探索,也许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
“生存还是毁灭”这段独白同样以问题为开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从整段独白的叙述结构来看,他与“跨越地平线”特别相似。问题之后紧接着便是对死亡的直接隐喻——“死了,睡去了”,接下来是对死亡如眠这一隐喻的延续——“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同时这也是个问题:“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梦的问题呢?文本独白的最后部分以排山倒海的反问表达了一个结局圆满的愿望:“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怕死后梦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存在,谁都愿意结束自己的一生,奔向死亡的怀抱。这也是对“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最坚决的回答,同“跨越地平线”解决问题时的延宕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的现实意蕴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死亡就是我们一旦醒时所见之事”[4]31,这样赫拉克利特就把死亡与现实交织在了一起。“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两段死亡独白都具有丰富的现实意蕴,这种现实意蕴可分为言语现实和心理现实两种:言语现实主要指的是在独白言语中直接呈现出的现实,也就是文本直接表达出的字面意思;心理现实则是言语现实的深层意蕴,需要联系具体语境,对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情绪进行一种客观的推演和判断,也就是字面背后所隐含的意思。
在“跨越地平线”中,安迪设想自己跨越地平线到达彼岸的言语疑问,恰是现实情景的直接呈现:“那边的天气怎么样?究竟是阴雨连绵还是晴间多云?或者是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还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进入让人感到疲乏无力的迷雾”是对现实感受的陈述。安迪设想自己能够“爬进”地平线的死亡区域:“要是我能找到它该多好,我就会爬进去,去见见那个正在往回走的我自己。就像你正在照镜子,却看见里面有个陌生人,于是惊恐地发出尖叫一样。”在这里安迪用的是经常表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虚拟语气,但这种言语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同现实的类比。“生存还是毁灭”同样如此,从问题选择开始到死亡如梦的追问再到两个连续的反诘,言语表达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现实烙印:“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的选择提问是基于现实;“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这样的假设也是基于现实;“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官吏的横暴和俊杰大才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反问更是一种言语现实,它让我们最直接地穿越、回归到文本所反映的时代的痛苦、不平、暴虐和伤痛的现实语境之中。
“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两段死亡独白,除了表现了人物直白地追问死亡的言语现实之外,更重要的是再现了独白者艰深的心理现实。《月光》是一部家庭伦理剧,夫妻相互背叛,父子形同路人,这都颠覆了传统的伦理价值取向,因此安迪在面对死亡时,虽然想见到儿子的心愿未了,但只能发出各种各样司空见惯、平淡空洞的疑问:“我能够看到那一边吗?或者这条地平线是无限延伸的?那边的天气怎么样?究竟是阴雨连绵还是晴间多云?或者是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还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事实上,正是这种味同嚼蜡的疑问展现了安迪面对无厘头的世界忧虑重重、彷徨无奈的心理现实。《哈姆雷特》是一部复仇剧,鬼魂的出现使得整个剧带有一种超自然的色彩。“生存还是毁灭”这段死亡独白出自于剧本第三幕第一场,当时哈姆雷特已经从父亲鬼魂嘴里得知父亲是被谋害的,因此他不得不面对母亲改嫁、叔父篡位的现实,而自己又不能为父报仇,在这样的思想重压之下发出了这样一段独白。这段独白通过死亡如梦、梦中又有痛苦的推演,提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疑问。显然,在直接的言语现实下表达的是一种犹豫的心理现实,只不过从一系列反诘来看,哈姆雷特强调思索、重视实证,不轻信任何理论和表象。他虽然深爱自己的父亲,但对鬼魂的话并不轻信,因此用演戏的策略来观察自己的叔叔,以求获得真相。这种伦理上的亲情使他复仇时犹豫不决,想到死亡时更是激情澎湃,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果说安迪的心理现实是从对世界荒诞的认识到内向型的犹疑,那么哈姆雷特则是直接对现实世界进行抨击。
三、“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所折射的时代主题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我们才能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5]66-67丹纳在这里强调了时代精神对创作的重要作用,品特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这两段独白就充分反映了各自所处的时代精神,具有时代性主题的意义。事实上,“跨越地平线”中对死亡本身的思考归根结底是一种质疑理性的、怀疑主义者的声音,通过多个“也许……也许……”“或者……或者……”这样的句式,主要关切的是死亡作为主体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强调的是独白者对理性的背弃,表达了一种非理性的时代主题。而“生存还是毁灭”对死亡本身的书写则是高扬理性,因为这段独白似乎能使我们听到独白者的心跳,能感知到独白者的思索和抉择,选择的句式不是像“跨越地平线”中“也许……也许……”“或者……或者……”这样的表达怀疑和推测的句子,而是像“……还是……”“……或是……”“谁愿意……?要是……”这样的表达选择或决断的句子。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段独白中,突出的是独白者对死亡思考的选择性问题,强调的是理性的主体,表达了一种理性的时代主题。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人文精神兴起,人得以摆脱神的束缚,进入人的主体时代。在《哈姆雷特》这部剧作中,哈姆雷特曾这样赞叹人类:“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303尽管这种感叹与哈姆雷特在“生存还是毁灭”独白中对人类黑暗现实的揭露以及整部剧中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强调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李赋宁先生指出:“这段独白并不说明哈姆雷特想借自杀来逃避替父报仇的责任,而是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家对生死问题的思考。”[6]132因此,哈姆雷特面对父亲的非正常死亡,除了在独白中对现实的揭露,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代表者的思考,所以“生存还是毁灭”对哈姆雷特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选择性问题,而“跨越地平线”体现出的是一个对于死亡本身思考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的问题。
《月光》创作于1993年。从20世纪开始,非理性主义成了风靡西方的思潮之一,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流传,在文学上的表征就是一种形而上主体的缺席和不确定性。在面对将要到来的死亡时,安迪对“跨越地平线”似的死亡的思考,反映的就是对死亡的一种不确定态度,这和《月光》整体语境上对理性和思想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这部剧中,理性、思想等遭到极大的怀疑,安迪的朋友拉尔夫就不无讽刺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属于思想的领域,对此我毫不怀疑。虽然,思想太多,或者自称为思想的东西太多也有麻烦,那就是它纯属扯淡”。[2]261在谈到死亡时,杰克和弗雷德兄弟俩就坦言:“死亡既是同义反复的又是相互矛盾的,它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哲学假设,直到世界末日”。[2]279其实,《月光》这部剧充满了迷雾、不定和矛盾,似乎在抵制着一切确定性。比如杰克和弗雷德具有多重、不确定的身份,安迪更是对理性发出了猛烈的抨击:“猴年马月之前,理性就已经完蛋了,从此以后消失不见了,所有的你那个著名的理性都扔进了粪坑里,在粪坑里咕嘟冒泡,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它的命运”[2]248。这是对理性直接的怀疑和放弃,难怪安迪在面对将要到来的死亡时,即“跨越地平线”时,疑虑重重。奥斯丁·奎格利就曾指出:“品特的戏剧令一代又一代人着迷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戏剧抵制那种全方位的概括”[7]7。
四、结语
哈罗德·品特的戏剧创作事实上是从戏剧表演开始的,其戏剧表演则是从表演莎士比亚戏剧开始的。他表演过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角色包括《哈姆雷特》中的霍拉旭、《威尼斯商人》中的巴萨尼奥、《奥赛罗》中的凯西奥等。华明先生认为“这段经历对于品特的戏剧创作有着很大影响”[8]42。事实上,除了本文所分析的这两段独白之外,读者还可以从多部剧本中找到这样的例子。2009年由美国蓝博特学术出版公司(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出版的由卡莉兹(Marcelle Calitz)撰写的专著《莎士比亚在品特戏剧中的影响》(Shakespeare’sInfluenceinSomeofHaroldPinter’sPlays)就对莎士比亚对品特的影响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国内关于莎士比亚对品特的影响研究很少,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布鲁姆在他的《影响的焦虑》中指出:“如果离开了四百多年来最具有影响的莎士比亚,又何从对‘影响’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研究……这一点也从某个侧面佐证了一条不乏讽刺的真理:我们基本上是由莎士比亚塑造的”[9]4。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品特的创作不仅有对前辈莎士比亚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创新。从“跨越地平线”和“生存还是毁灭” 这两段独白来看,品特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对时代主题的不同把握和表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