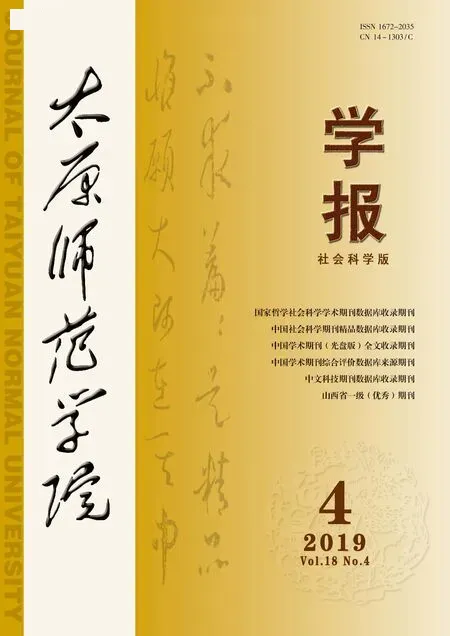文艺大众化与当代文艺创作
刘芳兵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 山东 威海 264209)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左翼时期的革命文学,文艺大众化作为一个口号被确定下来,从抗战爆发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大众化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和检验,最终确定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路线。可以说文艺的大众化历程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不仅实现了文艺自身的突破性进展,而且对中国革命建设也产生了巨大影响。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14,可见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与核心问题。坚持文艺批评的大众立场有利于当代文艺创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文艺更好地发展。文艺的“大众化”标准依然是衡量当代文艺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然而,文艺大众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当代文艺大众化存在哪些问题?怎样才能实现文艺的大众化?这些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
一、文艺大众化的标准
谈到文艺大众化,最权威的解读莫过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作了明确的解释:“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2]851
毛泽东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文艺大众化标准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的标准有两点:一点是是否与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另一点是是否能够真正深入大众的生活。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对群众充满感情和深入群众生活缺一不可。
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新文学的大众化历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延安文艺之前,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还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都没有取得成功,而是一直面临着文艺与民众疏离的困境,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读者群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是以文学作为启蒙大众的主要工具,大众在他们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中并不是主角,“仅仅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而存在”[3]11。他们其实不是去了解大众,而是一开始就以改变大众为目标,做大众的先生。而实际上他们对大众并不了解,他们要改变的是他们“想象中”的愚昧无知的大众,大众具体指的是哪一类人群,大众的需求和爱好是什么等等这些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是模糊的、不可知的。因此大众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知识分子与群众没有打成一片,这场启蒙运动仅仅是一场精英的上层文化革命运动,这种暗藏的精英意识发展到后来与大众越发疏离。
而到了左联时期,大众化的倡导者们逐步明确了大众化的对象——农工大众,也明确了革命的任务——创造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五四时期存在的问题,对文艺创作者一方提出了具体的改进要求:一是思想上,改变五四时期的精英立场,主张向群众学习;二是选材上,选用大众的、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题材,而不是五四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题材;三是形式上,利用旧形式、民间形式进行改造创新;四是语言文字上,提倡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以改变五四文学的欧化倾向。这些举措为延安文艺大众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这些进步也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真正有效付诸实践的大众化作品并不多见。左联对大众化的探讨如此深入为什么不能获得像延安时期那样庞大的群众基础?其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正是后来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周扬认为毛泽东“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4]1-2,也就是说延安文艺真正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延安文艺使得大众成为文艺的主体,大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了丰富的展现,文艺大众化终于从理论探讨走上了实践创作。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涌现出了许多深受工农兵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小说方面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烽的《吕梁英雄传》等;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歌剧有贺敬之等执笔的《白毛女》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作为一种权威理论确立下来,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建设。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艺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标杆,继承了延安文艺大众化的优秀传统,涌现出许多受大众喜爱的优秀作品:诗歌方面以贺敬之为代表的信天游体诗歌创作《回延安》和其他民歌体如郭小川的《祝酒歌》等成为大众诗歌的主流;小说领域有赵树理开创的“山药蛋派”、周立波的“方言体”小说以及“红色经典”叙事风格系列的《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等小说;歌剧方面有《洪湖赤卫队》等作品。延安文艺积累的文学大众化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大众化标准来看待当代文艺创作,有助于我们发现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新时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二、当代文艺大众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追求文艺的内在规律和作家主体性的张扬逐渐成为文艺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20世纪80年代精英意识的复兴使得文艺越发疏离大众。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艺的大众化又遭遇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5]48。可以说,当代文艺大众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带来的两种文艺倾向:一种文艺倾向,是20世纪80年代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文艺工作者过于张扬文艺的独立性与作家的个人性而产生的刻意疏离大众的创作倾向;另一种文艺倾向,是在市场经济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文艺工作者刻意迎合“消费大众”群体而一味追求市场效益的创作倾向。而这两种文艺倾向都偏离了“文艺大众化”的标准,没有坚持文艺的大众立场,或者是对文艺的大众立场产生了误读。总之,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1]10。
首先来看“纯文艺”倾向。这些文艺工作者追求作家个人的独立性和艺术作品的自律性,主张文艺的无功利性。这些所谓的“纯文学”“纯艺术”“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6]350这一类文艺理论家主张私人化的写作倾向,拒绝对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外部世界的抒写,拒绝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沉浸于私人隐蔽的内心世界,追求文学技巧和语言形式的先锋变革,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象牙塔文艺”。这类作品即使艺术价值再高,如果经不起社会的检验,终究还是没有太大的价值,更别说成为经典千古流传了。“如果说文学写作行为主要表现为一种孤独的精神历险,具有强烈的私人性的话,那么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就完全进入了大众领域,具有了强烈的大众性。”[7]因此,一个有责任、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只写一己悲欢,不能只顾个人情感的宣泄而完全不考虑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文艺评论的“大众化”标准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与此心理倾向相关的是另一些以“学院派批评家”自居的文艺工作者,这些学院派批评家们囿于大学一角,往返于高级学术交流圈内畅谈高深的文艺理论问题,尤其是对于西方文艺理论有着极大的热情,把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批评方法熟练地应用于当下中国的各种文艺实践,结果陷入了“强制阐释”的困境,甚至一些表面自圆其说的理论经过稍加推敲后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他们树起了文艺独立于广大人民群众之外的先锋旗帜,自认为是文艺界一股不与世俗合污的文艺清流,以这种“小圈子文化”为荣,以精英意识自居,殊不知脱离了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文艺将会无所依傍、不堪一击。“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1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求文艺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无可厚非,但是因此而疏离了文艺的根基——人民大众的生活,最终是肯定不利于文艺的长久发展的。从中外文学史的各种优秀作品来看,凡是流传久远的文艺作品一定都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时代重大问题的作品。
其次来看精英意识。具有这种创作倾向的作家以读者“读不懂、看不懂、猜不透”为荣,认为大众理解不了的作品恰恰证明自己艺术技巧的高超和艺术作品思想的深刻;认为文艺大众化不利于文艺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实现,不利于作家高雅的创作需求的实现和文艺精品的制作。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世俗化潮流带来的文艺商品化倾向的反击,是对一些庸俗低级趣味的大众文化的对抗。但是,这种文化精英主义意识使其丧失了读者,而且他们对当代大众的欣赏水平存在一定的误读,认为一味迁就大众会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高尚的艺术追求。他们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来看大众,认为大众是庸俗的,是没有较高的审美鉴赏力的,因而对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产生了误判。一方面,他们所理解的“大众”更多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大众”,它与现实中的人民大众群体是有很大区别的。新时代的人民大众,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不仅有能力欣赏高雅的文艺作品,甚至也积极投入到文艺创作的队伍中去,在他们中间也产生了一大批的文艺创作者。人民不仅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15。如今,“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1]32,事实上,当下中国人民群众对文艺的审美鉴赏力和欣赏水平还是很高的。从2014年“汉字英雄会”的热播到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的风靡,还有反腐力作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等的热播和当下《朗读者》的高收视率,可以看出人民是迫切需要一些文艺精品力作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由于“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1]16,因此,普及类的作品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大众与文艺工作者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关系。新时代的很多文艺工作者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为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也在不断成为文艺创作者。人民大众需要文艺,文艺工作者也离不开人民大众的生活。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跟上大众发展的脚步与需求,努力创作文艺精品以满足大众更高的审美追求。可以说,“对高品质文艺作品的需求,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最为核心的内容”[8]5。因此,新时代的文艺大众化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创作要求。
再次来审视别有用心的“文艺大众化”。市场经济影响下,“文艺大众化”成为一些文艺工作者追逐利益的借口。我们确实看到,“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甚至“如果发展正常和顺利的话,穷人将变成小众”[9]5。他们有更多的消费能力与闲暇时间来享受网络信息化社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参差不齐的文化商品。然而,与此同时,市场化的负面影响还带来了一些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当下文艺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等现象,这些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文艺作品大规模投入市场,严重损害了大众的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而这些文艺工作者正是利用“人民大众”在政治术语和社会主流之中的道德至高地位,打出“读者就是上帝”“走向大众”“为大众代言”等口号,表面上“大众”确实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优待,备受尊崇,实际上他们对于“大众”的生活和情感的描写却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歪曲的。一些创作者故意写一些粗俗不堪、暴力色情的东西来刺激大众的感官,只为赢得高收视率、高点赞率,严重污染了文艺的健康环境,贬低了大众高尚的审美追求,为大众抒写的背后是为了追求高收视率,赢得票房等实际利益。这种文艺“大众化”是“大众化”的异化,是把大众定位为市场经济下的“消费大众”群体,且自认为这些群体是低俗的、没有审美追求的,认为赢得了市场就是赢得了大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心安理得地赚取私人利益。这种“大众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真诚,“蜕变成知识分子一种自我保护策略,甚至还成了一些知识分子表白自己世俗立场和迎合市民趣味的借口”[10]127。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众化”标准,这就要从毛泽东时代提出的“文艺大众化”标准来看:文艺要为大众服务,前提应该是对大众充满感情。只有充满感情,才愿意真正投入到大众的生活中去,而不只是喊口号,停留于对“大众”的想象之中。同时,要对真实的大众群体,尤其是底层民众充满感情,关注他们生活的困境与情感的渴求。
三、当代文艺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以延安文艺大众化的标准来看,当代文艺创作要想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把握新时代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需求;二是深入人民生活,扎根群众。
(一)把握新时代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需求
要想实现当代文艺的大众化,必须要把握新时代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需求,努力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一切赞成、支持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大众的范围,也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11]9因此,当代文艺大众化的对象是更加多样的,也就需要多样的大众化路径。“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1]17“文艺大众化”的关键,就是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来创作文艺作品。“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就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把握新时代人民大众的需求,努力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是当前文艺工作者的一个中心任务。新时代的人民大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高、更强烈、更多样化。
首先,要把握大众多样化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下,由于社会经济成分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必然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同‘质’的‘大众’,如此多质多样的大众呈现形态,需要有多种多样的大众化路径和方法”[10]10。讲求文艺大众化的多样化,其实就是注重人民大众个人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新时代的“大众”不仅具有群体的意义,还具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注重描写具体的人的情感和追求,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这也是习近平文艺观念的一个特色。“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1]8习近平指出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就是为了充分满足人民大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是中国的艺术形式(比如传统戏曲、国画、民族歌舞等)还是世界的艺术形式(芭蕾舞、说唱、街舞表演等),“只要人民群众喜欢,我们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1]30。由于人民需求的多样性,优秀作品的范围就得到了大大的拓展,这就十分有利于文艺市场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也更有利于贴近现实和人民大众的情感与生活。
其次,要把握好大众需求的“高度”。文艺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文艺的通俗化,而通俗化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然而通俗不等于庸俗。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艺创作出现的一系列千篇一律、低级趣味的文艺作品正是把文艺大众化理解为庸俗化和简单化。通俗与庸俗的区别就在于,通俗是以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为基准,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文艺创作;庸俗是以粗鄙媚俗的手段“不负责任”地进行文艺创作。因此,对文艺大众化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所产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而市场化负面影响带来的一些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严重损害了大众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此时对文艺精品的呼吁正好可以清风正气,同时也能满足民众高雅的审美趣味和追求。当然,“高雅”不代表“高冷”,“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1]21。当下,仍有一些文艺工作者依然轻视和怀疑人民群众的审美鉴赏能力,甚至以作品无人能懂、以大众接受不了为荣,活在自己冷冰冰的文艺世界里孤芳自赏。殊不知,人民的需要和欣赏才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二)深入生活,扎根群众
文艺大众化的关键就在于文艺所服务和代表的对象。有学者指出:“大众不是位高权重的人,他们属于从属地位,经常称之为劳苦大众或者底层民众。”[12]263可以说,在中国占大多数的是“底层”群体(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等),然而反映和描写“底层”的“底层文学”却“处于弱势的地位”。[13]25“底层民众,这很可能是在当今社会里更加需要文学阅读,更容易接受文学的影响,然而又最少受到文学的垂顾,能够接触的文学资源最为匮乏的群体。”[14]文艺为大众服务,就应该考虑底层民众的需求。而当代文艺创作关于底层叙事存在的问题是:“粗看起来描写了普通人的经历和苦难,但实际上整篇都弥漫着作者的‘优越感’,作者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俯视众生的。”[15]8这里就存在一个写底层和为了底层的问题,这也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很多底层写作并不能被底层群众所接受?因为这些“底层”的叙事者们的潜在目标群体并不是底层、不是大众,他们表面上抒写了大众,而最终的理想目标要么是希望得到专业学者的认可,满足自己精英意识的虚荣心,要么是希望得到市场中消费者的认可,获得经济利益的满足。当然不能否认,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确实对大众充满同情,也愿意为大众抒写,但是这种情感不够热烈。“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怀常常只是一种乌托邦冲动,有时以想象的底层取代底层经验的再现”“底层经验的表述远未成功”。[16]62为什么现如今许多的底层写作没有和大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为这些“底层文学”的代言者们并没有真正为底层代言。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带着精英意识看底层或是借描写底层来抒发自己对于生活的愤懑。由于不愿意真正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因此对底层民众生活不能感同身受,也就写不出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文艺的大众化呢?只有深入生活、扎根群众。从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成果经验可以看出深入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丁玲曾经回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农兵生活后所取得的巨大的成果:“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17]64-65周立波也讲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如何创作《暴风骤雨》的过程:“从前,我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的方向确定了,创作的源泉明确了。我接受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才开始真正地注意深入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和斗争。”[18]正是因为有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这些亲身经历,才会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这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小说创作。因此,毛泽东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强调与人民大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强调深入工农兵大众生活,对我们当代文艺创作依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习近平对此思想做了继承与发展,指出文艺创作“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17。文艺创作最根本和最关键的方法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21。只有扎根到人民大众最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才能创作出反映大众关切、顺应大众意愿、获得大众共鸣的优秀作品,文艺创作领域才能充满活力。
总之,当代文艺创作要想实现文艺大众化,真正做到为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应该保持与人民群众情感的真实交融,为底层写作,为大众发声;另一方面要切实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关心他们,了解他们,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从而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