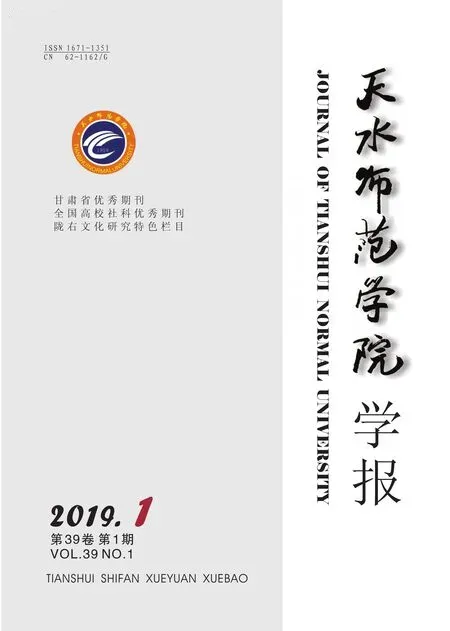理想文学语言建构的中国表达
王元忠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看文学,因为语言能够和写作者个体的感知经验一体化存在,所以从根本上讲,文学的写作也就是语言的写作。但是这样的看法,其所体现的毕竟只是对于文学语言表现的理想效果的一种期待,而在具体的文学写作实践之中,由于写作者内在心理活动的丰富、复杂和不断的变化,所以“词不达意”或者“言不尽意”的痛苦,也便遍在于中西文论的诸多表述之中,如何解决表达语言和所欲表达的内容之间的这种难以“和美”的痛苦,由是成为了从古至今中西理论思考都极为重要的内容构成。
不过,由于具体生存经验和认知思路的不同,在有关“词不达意”或“言不尽意”痛苦产生及其痛苦克服的过程中,中西文论表述显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有鉴于此,本论文扒梳中国既有的文献材料,从痛苦的发生、痛苦克服的方法寻找和古典表述的现代阐释三个方面,对于相关的中国表达进行一种个人的描述,力求从中寻找一些建构理想文学语言的智慧和启示。
一、“言不尽意”痛苦的中国发现
语言是人的文化或文明存在,所以从文化或文明的立足点看,人有关语言的故事也便和我们人生存的故事密切相关。
在有关人类早期生活状况的描述之中,西方人创造出了他们著名的“伊甸园的故事”,表述不同,但是由于可以沟通的人类历史阶段性经验的存在,我们中国人事实上也创造过我们自己的“伊甸园的故事”。
在中国描述人类早期生活的地理神话之中,各民族都存在着一些天地一体、人神共居或可以自由交流的叙事。《庄子·应帝王》所记载的“混沌七窍”和徐整《三五历纪》所记载的“盘古神话”中的原始洪荒时期的天地不分的混沌故事姑且不论,单是在有关连通人间和天上的有关“天梯”神话之中,《淮南子·地形篇》即有言讲:“昆仑之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1]90《大荒西经》有言讲;“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2]《地形篇》亦讲:“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1]90-91以此为基础,加工变形,壮族《卜伯的故事》、布依族《辟地撑天》、水族《月亮山》等也都有将巴赤山、大楠竹、月亮山意象等作为“天梯”的神话传说。正因为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所以清代大学者龚自珍在一篇文章中也煞有介事地讲:“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下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3]
在诸多神话和传说的叙事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两种基本的情节内容:第一,在人类生活的早期,人和神原本是共居或者讲最起码是可以自由来往的;第二,后来,因为神的不愿意利益均沾(如黄帝自己修行成功之后的“绝天地通”)或者神对于人的担心(如《卜伯的故事》中雷神因为害怕卜伯爬上天所以故意将天升高),所以这些故事的结尾,天和地、神和人都分开了,神居住于天上,成为人类仰望的对象;而人匍匐于地上,成为神俯瞰的对象。
人神关系的疏远及其所造成的人神之间交流的困难,给了远古的人类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痛苦。“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屈原的《天问》,考其本来,自当和人神分离之后人的不能周知的惘然密切相关。天问其实也可以说是问天,那么多的想知道但是却不能知道,《天问》中抛出来的一个一个的向天之问,因此也便形象地表征了被扔在地上的人类的不情不愿也难以真正合闭的嘴型。
“天意从来高难问”,这是在自觉到被神所抛弃之后的人类心理的真切体会,这体会,于天而言,是恼骚,是不满;于人而言,也便在认知的根底上,否决了人自己对于神(天)意揣测和描述的可能。从哲学层面反思前人有关天之奥秘的表达,老子因此也便强调了一切言说在言说本质上的虚妄特质。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可道之道即非常道,可名之名即非常名,他之说,源自于至为深刻的理性思考,但同时也附着了极为分明的内在悲哀。消极或悲观,不少人对于老子思想的看法,很重要的依据即在于他在对体现天意的“道心神理”认知上所显现出的这种否定性态度。
只是人在本质上原非一种驯顺的动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真切意识到了自己被神所抛弃的真相之后,重返天上,恢复人和神之间可能的交流的愿望及其努力因此也便相继出现。
先是神话。西汉初期的《淮南子》载古人之典,言“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5]其以原型的方式形象地表达了站在地上的人类借助于特殊的方式(吃不死之药)重新升天的可能。受其启示,或炼丹制药,或养心修道,在汉魏晋唐之际,各种羽化成仙、飞升天上的神仙故事和民间传说也便广为流行。
而后是封禅祭祀。《五经通义》说:“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6]古人以为,“王命神授”,所以为了谢天之恩,所以在遭遇改朝换代、天降祥瑞或太平盛世之际,帝王自当登临泰山,行祭祀之礼。古人之所以选择泰山为祭祀地,即在于他们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距离天最近,所以人想告天的话,神也便能够听得清楚一些。以此为习,推衍引申,后人也便有了登高望远和登高而赋的各种习俗。
如果说“羽化登仙”或“封禅祭祀”等传说和仪式还较为婉转和隐晦的话,那么巫及其后的卜辞的出现,则更为直接和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古人希冀能够和神(天)恢复交流的愿望。“巫”字从“工”从“人”,“工”的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和地,中间的"丨",表示能上通天意,下达地旨;加上“人”,就是通达天地,中合人意的意思。而且其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人,是复数的“人”,是众人,其所蕴含的意思就是祖先期望人们能够与天地上下沟通的意图。按中国古人的理解,巫就是上通下达、沟通神和人联络的中介人。巫之所以能够代表人类和神交流,最开始是因为他的“娱神”功能,“巫者舞也”,他能够通过舞蹈让神高兴,从而给人透露一些天神内心的意图和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做事的规则——也就是“泄露天机”。后来人的因素逐渐增强,借助于龟甲、兽骨或蓍草等法具的运作,巫即能揣摩或推测神(天)意,从而将人和神沟通的手段从感性的身体顺利过渡到抽象的符号,直至语言文字。
二、言不尽意解决的中国思路
因为文字的可通神意或者说“泄露天机”之功用,所以《淮南子·本经训》[1]168即传言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好像文字创造出来之后,世间的秘密藉此都可以为人所知了,侵害人命运的恶鬼们再也没有什么把戏可耍了,文字的出现断了它们的活路,所以它们始才悲从中来,彻夜啼哭。在这个有关文字的神话故事的叙事之中,清晰地显现了古人对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字的一种特别的骄傲——因为骄傲甚至不惜夸大它的功用。
但是与这个神话故事的讲述不同,从人和神鬼的想象关系之中走出来,回到人自身对于周围世界和人的黑暗的精神世界认知的描述之时,中国早期文献的记载里,存在更多的却是人对于“词不达意”的痛苦体认。前已述及,对于语言是否能够呈现至为深刻的天意(也即道)的问题,老子给予了较为消极的回答,他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并因之从根本上否决了言说的必要性,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进一步指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4]226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既然无法说清,那么还不如干脆不说。和老子不同,对于语言表意的效果,孔子曾有过较为肯定的说法,他说“辞,达而已矣”,[7]像是在说,语言可以将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周易·系辞上》有言记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8]599则似乎又说,言说者真正想表达的内容,语言是根本表达不清楚的,因为这种难以表达清楚,所以读者在《论语》等相关技术之中,也便不断能够看到孔子对于难以“知”、难以“言”的困惑和苦恼。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语言认知理念,他首先感叹“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并在此基础上,以“轮扁斫轮”的个体经验为例,说明“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9]221-222缘此,他以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不期精粗焉”,故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9]260也就是讲,在表达过程之中,人们能够说出来的,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粗糙的内容,而真正深刻的感受和体味,语言是根本就没办法讲清楚,因为无法说清,所以自然一说就错。他们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一些思考者,所以一直到魏晋时代,文论家陆机在谈及写作的困难之时,依然心有余悸地以为,自己总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10]
一方面在不断深入着有关“言不尽意”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失望也带来反抗,将言的问题置身于更为广大的思维空间,中国早期的先哲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寻求着解决问题的出路。
给人启示的首先依然是老子,他的“无为而为”,于内在的意义建构机制上,昭示了一种“不言而言”的智慧表达在言语交流之时的可能。于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通过“无中生有”和“有无相生”的“有无”关系的辩证阐释,给了人们意识到借助于表面上的不表达而完成实际上的表达的思路启示。将他的“有无”思考发挥和发展,他的思想传人庄子提出了“大小”之范畴,并于大小关系辩证转换的可能性揭示之中,直接启发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小见大”的表达智慧的发现。而在道家一路之外,立足于言说的现实效果的考虑,孔子曾有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1]其思考即在“言”之表意空间的建构一域,强调了“文(有文采)”的必要性。于此思考的基础之上,衔接道家一路的思考,回应时人对于“言不尽意”这一问题的深层疑问之时,《周易系辞上》有言描述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8]599-600这段话中,以《易经》的卦辞表意结构为例,孔子总结出了一条解决“言不尽意”问题的重要经验,那就是:圣人立象以尽意。受孔子的直接启示,经学家王弼将孔子看法进一步细化,于是在西汉时代,关于如何解决“文不尽意”的问题,人们也就便有了一种极为分明的意见: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12]
王弼的意见分明了一条思路:按正常的途经,言无法尽意,但此路不通并不是真的无路可走,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言虽不能直接尽意,但言可以造象,象生于意,意以象尽,所以借助于语言的造象功能,它也便能够间接地但同时也更智慧地传达呈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来。
王弼的“言象意”表意结构虽然不直接用于文学的阐释,但以此为方法论指导,借景抒情或者托物言志,通过种种的形象借托手段,中国文学也便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建构出了一整套解决“言不尽意”难题的中国经验。
三、中国经验的现代阐释
这种经验是语言的,但同时又是超越语言的,是在语言之外的一种意义的建构——也即也“意生言外”,于这种中国特有的解决“言不尽意”痛苦的智慧表达,刘勰谓之为“文外之重旨”的追求,以为既然“言征实难巧”,所以写作者就不应该一味地局限于言的本意,相反却应该从语言之中跳出去,“秘响旁通,伏彩潜发”,追求语言本意之外的言外之意。响应刘勰的主张,中国古代各种诗论、词话之中也便充满了有关“言外之意”追求的声音:钟嵘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主张诗歌的写作要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苏轼以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文也”,梅尧臣也以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袁中道更是认为“天下之至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国古人的思考和表述丰富而且生动,但是它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重复,如理论内涵的不具体、欠清晰,等等,所以要理解这些智慧表述的真正内涵,特别是要激活它们,让它们发挥具体的现实功用,就需要借助一些新的眼光对其进行重新的审视和阐释。
换一种新眼光去看,在解决“言不尽意”痛苦的“以象传意”或者“意生言外”的中国思路的表达之中,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如下三个面向的价值意义:
首先就是语言的表现功能开掘。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内含指称和表现两大功能。语言的日常使用或者日常的生活语言主要开掘的是语言的指称功能,其着重说明“是什么”、“有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如“花儿是红色的”、“树底下有几只小狗”和“一个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等等,但语言的文学使用却明显地弱化了语言的指称功能,相反更为注重语言的表现功能的开掘,其主要的目的因此就不在于说明言说者主体看到了什么,而是要呈现事物在主体心目之中具体的存在心态,如“弯下腰/我看见每一棵芨芨草的腰间都有细细的伤痕”,其所指因此也便自然地从外在转向内在,在将对象感觉化、想象化和情感化的过程之中,揭示主体在面对和感知对象之时内心的心理反应。
这种表现功能的开掘,若以“立言以造象,造象以传意”的“言象意”结构去解释,内中的情况事实上要更为清楚。日程的生活语言的使用,交流的目的即在于单位时间内最为简介和准确的信息传递,所以其对于语言的要求也便是“辞以达意”,言说者所要表达的意思,通过他所使用的言词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了。但是文学语言的使用,其本质的交流意图在于表现言说者自己,说明他幽微而且复杂的内在心理活动。他要表现的内容是个别的和丰富的,但约定俗成的一般生活语言其所能呈现的内容,更多是高度集约和普遍化了的公共经验,所以普通语言也便根本不可能完成写作者所意欲进行的表达,为此,古人别开语言表现之他途,通过“造象”这一手段的运用,在“言”和所要表达的“意”之间,楔进“象”这一中介因素,使文学的表达因之诉诸于读者的感知觉,让他们在具体形象的想象性复原和感知之中体味而不是直接说明作者的表现意图,藉此凸显文学表达所特有的感性而又丰富的审美效果。
其次就是文学语言的话语含蕴强调。体悟到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日常的语言总是不能完全予以呈现,所以中国古人强调从开掘语言的造象功能入手,借助于形象的建构而曲径通幽,最终完成意义的表达。“立言以造象,造象以传意”,在“言”与“意”之间“象”的介入,其所引发的结果,一是让语言的表意变得婉转和含蓄,意义并不直接依托于语言,“象”的出现阻遏了它们约会的时间,意义藏在了形象的里面、形象的后面,表意的延宕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也凭空增添了阅读的味道。话中有话或者言外有言,将意义藏起来,让语言和意义之间的距离人为地被加大,距离增加了过程但也增加了表达的质地,也只有在这种古老智慧的烛照之下,我们也才能更为清楚地理解一个国外名叫什克洛斯基的理论家,在谈及语言和艺术的关系之时,他为什么以为“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史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紧要的”。[13]是的,“象”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表达的性质,它让艺术的创造和接受从本质上成为一种对于形象的感知而非知识的了解活动,感知即目的,过程即艺术,在具体的感知过程之中,宛若孩子们所进行的捉迷藏的游戏,在种种意义的寻找之中参与的人因之而生发种种的发现的快感,寻找的难度越大,过程越艰难和漫长,最终的结果也便越有味道。
在婉转和含蓄之外,“象”的介入,使得参与者在对意义的寻觅过程之中,因为自我经验和期待无可避免的介入,因之也便在作者原意之外,在借助于语言而进行的文学形象复原或再造过程之中,别有或再造出种种虽不尽与作者同,但也并不出离或乖违文本的新的意义来。语言所形成的这种表达的别建或者再生意义效果,作为文学话语蕴含的深层变现特征,它不仅从文学接受的关键之处,保证了读者进行文学参与的热情和兴趣,而且也在文学意蕴建构的内在机制之中,决定了文学意义阐释的再造性、开放性、多元性和丰富性,“说不尽的《红楼》”或者“说不尽的阿Q”,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次就是文学语言的绿色生态主张。“言不尽意”的痛苦不独为中国所有,西方相关的文论事实上也遍布了类似的表述,但是在面对这一苦恼的时候,可以发现无论是什克洛夫斯基所倡导的“奇特化”,还是鲁里亚所强调的“内部语言”挖掘、布列东所主张的“自动化写作”,都体现出了一种对于日常语言本身的不信任,它们或是从自动化反应所造成的思维的钝化出发,或是从语言的外部转化所形成的个体经验的必然散失以及理性所造成的表达的人为束缚立论,认为日常一般的语言根本无从担负个体幽深心理经验的传达职责,所以在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之外,有必要重新寻找或者再造一种新的特殊的语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他们的探索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其认知并及实践的过程之中,自觉不自觉地,便显现出了一种主体与对象或者说表达者与表达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人为的紧张关系,缘此,变形、困难、阻碍、主体加工等强力动词也便频频出现于他们各类的表述。和他们的认知和做法不同,在理想的文学语言的寻求之中,中国古人的思考和实践更倾向于尊重对象本身,在日常语言外在形态不变的前提情况之下,弱化其指事功能而强化其表现功能,借助于其可能的“造象”功能的发挥,在外在的风平浪静之中,静水深流,于语言表现的深层,完成其所期望的表达的审美革命,从而在主体与对象、外在与内在、表达与表达物之间多重关系的和谐建构之时,具体印证同时也充分实践“天人合一”的深刻智慧。
除此而外,“言以造象”或者“不言而言”,在语言的表现功能或者话语含蕴的开掘之中,让文学的表达因为有意的隐藏或者虚位,反倒逗引读者加入个人的理解、期待和经验,进行更为多元和丰富的意义建构。“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者“说不尽的《红楼》”,中国古典表达之中的这种强调含蓄和节制的表达,不追求表意的真切和清晰,表面上看像是一种没有完成,然而更为深入地去看,这种有意识的不言或者节制,它却像是一种资源的适度开发,不尽就是为了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意在言外”或者“不言而言”,在读者无尽不断的开放阐释之中,“诗无达诂”,文学表达的效果因之更为理想。
当然,有关“言不尽意”痛苦并及相关出路寻找的中国表述,虽然内含了与中国文化整体相通的诸多智慧,但是由于其在认知形态上的模糊、跳跃以及表述形态上的感性化、碎片化特征,因此在理论的清晰和系统的纯度上以及现实指导和全球化对话参与的力度上,也便显现不少的缺陷和问题,缘此,如何系统地对这些既有的表述进行系统而清晰的理论提纯和梳理,对其施之于现代性或当下激活,使之更有力地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和更为广泛的国际交流,还应该有赖于更多专业人士更为积极的努力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