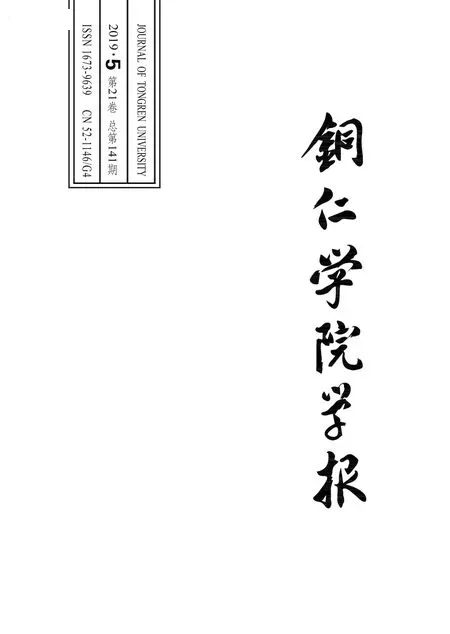“讴”义考辨
徐思澄
(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
从古代乐府到现代的歌谣运动,歌谣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为统治者和研究者所关注,并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对民众产生着深刻影响。在歌谣搜集成果逐渐丰富的现实前提下,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入,歌谣研究会逐渐由搜集工作转向分析和研究工作,以期“为民俗学立一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当代的研究更加关注科学的方法,对歌谣做出更精细、更完备的分门别类的诉求随之出现。
对文本进行分类,首先需要界定概念的定义和内涵。在歌谣之下,有歌、讴、谣、诵、谚等。关于歌、谣、谚,学界的考证和辨析较为活跃而充分,在古代就已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述;而讴则散见于各类文论和乐论著作,现当代论著也将它一笔带过,并无太多的展开分析,也没有系统的考据研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民意反映和教化作用相对较弱,在传统歌谣建制中不占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期的不重视,大量的讴散佚在民间,文本的缺失阻碍了研究的继续深入进行。此外,与歌、谣、诵、谚拥有确切的概念不同,古代文献中的讴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所指,即讴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获得了或引申出了更多的内涵:最早以劳动歌形式出现的“讴”,在经历了从地方民歌、宫廷俗乐到讴戏的发展过程之后,逐渐定型为一种唱腔的代名词。古代文献中的“讴”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所指,但它们之间并非矛盾冲突,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平行或继承关系。
厘清属类有一个更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即对文本的分析研究应当是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归属。这种分析既包括微观的对特定文本的文学或民俗学的分析论述,也应当包括宏观的结构性的分析,即建立门类的系统。具体而言,进一步界定歌谣大类中讴的概念及地位,有助于甄别出被划入歌类或谣类的讴,在新的体系结构中作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从田野调查的角度而言,确立讴的性质和特征,有助于更多文本的搜集,以供更深入的探究;抽象出一般性规律,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这种有目的的寻找和调查使得研究活动准确而高效。
一、研究现状与扩展分析:讴概念划分的诉求
从歌谣运动开始,现代歌谣研究逐渐步入学科建制阶段。作为歌谣运动和学科建制的主要讨论园地,《歌谣》周刊始终承载着重要的功能和意义。王娟的《〈歌谣〉周刊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发生与建设》一文对《歌谣》周刊的意义、影响和其中的成果作了总结,指出其对“界定学科范围、定义基本概念、梳理学科框架、探讨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而言的平台作用。文中提到了“邵纯熙、周作人、傅振伦、许竹贞、台静农、王肇鼎等学者关于歌谣的分类、特点、价值、功能和研究方法的讨论”[1],这一系列的讨论对梳理学科框架有着深刻意义。
其中歌谣的分类是歌谣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刘继辉在《中国现代歌谣研究的分类问题探讨》中比较了以周作人、顾颉刚、邵纯熙为主的“六分法”“歌者分类法”和“七情分类法”等三种歌谣分类理念。这些分类法基本上将题材、作者(自然或假作)、歌者(性别、身份、年龄)、情感等作为分类标准,而未对具体的“歌”“谣”等具体形式进行严格区分。在上述分类中,邵纯熙首次注意到了对“歌”“谣”二字的认识辩解,区分出了“民歌”“民谣”“儿歌”和“童谣”四类。[2]
笔者认为,从民俗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在厘清字义及其发展变化的同时,相关的时代或族群的文化特征将随之被梳理清楚;而从文学角度而言,这样的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确定具体歌谣文本的属性,进而分析其内涵,二者并非矛盾。歌谣可进一步细分出歌、谣、诵、讴等形式,且这样的分类思路在古代学者的论著中是有迹可循的,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按歌谣者,朝野咏歌之辞也。……及考其别,则有歌、有谣、有讴、有诵(不歌曰诵)、有诗、有辞,不特歌谣二者而已。
当代研究者对这一方面予以了更多关注。王娟的《“歌”、“谣”、“诵”小考》一文,对古代传统歌谣分类“合乐为歌,徒歌为谣”及“雅歌俗谣”进行了细致考证和分析,并将很少被研究者关注的“诵”体放入歌谣大类进行说明和分析。其中兼有对“合乐”“徒歌”含义的有力论证,本文沿用了其中“合乐”即为伴奏的结论[3]。关于“歌”“谣”之辨,舒大清有《谣本义考及与歌、风谣关系辨析》,其中收集了很多相关古代文献资料,从字源的角度论述了“谣”比“歌”多了一层“敲打缶器”的含义,对歌谣的分类研究有一定的启发[4]。钱志熙的《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则将歌谣放入诗歌史这一领域进行分析,认为乐章(入乐歌辞)可以视为从歌谣(徒歌)到徒诗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环节。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提到了关于“讴”的含义,认为讴在早期属于娱神俗乐,是较徒歌而言“一种更高级的曲调”,是从歌谣向乐章歌词与戏曲发展的一个桥梁[5]。关于“讴”,《“歌”、“谣”、“诵”小考》在对“诵”的分析中也有所提及。本文将基于此对讴在歌谣中的地位做出进一步阐释[3]。
二、“齐地之歌”:地方民歌
关于讴的含义,较早对其进行界定且广为接受的是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讴,齐歌也,从言区声”[6]卷三上,后世学者多依此说。作为一种文体或歌类,讴在古书中的关注度远小于歌、谣、诵等。在理解其内涵时可借鉴对比的材料较少,另一方面又缺少对文本实例的分析作为旁证,后世研究者往往以《说文》中的解释为本,并在此基础上对“齐歌”的含义加以阐释。
关于“齐歌”的说法主要分为“齐声而歌”和“齐地之歌”两种:汉班固《汉书》卷1上:“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颜师古注:
讴,齐歌也,谓齐声而歌,或曰齐地之歌。[7]卷1上
关于“齐歌”之所指,《艺文类聚》卷43引《说文》曰:
咏诗曰歌,独歌谓之谣,讴,齐歌也。[8]卷43乐部3
这里将独唱和齐唱作为区分谣和讴的标准。与之相对,认为讴是“齐地之歌”的学者则占多数,如明胡绍曾《诗经胡传》卷1引《梁元帝纂要》:“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9]卷1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表现,如唐徐坚《初学记》卷15《乐部上》“郑舞齐讴”下引张衡《南都赋》“齐童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崔琦《七蠲》“暂唱却转,时吟齐讴;穷乐极欢,濡首相煦”[10]卷15乐部上。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对这一争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师古注高帝纪曰:“讴,齐歌也。谓齐声而歌,或曰齐地之歌。”按假令许意齐声而歌,则当曰“众歌”,不曰“齐歌”也。李善注《吴都赋》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齐讴楚舞纷纷”。《太平御览》引《古乐志》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若《楚辞》“吴歈蔡讴”、《孟子》“河西善讴”,则不限于齐也。[6]卷 3上
可见,“讴”本是齐地音乐的代称,经历了词义扩大的过程之后,各地方的音乐均可以“讴”称之。
进一步地,虽然《说文》中“讴,齐歌也”可被理解为“齐地之歌”,但古代文献中的讴并非严格符合“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这样的定义。如《奏罢减乐人员》中有“蔡讴员”“齐讴员”,《招魂》中的“吴歈蔡讴”;《史记》卷 7正义颜师古云“吴讴越吟”[11]卷7。另一方面,除了用“讴”表示齐地以外的地方歌,人们也倾向于在“讴”之前加一“齐”字(即“齐讴”)来指代“齐地之歌”,而不是单用“讴”字表示齐地之歌。如崔琦《七蠲》:“暂唱却转,时吟齐讴。”可见相对于“齐地之歌”而言,讴在广义上来说指的是地方民歌。
三、讴的特征
讴作为地方民歌的代名词,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一系列区别于歌和谣的具体含义和特征。基于此,学者常常在对歌谣进行分类时将讴单独列出。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按歌谣者,朝野咏歌之辞也。……及考其别,则有歌、有谣、有讴、有诵(不歌曰诵)、有诗、有辞,不特歌谣二者而已。
钱志熙先生则在《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一文中将“讴”作为较徒歌而言的“一种更高级的曲调”来看,认为它是“从歌谣向乐章歌词与戏曲发展的一个桥梁”[5]。从这个角度而言,讴不属于歌或谣的任何一种,它应当同时具备相对于歌的民间性与地方性特征以及相对于谣的专业性与规范性特征。
目前最早明确的讴辞文本见于《左传》,此后关于讴的记载基本上属于侧面叙写而不载其具体文本内容。清杜文澜在《古谣谚》卷2中收录了《左传》中的4首讴:
宋城者讴。春秋左氏宣二年传,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华元骖乘答讴。又云:“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尙多,弃甲则那。’”(读皮为婆,宋役人讴也。)
役人又讴。① 又云:“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宋筑者讴。[12]卷2《春秋左氏·襄十七年传》,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晳,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
从形式上来说,4首讴基本上为四言,兼顾用韵,且与《诗经》的韵母系统相符[13],而《诗经》所载的民间歌谣大多为四言;从内容和功能上来看,它们与一般的谣一样,其讴词有实义且内涵丰富,是一种“民众表达自己态度和意愿而不必担心招致责罚的形式”[3],在《城讴》中甚至有以对讴形式出现的官民直接交流的内容。从创作主体上来看,《城讴》和《筑讴》均为筑城役人在劳动中所集体创作,一定程度上属于民间劳动歌的范畴。在古代文献记载中,这种劳动时齐唱的讴确实多见于建筑情境。《甘泉歌》正描写了秦始皇造陵时这样的场景:
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14]289-290
在《筑讴》之后,杜预注曰:
今版筑役夫,歌以应杵者,此盖其始也。其歌往往叙苦乐之意者由此尔。
可见这种讴在功能上的民间性和随意性。进一步地,筑城役人习惯于在劳动时有节奏地歌讴,除了消遣宣泄,还追求“举重劝力”的效果。如韩非《韩非子》卷11载: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15]卷11
以筑者劳作功效的高低作为评价讴者水平的标准,足见讴还有着现实功利意义。正如《吕氏春秋》所言,“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与徒歌不同,这样的讴对曲调也有一定的要求,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75中的《睢阳曲》:
《古今乐录》曰“筑城相杵”者,出自汉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唱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16]卷75
由上可见,讴作为一种建筑工人所唱的与劳动节奏密切配合且具有举重劝力功能的“杵歌”,是一种完全下里巴人的民间歌谣。以沔阳(今仙桃市)挑台基、筑堤坝时常会唱一种传统民歌“打硪歌”为代表的劳动歌,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讴在今天的变体。
除了前文所述的早期讴作为地方民歌而具有地方性,由于市民文艺的发展壮大,讴以其较强的民间性和特殊唱法逐渐在各地发展为各自的唱腔或戏曲种类并流传至今。举例而言,河南的“讴戏”(即豫剧,原名“河南梆子”,俗称“河南讴”“讴戏”“土梆戏”,传至山东发展为“莱芜讴”和“山东讴”)正是以春秋时期的“平公筑台”和“讴癸唱”为源头,吸收了“清代民间诸土腔”及“民间吹奏曲、古琴曲”的“倾吐劳动人民心声的一种地方戏曲”[17]301。再如广东的“粤讴”,经过清招子庸借“南音”唱法对其进行改良,从汉初说唱文学的一种(《张买传》:“侍游苑池,鼓攉能为越讴”),发展为清代的粤曲形式之一。
较“谣”而言,讴的专业性和歌唱性更强,具体表现为从民间到宫廷乐府存在着一批专业讴者:东汉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有“盖闻过高唐者,效王豹之讴;游雎涣者,学藻绘之彩”[18]卷92,孙该《琵琶赋》有“绵驹遗讴,岱宗梁父;淮南广陵,郢中激楚”[18]卷40,《列子·汤问篇》有“薛谭学讴于秦青”[19]卷5。王豹、绵驹、薛谭、秦青等皆善讴,都在“十二音神”之列,是较为专业的善唱之人。此外,宫廷俗乐的专业讴者则根据其唱腔或内容分为“蔡讴员”“齐讴员”等。在此之上,“讴”也有指代专业歌手的引申义,如《野田黄雀行》:“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续画品》:“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讴;泣血谬题,宁止良璞”;萧绎《七契》有“奇舞递作,名讴斯召”,都将“讴”作为专业歌唱演员的代名词。
宋陈旸《乐书》卷 197乐图论“舞雩”之下有“雩乐以舞为盛,后世或选善讴者歌诗而已。”[20]卷197清应撝谦《古乐书》卷上曰:“隋唐以前无今世曲,以诗歌入讴唱,即同于曲,其歌之之法今已失传。”[21]卷上讴不像谣那样简单易唱,有着不为大多数人掌握的更专业的发音方法,需要进行一定的学习;作为宫廷俗乐存在的讴,最初也源于民间的这种唱法。时至今日,讴作为一种唱法或唱腔留存于河南的讴戏和山东大平调讴腔中。讴戏形成于“明代的讴歌和明代以前的讴”,吸收了“清代民间诸土腔”及“民间吹奏曲、古琴曲”②;《讴曲旨要》中有“抗声特起直须高,抗与小顿皆一精”一句,与讴戏唱法中的“翻高腔”非常相似[22]。大平调讴腔则很有可能与秦青、薛谭等人的“讴”以及宫廷讴乐的民间流传有所关联。“讴腔”俗称“扬腔”,是一种戏曲中的发音方法。其发音高而细,类似于“讴”音,有呼、吸两种唱法,多用于表达激昂欢快的情绪③。
上述讴例对旋律均有要求,而在早期文献中也有讴曲合乐、合礼的情况出现,其背景多为宗教祭祀、宫廷表演,体现出极强的官方性和规范性。如宋玉《高唐赋》中,在一系列合于礼的前提活动之后,讴者在琴瑟伴奏的“雅声”下进行演唱:“紬大弦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惏凄,胁息增欷。”[18]全上古三代文又如景差《大招》[18]全上古三代文: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萧倡只。魂乎归来!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四上竞气,极声变只。魂乎归来!听歌撰只。
这里的讴与歌相和,配有专门的乐章和乐舞,有竽、瑟、钟磬等乐器,舞步与节奏相合。再如汉《奏罢减乐人员》中提到了“蔡讴员”“齐讴员”和“竽瑟钟磬员”[18]全汉文宫廷乐府采地方俗讴制曲入乐,使其在专业性基础上具备一定的规范性;民间的讴因此逐渐登堂入室,成为宫廷乐的一支,获得了专门的配曲和形制。由于其娱乐性较强,宫廷宴饮游乐等场合往往有讴的出现。讴的地位因此逐渐升高,唐徐坚在《初学记》卷15乐部上中甚至将“郑舞齐讴”归入了雅乐部[10]。但由于民间性和地方性的特征,讴始终与“雅歌”的概念有所区别,没有被“歌”类取代或包容。
此外,由于唱腔与讴的高亢清亮有所相似,有一种船歌也被称为“棹讴”。从东汉马融《广成颂》的“陵迅流,发棹歌,纵水讴淫”[18]卷18,到清黄景仁《渡青弋江》的“甫聆棹讴响,劳躅渺已忘”,棹讴始终存在于诗篇歌赋中,是文人雅士偏爱的意象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民歌民谣,文学作品中所记载的棹讴多与丝竹管弦相配,也有着一定的规范性。如班固《西都赋》:“棹女讴,鼓吹震。”[18]卷24左思《蜀都赋》:“吹洞箫,发棹讴。”鲍照《登黄鹤矶》诗:“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杜甫《渼陂行》:“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从“合乐为歌”的角度来看,棹讴唱腔独特且配乐,有着一定的制式,较一般的民间歌谣而言更为雅致,符合文士的志趣。当棹讴以这一特征超越一般的渔歌而被人注意时,其观赏性、表演性逐渐被发掘,进而发展为节日庆典或日常生活中的娱乐项目,从一般劳动歌中脱颖而出,并以较为固定的演艺形态流传至今。
四、结语
最早以劳动歌形式出现的“讴”,在经历了从地方民歌、宫廷俗乐到讴戏的发展过程之后,逐渐定型为一种唱腔的代名词。讴以其民间性和地方性区别于“歌”,以其专业性和规范性区别于“谣”,是歌谣中独立存在的一类;讴的这四个特征也是歌谣分类工作中用以鉴别讴的文本的参考依据。
注释:
① (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21,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古谣谚》中原句为“又云役人曰云云,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从其有皮,丹漆若何。’”李修生《全元文》说囊加歹为蒙古人,但明宋濂《元史》卷131,《列传》18载:“囊加歹,乃蛮人。曾祖不兰伯,仕其国,位群臣之右。……太祖平乃蛮,父麻察来归……”,说明囊加歹本乃蛮权臣之后,由于太祖灭乃蛮,才归顺蒙古,所以囊加歹为乃蛮人无疑。
② 《清代的讴歌与讴戏(下)》,《商丘市戏曲志(上卷)》,通述:卷4讴戏举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另,根据《“讴”的消失在豫剧声腔发展中的意义》一文,“讴”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行腔方式,其特点有四:1.字腔分离,真假嗓分明,本嗓唱字后,突然翻高八度行腔;2.“讴”字行腔在许多剧种是本嗓吐字,假嗓行腔,也有真假嗓结合的剧种;3.“讴”作为行腔旋律的字头之外,遵循翻高甩腔的规律,也用“喷(咦)”“啊”“呀”等字行腔,或者紧接本嗓字,按韵行腔;4.“讴”的发声方法在地方剧种中出现的术语多有不同,例如灵丘罗罗腔用“背宫音”唱法出之,怀梆则称之为“(挑)后嗓”,或者“挑帘”“挑簧”等。
③ 具体唱法是:在吸的唱法中,口成“O”型,口腔略紧,将气缓吸腹中,在吸气过程中发出“讴”音;呼的唱法是将气吸人丹田,口成“O”型,嘴角略往后拉,口腔略紧,将气缓缓呼出发出“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