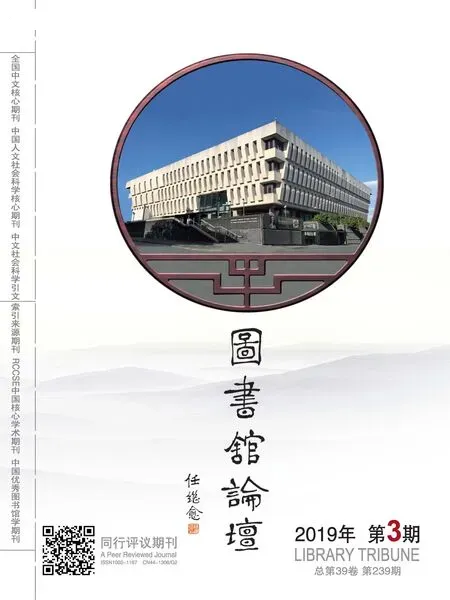我国图情档领域的谱牒研究:兼与史学、社会学范式比较
王新才,谢 鑫
0 引言
谱牒,或称家谱、族谱、宗谱,均是记录家族世系源流的文献。我国谱牒编撰可溯及商周时期,随宗族制确立与发展,虽形制、结构和功能有所变化,但大体上可以说编修不辍。谱牒之重,世人皆知。由于谱牒除了记录家族渊源之外,往往还留存有史志所未及注意或记录的细节,它们成为了珍贵的史料之一。
谱牒的价值发现以及跳出宗族本位对谱牒的科学研究始于近代。史学、社会学和图书馆界较早参与其中,均有论著发表[1]。谱牒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因传统宗族关系解体逐渐停止编修,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更遭遇无情损毁[2]。待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编纂和研究热潮才再次出现。在CNKI中用“谱牒”进行题名检索,可以发现,截至2017年,共有381篇文献,按数据库学科专题分类确定各自学科属性,历史学占71%,图情档占20%,其余主要是民俗文化等社会科学领域。文献情报机构是谱牒的收藏主体,图书情报档案学是谱牒研究当然的参与者。那么本领域的相关研究具体如何,特色何在,在信息时代学科发展背景下是怎样的走向?都是我们需思考的问题。事物的特点与意义相比较而存在,并因适当的比较而相得益彰。因此,下文回顾近40年我国图情档领域谱牒研究,将之置于“自我—他者”的对视中,即与史学、社会学比较,照见研究应有趋势。
1 文献获取及处理方法
独立研究对象是学科成立的根本条件,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完善,代表学者、著作、学术组织和刊物的具备,则分别从内外建制上标志着学科走向成熟[3]。学术期刊是知识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反映了该学科研究动态和走向。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研究对象各异,决定了三者研究取向的分殊;但另一方面,它们同属一个一级学科,联系紧密,相较于其他领域,研究范式无疑更具相似性,成果发表多有交叉。这种相似与交叉,使得从整体上考察图情档的谱牒研究,并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成为可能。同时,学科差异的存在,为学科间的交流提供了原动力,进而推动研究深入。
为此,我们在初步检索基础上,优化策略,限定条件。具体操作如下:时间截至2017年底,以“谱牒”或“家谱”或“宗谱”或“族谱”或“家乘”为题名检索关键词,在CNKI中检索图情档领域的26种CSSCI期刊(含扩展版),获得125条记录,删除通讯报道,得到116篇论文。对于史学与社会学,我们采取同样方法,在CNKI和万方数据库中,对CSSCI(含扩展版)所收35种史学、16种社会学期刊进行检索,去除非研究性及《禅门<曹洞宗谱>》等干扰性文章,分别得159篇和8篇论文。检索结果中,图情档的研究始于1979年,史学始于1981年,社会学最早见于1993年。分别下载论文的题录信息,经关键词控制、清洗后导入CiteSpace进行聚类分析。知识图谱显示了图情档领域的研究相对集中,关键词在“谱牒”“图书馆”“目录”“档案”“关联数据”等节点有明显聚集;史学、社会学研究主题既多且杂,“谱牒”“明清”“徽州”“宗族”“人口”等词频较高。CiteSpace这一分析工具的使用,可帮助我们把握宏观态势,但毕竟属于远距离观察。故而笔者下载检索所得全部文献,希望得到一种基于文本研读的内容梳理和学科反思,至于论文外部特征的分析则非本文重点了。
2 我国图情档领域谱牒研究回顾
谱牒作为文献资料被保藏,从而进入图情档视野,因此可以说本领域谱牒研究依托业务展开。文献梳理反映出其总的脉络是由研究谱牒本身转向谱牒馆藏建设开发,在后者以技术革新为界分为传统与现代,整个进程穿插着资源揭示和以谱牒为切入点的拓展研究。
2.1 关于谱牒的研究
谱牒研究以价值重申为发端。之所以用“重申”,是源于家谱曾被视为“四旧”遭到弃置、毁坏,始于1970年代末的价值探讨再次强调了该世纪之初的研究论断。从文献资料角度看,几乎任何事物的现时用途都有别于产生它的目的,谱牒亦复如此[4]。参照双重价值理论,成为档案的记录①于形成者有原始价值,于利用者有从属价值[5]。谱牒尊祖敬宗、寻根问源,对宗族而言此乃第一位;但利用者更重视其史料价值,与特定领域结合,便产生具体应用[6-7],作为精神纽带还可助力经济建设[8]、统战工作和民族团结[9]。王云庆将它们均归入文化价值,另点明谱牒的社会意义——宏观上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依附、反射关系,微观上对社会个体、群体所产生的认同感、约束力[10]。换言之,家谱不仅具备文本信息价值,还有作为行为方式的工具价值,体现出价值认识的系统化和深入化。沿此思路,谢琳惠论证了谱牒及家族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11]。
谱牒价值研究势必涉及属性问题。对此,图书馆界视谱牒为史料文献的一种,档案界从修谱目的及家谱内容入手论证了谱牒应属档案范畴[12]。然而,谱牒不断演化,决定它不可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档案。基于族权与政权的重合以及谱牒在人事管理活动中的作用,邓绍兴认为谱牒是最早的人事档案,随国家官吏任选制度改革,二者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和唐代的两次分离[13]。焦艳婷以现代档案的凭证和参考价值为判定依据,认定非文字形态时期的家谱仅留有信息内涵,甚至可说全无档案属性[14]。从历史上看,除皇族与孔府家谱外,宋以后谱牒已从族人身份证明逐渐变为家族组织存在的表征。祝虻认为是基层社会变迁和谱学发展,使谱牒完成了从族人档案到家族档案的属性转换[15]。由此可见,谱牒虽然具有图书形制,性质却需具体看待,应充分考虑其家谱发展史及其现实收藏情况,相应的资源建设需要多种文献机构协作及推动。
谱牒与宗族并生,宗族变迁推动前者演进并打上了时空烙印。时间指向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谱牒起自商周,辨别士庶、择定婚姻、征发徭役等主观需要促成它在魏晋南北朝的繁荣[16],客观环境是此时用于选官的九品中正制[17],以及家族迁徙、华夷杂处的现实情况。唐朝谱牒延续上一时期的部分特点,但姓氏排序已转为以现世门第为依据,迎合政治需要。杨小红指出官修谱牒在唐的由盛而衰蕴含着质的变异,渐渐为强调社会意义、重视家族历史的私修谱牒取代[18]。明清时期谱牒大盛,长江中下游流域及以南地区,因地理环境独特、人文昌盛、宗族制完备及经济发达,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家谱[19]。它们从私家手中流出,经收购、征集最终进入公共文献机构,令谱牒有了双重地域属性。所以,谱牒特征研究有集中于家谱归属地者,如湖南[20]与福建[21]等地;有注意收藏地者,如中国大陆以外公藏机构[22]、宁夏图书馆[23]等,为古籍调查、谱牒开发奠定了基础。
2.2 谱牒馆藏建设与开发研究
信息保存、组织、利用是现代图书情报档案学的核心,谱牒馆藏建设与开发因而称得上最具本领域特色。因图书馆收藏古谱最多的缘故,图书馆学于此用功最勤。图书馆学自产生后历经文献处理、信息技术和知识处理三个范式,与之相应,谱牒馆藏研究以技术应用为界,分为文献入藏、书目控制阶段和面向利用的数字资源组织与开发阶段。
收集乃馆藏建设第一要务。张希周[24]、许华安[25]从思想认识、具体方法等层面讨论了谱牒征集整理;黄霄羽提出馆藏建设“以人为本”和提供服务“以民为重”的原则[26]。入藏之后,编目及咨询服务得到了关注[27]。根据谱牒与传记记载对象、范围的不同,桑良知认为谱牒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应单独立类、细分子类,而非从属于传记、笼统立类[28]。依照《古籍著录规则》著录时,需结合谱牒特征制定细则,明确题名、谱籍、著者等条目[29]。从20世纪90年代起,档案馆、图书馆等继承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相继编纂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国家谱总目》等大型书目。围绕它们,学界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如体例不纯、凡例不清[30],归属地错误、收藏单位或刊刻地作为谱籍著录[31]。
21世纪以来,数字资源建设愈发重要,于谱牒亦有此趋势,体现在家谱编辑手段自动化,载体形态数字化,开发利用网络化[32]。谱牒资源清查及各类家谱工具书的编撰出版为数据库建设提供了支撑。谱牒数据库建设经过了目录数据库到全文数据库的建设历程,张奇提出在全文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适时建立全国家谱联合目录数据库,最终建成网上家谱人名信息数据库,实现对谱牒核心内容世系图的全面检索[33]。家谱数据库的建设关键是主体数据内容确定和多条件检索系统设计[34];陈晔通过“浙江家谱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的建设实践,基本解决了家谱数据描述格式、繁简字转换、数据排序、从数据库中自动生成并输出全文以及提供多种检索方式等问题,为数据库开发提供了示范[35]。
数字化时代,文献级别的信息系统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图书馆组织对象已从文献转向信息和知识,组织方式也从信息组织到知识组织的发展过程之中。语义万维网技术尤其是关联数据技术有助于加强谱牒规范控制,对姓氏、年代、人名、地名等字段数据采用概念匹配,增强必要的准确性,实现聚类功能和关联关系发现[36];建立知识本体可解决家谱多粒度知识和家谱管理模型中静态知识的描述与动态知识的演化问题[37]。上海图书馆作为全世界谱牒收藏量最大的机构,在此方面作了尝试:以家谱数据为起点,构建了基于书目框架本体设计的历史文献数据服务平台,相关技术的应用使它可提供针对普通用户的寻根搜索服务和针对科研人员的数据挖掘服务,支持书目控制的可持续发展[38]。这些研究与实践不仅对谱牒资源开发,而且对所有文献机构的知识服务都有借鉴意义。
2.3 谱牒拓展研究
谱牒潜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具体运用才能转化为现实效用。当深入谱牒文本内容并将视野进一步扩大,拓展研究已指向了与之相关的行为、业务,以及谱牒背后的历史文化,见仁见智,各擅胜场。
谱牒作为文献实物,它是文献事业的反映;作为馆藏,它与机构业务相关。丁红通过调查,发现木活字为浙江谱牒的主要版本形式,认为浙江家谱在中国木活字印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当代木活字印刷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家谱纂修过程中市场机制的激活作用[39]。同是针对《中国家谱总目》,陈旭红从其收录探讨了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问题,由公众需求、馆藏特色、时局发展和地方实际出发,以点带面,建立收集、整理、利用的良性循环[40];李勇慧则从合作编目着眼,分析了图书馆共建共享的运作机制[41]。林红状以南开大学图书馆家谱研究文献数据库为例,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古籍特色数据库建设思考,如发挥大学图书馆教育职能,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等[42]。
跳出图书文献事业,在其他史实考证上,石光伟运用《石氏家谱》考订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始建于1644年,负责人为石氏先祖吉巴库[43];同样使用谱牒材料,张晓光根据《付察哈拉家谱》及《吉林通志》等记载,确定该总管衙门设置于1657年[44]。这从侧面反映出谱牒作为史料在研究中的局限,使用者需谨慎对待,多方求证。李淑清考证了清代福建厦门水师提督陈汶环的《陈氏宗谱》及后裔情况,梳理出陈氏家族族源、发展和迁徙历史,表彰了陈汶环在保卫黑龙江领土等方面所作贡献[45]。郑幸利用上海图书馆所藏《慈溪竹江袁氏宗谱》确证了袁枚原籍浙江慈溪的说法,同时增补了他的若干生平事迹[46]。
3 与史学、社会学范式下谱牒研究的比较
史学是一门揭示社会历史进程的科学,由此不难推知图书情报档案学与它的学科差异。图情档侧重资源管理,史学致力于使用资源获得更大发现。作为典型的文献驱动或材料支撑型研究,开展历史研究第一步就是从文献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具体到谱牒,便是随文入观,以臻妙境,即以资料发现为先导,继之以深入研究。这中间,由于传统文献学的交集,史学的谱牒研究与图情档有一定重合和交互,但更多是由学科范式导致的不同。
首先,二者重合体现为《文献》《历史档案》等期刊上存在大量谱牒“发现”“考述”类文章。重合之外,图书文献机构所编书目得到史学界肯定,学科互动与交叉发文不容忽视。历史学者李晓方关于明清县志族谱化的研究[47],以及张爱华所提出的清代县志与族谱“在编纂过程中出现了官民互动密切、双向流动频繁的重要动向”[48],显然是图书馆员王燕飞所持“家谱与方志关系密切”[49]论点的深化。发文方面,图情档不少文章发表于史学刊物,如杨冬荃介绍了历代皇族谱牒的源流演变、修纂制度和流传情况[50];董润丽、朱永慧对吉林大学所藏21种稀见抄稿本家谱作了叙录[51];陈建华按谱籍统计各省市族谱存量,认为是经济条件、谱牒文化及修谱机制的差异导致了数量的悬殊[52]。历史学者王开队借鉴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路径,探究了存世徽州族谱中人物和地理信息数据化的可行性、基本原则及难点[53],成果发表于图书馆学期刊。分属图书馆和历史系的王志双、王菲菲由《虎邱林氏族谱》切入,揭示家族历史溯源过程中的粉饰和虚构现象,同时解释了何以元代谱牒研究缺失——与该时期儒家传统断裂及相关记述鲜见有关[54]。
其次,在家谱史及相关宗族史方面,史学研究者发挥他们的特长,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氏族由来、谱牒产生与发展、谱牒与方志关系、谱学与谱例变化、谱牒作用价值等问题上[55-56],足以与图情档领域研究相互启发。翟屯建比较明中叶近世家族制度形成以后的徽州公修族谱与私撰家谱,指出作为主要形式的公修族谱规模与篇幅更大,多刻板流传,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反映的是文献历史,而私撰家谱则规模较小,多抄本,更接近于历史实态[57]。钱杭讨论了山西沁县族谱中“门”的概念,立“门”既与移民宗族在沁县的发展阶段有关,又反映了族人以整合兄弟关系来增强宗族内向性和凝聚力的要求,“门”及“门”型系谱构成中国“房”型系谱之外的另一种世系学实践类型[58]。以他们为代表的研究,历史兴味更浓,自然是由史学训练和人类社会学影响所致。对谱牒、祠堂等宗族设施及活动的考察,丰富了对宗族及其制度的认知,对文献整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史学研究者对材料的敏感令其目光并未局限在谱牒及宗族本身上,例如,林金枝从福建侨乡族谱探讨了南洋华侨出国原因、历史、人数及侨居地区分布趋势等问题[59];赵发国据家谱资料绘制了各家族世系外迁人口表、外迁分布表、外迁人口婚姻表,以此分析清代登莱二府的人口迁移[60];基于对民国徽州谱牒所载族规家训的考察和分析,徐国利描画了民国时期基层社会职业观变迁情况[61]。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也有涉及我国藏书史者,如卞孝萱以《丁氏家谱》所记慈善活动为资料窥测其财力,揭櫫丁氏溯江沿黄、营业燕齐,方建成八千卷楼的历史[62]。谱牒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的重要史料,其价值在此得到充分体现。它们揭示了文本之下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文化意识,主题不一而足。图情档领域的拓展研究虽有类似者,但毕竟是少数,且与研究者的教育背景相关。
当今历史学在叙事传统之外,还有社会科学化和科学化两个趋势,前者分析方法强调理论视野与实证结合,后者主张采用一切科学分析手段和工具解读海量史料[63]。前文所述许多研究业已摆脱传统叙事手法,采用了量表统计或计算机处理技术,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和技术工具倾向。在这点上,社会学领域表现更为强烈。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及人类群体的学问,因此与其说它以谱牒为研究对象,毋宁单纯说是以之为材料。世系作为谱牒基本内容,就古代而言,它往往比官方的丁户数据更为翔实可靠,可用于了解人口消长、迁徙。事实确实如此,社会学的谱牒研究基本集中于人口学领域,如陈干华通过对谱牒所录生育、性别、婚姻、寿命及迁居等数据的统计,总结了客家人口历史发展规律[64];陈熙以家谱人口数据构建虚拟的家族支脉,得出结论:仅有13.61%的人在经历清朝两百余年生存竞争后,能够拥有后代[65]。人口研究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对谱牒凡例、族规等文字叙述的解析,考察中国妇女地位变迁[66]。总之,社会学研究已远远逸出了图情档的研究范畴,学科及研究的差异性不言而明。
4 图情档领域谱牒研究前瞻
图情档与史学、社会学谱牒研究范式的比较,属于学科交流,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给该领域工作和研究以他者及用户的视角。图书情报档案学整理文献、保存信息、传播知识,在谱牒研究中的角色,恰是其在现代学术体系乃至社会发展中定位的缩影,因为研究内容与文献情报事业相关,图情档往往“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并非说我们的研究层次低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更不是说研究徒劳无功,而是学科各有侧重、分化发展使然。此种情形下,图情档学科何以自处,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这成为本领域谱牒研究前瞻的出发点。
4.1 明确本学科研究特色
谱牒不为某一学科专有,虽然出发点一致、取径不同,也能达至不一样的境地。以历史学和社会学为例,二者的谱牒研究同会涉及社会问题,但是史学面向过去,作纵向说明,社会学面向未来,是横向阐释。专业产生价值,唯有专业研究才能避免雷同,彰显存在意义。因而,图情档欲在谱牒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不明确该领域研究特色——增加馆藏的基础上,以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眼光与手段整理、修缮和保护古谱,更为关键的是面向科研和利用的数字资源建设研究。这既是过去40年图情档谱牒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最具有优势的部分。
谱牒是一种具有图书形式和档案属性的知识载体,即文献,由此出发,图情档领域的研究都有落脚点,涵盖古籍整理、档案建设和知识组织。虽然谱牒资源建设的研究和实践早在本世纪初已然开始,但其中的一些设计方案、计划建议仍停留在设想阶段,目前尚无全国性家谱学术平台与综合门户网站,而部分已建成的数据库无法稳定使用②,检索尚且不易,遑论其他。同时,因家族的存在及家族文化的弘扬,新修谱牒持续增长,相比以往,它们外形更多样,内容更丰富,表达手段更先进[67],其编撰可能从传统的、集体的、乡村社会的配套仪式变成个人的、存在于城市和网络空间的孤立的仪式[68],对于这部分新生资源的保存是资源研究的应有之义。图书馆扮演着社会文化均衡器角色[69],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建构行为和结果[70]。鉴于谱牒的价值和属性,其馆藏建设、文本解读及开发利用,对文献及文献机构功能作用的发挥有着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研究从馆藏小文本向社会大文本的转变,参与到社会文化互动中。
4.2 图情档领域协调合作
回归谱牒资源本身,目前存世的古本谱牒约50000种,公藏于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多种文献机构,尤以图书馆为最多。1997年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由国家档案局联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现名为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联合编撰,上海图书馆因未及整理而没能参与。2005年,由浙江省、市、县三级图书馆、档案馆、方志办等联合编纂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问世,鄞州区档案馆所藏13种家谱却未能收入[71]。窥一斑而知全豹,由于机构性质、所属系统隔阂,我国各机构间文献共享水平还待提高。这对图情档领域谱牒研究造成了物质层面的阻碍,也不利于其他学者利用。较为明显的是,尽管档案学界视谱牒为一类档案,但由于手中所占资源较少,因而研究多止步于价值、性质及演变史等理论探讨。
图情档领域内的协调合作,在实践方面是推动各机构数字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在研究层面,则是相关平台技术、制度的设计;至于谱牒,还需在资源组织建设中发挥各自所长。图书馆学侧重信息资源的组织,档案学擅长文献保护与信息保存。回顾我国图情档谱牒的研究历程,不难发现情报学期刊文章的缺位,但它们三者本是相互交融,在信息开发、知识服务中很难说没有情报学的“魅影”。史学和社会学相通之处,在于它们均强调客观材料的获取,甚至主张竭泽而渔地发掘和占有资料,属于用户层面。从其研究模式及传统谱牒特征的角度考虑,需要加强实体谱牒修复与辨伪、多版本对校和残本补配等技能;而数字资源的组织,则需解决图像转换、提高繁简字转换和手写印刷体辨识准确率、考虑到量化研究、文字与数字转换等技术。在字符全文数字化的前提下,要充分兼顾时空特征,支持聚类分析、数据挖掘和可视化等功能,带动方志等其他类型古籍资源的整理与开发,多角度为用户呈现所需资源,为知识探索与生产提供更多可能性。
4.3 借鉴与跨学科合作
梁启超有曰:“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72]然而,谱牒数目巨大,所涉甚广,分科是必然,合作也是必需。谱牒中有文字、有图表,有大量人、地、时、事、物信息,对于习惯了在有限资源集合中精耕细作的人文社科学者而言,单纯依靠人工的爬梳剔抉,难免望洋兴叹;对于掌控谱牒资源的图情档工作者来说,倘或缺乏大胆假设和历史的比较眼光,那么也无从完全发掘这些陈旧资料的潜在价值。所以图情档的谱牒研究不应当是封闭、保守、孤立的,历史学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应积极吸收;涉及到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保存时,书斋研究之外,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均可为我所用;同时,将谱牒视为编者意识结构及社会性、文化性规范的记录加以解释,这一研究思路也值得借鉴。
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是西学东渐、旧学新知共同作用的结果。近3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三次演变,分别以文献、信息资源和知识为逻辑起点[73]。图情档领域的发展转型,既跳出了传统文献学的园囿,又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渐行渐近。在人文社科领域,技术体系对学术资源组织、研究手段变革,甚或是研究范型转换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从索引、通检工具书编制开始,到藉由网络及数据库博引史料的“e-考据”,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计量史学”,再到如今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虽然这几者研究进路不一,但其本质相似,均强调批判性思维与技术工具的结合。这一切都为图情档与史学、社会学等在谱牒研究乃至更多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机遇。
事实上,上海图书馆已就谱牒数字人文开始了探索。夏翠娟、张磊利用关联数据的知识组织功能,制作“上川明经胡氏”的家族迁徙图[74],其出发点是图情,研究结果无疑是沟通史学和社会学的,实现了传统人文研究难以轻易完成的对语料文本在更大趋势上的考察。数字人文是多学科研究者在问题意识下的集聚,最终导向人文主义的学术产出。其技术体系包括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VR/AR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75]。图书情报档案学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决定它应该参与进来。同时,学科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在这一研究模式中,该领域最重要的角色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资源建设,正如谱牒研究中一样。人文研究还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领域,蕴藏丰富的谱牒固然是一个小的方向,但不失为图情档与史学、社会学发生更多关联而创造良好的开端,有利于在实践中建设开放的学术文化,探索跨学科运行机制。
5 结语
图情档领域的谱牒研究历程,可以说是学科发展的映射,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通过学科间的对视与交流,图书情报档案学能够于谱牒领域明确定位,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合作中扬长避短。本文通过梳理期刊文章角度来回顾谱牒研究历程,提高可操作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如专业期刊之外,尚有大量的综合类期刊和学术专著遗漏;研究者的教育背景未能深入考察,对于学科交叉机制研究不足。
注 释
①黄坤坊等人在翻译该书中文版时(档案出版社1983年出版),将原书中“Records”一词译作“文件”,笔者倾向于将其译为“记录”。
②笔者于2018年4、5月间多次访问谱牒相关数据库及网站,其中“中华寻根网”、国家图书馆“中国谱牒库”等均不可用。
——写在《图书与情报》“图情档青年学者专辑”出版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