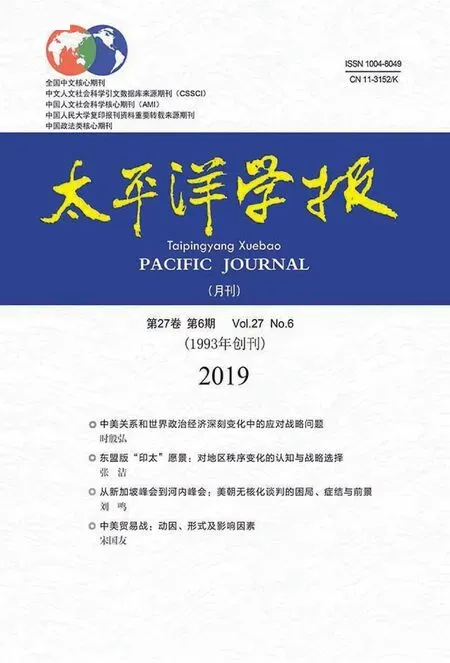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
宋国友
(1.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逐渐把其竞选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实践,对多个贸易伙伴发起贸易限制措施。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焦点国家。为实现其对华经贸目标,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了有史以来国家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战”。面对特朗普政府凌厉的贸易攻势,中方也采取贸易反制措施,中美经贸关系遭受重大冲击。进入2019年上半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仍然起伏不定,贸易谈判历经多轮无果而终,美国于5月10日对华发起第四次加征关税,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哪怕未来中美能够最终达成贸易协定,双方战略竞争态势更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中国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本文主要分析此次贸易战的动因、表现形式以及贸易战的影响因素,力图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动因
要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必须要理解两国贸易战的发生动因。或者更为具体地说,要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分析为何对华发动贸易战,因为这一次中美贸易战是由美方单边发动,中方被迫应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动因绝非某一单一因素推动,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也加入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决策进程中,彼此协调或冲撞,争夺政策主导权。在中美贸易战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动因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因此要动态观察,避免在某一学科或者某一观点下僵化地看贸易战的发生。总体上,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存在四大动因,每个动因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第一是经济动因。经济动因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最初原因,但是在经济诉求中,又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特朗普希望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能够降低。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有375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7%。①根据中方数据,中国2017年对美有2 75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特朗普从朴素但错误的经济感觉出发,认为美国对华存在如此大的贸易逆差是一种美国对中国的单方输血,损害了美国经济健康和竞争力的同时却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希望对这种模式加以改变。从中美贸易战的初始阶段看,两国斗争主要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其次,特朗普还希望能够维护美国对华长期的经济优势。这就带来了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对华施压,包括集中于“中国制造2025”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的交锋。再次,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政府推动在美国国内降税后,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试图打击中国出口,增加中国市场对外资的不确定性,旨在推动制造业回流,扩大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最后,为了更好打开中国市场,维护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特朗普也希望中国改进外资政策,降低美资准入门槛,通过取消股份占比等要求“更为公平”地对待美资企业。
第二是战略动因。从二战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历史进程看,当崛起国在实力上接近美国的时候,美国迟早会发动不同形式的贸易战,以确保其经济实力不受挑战。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战略界已经有诸多鹰派要求对华进行战略防范。②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白邦瑞的论调。参见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St.Martin's Griffin, 2016。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大致上有“接触”和“遏制”两种选项。如果美国政府选择“接触”作为对华战略的主轴,两国经贸关系更容易顺利发展。在此战略设计下,美国倾向于认为对中国开放市场以及把中国纳入到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有利于接触战略的实现。如果美国政府更加偏重于对华遏制,那么保护型的对华经贸政策会作为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经贸关系便会遭遇严重挫折。近几年来,美国国内战略界对于对华政策辩论越来越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美国对华所采取的接触战略基本上效果不大,甚至是无效的。③Aaron L.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Vol.60, No.3, 2018, p.7.竞争和博弈因此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常态性的,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也因此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保护、限制和冲突特征。④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这两大战略报告短时间内的相继出炉,以及在报告中所传递的对华战略防范基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两国建交40年以来的重大调整。在战略层面,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的战略诉求可以细化为三条:一是要确保实力优势,维护美国经济实力及总体实力尽可能保持对华的竞争优势;二是要确保模式优势,维护美国在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上的全球吸引力;三是要确保秩序优势,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以及地区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⑤Markus Brunnermeier and Rush Doshi and Harold James,“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How Great Powers Compete Economicall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1, No.3, 2018, pp.161-176.
第三是政治动因。政治诉求在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中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一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其巩固政治基本盘的考虑。从2016年的总统大选看,五大湖及中部地区的“铁锈地带”是特朗普的重要政治支持力量。特朗普如果要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在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的格局下,必须要继续获得这些基本盘的强烈支持。特朗普对华打贸易战是兑现其竞选承诺的必然要求。如果通过对华打贸易战,能够让特朗普向其支持者展现其维护美国利益的意志,并且能够宣布获胜,更加能够提升其在这些区域的支持度。在2018年中期选举期间,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等方式不断提及对华贸易战,以显示其对华强硬和为美国利益战斗的形象。二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政治诉求。在打贸易战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中国对美国进行“不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求中国按照美方意愿进行改革。同时,美国国内部分战略人士认为中国离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期待越来越远,失望感和挫败感强烈,因此也要求特朗普借用对华贸易战塑造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总体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诉求不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涉及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的若干方面,特别是其在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特朗普希望借助贸易战能够让中国有所调整和转变。
第四是个人因素。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强烈影响。如果不是特朗普当选,即便是上述因素都存在,那么中美摩擦的主要领域可能不是在经贸领域,而是在安全或者意识形态领域。即使是在经贸领域,也可能不会以这样一种反复极限施压、近乎失控的态势出现。特朗普个人风格对中美经贸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特朗普是美国二战以来唯一从商界跨入政界并当选为总统的。这一经历使其更为重视经贸领域,更为看重经贸领域的利益得失,而且也更为相信自己处理经贸摩擦的能力。二是特朗普过于显著的冷战思维理念。虽然经商,但他深受经济民族主义影响,突出美国利益优先,奉行单边主义,现实主义导向明显。三是特朗普反建制派出身。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输出通常是各种力量国内博弈的结果。如果是建制派当选美国总统,与各种利益集团都有或多或少联系,会更为慎重行事。但特朗普以政治素人面貌出现,与华盛顿各种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联系较少,不易受到传统利益集团的游说及制衡。而从其选民基础看,反全球化的“铁锈地带”成为其政治基本盘,因此其抵御偏好自由主义的金融圈和跨国公司的政治免疫力也较强。四是特朗普政府的小团体决策模式。特朗普用管理公司的方式管理美国政府,倾向选用忠诚度高和执行力强的团队成员。决策过程不透明,决策讨论时间不充分,缺乏团队内部的平衡力量,因此制定的政策容易过火,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2018年春季来自于高盛的科恩辞去总统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之后,小圈子决策模式对特朗普经贸政策的纠偏力量更是大为削弱,其对华经贸政策屡走极端。
应该说,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初心”在于实现其经济诉求。但随着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无法迅速解决,更多的非经济因素被卷入贸易战当中,美国国内对华战略鹰派也不断利用贸易战不断恶化的事实,把自身的议程注入特朗普对华经贸决策当中,引发了更为复杂的局面。在贸易战短期无法结束的情况下,中国也不断动态评估美国对华贸易战,并且采取更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反过来又迫使特朗普提高赌注,对华不断加大施压力度。在某种程度上,中美贸易战出现了恶性循环的不利局面,综合性、艰巨性不断增大。
二、中美贸易战展开的主要形式
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战过程中,形式多样,多种战法并用,力求尽快打赢,迫使中国单方答应美方的各种要求。中国也在美方重点攻击的方向上见招拆招,希望有效回击。大致上,中美双方围绕以下六方面展开了攻防。
第一,“道义战”。特朗普对华进行经贸战,首先要把自身放在“得道”一方,而把中国描述为“失道”一方。为此,特朗普政府对内对外广泛诉说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主张中国通过各种不公平贸易措施,导致美国对华有超过5 000亿美元的逆差。特朗普还多次把美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等归咎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凸显本国受害者的“有道”角色,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特朗普政府官员极力攻击中国的相关政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经贸政策不公平、不对等,不利于美国公司竞争。①孔庆江、刘禹:“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及其应对”,《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47页。特朗普政府还指责中国强迫美资企业转移技术,通过网络手段“窃取”美国机密,严重损害了其利益。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甚至使用了“经济侵略”一词暗示中国对美经贸行为,宣称不再“忍受经济侵略和不公平贸易行为”。②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17.中方则主张,中美贸易失衡成因复杂,美方自身消费过多、储蓄率少以及美元国际地位等原因,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原因。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即便数据上表现为美方对华有贸易逆差,但经贸利润较多流向美国,在直接投资领域,美国在华投资获得了巨额利润,更不用说中国稳定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国债,帮助其降低通货膨胀。因此,中美经贸关系的利益分配整体上是大致平衡的。美国不是受害者,中国更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经济发展。为突出自身反击的道义感,中国每次都是在美国首先发起对华关税征收之后才加以反制,强化自身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被动属性。然而,从对华施压策略角度,特朗普政府对上述美方受益面几乎不谈,一味突出其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受损的片面观点。
第二,“法律战”。在法律领域,有两个相关议题。一方面是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法律基础及中国回应。“301条款”是美方对华贸易战的法律基础,贸易战中美国政府对华输美产品征税的法律依据是其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基于“301条款”,特朗普政府对华进行贸易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特朗普政府认定中国进行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强制”要求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等。调查结果还指控中国或是以低价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或是通过网络间谍“窃取”商业机密,以及通过国家控制的对外投资“掠夺性地”对美国公司和技术的恶意收购。④USTR,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Related toTechnology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中方则强调切实履行知识产权保护。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依据“301条款”对华调查是典型的用国内法来对华施压。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机制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而是主要诉诸国内法实施单边威胁,然后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另一方面是中国通过国内的立法行为以缓解美国对华进攻态势。针对美国政府所谓的中国不公平竞争等指责,中国全国人大2019年春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用立法行动促进内外资企业规则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三,“身份战”。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身份上对中国再定义,改变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其一,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借助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了巨大的特殊待遇和优势,逃避了本应承担的更多责任,因此极力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希望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做出更多的承诺。中国强调,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在也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享受了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如果不再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就会超越国情而过多承担义务,会损害自身的正当利益。其二,美国试图剥夺中国本可以自动获得的“市场经济体”身份。根据中国入世协议第15条规定,中国允许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做法,但明确要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即2016年12月11日终止。但特朗普政府拒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继续拒绝执行15条规定,并向世贸组织正式提交文件,反对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借此对华在“双反”调查中继续采用替代国的机制。中方主张,第15条相关规定是中国为了入世所接受的额外条款,具有明确的时间阶段性。15年是当时中美都同意的期限,美国如今在15年之后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是违反承诺的毁约行为,明显缺乏诚意。
第四,“技术战”。美国主动把贸易战延伸至技术战层面,既用技术战对华施加更大压力,又在技术角度限制中国对美长期竞争优势,牵制中国制造升级和技术创新。①James A.Lewi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China”,CSIS, Nov, 2018,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81130_Technological_Competition_and_China.pdf.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并得到特朗普政府批准,根据这一法案,涉及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需要预先获得美商务部批准,包括商务部有权对该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建立管制。法案还要求商务部必须考虑该技术的潜在最终用途。为提高对华技术战的精准性和预见性,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2018年11月还试图扩大对华出口控制,出台了一份更为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通知。该方案将把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脸部识别和声纹技术等14类新兴技术领域列入出口管制,其目标试图在美方所定义的关键技术领域对华实施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优势。②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mmerce, “ Review of Controls forCertain EmergingTechnologies”, FederalRegister,Vol.83, No.223, November 19, 2018,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8/11/19/2018-25221/review-of-controls-forcertain-emerging-technologies.中国提出,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是导致其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美方如果在这一领域继续加强限制,只会使得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第五,“联盟战”。美国试图联合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竞争中性、世贸组织改革、劳工“自由结社”、全球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国家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等若干议题上结成对华“统一战线”。特别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美国试图联合其他发达经济体,打造基于所谓“规则”的经贸阵营对华施压。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对中国施压,特朗普政府还调整了其曾经的“多点开花、多线谈判”的贸易谈判策略。特朗普一度同时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施压,并且几乎同时推进多场重要贸易谈判。为赢得其他经济体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后来悄然改变了节奏和力度,或者提早结束贸易谈判,达成了美加墨贸易协定,或者延后了谈判进程,比如把美欧贸易协定谈判和美日贸易协定谈判放在中美贸易协定谈判之后。特朗普政府还和欧盟、日本建立起机制性的对话机制,加强在重要问题上的对华协调。③Ana Swansonu, “U.S.Joins Europe in Fighting China’s Future in WTO”,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18.中国同样意识到构筑“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形成反对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由贸易阵营,加强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对话与沟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共同反击特朗普政府自身利益第一的国际贸易政策。
第六,“公司战”。为配合对华贸易战,特朗普政府还针对特定中国公司进行了精准的“点穴战”。一是对中兴公司的制裁。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期限为7年。经过2个月左右的交涉博弈,中兴在做出了一系列的保证后,终于被解禁。期间中国耗费谈判资源,美国获得一定谈判优势。二是对福建晋华公司的禁售。2018年10月,美国商务部以涉嫌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认定福建晋华公司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活动,决定限制美国公司对福建晋华的出口,并将其纳入《出口管理条例》第744部分附件4的实体清单。美国政府还认为福建晋华即将获得大规模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的能力,未来将对其军用系统供应商造成威胁。三是对华为公司的打击。在2018年12月,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扣押华为首席财务官并寻求引渡至美国。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限制相关公司对华为出售技术产品。面对美国对中国特定公司的打击行为,中国政府也在公司层面发起了反击。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政府未批准美国高通公司对恩智浦公司的并购申请。
总体而言,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起方,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对华攻势凌厉,手段变化较多,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压力。但中方并未被美国击垮,而是展现反击美国的决心和意志,采取各种措施反制美国,逐渐消耗美国的耐心,塑造对美经贸“持久战”之势,不断迫使美国回归到谈判方式和中国解决贸易争端。
三、中美贸易战走向的影响因素
中美贸易战不断变化反复,延烧一年有余,可谓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最大的不确定性事件。从贸易战进程来看,贸易战的走向受到多重因素的塑造。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受到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不仅直接塑造着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还预示着两国关系互动的新态势。
3.1 经济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中美两国贸易战直接经济成本。中美贸易战对双方均带来经济成本。这些成本大致上可以从对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贸易、就业、税收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行衡量。经济成本大致能够测算,中美两国对此也均有大量研究。例如,根据李春顶等人的研究,一定烈度的中美贸易战可能会使得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1.4%和0.11%,贸易分别下降4.9%和5.1%。①Chunding Li, Chuantian He& Chuangwei Lin,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Possible China-US Trade War”,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Vol.54, No.7, 2018, pp.1557-1577。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经济影响评估,还可参考 Marcus Noland,“US Trade Policy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13, No.2, 2018, pp.269-273; Meixin Guo, Lin Lu, Liugang Sheng and Miaojie Yu,“The Day After Tomorrow:Evaluating the Burden of Trump’s Trade War”,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17, No.1,2018,pp.101-120.理论上,如果一方遭受的经济战成本巨大以致难以承受,那么就有可能在谈判中被迫妥协让步,满足另外一方的要求,从而结束贸易战。不过,显性的经济成本可以估算,但忍受经济成本的能力和意愿难以测量,其与一国的战略承受度和政治回旋力高度相关。因此,只要这种经济成本不是致命性的,还必须把两国综合的承受能力带入加以考虑。困难的是,对于耐受度的衡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意志考量。
第二,其他经济相关因素。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看,直接的贸易战成本对任何一方的冲击都不是致命性的,总体上负面冲击可控。这时,就需要分析贸易战直接经济成本之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具体而言,如下两个指标更为关键。一是中美两国短期内的经济增速。如果在贸易战之下,美国经济增速仍然较高,那么特朗普打贸易战的动力更为充分,如果经济增速下滑明显,其打贸易战的动力就相对不足。二是美国金融市场表现,特别是其股市表现。本来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损的民众和公司,也因为股市上涨而部分抵消了可能遭受的福利损失,因此缺少足够动力游说特朗普。在贸易战的阴影下,如美国股市持续上涨,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动力充沛;如美国股市持续下跌,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动力不足。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201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表现不错,全年经济增速为2.9%,为3年来最高。如果分季度看,2018全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2%、4.2%、3.4%和2.2%,在经济增速超过3%的时候,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更有底气,分别在7月、8月和9月三次对华加征关税。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表现不好的第四季度,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施压上有所缓和。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表现良好,达到3.2%的年化增幅,特朗普宣布新一轮对华关税加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股市表现日益成为其对华贸易战决策的短期参考重要变量。在2018年前三季度,美国股市总体涨幅明显,特朗普以为中美贸易战对美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减少了后顾之忧,对华持续极限施压,贸易战不断加码。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美国股市一改前期大涨态势,转而大幅下跌。到2018年11月中旬,相较于10月初最高点,标准普尔指数跌幅为9.7%,连连大跌之下,标普指数已然回到2017年12月初水平。换言之,美国股市2018年全年的涨幅几乎全数尽失。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总体上也呈相似变化趋势。随着美国2019年美国股市第一季度有所上涨,特朗普政府又无所顾忌,对华再度施压,提升2 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关税。
而美国股市的表现和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进程又是密切相关的。美国股市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的下跌原因,是多重原因叠加的结果。一是美联储持续加息。2015年底以来,美联储已经加息8次。2018年就有加息3次。二是特朗普减税红利几近消失。①Thomas Heath, “A Year after Their Tax Cuts, How Have Corporations Spent the Windfall?”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4,2018.最后一点直接的经济因素就是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走向不定。观察2018年以来的美国股市表现,几次大的波动与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关系密切。总体而言,每当特朗普威胁或者宣布对华关税惩罚的时候,美国股市基本以下跌为主,甚至是大跌。例如,在特朗普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后的3月22号和23号,美国股市连续两天大跌。2018年10月份美股的连续大跌与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上的强硬表态高度相关。在2019年5月美国政府决定把2 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从10%上升至25%、中国据此也宣布了对自美进口600亿美元产品加大关税报复措施后,美国道琼斯和标普一天之内跌了2.4%,纳斯达克跌了3.4%。而特朗普缓和对华贸易态度的时候,美国股市大都会迎来上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交易时段有2018年5月初、11月初和2019年5月中旬。
从上述两个经济因素看,随着美国对华相继征收340亿美元、160亿美元以及2 000亿美元数额不等、税率不一的惩罚性关税,以及中国基本上在同一时间所进行的贸易反制,中美贸易战规模不断扩大,两国承受的直接经济成本不断增加,各自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金融市场波动日益明显,对双方累积性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中美两国没有赢家,两国经济冷战的恶果或早或晚都要出现,美国同样会面临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3.2 政治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中美两国元首互动。中美两国元首在中美关系中起到引领作用,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关键角色不可替代。②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13-14页。如果中美两国元首保持顺畅沟通,密切联系,解决中美贸易战的概率就会加大;如果中美两国元首没有互动,甚至是彼此对立,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2017年中美两国元首互动氛围良好,实现海湖庄园、德国汉堡以及北京三次元首峰会,达成较多共识,确保了2017全年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2018年,由于特朗普威胁和推动对华贸易战,中美两国元首互动情况并不乐观。直到2018年11月底以前,中美两国元首没有任何见面,这不利于中美贸易战的解决。2018年11月份以来,中美元首有了较好的互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11月1号进行了通话,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了会谈,确定了90天的新谈判时间表,12月29日再次通话。2019年1月1日,两国元首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两国元首的积极互动为避免中美贸易战的恶化提供了机遇。在总体良好的首脑互动惯性推动下,虽然在延展的90天谈判时间内,中美仍未取得最终的贸易协议,但是双方都宣布暂停征收新的关税,并且同意继续进行贸易谈判。
第二,特朗普政府团队成员变动。特朗普团队成员在塑造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特朗普团队成员在对华施压这一总目标上没有差异,但是可以大致分为“逆差减少派”和“结构调整派”。“逆差减少派”主要以华尔街出身的官员为主,包括美国财长姆努钦、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等人。这一派强调对华贸易摩擦要注意对华施压的力度和规模,不主张挑起与中美的全面贸易战争,要避免两国经贸关系全面恶化。“结构调整派”包括贸易和产业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等人,主张必须利用这次贸易战的机会,迫使中国进行根本性的经济结构和其他领域调整。这两派互相对立,争夺对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上的主导权。在不同的阶段,特朗普在坚持自己看法的同时,也被不同的派别观点所塑造。当“逆差减少派”对特朗普有更多影响时,中美贸易谈判较为顺利;当“结构调整派”有很大话语权时,中美贸易谈判往往遭遇变数。从美方团队成员变动看,随着主张中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莱特希泽取代姆努钦成为2019年以来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首要负责人,莱特希泽在特朗普决策团队中的作用相对提升,而姆努钦的地位相对弱化。这加剧了中美贸易谈判的困难程度。
第三,美国选举政治。美国政治本质上是选举政治,因此选举考虑对于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有观点认为,特朗普之所以2018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态度强硬,就有着眼于中期选举的考虑。①Feng Lu, “China-US Trade Disputes in 2018: An Overview”,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Vol.26, No.5, 2018, p.98.未来中美贸易战走向,更要考虑2020年的总统大选因素。如果特朗普认为对华打贸易战有助于其和共和党的竞选,那么会有很强动力不断挑起贸易纠纷、打贸易战;如果打贸易战不利于其选情,那么特朗普对华打贸易战的动力就不足。
从美国国内选举政治的角度,可以把2018年11月揭晓的中期选举作为观察美国国内政治及中美贸易战发展的重要观察指标。此次中期选举,美国政治的“三化”特征延续。一是政治版图固化。民主党固守东西海岸,共和党占据南北中的格局表现得依然十分明显。二是政治极化。两党及其支持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对立。三是政策运行僵化。特朗普推动的众多国内立法议程不仅受到民主党国会的掣肘难以落实,其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也可能受到民主党的严厉审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三化”特征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特征,即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特朗普助选的绝大多数议员及州长赢得选举,对特朗普失望或者反感的共和党议员或者主动离任,或者遭遇选举失利。特朗普因此对于共和党的塑造能力更强。就在中期选举结束不久,特朗普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而明显没有遭遇党内的反对,表明其对于共和党的影响力加大。反观民主党一方,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尚没有看到相对出挑的政治人物。特别是随着“通俄门”调查结束及其结果公布,特朗普竞选连任的不确定性减少。只要特朗普不遭遇颠覆性的错误或者打击,其在共和党内部应该不会出现能够匹敌的挑战者。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下,中国更应重视特朗普个人作用,积极推动中美元首互动。显然,特朗普也很清楚,中美贸易战的走势,将会塑造其2020年的竞选结果。特朗普希望把中美贸易协定打造为其竞选连任的加分项,而不是“负资产”。中国因此要紧紧抓住特朗普,并塑造之,争取其本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能够积极调整。但是,同样是从选举政治出发,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其国内各政治力量将会继续拿中美贸易问题做文章,中美贸易摩擦还将会反复出现,甚至不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四、结 语
中美贸易战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重大历史交汇期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爆发的冲突性事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经贸领域,还会产生重大的指向意义,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总体而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表明中美关系有出现结构性变局的趋向,如果双方管控不当,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愈发接近美国,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有从战略稳定向战略冲突发展的趋势。①宋国友、张家铭:“从战略稳定到战略冲突?中美建交40年的经贸关系发展评估”,《美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2辑,第13-18页。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传统的“压舱石效应”有所弱化,而且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双方竞争的诱发因素和斗争领域。
不过,从中美贸易战的进程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对华固然有打压和防范增强的一面,但是中国应对美国施压的能力和手段也在相应增加。中国并不是单纯被动挨打的一方,可以通过“打”和“谈”相结合的策略对美施展影响,形成压力,迫使其调整对华政策。在中方的反制下,美国最终还是要回到和中国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其所关切的各种利益。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贸易战证明了斗而不破、战为求和仍然是中美博弈的主基调,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可能确实引发某一方不满意之处,但其形成的巨大共同利益以及相互确保经济伤害能力可以维系双方关系的总体稳定。只要中美不发生重大的战略误判,不被极端政治势力所绑架,在经济利益的不断交融中协调彼此定位,两国关系的和平前景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