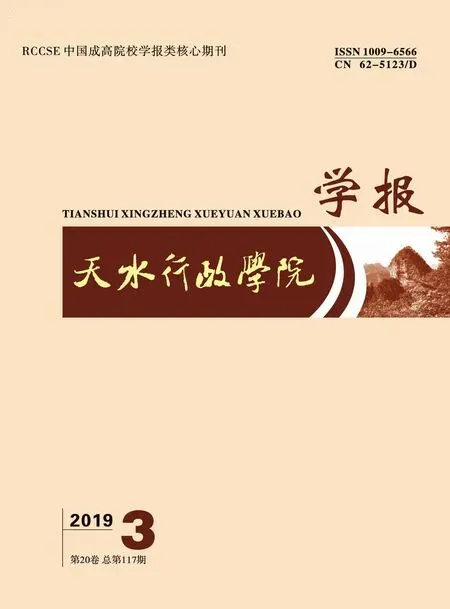“互联网+”背景下我国法院ODR 的问题与克服
林 静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一、ODR 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自1996 年美国拉开ODR 的研究帷幕时起至今,国际层面对于ODR 的定义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我国学界关于ODR 的翻译虽存在不同的版本,但普遍赞同其为“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形式,即直译为一种在线纠纷解决的机制。既涵盖了传统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各种基本类型,又突显了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综合运用,进而实现了争议的在线解决,并凭借这一特性在一些距离较远、争议金额较小的纠纷中,得到广泛的适用。而关于ODR 的概念,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作广义与狭义的区分[1],前者是指ODR 应分为法院ODR 与法院外ODR 两类,后者则仅将法院外ODR 纳入该机制的讨论范围。在“互联网+”这一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法院外还是法院系统内部,均无法回避这一潮流,故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如何完善我国法院ODR。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最早研究ODR 的国家,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均处于该领域的前列,随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涉足该领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关于ODR 的关注则较晚。虽然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争议解决中心在2001 年便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联合打造了“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是世界范围内排名第四、亚洲地区排名第一的国际通用的顶级域名争议解决机构[2]。但令人遗憾的是,因该中心在当时仅处理域名领域的争议,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ODR 平台。直到2004 年,我国才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在线争议解决机构,即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其以“公平、公正、快速地解决线上争议”为服务宗旨[3],当双方产生纠纷后,任何一方均有权通过互联网向该中心提出申请,并在对方接到通知且同意使用该方式后,中心便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启动该纠纷解决的程序。另外,当事人在具体使用何种在线方式上还享有决定权。随后,我国关于ODR 的实践,不仅体现在一些官方的组织上,如: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投诉和解监督平台、深圳市成立的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众信中心”)等,而且部分电商平台亦做出了尝试,如阿里的大众评审、京东的纠纷在线申诉等机制。同时,法院ODR 的实践亦如火如荼的进行,如我国电子法院的成立、e调解平台的推出等,均为ODR 机制在我国的良好运行而助力。
二、我国法院ODR 的实践
关于电子法院的建设,我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2 年便在司法拍卖、支付宝执行查控等方面与阿里进行了合作,根据数据可知,94%的涉诉资产是通过淘宝网进行公开拍卖,其成交率相较于传统的拍卖而言,高出近十三个百分点,平均溢价率比传统的高出了约20%,进而节省了12.7 亿余元的佣金。2015 年更是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电子商务网上法庭,通过与阿里旗下的一些电商平台进行合作,解决网上交易、小额贷款等纠纷,开创了法院审判的新模式。截至到2015 年11 月30 日,网上法庭共收到案件813 件,诉前调解196 件,原告撤诉231 件,判决15 件[4]。根据2017 年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可知,截至2016 年9 月,电子商务法庭共收到14502 件起诉申请,诉前调解了266 件,撤回的案件数达4227件,退回了5832 件,已判决的为106 件。电子法院极大地节约了双方当事人的解纷成本,同时,对于法院而言,不仅提升了办案效率,亦契合了阳光司法这一理念,利于法院良好形象与威信的树立。随后,在2016 年的8 月份,浙江省高院首次提出了设立互联网法院的构想,并在一年后成功落地,成为全球首创。截止2018 年10 月末,杭州的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总数已达14233 件,已审结的多达11794 件,既具备法院审案、结案件的传统功能,又顺应了“互联网+”背景下司法领域创新实践的要求[5]。位于该领域前列的不仅有浙江省,吉林省高院亦在全省法院系统中进行“电子法院”建立的尝试,并形成了起诉、立案、审理、裁判以及执行为一体的“一站式”在线服务,为法院ODR 的发展助力。
“e 调解”平台以互联网为基诞生,由我国法院与互联网媒体(新浪网)联合打造,其作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既具有ODR 的共性,同时对于法院的司法资源亦是一种节约。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的实践中,自2015 年平台在该区上线后,截止11 月末该平台共受理网上调解案件125 件,主要案件类型有物业纠纷、劳动争议等,调解成功率超过50%,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6]。此外,该平台的操作方式简便,仅需当事人拥有一台具备视频、摄像功能的电脑即可,且在进入平台界面并录入相关信息后,便会收到与之相关的案件庭审录像及裁判结果的推送,使得当事人可以事先预测自己面临的诉讼风险,从而选择更为经济的方式,如通过调解予以解决。在获得大众青睐后,各地关于“e 调解”平台的实践如雨后春笋,如江西赣州、广西梧州以四川成都等,均通过平台进行案件的处理。其中,成都市中院及试点地区的基层法院,通过“e 调解”受理了线上申请161 件,双方均同意调解的有106 件,调解成功89 件,成功率为83.97%。
综上,我国与ODR 相关的实践,虽然走着与世界ODR 相似的路线,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仍有一些难题需要克服,从而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社会。
三、我国法院ODR 实践中的问题
(一)未能充分利用法院外ODR
自电子法院、e 调解平台等在实践中适用以来,无论是对于双方当事人还是法院本身而言,纠纷解决的成本均得以降低,同时,亦因法院系统对ODR的尝试,使得该机制在社会大众间的威信得以提升。根据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的报道可知,该院自2018 年2 月起推广ODR 平台,截止今年10 月份,该平台已在线受理了5000 多件纠纷,其中4244 件已经结案,结案率高达84.88%,提前完成了该院的既定目标[7]。由此,ODR 这种解纷方式已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但是,当前社会中纠纷的数量近乎以“指数爆炸”式予以增长,这对司法系统而言仍旧压力巨大,因此,有的地区尝试引入了法院外ODR,并形成了“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纠纷解决模式,且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然而,上述做法仅为个例,即浙江省诸暨市法院的有益尝试,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但法院关于电子法院、e 调解平台的实践,则广泛在不同省份的不同地区展开,无疑会增加法院ODR 的线上纠纷量,加之我国法院系统内对于该方式熟练运用的法官占比较小,致使其办案压力不减反增。
淘宝网作为我国范围内最大的电商平台,其纠纷解决机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2014 年淘宝网的年交易总量突破了2.4 亿元,且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达8%,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的纠纷,其中通过淘宝网自身的在线解纷机制得以处理的案例达737204 个,进而避免了该部分纠纷涌入法院。纵观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ODR 平台,即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的发展而言,其成立后虽处理过一些在线的纠纷,但目前这一中心已不再提供服务,其原有网址界面内容已转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平台,虽然中心仍旧提供在线服务,但因其在建,故该平台还不能进行纠纷解决的实际操作。原中心运行对于电子商务领域纠纷的处理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其在大众间缺乏知名度,故逐渐被人们所忽略、遗忘,最终难以为继,被迫作出调整。该平台虽然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亦可让我们认识到其具有的对法院ODR 起补充或是辅助作用的可能性,这不仅分担了法院的办案压力,还使ODR 在我国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由此,我国法院系统在关于ODR 的实践中,虽认识到自身以外ODR 平台的存在,但因未能对其展开充分的利用,故使自身于实践层面收获的效果大打折扣,且欲将法官从案件处理中予以“解放”的设想依旧未能实现。
(二)专业人员的数量有限
根据各地的实践报道可知,以电子法院、e 调解平台等为代表的法院ODR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经由官方的推广,该种纠纷解决方式逐渐获得大众的信任与青睐,这一方面说明法院系统有关ODR 的尝试应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由此带来的问题,即法院系统内关于该部分的专业人才匮乏,在一个市两级法院1600 余名法官的队伍中,其中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仅有30 人,占总数的2%不到,该市法院中配有该方面人才最多的为4 人,最少的仅有1 人,这无疑使法院的信息化建设面临较大的阻力。诚然,法院系统可以引入法院外ODR 平台,并充分利用平台上的调解或是仲裁人员,以此缓解自身的压力。如前文提到过浙江省诸暨市法院的做法,即对社会上调解资源予以利用。但在该平台已注册的122 家调解机构的459 名调解员中,既有律师、专业调解员,也有乡镇或是街道的人民调解员存在,由此,近500 名调解人员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使得争议处理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而言,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产生的纠纷数量也会有所不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如浙江、深圳等地区的调解人员在较多实际案例的基础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利于形成抽象的规则与规范,而且也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故其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由此,我国法院ODR 领域专业人才的缺乏,不仅体现在解纷人员整体上数量的有限,而且也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平台的人员在能力水平上存在着差异。法院系统对此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完善措施,助力法院ODR。
四、既存问题的克服
(一)引入法院外ODR,增建衔接路径
首先,应在观念上作出转变。对于法院外ODR我们应认识到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所处的定位,并重视其在解纷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如前所述,ODR 在电子商务领域如鱼得水,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使人们将纠纷解决的视野由传统的线下转移至线上,但遗憾的是,因为非官方性、自负盈亏等原因,导致一些法院外ODR 并未能顺利发展,公众基础亦不牢靠。当前我国法院ODR 的实践,因其以法院甚至是国家的政策为依靠,故运行的较为顺畅,大众的接受程度也很高。由此,借ODR 在我国良好发展之势,法院应在观念上意识到法院外ODR 填补漏洞的功能,诸如淘宝网、京东等电商平台,在其数以亿计的成交量背后,平台自身的在线解纷机制发挥着较大作用。改变依赖法院一家解纷的传统思想,重视自身以外的解纷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社会。其次,增建衔接路径。我国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深挖法院外ODR 平台的优势,积极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成功地吸收了122 家调解机构且拥有459 名调解人员开展线上的调解工作,截至2018年10 月,平台已受理了5000 多件纠纷,其中调解成功的有2561 件,成功率突破60%,该院做到了调解资源的有效整合,减轻了本院的办案压力。故我们可以对该法院的具体做法进行参考并适当借鉴:一是整合好本地区多元的线上解纷资源,诸如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业调解甚至是电商平台自身的在线解纷机制,均可考虑适度与本地区法院实现对接,充分利用社会上的解纷资源。二是确保案件分流便捷。在当事人起诉至法院且双方选择在线平台予以解决后,法院须首先对纠纷进行判断,认为可以由其他线上调解平台先行处理的,在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后转至适宜的在线平台,不仅使法院外ODR 平台被充分利用,而且节省了本院的司法资源。最后,强化衔接保障。自我国开始研究ODR 至今已十年有余,虽仍未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加之当前“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以ODR 为代表的线上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拓展其适用的领域,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解纷力量,故在我国追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格局的当下,有必要将ODR 置于该全局中予以考虑,使ODR 在制度层面得到承认,进而保障了法院ODR 与法院外ODR仅是在不同机构运行,但在实质上仍是平等的。实践中,双方在法院外ODR 平台上进行争议处理后,因一方未能自觉履行裁决结果,致使另一方寻求法院救济的,法院应根据对接的相关程序与规则对该裁决的效力进行认定,确保裁决结果的顺畅执行,从而使法院内外ODR 平台的衔接发挥实际作用。
(二)建立ODR 专家库,完善培训机制
第一,由法院系统主导,建立本地区的ODR 专家库。诚如上文所述,法院ODR 与法院外ODR 实现对接,这一尝试可在运行较为成熟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法院系统予以推广。由此,有必要对平台上的解纷人员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诸如在本地区成立一个专门的ODR 人才库,将该方面的专家通过互联网“汇集”在一起,以便其提供更好、更持久的服务。我国众信中心对此进行了尝试,在其建立之初,便有ODR专家库这一板块,其中包括律师、调解员以及仲裁员,其处理的纠纷类型也较为全面。我国法院系统可参照此,将本地区其对接的ODR 平台上的解纷人员纳入该专家库,并可按照其身份(即职业)或是擅长的领域,进行分类方便管理。此外,一个省份可以市级为单位,在不同市成立一个其辖区范围内的ODR专家库,该专家库的成员可被本市辖区内任意一级的法院所调用,且由市级法院联合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同时辅之以激励机制,以保证其解纷的积极性。第二,依托本地区ODR 专家库,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方案。因前述解纷平台的侧重各有不同,故其人才选拔的标准也会不同,不仅表现在专业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个人能力方面也存有差异。由此,有必要对本地区专家库中的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如“硬件”上对在线解纷操作流程的掌握,“软件”上对有关专业知识进行学习;可设置一定的等级,并颁发相应的资格培训证书,并且只有合格的人才可成为专家库的成员,以此来激励其学习的积极性,进而为当事人提供更为优质的选择与服务。第三,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最大的优势与特点,便是其综合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使不同地区的ODR 专家库成员通过该技术,实现解纷经验与资源的共享,既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可提升整体的解纷水平,保障解纷的效果,使大众满意,群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