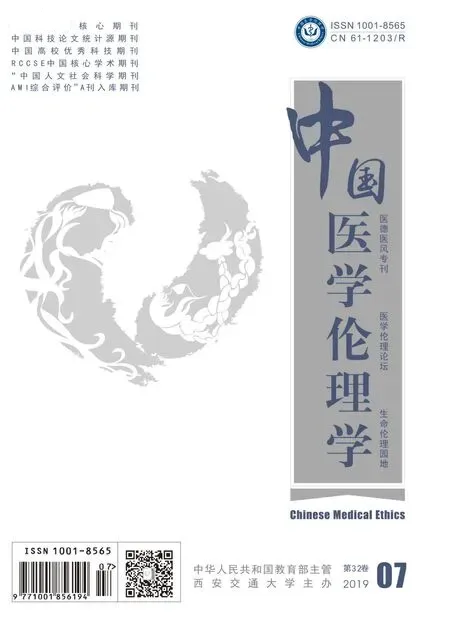医学人文是什么、讲什么、怎么讲?*
翟海魂
(河北医科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17)
医学人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成立,恰逢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人文”事件的百年节点:一是100年前,发源于北大的五四运动,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中国人文领域进步新的起点;同是100年前,威廉·奥斯勒在《旧人文与新科学》主题演讲中,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应当互相融通,首次提出了“医学人文学者”的概念。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依托北京大学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医学人文事业进步的基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诞生,一定会再创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的辉煌,引领中国医学人文发展的未来。
借这个机会,我就以《医学人文是什么、医学人文讲什么、医学人文怎么讲》为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1 “医学人文”是什么?
“医学人文”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它究竟是什么,理解和解释似乎多种多样,并没有真正形成学理上和理论意义上完全一致的认识和界定。由此我们想到物理学家布里奇曼说过的一句话:要发现一个词的真实意义,就应该了解人们用这个词做什么,而不是对这个词说了什么[1]。同样,对“医学人文”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去定义,也可以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乃至漫长的讨论,但我们可在这种探索和争论中转换一种视角来把握“医学人文”这个概念,把对它的关注点转向“为什么需要这个词,准备拿它来做什么,或者说实际上正拿它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上来。尽管这样看待“医学人文”可能不能给出它究竟是什么的答案,但是希望能够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线索和视角。
1.1 “人文”概念的文化源流视角
“医学人文”是一种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赋予。“历史基于时间,却始于语言”[2]。从词源学意义上看“人文”一词,无论是汉语还是西语,其词义都深刻地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汉语的“人文”一词最先是在与“天文”一词的对应中产生的,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提并论,“人文”被规定为“天之文采”之外涵盖一切“人事”的“人之文采”,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和伦理特性。与汉语“人文”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语词是“Humanities”,该语词来源于拉丁文的“Humanitas”一词,而这一拉丁语词来源于希腊文“Paideia”,该词的词义是“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之品质的途径”[3]。这与古希腊时代有闲阶级特别是哲学家们崇尚智慧、谋求真知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西方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还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文”一词在历史的变迁中都具有了双重含义:其一指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思潮;其二指的是对教育作用的信赖和推崇,也即坚信教育可以培养出人的包括追求学问和知识在内的人性[4]。人文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的母体,也是人类文化的起点和归属。医学作为从人文文化母体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生命文化领域,其成长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过人文文化的哺育和滋养。
1.2 医学发展的历史视角
人文性是医学的内在规定性。医学与哲学本是同根生,在古希腊哲学家眼里,哲学是面向灵魂的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医学近代以后才从自然哲学中脱胎出来,并以生物医学的形态演进,分科不断细化,体系不断扩充,对生命的微观认识不断加深。这是医学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不经历这个阶段的进步,就没有现代系统医学形态的形成。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同样的道理,正因为现代医学的“高级形态”中蕴含着医学的“中、低级形态”,我们才可能通过反观早期医学,去发现医学的内核及其演进过程的任何阶段,都从未缺失过人文的眷顾。只是在某些特定阶段,医学将其进步归因于“生物性”主导,相对于这种生物性的耀眼光环,医学的人文特质显得有些暗淡。医学发展到今天,大量源于医学的生物特性并与其交织在一起的非生物性问题和难题层出不穷,必然需要我们唤醒医学内核中的人文要素,激活医学的人文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医学沿着生物医学方向演进的过程,是医学进步的必然代价和必要付出,是医学从理性医学发展为理想医学的必由之路。
1.3 高等教育发展史视角
高等医学教育脱胎于人文。最早兴起的大学是1088年在意大利建立的波洛尼亚大学。大学是学者的行会。此前还出现过只有医学的被称为“希波克拉底之国”的萨勒诺大学,遗憾的是这所医科大学只存在了两百年便销声匿迹。中世纪最初的大学,一般设立法学、医学和神学三个学院,当然也有文学院。文学是预科,通过预科学习后,再升入其他三个学科进行学习。这三个学科为调节当时社会的三大关系培养人才:神学调节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按照宗教的说法),法学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医学则是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大学的医学被称为“光芒四射的恒星”,照亮了“文科”中的其他学科[6]。实际上,那时大学里的医学,是特殊类型的哲学,与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所以我们说,医学人文是医学的一种本质属性,是医学发展的理性回归,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基础。古代医者对患者的所谓人文关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今天的医学重新唤醒人文与回归人文,绝不是回到原初的医学模式,就像哪怕是再高级的猴子的解剖图谱也指导不了今天人的解剖一样。
2 医学人文讲什么?
冯友兰先生治学有一个命题:“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照着讲”是守望、延续和保持;“接着讲”是扬弃、创新和发展。对于医学人文,我们既要“照着讲”,这是对千年本真医学的坚守和传承;更要“接着讲”,与时俱进,努力为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培养所需要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符合新时代新医学的特征,也符合新时代对医学教育的要求。
“照着讲”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要坚守的医学人文精神:仁慈博爱、敬畏生命、公平公正。这是医学人文精神的灵魂、精髓和基础。接着讲,讲什么?我们认为这样五个方面应该是对医学人文新的诠释:家国情怀、思想方法、终身学习、包容共赢、团队合作。
第一,家国情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医学由临床治疗模式向“大健康”模式的转变,健康目标的实现需要将对个体的关照统一于对人口、群体的关照。医学领域要心系国家和民族,以不可替代的医学人文特性和宽广的医学人文情怀,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病患和弱势群体,让百姓在感受医学的温暖中体验社会改革和进步的获得感。
第二,思想方法。以现代医学回归人文为契机,通过医学人文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医学的再融入过程,全面和系统创新医学方法论体系。比如从哲学、道德哲学、应用伦理学到生命伦理学这样一个哲学学科体系与生命医学科学的关联上,把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复盘思维等哲学思维方式有机运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和临床医学诊疗;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哲学方法,重新审视医学的历史和现状,医学的体系及其内部关系,回答医学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的问题。
第三,终身学习。生命的自然进化、特别是现代生命科学对生命的人工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健康需求的改变、疾病谱的更新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医学的全面进步,都一再说明“变化与发展”是医学的规律。医学人文在现代医学中价值和作用的凸显,也说明了这一点。医学观念需要更新,知识结构需要调整,新的信息需要把握,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所有从医选择的人需要终身学习,这也是医学人文本性的一种自然延伸和基本要求。
第四,包容共赢。正是医学包容,医学才得以能够在不同的模式下都得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学是一个不断精进、分隔又不断走向融合的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文。因此,开放和包容变得更加重要。
第五,团队合作。从事医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医生、医疗服务人员、医学技术人员的团队协作[7]。团队精神是现代医学职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
3 医学人文怎么讲?
上述对医学人文问题的阐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抑或可以说是在拓展意义上来谈的。我们认为真正将这些对医学人文问题的认识落地,需要通过医学教育过程来完成,至少要构建一个体系,做好两件事。
构建一个体系即课程体系。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说过,学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能学到什么、学得怎么样,同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我们认为,学生进入什么样的人才培养体系,就进入了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而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最重要的便是构建医学人文的课程体系。
构建课程体系,要从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组织实施、质量评价着手,做好“六个”转化的往复:把需求转化为培养目标,把培养目标转化为课程结构,把课程结构转化为教学内容,把教学内容转化为组织实施,把组织实施转化为教育评价,把教学评价转化为教学改进[8]。
课程体系构建后,如何完成体系的运行?需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教好。一般课程目标有三类:知识、能力、情感。人文教育的目标,主要体现在情感目标上,核心是价值观。情感目标的实现,要经历“理解-接受-内化-外行”的过程。接受,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要重视接受的研究,要使教育与接受形成合力,形成双向互动。用传授知识的形式和方法进行情感教育,怎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二件事,学好。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这个文件里,对“教育”和“学习”有一个定义:“教育”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有组织的、持续的交流来引发学习的有意识的活动”。“学习”是“个人通过经历、实践、探究、听讲,而在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技能、胜任力或者行为方面的获取或者改变”[9]。简言之,教育在于引发学习,学习在于获得和改变。学习的途径先是经历,然后是实践、探究,最后才是“听讲”。
如何能够学好?六个方法最有效:基于建构的学习最有效,基于问题的学习最有效,基于兴趣的学习最有效,基于实践的学习最有效,基于合作的学习最有效,基于反思的学习最有效[10]。
马克思说: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11]。教学是最高的理解形式。如何让医学人文的“爱”,有幸、有力地让学生们接受,是对我们这些医学人文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考验。这需要我们持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