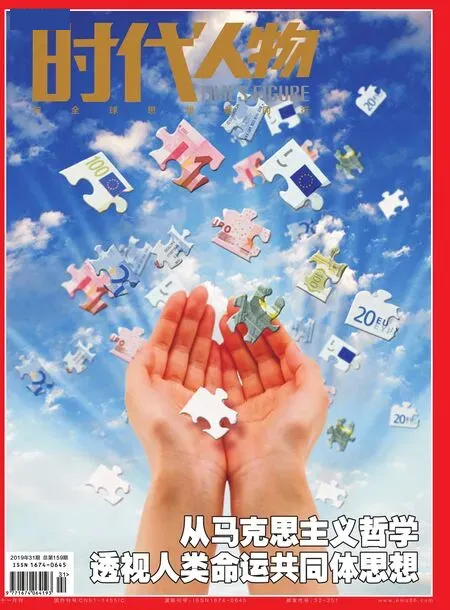共情在高校辅导员“一日常规”管理中的应用
□文|刘旺
(作者单位:三江学院)
2017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说明,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辅导员岗位缺口不断增大,师生配比高达1:300,这无疑对落实“以生为本”的精神、贯彻“教育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理念,带来巨大挑战。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能否利用共情理论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并有效解决问题,帮助大学生提高应对类似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高校思政工作的育人目标。
共情概念的由来
共情概念在西方出现已有百年之久,最早德国哲学家Robert Vischer(1873)在《视觉形式感》一文中用德语“Einfuhlung”来表达人们把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主动投射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种现象。德国美学家、心理学家Theodor Lips后来将共情概念应用于心理学,他认为,共情是共情者被动地、直觉地对共情对象进行模仿而获得的感受。英籍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Tichener在1909年“关于思维过程的实验心理学讲稿”中首次用英文“Empathy”代替德语“Einfuhlung”,并将共情定义为一个客体人性化的过程[1-3]。共情目前广泛应用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医护关系、师生关系等领域。
在工作中运用共情意味着辅导员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每一位学生的角度、用学生的心理、从学生的眼光来体会他们的所思所行,真正走近学生的内心。大学阶段是学生人格完善、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在校期间日常行为的管理者和健康成长的引导者,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高校辅导员运用共情的必要性
辅导员队伍本身的特殊性。绝大多数高校招聘辅导员的要求是中共党员,具有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不超过28周岁,思政类相关专业优先。很多应届硕士一毕业就考进高校任职辅导员,他们与自己所带学生的年龄相仿,并且正在适应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换,有与学生产生共情的优势。同时,辅导员的本科和硕士专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为主,大部分辅导员的专业与所带学生的学习专业完全不同,一开始很难快速找到共同话题,因此需要通过共情来助推日常工作的开展。
辅导员工作内容的特殊性。辅导员除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很多琐碎的一日常规工作,如检查学生到课率、检查学生夜不归宿、医保报销、评奖评优、党团建设、调解学生矛盾等等。将近1:300的师生配比,使得辅导员每天都要忙于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无法探索思政教育工作新模式,无法进行思政教育课题研究,更无法从日常工作中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工作热情,而产生职业倦怠。辅导员需要发挥共情作用,通过培养自身和学生的共情能力,有意识增强学生的自理和自控能力,构建和谐友爱、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从而能够适当减轻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压力,有余力进行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
“千禧”代大学生的特殊性。00后大学生相较于90后大学生,有很明显的特点。情感方面,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感觉良好,想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性格方面,特立独行,有强烈的叛逆心理,不善于接纳别人的建议;意志方面,抗压能力差,忍耐能力弱,不能持之以恒,过分追求轻松的生活;认知方面,遇事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过于片面和执着,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但学习专业知识兴趣弱;行为方面,依赖手机和网络,不会对时间进行有效管理,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思想方面,思维活跃,有创新意识,但缺乏团队合作能力。正是由于以上种种特征,需要辅导员在工作中实施共情,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探寻学生的真实想法,感悟和体验学生的生活情绪,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从而引领学生自我成长。
共情在辅导员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辅导员工作包含很多项,本文基于的“一日常规”工作,是指辅导员每天都需要面对的工作或者可能随时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将依据几个真实的案例,探讨共情在一日常规工作中的应用。
倾听和分享。寝室是在校大学生主要生活场所之一,有调查显示,除去正常的7-9小时睡眠时间,大学生每天还有近6小时的时间是在寝室度过的。虽然一个寝室只居住4-6名同学,但大家的家庭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习惯也不同,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小型社交圈。据调查有60%的同学认为某一位舍友就是自己最讨厌的人,33%的同学认为在寝室里感觉不到温暖,潜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4]。笔者作为一名一线辅导员,经常在深夜收到QQ留言:“导员,我经过深思熟虑,恳请帮我调宿舍,再待在这个宿舍我就要抑郁了”、“姐,我受不了某某了,一直在敲键盘,根本睡不着”、“他们都针对我,整整2天没有和我说话了,我快要憋死了”。当辅导员收到学生对宿舍矛盾的抱怨讯息时,应当及时与当事人沟通,把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不能任其发酵。
对于强烈要求调换宿舍的这位同学,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邀请她来办公室聊一聊。以询问的方式引导她讲述事情的经过,如:“现在心情怎么样?方便和姐说说吗?”要让学生感觉到是在关心她并且已经感受到她痛苦的状态,辅导员是要帮她分担,而不是毫无表情甚至不耐烦的问:“又怎么了,你怎么老和同学相处不好?”在引导学生讲述事情的过程也是帮助她排解负面情绪的过程,当然在倾听的同时,也需要用一些简单的词汇,如:“然后呢”、“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呢”,或者眼神交流,或者肢体语言,如微笑、点头等和学生进行互动,鼓励她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辅导员只需要把学生释放出来的信息稍加归纳就能知道,大部分的宿舍矛盾都是由于寝室成员间缺乏沟通、不能相互体谅造成的。一般情况下,趁寝室矛盾还没有激化,辅导员沟通较为及时,当事人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心情平复后,事情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只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才可以共情,而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体会如果是自己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会如何处理。还可以主动与学生分享,自己在学习、工作中遇到类似矛盾时心理的变化过程,以及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是如何一步步解决问题的,甚至可以和学生一起剖析当时自己的处理方法存在哪些不足,现在再遇到那样的情况会怎么做。从认真倾听学生的叙述到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会无形中走近学生的内心,让学生知道不是只有自己会陷入困境,重要的是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
倾诉和感化。笔者任职的高校是一所民办大学,基于民办应用型大学和本校学生的特性,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更多倾向于制度管理、半封闭式管理。出于安全考虑,学校有一系列的条条框框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宿舍楼晚上查寝就是其中一项。根据学生手册规定,迟归(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宿舍)、夜不归宿(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回宿舍)、代查寝(学生利用宿舍管理员查寝的时间差给非本宿舍的学生代答到)等情况都是违反宿舍管理规定的。上级部门为了加强管理,会将学生违反规定的数据与辅导员所在学院和辅导员个人年终考核挂钩。如此,辅导员戏称每天晚上的22:00-22:30就是“黑暗半小时”,这半小时是宿舍查寝时间,宿舍管理员发现问题就会与辅导员联系,辅导员则需要立刻联系学生确认其是否安全。当然,事情并不是到确认学生是安全的就结束了,第二天还会面临被上级部门通报批评。
对于宿舍查寝,每一位辅导员都会格外强调,但效果并不理想。笔者曾在同一个晚上连续接到5个学生夜不归宿的电话,当时非常激动,立刻联系5名同学的父母,告知其子女在校期间不遵守校纪校规的恶劣行为,要给予通报批评处分,还叮嘱父母一定要好好教育子女,做好学生的本分。过了将近半小时,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反省刚才的行为很是后悔。思考很久后,决定写一篇QQ日志,将自己的不理解、心中的愤懑、打电话给学生家长的目的、对学生寄予的期望、希望得到的回应等等都表达出来。欣慰的是,日志被查看750次,76人点赞,27人评论,第二天5名同学分别来找我表达了歉意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会犯相同的错误。
其实,笔者写这篇QQ日志,一方面是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另一方面是在公众平台上示弱,表达辅导员的工作也是需要被理解、被支持的,辅导员和学生共悲喜、共荣辱。通过分别与5名夜不归宿同学交谈,得知3名同学是抱着侥幸心理不会被宿舍管理员查到;1名同学是在实习单位加班没有来得及请假;1名同学是怕得不到批准不敢请假。得知真实原因后,笔者在交谈时透露出:“作为一个近300名同学的辅导员所要肩负的巨大压力和责任,这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没有用的,需要每一位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共情,体会辅导员工作的不易,从而认识到违反校纪校规带来的后果不是个人可以承担的,进而自发约束自己的行为。
适度和引导。目前国家资助体系日趋完善,学生申请受资助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如生源地贷款、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励志奖学金、省精准扶贫家庭学费减免、家庭困难学生医保费减免、家庭困难学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等等。申请这些资助项目的前提,是通过每年一次的困难学生家庭情况认定。那么,如何进行贫困认定,贫困认定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都需要辅导员把关。为了让更多困难家庭同学受到资助,贫困认定需要提交的材料越来越少,由以前需要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盖章证明到现在只需要学生写一份家庭情况说明和承诺书。难免有缺乏诚信意识的非困难同学也提交材料,这无疑增加了认定工作的难度。德育作为国家资助体系的补充,要求辅导员在进行资助工作的同时,不忘育人。每年贫困认定等级由辅导员、班长、团支书、生活委员和2名学生代表组成的贫困认定小组完成。为了解申请贫困认定学生的详细情况,在审查材料的同时,笔者会分别与申请人交谈,这便是“育人”的最佳时机。
当然,交谈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一上来就问:“你们家年收入多少”、“爸妈在外打工还是在家务农”“你看起来不像贫困生啊”等过于直接的问题,家庭困难的学生往往内心比较敏感,涉及到家庭情况问题时容易有抵触情绪。这就需要辅导员实施共情,从关心学生着手:“最近学习生活都还顺利吗”、“爸妈身体怎么样?工作忙吗”、“今年家里有什么突发情况吗”,通过聊家常的形式获得需要的信息。当然,资助工作中实施共情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不能让学生认为要在辅导员面前“哭惨”“比惨”才能获得资助,否则会无形中加大贫困学生的心理压力。这便是育人的第一层含义,帮助受资助的困难同学克服心理障碍、做好心理建设,安心完成学业。
育人的第二层含义是向同学传达资助工作的原则,资的是真正困难家庭同学,助的是确实需要帮扶的对象。有的同学在第一学年获得很多种资助,到第二学年会认为去年获得的资助今年应该顺利成章的也获得,如果没有获得便会心理不平衡,甚至认为资助工作不公平。这就需要我们在宣传资助政策时注意引导同学,教育资助发挥的是“雪中送炭”的作用,不能对教育资助产生依赖心理,更不能认为哪一位同学获得资助是理所应当的。
共情在高校辅导员“一日常规”工作中的合理应用,有利于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有利于增强学生换位思考的能力,培养具有共情能力的大学生;有利于减轻辅导员事务性工作的压力,探索思政工作新模式。成功运用共情理论的案例有很多,需要辅导员内化于行,逐步提升自身的共情能力,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合理运用,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