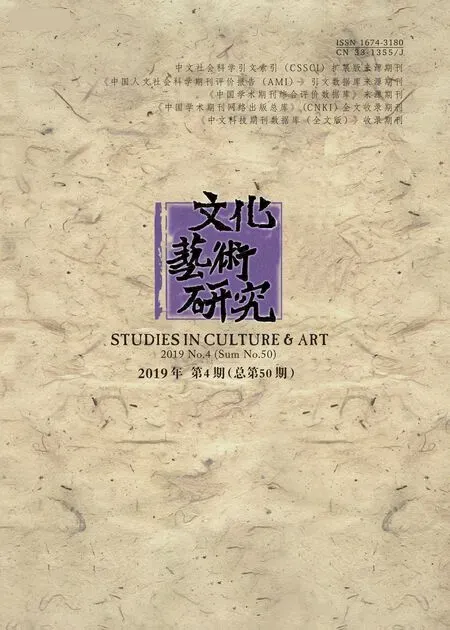春深劝农焕烟霞
——论《牡丹亭·劝农》中的意趣
王 翼
(广西科技大学,广西柳州 545006)
《劝农》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第八出戏。正如田晓菲在《“田”与“园”的张力:关于〈牡丹亭·劝农〉》开头说的那样:“它从来不是戏曲批评家以及《牡丹亭》爱好者的主要注意力所在。”[1]27历来《牡丹亭》的爱好者都沉迷在柳杜二人浪漫荒诞的爱情中,对这出夹在《闺塾》和《肃苑》(常同《惊梦》并作一折演出)之间,和主线剧情无关的“热闹戏”,不是无暇顾及就是不屑一顾。甚至在许多方面和汤显祖甚有戚戚之感的王思任(1575—1646)也曾在点评中下过论断:“不为游花过峡,则此出庸板可删。”[2]实际上,同时代乃至后代的《牡丹亭》改本、演出本大多删去了《劝农》这出戏,比如冯梦龙的《风流梦》、当代白先勇排的青春版《牡丹亭》。
汤显祖对这样的做法会认同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汤显祖在《与宜伶罗章二》中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3]53从汤显祖的评论来看,“增减一二字”都与“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更遑论占据了整整一出戏份的《劝农》?只怕汤老先生越发要失笑“总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4]了。田晓菲总结过现代学者对《劝农》一折的看法:“把它视为剧作家对杜宝这一人物的正面处理,使杜宝的形象立体化,并且多多少少反映了剧作家本人的政治理想。”[1]29这些固然都有可能是汤显祖不惜笔墨创作这出戏的原因,但是杜宝的形象在《牡丹亭》的后半部分还有着充分的塑造,作者的“政治理想”又何必不合时宜地横插在柳杜二人的感情主线之中?《劝农》究竟在《牡丹亭》里发挥着什么作用,汤显祖原作的“意趣”究竟又在何处呢?
一、《牡丹亭·劝农》的自身魅力
令人惊讶的是,被文人视作“庸板可删”的过场戏《劝农》,却曾是《牡丹亭》被搬演最频繁的折子戏之一,“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喜庆宴会场合,《劝农》几乎不可或缺”[1]27。在清宫《升平署曲目》记载中,有《劝农》曲本5册,每年三月初一均要演出“以应节令”,或作为开场的吉祥戏。[3]336—337文人阶层的批评和世俗阶层的热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一方面,这叫人佩服汤显祖独到的眼光和笔力:既能写出士大夫阶层为之击节叹赏的《惊梦》《寻梦》,也能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劝农》,在一部作品中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来自不同世界的声音;另一方面,作为折子戏的《劝农》,在众多的节令戏、吉祥戏里脱颖而出,必然有其魅力和道理所在。
(一)《劝农》藏风雅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劝农》问世以前,戏曲舞台上还有过其他版本的“劝农”戏:《五伦全备忠孝记》第十七出《问民疾苦》,《赵氏孤儿记》第八出《赵盾劝农》,以及据此改编的《八义记》第八出《宣子劝农》。[1]43但这些“劝农”戏都没有像《牡丹亭》里的《劝农》那样,单单作为一出折子戏风行一时。究其原因,恐怕和汤显祖在《劝农》中匠心独运的构思、通俗而不鄙陋的科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翻阅之前的几版“劝农”,虽然戏中也不乏插科打诨制造笑料,但它的舞台表演形式十分单一。基本采用了老爷和农夫们的二元对话体。不是老爷对农夫们灌输务农如何好,宣读教民榜文(《问民疾苦》),就是农夫们自述务农怎样快活,甚至念了长长一段顺口溜似的“村居乐”以证明务农的好处(《宣子劝农》)。不论哪种对话模式,都伴随着一种刻板的说教气氛。
《牡丹亭》的《劝农》却有着更加活泼的风貌,汤显祖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一个古老的形式描写官民之间的交流:观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方式在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5]131《汉书·艺文志》云:“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中国传统的看法中,诗歌被认为是心底流淌出来的语言,最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感情。而“感情之愈近于纯粹而很少杂有特殊个人利害打算关系在内的,这便愈近于感情的‘原型’,便愈能表达共同人性的某一方面,因而其本身也有其社会的共同性”[7]。上古的政治思想认为想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如何,最好的方法就是倾听当地百姓们所唱的歌谣,因为它能体现出百姓生活的真实风貌。《礼记·王制》有“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说法。采诗观风的政治制度自周代后逐渐衰微,汉代仍有乐府制度,但其所产生的政治作用已难以与前代相提并论。汤显祖在自己的作品里复原了一些上古政治的遗风(或者说是他心里的理想政治方式),在这里,村民们是淳朴的,他们无心地吟唱着各种村歌。杜宝作为一方太守,在乡间查看农事时有意倾听这些村歌,又适时地进行评点,潜移默化地教化百姓,最后花酒相赐,皆大欢喜。把观风这种形式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得舞台上的演出更为活泼,田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依次登台唱一支村歌,载歌载舞的画面大大丰富了原先两个群体间一问一答的呆板样式;村民们唱的歌词也深得风雅之趣,如“泥滑喇,脚支沙,短耙长犁滑律的拿”[8]41、“乘谷雨,采新茶,一旗半枪金缕芽”[8]42之类,不正是《诗经》“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豳风·七月》)[5]388、“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衤颉之”(《周南·芣苢》)[5]281千年后的回声吗?马一浮先生说:“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缘感而发,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言之粗妙。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亦尽有得《风》、《雅》之遗意者,又何人不可学邪?”[9]
(二)风雅有教化
在《“田”与“园”之间的张力:关于〈牡丹亭·劝农〉》一文中,田晓菲将《劝农》的魅力归结为其自身潜在的喜剧因素。例如农夫上场之后:
[孝白歌](净扮田夫上)泥滑喇,脚支沙,短耙长犁滑律的拿。夜雨撒菰麻,天晴出粪渣,香风合奄鲊。(外)歌的好。“夜雨撒菰麻,天晴出粪渣,香风合奄鲊”,是说那粪臭。父老呵,他却不知这粪是香的。有诗为证:“焚香列鼎奉君王,馔玉炊金饱即妨。直到饥时闻饭过,龙涎不及粪渣香。”与他插花赏酒。(净插花赏酒,笑介)好老爷,好酒。(合)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把农夫们俊煞。(下)[8]41—42
田晓菲认为“大多数人,除了《吕氏春秋》里面的海上逐臭者之外,都会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知道’龙涎香才是香的,粪渣才是臭的,哪怕饥饿的时候,也绝无认为粪渣好闻的道理。杜宝的论断,就像‘有史为证’的套话所显示的那样,代表了一种来源于诗歌,来源于书本,更来源于主观意识形态的‘知识’与‘证据’,排除了感官的体会,与实际生活经验背道而驰……可以说杜宝这一论断实现当可笑的……谁又能肯定,扮演农夫的演员,或者台下的观众——不是宫廷里的观众,而是乡下过节看戏的百姓——没有在此对‘好老爷!’发出揶揄的笑呢?”[1]51—52
事实上,综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我们会发现汤显祖无意在这里制造任何的“笑料”。杜宝说的“有诗为证……”绝不是什么喜剧用意。如果呆板地认为普通百姓从生活经验出发,知道龙涎香香于粪渣,是否也能推理出老百姓未必知道龙涎香更香,因为他们可能从未有机会嗅过龙涎香。
“焚香列鼎奉君王,馔玉炊金饱即妨。直到饥时闻饭过,龙涎不及粪渣香。”的确,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龙涎香是香的,粪渣是臭的,“哪怕饥饿的时候,也绝无认为粪渣好闻的道理”。然而,一个人到了真正饥饿的时候,即使龙涎香再香气扑人,也绝不会为了一堆龙涎香而舍弃一碗冷米饭。说到底,这并不是粪渣和龙涎香谁更香的问题,汤显祖通过杜宝之口提醒大众:人生究竟以何为根本?古往今来的经典作品都在讲述同一个道理,比如贾宝玉在馔玉炊金之时,连袭人家过年桌上摆的东西都“总无可吃之物”,那时的他,自然觉得龙涎不及粪渣香是笑话。待到“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之后,恐怕才会明白,人生日日有米饭数碗足矣,何必百事不知足,为名利昼夜营谋以致亡败呢?当然这样的道理,“乡下过节看戏的百姓”是未必听得懂的(只是“未必”,因为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终身以务农为业,不愿为官之人),汤显祖也不尽是说给“乡下过节看戏的百姓”的。事实上,乡下的百姓大概很少有人听得懂这首诗——尽管这诗已经很通俗了,且真看戏的时候眼睛和耳朵都被表演和音乐吸引去了,其实很难有心情去“听”什么。上文已经说过,《牡丹亭》不仅在民间,也在文人阶层广受欢迎,《劝农》更曾是宫廷贵族钟爱的折子戏,这种以农为本、不要舍本逐末的教导,对于上层社会的人似乎更具教育意义。清末庚子事变,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颠沛流离,衣食无着之时,大概真的有“直到饥时闻饭过,龙涎不及粪渣香”之叹了。汤显祖在此有意借南安太守杜宝之口,完成他教化大众、移风易俗、点醒世人的心愿。如晚清人评《牡丹亭》说:“贤人君子不得志于时者,思为移风易俗之助,往往作为曲本,以传播民间。”[3]102
同样地,我们再看牧童上场那一段:
(门子禀介)一个小厮唱的来也。
[前腔](丑扮牧童拿笛上)春鞭打,笛儿唦,倒牛背斜阳闪暮鸦。(笛指门子介)他一样小腰扌叚,一般双髻髟查,能骑大马。(外)歌的好。怎生指着门子唱“一样小腰扌叚,一般双髻髟查,能骑大马”?父老,他怎知骑牛的到稳。有诗为证:“常羡人间万户侯,只知骑马胜骑牛。今朝马上看山色,争似骑牛得自由。”赏他酒,插花去。(丑插花饮酒介)(合)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村童们俊煞。(下)[8]42
所有的圣贤都劝人不要贪着名利,但是“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司马迁也感叹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同‘攘攘’)皆为利往”。即使是“清乐乡”的小牧童,看见有人骑高头大马仍旧会发问:为什么他骑马,我只能骑牛呢?对此,杜宝也回答得很妙:“常羡人间万户侯,只知骑马胜骑牛。今朝马上看山色,争似骑牛得自由。”颇有几分像《史记》所载秦相李斯的结局:“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10]可惜世人一般都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田晓菲说这些“宣传未免找错了对象,……对那些父老乡亲和牛背上的牧童来说,恐怕只能是‘只知骑马胜骑牛’。”[1]53这说的固然有理,但也太绝对了一些,按照中国传统,乡野山村从来是隐士高人的栖身之地。即便是对乡人的“宣传”,也未必错了对象。因为这不是哄骗小儿之言,而是人生的大道理。现在听进去了,日后总有醒悟的一天。否则至死不悔,临终之际还惦念着级别、职位、头衔不肯瞑目者大有人在。有几人能在握权之后有杜宝这样的胸襟,又有几人在临死之际能像李斯一样自我反省。
这样恬淡自然的生活,与其说是中国文人理想化的田园生活,不如说是中国文人追求的田园生活。据史书记载,汤显祖确实在遂昌实践过自己的政治理想,到任后即拜谒孔庙,走访士子,兴建书院和射堂,创建“尊经阁”,重建启明楼,振兴教化;更亲自下乡班春劝农,奖励农桑。因此使得遂昌呈现了“琴歌积雪讼庭闲”“市上无暄少斗鸡”的升平景象,他也自诩为“仙令”。a经过汤显祖几年德刑兼施,遂昌赋成讼稀,社会安宁,百姓和乐。见参考文献[11]。[11]在《劝农》中,汤显祖还借机“透露”了实现如此清平政治的方法:杜宝到清乐乡后,询问村民们是否有“无头官事,误了你好生涯”?村民们回答:
(生、末)以前昼有公差,夜有盗警。老爷到后呵,
[前腔]千村转岁华。愚父老香盆,儿童竹马。阳春有脚,经过百姓人家。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真个,村村雨露桑麻。[8]41
“以前昼有公差,夜有盗警”,公差和盗警并不是坏人,而是公人。以前昼有公差,夜有盗警,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正是官府作为、治安保障好的体现之一。但是在“清乐乡”父老的眼里,这却是社会不太平的表现。原因很简单,有公差和盗警正说明白日村民间有纷争或交不上税,晚上还有小偷和强盗。而杜宝到后,并未加派人手解决这些问题,公差和盗警反而不见了,因为村里“雨过耕绿野”“雨露桑麻”,户户家给人足,纷争和偷盗就自然消失了。在传统治国思想中,最次一等是以法治国,其次是以礼治国,最高境界是道家强调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把问题化解了,表面看自然也就无须人来作为了。
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安排一个“清乐乡”,又安排一场“劝农”,确实大有深意。劝的不仅是戏里的农民务农,更劝的是戏外的观众“务本”。一个人反观自身,向内追寻,才会真正带来内心的宁静与祥和,一个地区、国家的政治也只有做到自身的清明,才抵得住外来的忧患。这场戏中,唯一用来打趣的是两个公人,他们与清乐乡乡民相对,代表了桃花源以外的世俗世界:
[普贤歌](丑、老旦扮公人,扛酒提花上)俺天生的快手贼无过。衙舍里消消没的睃,扛酒去前坡。(做跌介)几乎破了哥,摔破了花花你赖不的我。(生、末)列位袛候哥到来。(老旦、丑)便是这酒埕子漏了,则怕酒少,烦老官儿遮盖些。(生、末)不妨。且抬过一边,村务里嗑酒去。(老旦、丑下)[8]40—41
公人上场便自夸能干,“天生的快手贼无过”,一下就从衙门扛酒到了前坡。然而话音未落,“能干”的两人就把酒坛打破了。结果第一反应就是“摔破了花花你赖不的我”。善于夸耀自己和推卸责任,正是世俗社会“智巧”的体现,其结果只能是争吵甚至争斗。天真纯朴的清乐乡村民则把事情揽过来说不妨,还请去村里喝酒,化干戈于无形。两相对照,读者当昭然自明。
一段短短的“劝农”表演,不仅用了观风雅的形式,又唱出了包涵“风雅”趣味的乡里歌谣,更将作者为国为民的教化深意融入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戏外观众,可谓深得“风化”本意了。
二、《劝农》在《牡丹亭》结构中的作用
“吴吴山三妇合评本”中有“劝农公出,止为小姐放心游园之地”一说,这也是最普遍的对《劝农》结构作用的看法。但是对于注重剧情紧凑的戏剧而言,这些完全可化为《肃苑》里春香的一句话——“老爷下乡,有几日了”,以了结此事。清代众多戏曲和曲谱选集,除《学堂》《游园》《惊梦》这几出必选之外,唯一恒定不变的就是《劝农》。[1]28—29既然汤显祖将其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来,除去本身形式引人入胜,必定还有其他不可忽略的作用。
(一)“天下随时”的深意
在古代社会,传奇一贯被视作“小道”,但是明清传奇作者却不轻视自己的工作。如孔尚任就在《桃花扇小引》里写道:“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12]使传奇上接春秋,下合词赋,进入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体系中。汤显祖显然也把创作传奇看作自己的千秋事业,当有人问他:“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讲学?”汤曰:“此正吾讲学……”[3]42因此,中国杰出的传奇剧作家们都有着更为博大的胸襟和野心——他们期望借传奇燃千圣之心灯,以“小道”起到启发民智、劝化民众的作用,所谓“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13]1。通俗地说,就是把经典中的道理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牡丹亭》重新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只是整本《牡丹亭》里的一条主要线索,围绕着这条引人入胜的线索,汤显祖把握住一切机会扩充这部传奇的视角。
“劝农”一事并不是汤显祖的发明,中华文明以农耕为本,农业生产对社会安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奖励农桑。早在先秦典籍中就不乏类似的记载。农业也是和大自然联系得最紧密的产业,因此,中国文化中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时”。《尚书·尧典》的开篇首先就记载了尧帝“敬天授时”的过程。《周易》尤其强调“时”的观念,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系辞上》)[5]82,“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彖》)[5]34。其“易”的变易之义,正是建立在“随时”的基础上。质朴的农业社会形态,使得人们天然地对“时机”有着更加细腻的感受和认识,“同自然界的不可抗拒的四季时令一样,人生社会及精神领域同样存在这样不可抗拒的‘时’和‘时令’,人类同样要遵循和顺应这个结构变化的规律”[13]307。
《礼记·月令》也反映了这个思想,描绘了人与自然是怎样相偕而动的。初春时节,“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14]1356—1357等到孟夏之月,景象又是不同。如果春季行了夏、秋、冬的节令,都会带了灾难性的后果。《孟子·公孙丑》里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中国古典文学,几乎都对“时”有着高度的敏感。回到《牡丹亭》,杜丽娘上场的第一句唱词就是“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随着春天的到来,青春也开始在这个十六岁的姑娘身上逐渐苏醒。当然,此时的杜丽娘还是懵懂的,只是应了《礼记·月令》所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活在天地间的人,又如何能逃离“时至”的力量。然而,遍读圣贤经书的杜宝却不能通达经书中的道理,他听春香说小姐在绣阁“打绵”(春困)后大怒,觉得女儿疏于管教,于是为杜丽娘请来了只会照本宣科的陈最良教授《诗经》。讽刺的是,《诗经》首篇也是一幅“春时”之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真是“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物色相召,人谁获安”[15]?经过经书的启蒙,杜丽娘一下由朦胧的情愫转为希冀早谐佳偶的春思。如果说这些表明春时给人以巨大影响的文辞太过典雅,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丫鬟春香伺机大闹学堂后,更直接而又具喜剧意味的戏份开演了:《劝农》。《劝农》一开头,就由皂隶、门子们点出了时令:“[古调笑]时节时节,过了春三二月。”[8]40杜宝作为地方太守,深知时值万物生长的好季节,因此到乡间劝课农桑。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时来”和自己的女儿有什么关系。他游览乡间春色,也受到了自然的感染而唱道:“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畴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儿叉。雨过炊烟一缕斜。……[八声甘州]平原麦洒,翠波摇翦翦,绿畴如画。如酥嫩雨,绕塍春色䖃苴。趁江南土疏田脉佳。”[8]41但却始终不曾觉得春天对杜丽娘有着何等影响。虽然杜宝刻意地阻断一切可能勾起女儿“春思”的途径,但是春时的来临是平等的,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当穿红着绿的采桑采茶妇女拥到舞台前欢乐地唱起劳作的歌谣,享受着“时节时节”所带来的新一轮忙碌的生活时,杜丽娘却在太守府“立小庭深院”,踌躇着“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哀叹落红成片,“辜负了春三二月天”,反而成了一幅更为动人的春至之景。
可惜剧中的杜宝并未从农夫农妇处体悟到“时”的深义。《周礼》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5]733以诗礼传家的他忘了《国风》那首《摽有梅》里清婉的劝诫,“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5]291。不顾夫人的提醒和实际情况,在杜丽娘病重之际,他仍牢牢守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古训,认为“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不能随时变易,以致嫁娶失时,杜丽娘最后恹恹而终。《劝农》作为一道亮丽的舞台风景,提醒着戏里戏外的人们“与时偕行”的重要性。如果少了《劝农》这笔,我们的目光就只局限在南安府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无法把发生在杜丽娘身上的故事和整个自然联系起来,也就无法领悟中国古典哲学里“天人合一”的深刻含义。
(二)演出形式的多样化
值得注意的是,《劝农》的前后两出戏《闺塾》《肃苑》都是以贴旦(春香)为主的戏,先不论演员是否能保持好状态接连演出两场贴旦的重头戏,单从看戏的角度而言,观众的阶层不同,口味也各异,两场贴旦戏串在一起——即小贴旦有多么的活泼可爱,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劝农》里上场的人物众多:外、净、生、末、丑、贴、老旦悉数登场,扮演了皂隶、公人、太守、农夫、牧童、采桑女、采茶女等角色。可以想象,有限的舞台上这么多的演员插科打诨,这是多么热闹又吸引人眼球的一出戏,一洗前后纤弱的深闺景象。须知,不是每个人都欣赏“私定终身后花园”这样文绉绉的戏,鲁迅先生就曾在《社戏》里坦言,他儿时“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16]。作为一个优秀的剧作家,必须要做到让自己的作品更富包容性,作品排演出来后可以面向不同层面的观众,让他们坐下来看完它,从而接受它。
作为《学堂》(即《闺塾》)和《游园》之间的过渡,《劝农》这出“游花过峡”的戏非常出色,成功调节了上下两出戏雷同的舞台气氛,使整本《牡丹亭》为之生色。
结 语
如果说“《左传》所记春秋外交间诸侯交接往来中的赋诗活动,其实质就是大型的艺术表演”[14]202,那么《劝农》也可以说是一场富有淳朴乡土气息的小型观诗集会。在杜宝与村民亦说亦唱的诗意对话中,观者的情绪也一下从前后出戏杜丽娘的春思惆怅中得到了调剂——这也许就是诗歌“起兴”的魔力。在《牡丹亭》诞生后的一两百年间,这出戏不断上演,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伴随着戏里营造的其乐融融的气氛,词曲间所传递出的哲学思想也自然了无痕迹地传递给了观者,使身在荣华或志在富贵的人们能够看到生命本真的一面,对平静的田园生活产生憧憬和向往,减少一些人事上的心机算计,在心灵上有所寄托和回归。事实上,“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情节的新奇曲折以及结构的变化更新等方面的叙事法则,戏曲批评相对来说较少关注,或探讨得并不充分”[17],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劝农》总是被排挤在《牡丹亭》舞台表演甚至学术研究之外。如果删去了《劝农》,《牡丹亭》就失去了它的另一面,变得单一且单薄。作者“欲擒故纵”的叙事手法得不到充分体现,我们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评说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深刻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