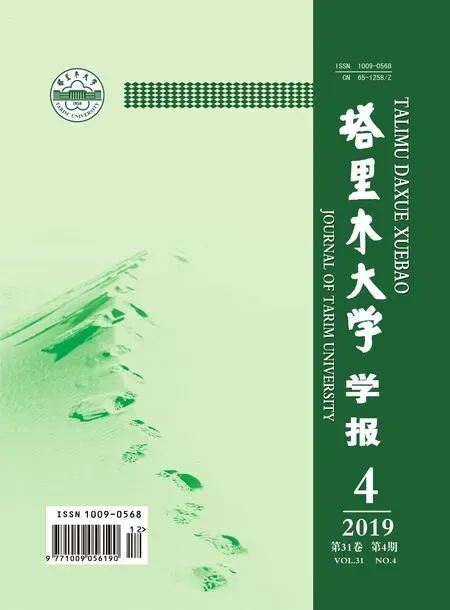“用胡杨精神育人”的德性伦理教育探析
龙 容 肖 涛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
“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战线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分析“用胡杨精神育人”的深刻内涵,乃是在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
“用胡杨精神育人”是一个带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蕴含着“胡杨精神”和“育人”两个方面的意义。胡杨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如何通过教育得以传承和发扬?在价值多元、利益幸福观和享乐幸福观盛行的当下,引导公民选择自我奉献、艰苦奋斗等纯洁高尚价值观、道德观是否可能?本文从德性伦理视角对“用胡杨精神育人”进行探讨,以期加强我们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认识。
1 胡杨精神的内涵阐述
1.1 胡杨的自然属性
胡杨是新疆最古老的树种之一,被誉为沙漠脊梁。新疆库车千佛洞、甘肃敦煌铁匠沟、山西平隆等地,都曾发现胡杨化石,证明它是第三纪残遗植物,距今已有6500 万年以上的历史。在《后汉书·西域传》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着塔里木盆地有胡桐(即胡杨),塔里木盆地的胡杨林由复杂的动态演替系列所组成,在历史上伴随着河流的迁移而迁移,胡杨能在因水断流的故河床上生长,因此林地面积也随着扩大。[1]
胡杨树能在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对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千百年来扎根于沙漠腹地,与风沙、烈日、寒霜进行着顽强抗争。一旦缺水,胡杨会使地面上的树枝枯死,让地下的根继续维持生命。一些看上去失去了生命的胡杨,只要遇见水源,还会重新抽出新芽。胡杨根植荒漠,为大漠提供了最为壮观的植被景观,同时默默地为人们提供优良的建筑木材,为牛羊提供嫩枝和树叶。若将胡杨树干锯断,流出的液体很快变成胡杨碱,可以用来制作肥皂等生活用品。由此可见,胡杨树不仅具有令人叹服的顽强生命力,而且也有不小的经济价值。
1.2 胡杨自然属性的意义延伸
胡杨坚韧的生长特征和顽强的生命力在被人们研究和歌颂的同时,亦备受文艺界创作者们的喜爱。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到,在远古的西域文明中有许多关于胡杨的文字记载,赞美大漠胡杨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现当代文学中同样不乏对胡杨的礼赞。“胡杨”以一种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懈奋斗、与无情的命运作斗争等形象出现在各类文艺作品当中。这些作品或是对胡杨本身的赞美,或是以物比人,通过胡杨赞美人的品格,如:1984 年张鸿铎写了《荒漠林佳话》;1986 年巴彦淖尔报社记者杨厚杰写作《一棵老胡杨》以赞美林场工程师李进富;同年,舒宗范作诗《致新疆胡杨(外一首)》歌颂胡杨的高贵品格;1987 年许秀江撰文《胡杨——顽强的荒漠树种》;而童庆炳更是引用胡杨来悼念一位逝去的可歌可泣的人物;1995 年,刘惠生的《胡杨颂》、祁云川的《沙漠卫士——胡杨》、刘中汉的《沙漠骄子——胡杨》均从不同的角度称颂胡杨的品质;2009 年,曾长江写下《胡月皎皎照流金羌笛悠悠鸣新音——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堃》;2015 年张大辉用胡杨赞美一位检察官:《大漠胡杨——记新疆喀什检察分院检察官阿布来提·铁米尔》等等。
在以上的一些作品中,作者或者研究者会将具有吃苦耐劳、默默奉献、顽强生存、扎根边疆等品质的人以比喻的形式与胡杨树进行关联,以树的特性指代人的品格,将有以上特性的人格提炼为以胡杨品质为代表的一种精神。如今,胡杨不仅仅以单纯的树木形象存在于世,更展现了一种具有西域特色的生态文化,沉淀为自强不息、默默奉献的精神品质。“胡杨文化”、“胡杨精神”正是在古往今来的这些作品或人际传唱的故事中逐渐沉淀、清晰,从而形成其独特的顽强、奉献的文化风貌和文明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胡杨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胡杨精神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胡杨精神中所蕴含的艰苦奋斗、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充分体现了追求责任、自律、奉献、刚毅、勇敢、仁爱、利他、集体主义等中国品质,这些德目无一不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
人是群体性动物,在所属环境中寻求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是人的天然属性。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某些人物、事件产生独特的情感认同,进而转化为对某种精神的秉持。中国自古流传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均是由群体价值观念的长期积淀而成。从一棵普通的“胡杨树”中凝练出一种精神,并将此精神延续、传承,同样蕴含着这样一种价值沉淀机制。
2 “用胡杨精神育人”之品格教育的哲学基础:德性伦理
人们赞美胡杨,不仅因为其风姿,更因为胡杨的生命力中蕴含的“艰苦奋斗、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等品格,它包含着一系列中西方的传统道德观。要从德性伦理角度探析胡杨精神和胡杨品质的传承,就会有这样两个绕不开的问题:德性是否是可教的?德性将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
2.1 德性是否可教
德性即人的“道德品性”。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便被提出。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即知识”。他和柏拉图认为,作为知识的德性是可教的,德行的知识是不朽的灵魂里固有的,凭回忆可以得到,毋需他人教导。哲学家的任务不是教人传授德性知识,而是将人灵魂中固有的德性知识“接生”出来。[2]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上述观点与中国儒学的性善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子言有教无类,贩夫走卒皆可束发受教。孟子言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四心乃仁义礼智之端,是人所固有,随时而发现,无待于习。“仁义是人之良知良能,乃不待学不待虑的;一切道德,皆出于人之性。”[3]儒家依据人的教化理论,主张通过求知而完善自己,个人严于律己,正视错误而后能公开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就是达到圣人之境的途径,《论语》中子贡曾提出:“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食焉。过也, 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4]程颐亦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5]不难看出,在儒家传统中,人人皆可以为“圣”,孟子的“四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中逐渐显现。但这个过程,是需要人们倾注无尽的摸索与思考,不断进行修正才能得以实现的。
顺着中西方的思想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关于什么是自律、责任、刚毅、勇敢、仁爱等知识性德性是可教的。胡杨精神中所蕴含的这些德目可以在知识传授或榜样教育的过程中,使受教育者获得对于美德的认知,获得对于世间万事是与非的衡量标准,这是需要教育来完成的。因此后天的培育对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理型世界”里先天拥有一种完美的德性,现实世界里的德性从理型世界里的完美道德抽离出来分散在个体身上,人们可以通过追求和探索获得理型世界里的完整的德性。儒家则认为人出生时心境都是相同的,是顺天应命且合乎德性的,而后天的客观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产生了影响,如“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6]德性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但人们在后天的实践中会显露哪部分的德性,则要归因于后天的教育环境。环境对一个人性情的养成起着制约作用,人所在的环境对善性有遮蔽或充阔的影响,通过后天引导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人们才得以形成最终的善或恶的习性。
2.2 德性如何施教
在当代的教育实践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知晓美德之人不贯彻美德。即便懂得何为美德之人不一定遵从美德,就比如,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善良,但行使善良的人在现实里却不一定会被善待,久而久之便不行善。
卡尔(David Carr)等一些品格教育家,基于现代人本主义和德性伦理的立场,认为德性教育通过发展品格和改善人际关系,帮助人们思索和追求有价值、体面、圆满的“好生活”,特别是要让年轻人懂得基于人类的一些积极、正面的价值、原则或品质,诸如诚实、公平、友爱、自我克制等而生活,比之于不诚实、放纵、偏见、自私自利等而生活,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7]因此,在“以胡杨精神育人”的教育实践中,德性还需行使这样一个教育功能:在践行美德的过程中,用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涵养学生潜意识里的道德品质,使学生通过受教育将胡杨精神所包涵的文明、奉献、坚韧、自强等品质根植于心。这也就解决了知晓美德之人不贯彻美德的矛盾,因为这样的德性涵养教育的最高追求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美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胡杨精神中所蕴含的自律、责任、刚毅、勇敢、仁爱、利他的德目可以在知识传授或榜样教育的过程中,使得受教育者获得人性本身的觉醒。
价值观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8]。“用胡杨精神育人”承担着帮助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教育责任。价值观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把艰苦奋斗、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等价值观的要求变成学生们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一般通过系统的教育才能得以实现。
3 “用胡杨精神育人”中存在德性伦理教育的可能性
3. 1 “用胡杨精神育人”依托德性伦理教育的涵化效果
人的普遍异化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教育提出了一个富有时代性而又艰巨的任务:关注品性的指引与涵养,关注实践理性和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使受教育者在一个情感舒畅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中领会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胡杨精神”蕴含着一系列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重要德目,这些德目可以通过知识或者道德实践进行传递。在“用胡杨精神育人”的教育体系中,德性伦理的教育占有绝对的比重。在胡杨精神教育过程中,不是通过将胡杨精神的德目变成学生不得不恪守的原则规范,而是以培养人的道德意识、奉献意识为目标,将奉献、正义、刚毅、勇敢、仁爱、利他、自律等德目内化为个人的高尚情操。胡杨精神不是规范化、模式化的行为框架,而应更多地具有自在的道德特征。
就如60年来坚持“以胡杨精神育人”的塔里木大学,其名称几经改易,但胡杨精神一直未变,兴疆固边的初心和宏愿也一直未变,始终传承南泥湾优良传统,发扬“抗大”作风,以国家利益为至高利益,忠诚履行屯垦戍边职责使命,形成了“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励志图强”的优良校风,培育出以“艰苦奋斗、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为主要内涵的胡杨精神,明确了“做塔里木文章、创区域性优势、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思路,形成了“环塔里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研究特色,彰显了“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的鲜明办学特色。这就是“以胡杨精神育人”教育模式中依托德性伦理教育的典型——抛却法典性的规范,不是规范守则的明文强制,而是以典型事迹和言传身教将胡杨精神代代相传。胡杨精神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在自己的意识里形成一套随时遵循的行为守则,而非外界的强制法令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做。通过胡杨精神典型、先进人物进行榜样教育,用前辈的事迹潜移默化地涵养学生的品格,使其在自己的思想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比简单的条文灌输和理论背诵更加深刻,把对“胡杨精神”的教育提炼为一种常态教育模式,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德性伦理学批评道义论和结果主义等的伦理学依赖于期望应用于所有情境的规则和原则。批判的视角就在于这些规则和原则是模式化的,不能适应所有道德情境。正如学者江畅所言,如果问题是变化的,我们就不能期望在一种不允许有例外的刚性和固定的规则中找到他们的解决办法。德性伦理不能被囊括在一种规则或原则中,这就是“伦理学论题的不可法典性”。[9]
3.2 德性伦理的“目的价值”贯穿胡杨精神育人宗旨
为什么要倡导“胡杨精神”?德性是目的价值还是工具价值?或者说人们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主动追求德性还是为了德性本身而追求德性?如果说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那么德性是幸福的一部分还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这即是德性的“目的”问题,也正是“用胡杨精神育人”的宗旨问题。
当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战胜了生活中的种种关于陋习的诱惑如懒惰、自私,履行了一定程度的无私义务时,通常会在内心产生平静和充实之感,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幸福。这其中德性就是关于克服惰性、自私等恶习的报酬。于是幸福论者就说,这种极乐、这种幸福就是他为什么要合乎道德地行动的真正原因。不是某种规则或法律上的义务概念直接规定他的意志,而是仅仅借助预期的幸福,他才被推动去履行自己的义务。
因此,在“幸福的义务性”中就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循环论证。当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克服奢逸、惰性、欲望等充满诱惑的条目而获得道德值的增长,那么在他认识到这能使他幸福之前,他必须先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是一个人的意志认识到自己在践行德性义务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幸福感,而不是因为想到这能使他幸福才去践行义务之事。这就意味着这必须是一个人自发的道德感,这样才足以证明德性在一个人心中的根植程度。但矛盾的是,人们最初正是带着获得幸福的期望才竭力去学习、领悟关于履行义务的德性。
康德在他的幸福观里提出了消解这种矛盾的方式——设立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目的”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概念,是行为主体在采取行动时内心所期待的这个行动所能带来的某种结果。这个目的是由每个个体为自己设定的,而不可能被他人强制拥有。一个人如果能够较少地被别人强制着去拥有一个目的采取某种行动,那么他的行为就能更多地由他的道德情感来支配,因而就越自由。“我有责任使包含在实践理性概念中的某种东西成为我的目的,它可能与出自感性冲动的目的相对立:这就会是一个本身就是义务的目的的概念。”[10]
“用胡杨精神育人”的宗旨就是培养人“自发的道德感”,也正是人们真正追求的通过践行美德而获得的“幸福感”。德性伦理学中的“目的价值论”为这种幸福感的获得提供道路。德性伦理使一个人按照道德标准为自己设立一个义务从而进行自我强制(而不是由规范条文强制),这个义务在自由意志中转化成个人的目的,这便达到个人德性意识的觉醒。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道德的指引下去拥有一个目的,而不需要他人将何种目的强加给他。否则的话,他将不会拥有任何目的,也不会是在绝对的意愿中履行自己的义务。
教育可以使人为自己本身设定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因为此时是被教育者在强制自己,这与自由是完全契合的。这就是胡杨精神教育的关键之处:让学生自主习得有关于德性的知识。将自我奉献等“义务性”的德目内化成心中的目的和信仰。通过长期的、严谨的知识传授、模范感染、社会实践使学生获得良好的道德习惯,更要让这种道德习惯积淀成一种条件反射性的、稳定的原理的某种结果,以保证这些习惯在面对新的诱惑的时候能够不被瓦解。
3. 3 德性伦理教育使人关注“自我完善”和“他人幸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现代文明弊端的日益暴露及其日趋严重的后果,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以及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环境下,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德性幸福观崩溃,逐渐形成了普遍信奉的利益幸福观和享乐幸福观。前者以追求和占有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为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后者则以使感官获得最大满足为唯一要求,而这种追求又必须以占有更多的资源为条件,因而利益最大化成了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幸福观之关键。自近代直至今天,西方的幸福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占有更多资源为核心,以获得欲望的尽情满足为指归的幸福观。而这种幸福观在近代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中得到了表达、论证和倡导。
当代人要克服冷漠、偏执、虚假、自私等道德缺憾,就要拥有并表现出公民资质和公民品格。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到摆脱狭隘的世界观和利己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个体是不成熟的,其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则远远不能达到。
在当今的价值理念中,倘若人们坚信幸福的可获得性,那么获得幸福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人的生活追求,这便涉及到西方古代德性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生活”。由于不同思想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因而对好生活的含义和结构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其主要分歧是快乐主义与德性主义的分歧。前者强调好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后者则强调好生活是一个德性之人过的生活。现代德性伦理学家从古典思想中受到启发,重新开始探讨好生活的含义、结构及其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今天,虽然思想家一般都肯定好生活是人应该过的生活,但有些思想家并不认为一个人的好生活就是他的幸福生活。他们认为,真正的好生活除了个人的幸福生活之外还包括对他人的关爱或仁慈等,甚至主要在于后者。
康德在其德性理论中提出“自我完善和他人幸福”。[11]倘若一个人认为“人格的完善”是他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应当建立在帮助他人获得幸福的基础之上。同时必须是这个人主观能动的实践结果,而不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应激性行为。因此,自我完善是人的能力(或自然禀赋)的陶冶,同时也是对遵循一切一般道德思维方式的陶冶。[12]同时,一些人还在道德幸福和自然幸福之间做出区分,道德幸福是指一个人自我行为的满足,自然幸福是指一个人对大自然的赐予的满足。而在这里,道德幸福则往往表现为“自我完善”,因为在仅仅意识到自己的正直时感到自己幸福的人,才是拥有了自我的完善,而这种完善正是因为使他人获得了幸福。因此,如果关键在于幸福,把幸福当作自己的目的来追求,那么,这种目的必须是其他人的幸福,人们由此也使其他人的渴望成为自己的渴望。
这就是德性伦理教育范畴内的“用胡杨精神育人”所期待的最理想的境界——将幸福与自己的完善视为一体。培育学生关于无私奉献、坚毅勇敢、艰苦奋斗等道德情操,在关照他人的过程中形成“品德愉悦感”,从而获得快乐、幸福的体验。而当关于“做好事而感到快乐”的德性成为一个人的道德品格,自然地就有了“乐于助人”等实践的自发产生。人们不再依据他所拥有的金钱、地位而建立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一个人幸福感因为他获得了德性上的满足而产生。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此——使人们在意识里树立起关于获得幸福生活的途径,即践行德性的生活,获取道德上的满足与愉悦。
4 结语
正如爱因斯坦提出的,能让人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超个人”的价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能力。通过强调德性伦理教育,用胡杨精神涵养学生好的品德,培养有道德、有责任、乐于奉献、敢于吃苦、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塔里木大学在6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正是秉承传承南泥湾优良传统,发扬“抗大”作风,用胡杨精神和理念倡导责任、忠诚、坚毅、勇敢、自律、奉献等高贵品质。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学校在强化育人导向的同时,不仅要使学生从知识层面了解这些品质的高贵性,更要有意识地将胡杨精神中所包含的上述德目内化成学生心中的高尚情操,培养一种关于道德的愉悦感,而不是用法典性质的条文规定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教会学生自己为自己设立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在勤勉吃苦、默默奉献、帮助他人等道德行为中获得内心的幸福感,从而将此类品格的践行以一种使人获得快乐的方式根植内心。
大学承担着立德树人这份最庄严、最神圣的使命,高校尤其是新疆高校,需要大力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掌握胡杨精神的主要内涵,明晰其历史渊源,阐释其基本含义,用心把艰苦环境创造为磨炼学生的机遇,加强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培养学生思考、分析、明辨是非、正确抉择的能力,才能使青年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变的社会思潮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