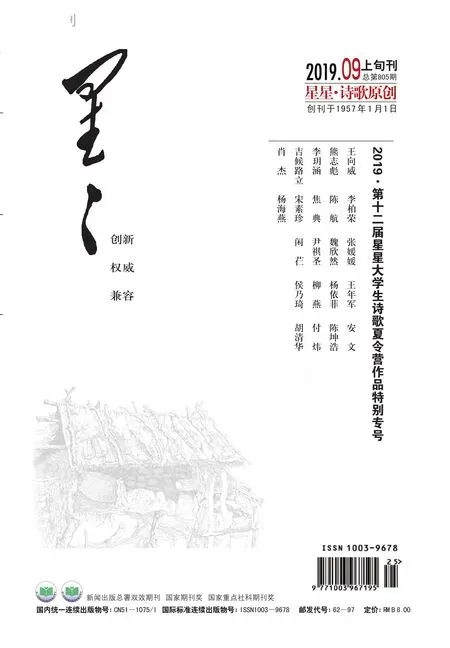折纸游戏(组诗)
杨依菲
落日与石榴——献给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家族》中的小汉诺
一次握拳的迸裂
是千百瓣出奇的大云朵,
是飞机成群陨落如夏蚊。
迷恋过黏滞、滴坠的金黄,
如何再去逐猎商业的辉影?
蔷薇色穹顶,灼唇的风,
糊满贵重油彩的童年。
末日的轰鸣,
父辈的咳嗽,
不争气的侏儒。
心的双层牢墙间,
一只裹满鲜血的拳头剧烈地晕眩。
汉诺,你誓不死于不美的一切。
春日沪行
春日沪行,江边的游子练习相爱如初。
深茄色的鸭羽,镰刀,半融的浮碴,硫磺,
去年的签名,都一一避让开,她的呼吸
才缓缓上浮。防备的人已决心水落石出。
防备的人过去分不清谁是敌手,也料不到
人间的紧握,足以使皮肤脆成纸。当胸口被报时鸟
的红足踩遍,引爆一只无人光临的空火柴盒:
“你,那么温柔,我却一直把你当野兽。”
在阵阵颤瑟里,春日怀着耐心
观看他们,像女儿踮起两条匀细的小腿,
全无倦意。
梯
我人生常有的失败,例如:
从梯子的半截摔下来
后来,即使站立
也忘不了屈服时
天空——
云缀成的脊椎弓成弧形
关怀,私密地向我弯曲
——最为芳香的创可贴
同样贴在伤口上的,还有一些名字
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李白,布尔加科夫,卡夫卡
——像大于全人类的行星在黎明爆炸
滚烫的火烬已被风收走
银灰色的边缘还在寸寸起烟
当初,他们也在梯子脚
有过同样的蜷曲?
由木头,到钢铁,到抽象
日新月异的梯子林
笨拙的人,是否只配游走在大厦的地下室里?
是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人们把梯子也搬进诗歌里
得胜的人站在梯子顶
妙语连珠地投掷阴影
(我可否只是写诗,而不被质问有没有才华?)
阴天时,就连云也连成了梯子
擅长攀爬的人看什么都有高低
但那夜莺不屑眷顾的边境,也会有秋
也会从沁凉的风中,旋落下澄金的,苍老的心
(再普通的人也珍重自己的痕迹!)
或许某天,这些梯子,连同帝国
会被一架架搬出去
攀爬、攀比
不会再是生存的最优姿势
眼里装满云朵的人
不会再仅仅是个失败者
哪怕他狼狈,贫穷,默默无闻
活在梯子底下
双脚被废墟紧紧咬住
松开拳头,天空会朝右展开
获得了资格的名字漂浮其上
数量漫无边际
岁末的怀念
“我来到世间定有些缘由
我的手脚是以谁的手脚为原型?”
——西川《虚构的家谱》
在成都,爷爷奶奶
戴好了毛线帽,扣好了羽绒服
一个不是他们子女的人,为他们拍照
他们朝那人笑,毫无瓜葛地
爷爷奶奶在成都,初雪
如一笔新近支出的审美消费,护士们连夜
拆盒,将养老公寓的小绿园布置好
供爷爷奶奶两人
搀扶着,一同站在
一个不是他们子女的人面前
小园晴雪,溢遍绿树的杯,映亮他们拐杖下
黝湿如酒的地面,映亮他们手背
和脸上的奇迹:洁净,全无皱纹
伶仃的雪从不斟酌其依偎
爷爷的声音来自一千八百公里以外
他说菲菲你记得吗?
你小时候,乖得很哦,每个周末到爷爷家
都舍不得走,你爸爸妈妈拉开门的时候
你就扑到爷爷身上哭,把爷爷亲得满脸
都是你的口水,滴滴答答的,你记得到不?
我不记得了
如何在天使宾馆和电信路上摔跟头
不记得了,抱我走路的那人
是谁,为何汗流浃背
是那个太过年轻的人,从不用爱表达爱
还是那个眼角微翘的人,心胸狭窄而美丽
亲人的表情铸造着孩子的眼睛
我不记得了,成都
如今出落为大都会,但最贵的记忆
关于一家一家的小故事,关于有些孩子想远走
关于夜晚的一颗紫葡萄,碾碎另一颗
我如何洗净胃里
北方遥远的血,爷爷奶奶在成都,成都
炫耀它持有的全部人质
何时玉林路的灯火初具规模,何时出发的消息
敷满早晨八点,答之以雪中的干燥吗:我不记得
诗观
诗不是悬空的网,而是在生命的肉里交叠的神经末梢。比喻不是木匠活,比喻是千真万确的,是诗人从种种庸常与阴暗之处目睹的“活生生的游戏”。二手的诗歌没有必要写,正如能被陈言滥调所概括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