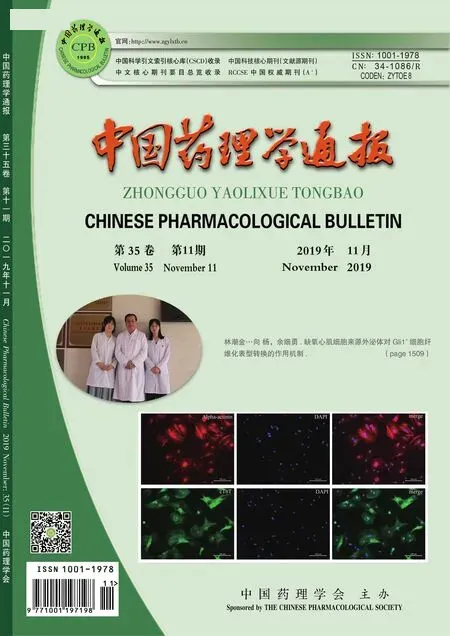κ阿片受体中枢副作用评价方法和发生机制研究进展
马 艳,刘景根,王瑜珺
(1.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2.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203)
疼痛是患者就医的最起始信号,其中包括炎性疼痛、神经疼痛和癌症晚期患者经受的癌痛等。疼痛影响的患者甚至超过糖尿病、心血管病和肿瘤患者之和。以吗啡为代表的μ阿片受体激动剂是临床治疗中、重度疼痛的主要镇痛药,但此类药物会引起用药欣快感、耐受和呼吸抑制等副作用,存在成瘾、药物滥用和死亡的高用药风险[1]。因此,寻找安全有效、副作用小的新型潜在镇痛化合物是当务之急。为避免μ阿片类镇痛药物介导的副作用,长期以来κ受体激动剂都是新型镇痛药物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1 以κ阿片受体为靶标的代表药物
κ阿片受体激动剂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治疗瘙痒,而不引起成瘾、呼吸抑制和便秘等吗啡样副作用,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其烦躁不安、镇静和致幻等中枢副作用也限制了这类化合物的成药可能。目前,临床以κ阿片受体为靶标的药物,如喷他佐辛、纳布啡、布托啡诺等均为κ/μ混合激动药物,κ阿片受体选择性激动剂只有2009年日本上市的用于尿毒症患者止痒药物纳呋拉啡。
1.1 喷他佐辛(pentazocine)70年代发现的苯基吗喃类镇痛药物,主要激动κ阿片受体,对μ受体具有部分激动或较弱的拮抗作用。喷他佐辛适用于中、重度镇痛,具有较弱的焦虑副作用和较低的成瘾性。临床广泛用于手术痛、慢性疼痛、癌痛等。该药物术后镇痛的不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和多汗等,且发生率较低[2]。有文献报道,喷他佐辛还可以用于治疗其他镇痛方法引起的不良反应[3]。
1.2 纳布啡(nalbuphine)纳布啡是一种半合成混合型阿片受体激动-拮抗剂,为强效κ阿片受体激动剂,对δ受体无激动作用,对μ受体具有拮抗作用,拮抗药效是喷他佐辛的11倍,足以拮抗掉吗啡等μ激动剂引起的呼吸抑制。具有镇痛效应强,呼吸抑制、恶心呕吐、皮肤瘙痒等副作用较弱的优点,广泛应用于术后镇痛、临床麻醉等。自1965年合成以来,在国外得到广泛应用。2015国产化上市,近两年国内临床应用逐渐增多[4]。
1.3 布托啡诺(butorphanol)14-羟基吗啡喃系列镇痛药物,是一种合成的阿片受体混合激动拮抗剂,其体外阿片受体亲和力为1 ∶4 ∶25(μ ∶δ ∶κ),为强效κ阿片受体完全激动剂,对δ受体激动活性低,对μ受体有部分激动作用。该药物具有镇静作用,但成瘾性低,无耐药性,无烦躁不安、焦虑等不适感,呼吸抑制弱[5]。1992年,美国开发出布托啡诺鼻腔喷雾制剂用于缓解剧烈疼痛。
1.4 地佐辛(dezocine)阿片受体混合激动拮抗剂,镇痛作用强,而副作用弱。2009年,扬子江药业集团在中国将地佐辛按3.1类新药开发,独家上市后,迅速占据国内镇痛药物市场。2016年,地佐辛的销售额在全国达到6.3亿美元,占全国阿片类镇痛药市场的45%以上。早期研究表明,地佐辛对μ受体具有激动作用,在动物和人类中均能产生与吗啡等效甚至更强的镇痛作用[6]。同时,地佐辛表现出一定的μ拮抗活性。与μ完全激动剂吗啡相比,地佐辛安全性较好。根据以上资料,地佐辛被认为是μ部分激动剂[6]。Liu等[7]对地佐辛的分子靶点进行表征,证实地佐辛为κ部分激动剂。由于地佐辛结构上与喷他佐辛有相关性,地佐辛最初被鉴定为κ受体激动剂,体外功能测定表明地佐辛为κ受体拮抗剂,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重摄取抑制剂。近期我们课题组结合体外功能性[35S] GTPγS实验和体内药效实验证实,地佐辛是κ部分激动剂和μ部分激动剂,对μ受体的亲和力高于κ受体[8]。
1.5 纳呋拉啡(nalfurafine,TRK-820)Nagase等[9]于1998年发现新型κ受体激动剂-纳呋拉啡。Wang等[10]明确了纳呋拉啡对κ阿片受体的高选择性。纳呋拉啡具有较强的G蛋白偏向性,动物实验结果显示,镇痛剂量下不引起烦躁、镇静等作用,临床不产生致幻,因此,纳呋拉啡被定位为低副作用的镇痛剂和止痒剂[11]。然而,最近在大鼠颅内自我刺激实验中发现,高剂量纳呋拉啡会诱导烦躁不安厌恶效应,因此,纳呋拉啡的G蛋白偏向特性可能不足以保证它的安全性[12]。此外,临床试验显示,纳呋拉啡在镇痛剂量下存在严重的镇静作用,但是这种副作用在低剂量(止痒剂量)下可避免[13]。2009年,纳呋拉啡软胶囊剂型在日本上市,用于治疗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相关瘙痒症。2015年及2017年,纳呋拉啡在日本获批用于治疗慢性肝病患者瘙痒症及腹膜透析患者瘙痒症。2018年,中国生物制药公司三生制药和日本东丽公司(Toray)签订独家许可协议,在中国内地开发及商业化该产品。纳呋拉啡从小鼠模型成功转向临床市场,并转向商业化发展,最终被血液透析病患与尿毒症瘙痒患者接受,是目前κ阿片类选择性药物领域中唯一市售产品。
1.6 KORSUVA(CR845/difelikefalin)由Cara Therapeutics公司开发,是一种作用于外周的新型高选择性κ受体激动剂,CR845在人和动物中均表现出强效的镇痛、抗炎和止痒特性。由于CR845难以穿透血脑屏障,可以有效避免中枢副作用。该注射剂于2018年初启动针对术后痛和止痒的关键性临床III期试验。
2 κ阿片受体激动剂伴随的副作用及评价方法
在临床前研究阶段,动物模型和研究方法的恰当选择是发现和评估新型先导药物的重中之重。κ受体激动剂产生镇痛的同时也会伴随镇静、烦躁不安和致幻的发生。镇静的评价方法和手段较多,自发活动和转轮实验均能作为镇静评价指标。目前,国内外尚没有针对致幻的动物行为研究方法。烦躁不安作为一种负性情绪,评价有一定的难度,近年来对κ受体激动剂,尤其是G蛋白偏向性配体的开发促进了该评价方法的成熟。
2.1 条件位置厌恶(conditioned place aversion, CPA)激活κ阿片受体会引起人类的烦躁不安和啮齿动物的类似烦躁状态[14]。在啮齿动物中,CPA行为是烦躁不安的客观测量方法[15]。通过将特定的环境信号与药物引起的情绪搭配,使动物对二者形成联系并建立条件反射,当动物再次处于相同环境时,会表现出厌恶和逃避。CPA模型建立分为3个时期:条件化前期(1 d)、条件化期(6 d)、测试期(1 d)。测试期动物在伴药箱一侧的停留时间与条件化前期动物在伴药箱中的停留时间的差值,即为CPA值[16]。Anderson等[17]用CPA模型评价选择性κ激动剂U62066介导的烦躁情绪,发现成年大鼠给予0.1、0.2 mg·kg-1U62066均表现出明显的CPA。Laman-Maharg等[18]观察到κ受体激动剂U50488介导明显的烦躁不安,同时存在性别差异,在♂加利福尼亚小鼠中,10 mg·kg-1的U50488可以引起CPA,而对于♀加利福尼亚小鼠,2.5 mg·kg-1U50488即可引起明显的CPA。值得注意的是,应激也会促进内源性强啡肽原释放,进而激活κ受体产生CPA,但该作用依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CRF)。由CRF引起的CPA可被强啡肽基因缺失、κ受体拮抗剂或CRF2受体拮抗剂antisauvigine-30阻断。但是,外源性κ激动剂U50488直接诱导的CPA不可被CRF2受体拮抗剂阻断[14]。
2.2 颅内自刺激(intracranial self-stimulation,ICSS)κ受体激活在动物中引起的烦躁不安是难以直接测量的,CPA模型中体现出的厌恶指数可以作为一个指标[19],但是厌恶情绪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众多脑内信号分子。有研究将动物对腹侧被盖区- ICSS低应答频率反映出的快感缺失,作为体现κ受体激动引起的烦躁不安的另一个指标。在该实验中,将电极埋于鼠脑,通过动物自己按开关通电流,以进行自刺激。这是Olds等[20]发现的现象,在奖赏系统中,动物按开关的频率可高达每小时5 000次。ICSS的产生部位为以丘脑下部为中心,扩展到大脑边缘系统及中脑顶盖,而大脑新皮质、丘脑和小脑无此作用。通过按开关引起的对脑的奖赏刺激,可使动物学习。有效学习与自刺激有效部位得到奖赏有一定联系。将能产生自刺激的部位称为奖赏系统,与此相对,将动物会躲避按开关的刺激部位称惩罚系统。ICSS作为一种实时监测方法,是对CPA实验的有力补充。κ受体激动剂通过抑制脑中奖赏效应增加ICSS阈值。另外,系统操纵刺激频率产生“频率-反应率”曲线(类似于药理学剂量-效应曲线),实验通过频率曲线的改变评价动物情绪。ICSS中这种“曲线移位”方法的优点是它可以将刺激敏感度与动物的运动应答能力分开[21]。具体而言,频率-速率曲线的横向移动通常代表刺激的敏感度变化,而垂直移位被解释为运动效应的改变。研究表明,κ受体激动剂U50488、U69593介导动物产生烦躁不安,均会增加ICSS阈值。而κ受体拮抗剂norBNI、5′-acetamidinoethylnaltrindole(ANTI)预处理会阻断U50488、U69593介导的ICSS阈值升高[19,22]。实验证明,具有G蛋白偏向特性的阿片受体激动剂RB-64,triazole 1.1,不产生明显的烦躁不安,不会增加ICSS阈值[22,23]。临床止痒药物κ受体激动剂纳呋拉啡在小鼠ICSS实验中也不会引起阈值的升高,提示该药物在止痒剂量范围内不产生烦躁不安副作用[16]。
3 κ阿片受体介导烦躁不安的潜在分子机制
近年来,在利用CPA和ICSS评价κ受体激动剂烦躁不安副作用的同时,介导该作用发生的分子机制也引起众多关注。
3.1 β-arrestin信号通路“功能选择性”也叫“激动剂偏向性”,是用来描述G蛋白偶联受体配体选择性地激活G蛋白信号通路,而不是激活包括G蛋白、β-arrestins和(或)激酶在内的所有信号。功能选择性意味着,有不同偏向性的配体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效应。Bruchas等[15]发现,κ受体诱导的p38 MAPK磷酸化介导了动物烦躁不安的发生,与镇痛作用无关,并且p38 MAPK的激活是由β-arrestin2通路介导[24],表明β-arresin2通路和烦躁不安副作用相关。Triazole 1.1是由Brust等[22]新发现的G蛋白偏向性κ受体激动剂,他们发现Triazole 1.1和传统κ受体激动剂一样具有镇痛和止痒作用,但不会诱发镇静、烦躁不安和多巴胺释放减少。但是,有研究利用β-arrestin2敲除鼠发现,敲除β-arrestin2损伤了动物的行为协调性[23,25],动物仍然表现出烦躁不安,同时也不影响κ激动剂的镇痛和止痒作用,证明β-arrestin通路和动物的运动协调性相关,但和烦躁不安通路无直接相关性。他们进一步对G蛋白偏向性配体RB-64进行检测,发现RB-64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和CPA副作用,但没有镇静和快感缺失副作用[23,25]。因此,现有资料表明,β-arrestin偏向性信号传导与烦躁不安、运动失调有一定的相关性。目前,主要利用偏向因子(G蛋白/β-arrestin2)来描述配体对G蛋白和β-arrestin2的偏向性,偏向因子计算:对G蛋白的激动能力(35S GTPγS binding实验)/对β-arrestin2的招募能力(DiscoveRx Path Hunter Enzyme Fragment Complementation,EFC技术)[26]。
3.2 p38 MAPK研究表明,κ受体介导的烦躁不安依赖p38MAPK通路的激活[15,24],而p38 MAPK的激活由于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3引起受体磷酸化,进而招募β-arrestin2所致[27]。本课题组前期也发现,κ阿片受体激动剂U50488介导的CPA依赖杏仁核p38 MAPK磷酸化,选择性p38抑制剂SB203580可以阻断U50488介导的CPA行为[15,28]。Ehrich等[29]发现,多巴胺神经元中的p38αMAPK在κ阿片受体介导的厌恶情绪中起关键作用,腹侧背盖区内κ阿片受体活化引起p38αMAPK磷酸化是κ阿片受体介导条件性位置厌恶所必需的。恢复κ阿片受体敲除鼠腹侧背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中κ受体的表达,动物重新产生κ阿片受体依赖的负性情绪。进一步发现,在多巴胺能神经元中,κ阿片受体激活p38αMAPK引发烦躁不安负性情绪,而κ阿片受体激活p38αMAPK与κ阿片受体抑制多巴胺释放过程无关。
3.3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2018年,Liu等[30]利用磷酸化蛋白质组学方法,对κ受体信号介导的信号作了全面的评价,通过对近50 000个不同的磷酸化位点定量分析,发现mTOR信号通路与κ受体介导的烦躁不安副作用存在相关性。mTOR复合物能激活p70S6激酶,进而增加核糖体蛋白S6的磷酸化,导致蛋白质合成增加。他们发现,抑制mTOR通路激活可以消除κ受体引起的CPA行为。Liu等[16]进一步利用该方法结合行为学实验,比较了经典κ受体激动剂U50488和不会引起烦躁不安副作用的纳呋拉啡的异同,证明mTOR信号通路介导κ阿片受体激活引起的烦躁不安厌恶情绪。在纹状体和皮质中,U50488激活mTOR通路程度明显强于纳呋拉啡,而且mTOR抑制剂可以阻断U50488诱导的CPA。另外,可以引起CPA的U50488和不产生CPA的6′-GNTI在调控小鼠纹状体和皮质中mTOR通路方面也存在差异[30]。因此,κ阿片受体激动剂激活mTOR通路的能力或许可以作为区分κ阿片受体激动剂产生不同程度烦躁不安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p38MAPK通路的激活在该方法中未被发现。
阿片类药物是最有效的止痛药,但长期使用的严重副作用限制疼痛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阿片类药物滥用。与κ阿片受体激动剂不同,κ阿片受体激动剂在镇痛止痒同时不引起欣快感,有效避免了药物滥用和成瘾,而且κ激动剂不会引起呼吸抑制,极大地增加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性,相信κ阿片受体激动剂研究将为设计开发新型阿片镇痛药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