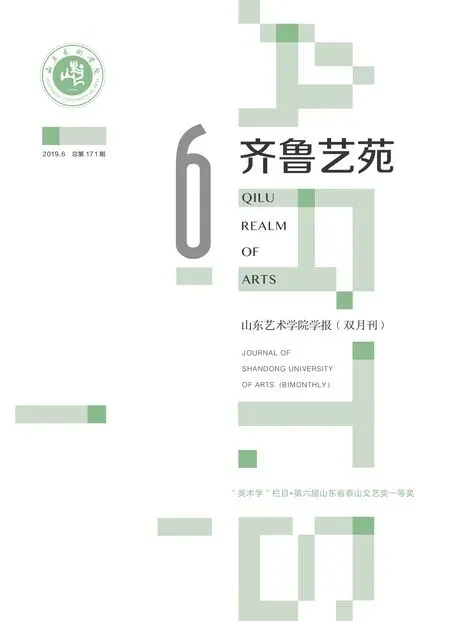宏观与精英的背后
——论艺术博物馆对小人物的叙事构建
陈 名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000)
一、宏观与精英史观溯源
无论是大英博物馆亦或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充斥其中的精美艺术品以及炫目多彩的古董文物在展厅中熠熠生辉,它们的存在无不昭显着这些博物馆的高贵。然而这些精心设计的陈设绝大多数都是博物馆按照艺术史发展脉络的罗列,所呈现给观众的也是所谓的“艺术之精华”。
在这些作品中透露出的固然是历代文化精华所在,是艺术发展史的视觉呈现,然而这些按照大历史发展脉络进行陈列的做法却面临着双重责难:一为按照朝代更迭的方式去诉说艺术的发展,其固然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对其发展历程做一个俯瞰式的概括,但这种大脉络式的宏观叙事(Grand narrative)是高度抽象化的,这种叙事语言的背后会损失细节;其二,在艺术博物馆陈列出的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品其实都是精英化的产物,博物馆实质上只是精英艺术的陈列之所,正如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F. Pareto)所表述的:“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1](P13-14)所以精英主义实则只是宏观历史的代表,其背后是对小人物的排斥,在他们的身上并不能看到小人物的存在,精英艺术是否就可以成为艺术发展的代言人亦开始受到质疑。
剖析艺术博物馆的这双重责难,不难发现这些宏观和微观、精英历史与小人物历史之间的选择问题,即博物馆在进行展陈叙事的时候其所选择的叙事观念问题。毫无疑问,目前对于绝大多数艺术博物馆而言,其选择的展陈方式大多是以宏观历史作为背景的陈列,其背后的观念也即是所谓的“大历史”(History)或“元叙述”(Metanarrative)理论。艺术博物馆陈列的大历史观念渊源流长,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之所以可以形成大历史观念的根本在于17世纪以后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以及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让人们对于控制、改变自然的热情膨胀到无以加复的地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人类可以认识、改造自然,那么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认识也是可能的,继而认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也可以总结把握的。所以历史是可以总结和抽象出规律的理念成为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尤其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共同认知。伏尔泰(Voltaire)甚至提倡要用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提出了“历史哲学”一说,该说是一种剖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哲学概括的社会历史理论。[2](P85)从现象中高度归纳总结出人类发展的规律,去认识人类的历史预测人类的发展。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在其著作《新科学》(New Science)一书中认为历史是可以科学化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行为的总和,而人类的行为又是可以量化考察的,所以历史是可以进行科学化的演绎,并总结抽象出历史的规律,这个历史的规律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大历史观,而充当大历史观主角的则是历史浪潮中的一个个精英人物。换句话说,大历史观念的陈述其实只是一部由精英人物构成的历史发展规律史而已。这种大历史发展观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的艺术史研究,温克尔曼(Winckelmann)就以宏观历史的发展脉络为前提,遴选古希腊艺术中的精英之作,写就了第一部艺术史专著——《古代美术史》。
宏观与精英史观双重关照下的艺术史对艺术博物馆的陈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卢浮宫成为面向公众的国家博物馆,为了能够起到教育公众的目的,按照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陈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布展方式,正如时任卢浮宫中央艺术博物馆行政委员会的勒布朗(Chales Le Burn)在其《对国立博物馆的反思》一书中所强调的,完美汇集了艺术和自然所产生的最珍贵物品的卢浮宫,应该在悬挂时呈现出艺术诞生、发展、达到完美,最后趋于衰落的不同阶段。[3](P70-71)而这种视觉艺术史的布置不可避免地也成为了大历史关照下精英群体的呈现,而艺术史发展中的那些小人物却被人为地抹去了。
二、小人物叙事的微观史学支撑
对精英以及大历史观念产生怀疑的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赫尔德生活在德国北部的普鲁士(Preußen),他通过观察发现普鲁士地区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与当时时兴的大历史精英史观并非保持一致,难以用大历史的发展观念去描述普鲁士地区,也难以找到小人物与精英直接的关联。在他看来所有抽象概括的历史都是苍白无力的, 任何一般的、普遍的规范都不能包容历史的丰富性,每一种人生状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4](P224)由此赫尔德对历史叙事的大历史观产生了质疑,即大历史并不是各个小人物的综合,在大历史中找寻小人物是徒劳的,这也就意味着由精英构成的大历史其所涵盖的历史事实也存在缺陷,作为历史构成的小人物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已经被精英群体乃至宏观历史所掩盖。
作为宏观叙事的反拨,对于博物馆挑选艺术精英并按照艺术史脉络进行展陈的质疑也开始出现,艺术博物馆所谓的可视艺术史究竟能呈现多少艺术史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学者的怀疑,正如黛博拉·简·梅洁思(Debora J.Meijers)所言:“陈列设计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其实与艺术史学者并没有明确的不同;而艺术史学家则越来越注重到他历史描述的方法论和文学性。在历史学的一些领域,对于这种应当属于19世纪的‘历史进化论’的不信任意见正在不断地增长……”[5]于是对小人物叙事的介入成为了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思考方向。尽管对于艺术发展史中的人物研究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并非新生事物,如果以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名人传》为起始点的话,至今已有将近500年的历史,这种对艺术家传记式的个体研究直到现在依然是艺术研究的常用手法,但这种研究仍然是对艺术精英的诠释。如前所述,艺术精英的存在虽然是个体人物形式,但其实质仍然是宏观历史的代名词,所以其与艺术博物馆对小人物的叙述介入并不能简单对应,并不能为艺术博物馆的小人物叙事提供完善的理论支持。
要想为艺术博物馆寻找小人物叙事观念的理论支撑则可依托历史学界的微观史学派的史学理念。微观史学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初就已现端倪,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意大利形成,旋即影响到法国、英国、美国。当然,这种对小人物微观历史的重视并非空穴来风,它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处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末期,意大利国内保守主义的复辟,让历史学家们对原先的元叙事理论产生了怀疑,原先在历史研究中注重考察社会的整体历史,并对整体历史进行的概念化、抽象化、结构化的做法受到了责难,为何历史并没有朝着所谓历史脉络的进程前行,为何小人物在历史的演进中有时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成为了意大利学者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于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重要的微观史学家投入到了小人物的研究之中,比较重要的有卡罗·澎尼(Caro Poni)、爱德华多·格莱迪(Edoardo Grendi)、卡罗·金兹伯格(Caro Ginzburg)等人,其中又以卡罗·金兹伯格最具代表性。卡罗·金兹伯格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6](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中以“提名法”(1)所谓“提名法”即选择历史发展中的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等进行深入剖析。的方式,对生活在16世纪的一个磨坊主进行了考察,16世纪的磨坊主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个邪恶的代表,是与高利贷者、收税员等差不多的社会角色,也即压榨农民的代名词,对于农民来说这位磨坊主甚至是撒旦的使者。然而磨坊主本身并不这么认为,金兹伯格在结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磨坊主的世界观进行重建,还原了当时历史条件的种种之因素,从磨坊主的角度对16世纪的意大利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解剖,虽然选择了历史上的小人物,但却从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了整个16世纪意大利社会的情况。
通过对金兹伯格研究的思路梳理,我们发现,对于社会小人物的介入,并不是为了去还原某个人某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做法与稗官野史般的奇谈怪论并无二致。对小人物介入的目的,是要从微观的角度去还原大历史的背景,以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但就如乔治·鲁德(Geoge Rude)所指出的,对于小人物的叙事有着一定的缺陷,在他看来针对小人物的介入很难用来分析大的社会动向,小人物的身上看不到政治的影响,因为小人物的生活相对较为安逸,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往往存在不一致性,所以当眼光局限在小人物身上的时候,其研究往往会使得历史学家的研究沉浸在对小人物的个性化描述中,而这种描述往往是带有文学色彩的,在微不足道的事情里夸夸其谈却忘记了历史本身。[7]这样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小人物的叙事描述上,实际上对于艺术精英的描述也同样如此,瓦萨里《名人传》一书中也带有大量道听途说的成分,其中的批评意见也含有大量的主观偏见。这也暗示了对艺术博物馆在针对小人物进行描述时可能难以反映出其在艺术史发展过程中的真实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却无异于无限放大了小人物叙事的主观色彩,甚至仍然透露出了精英文化的傲慢,即对小人物的鄙夷和轻视。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小人物不仅是艺术史发展的参与者,更是艺术史的重要组成,对小人物的蔑视,是人为地将小人物与艺术史相隔离,其结果是当我们提及艺术发展历程中小人物的时候往往用的是艺术发展的宏观叙事语境去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种用抽象而又高度概括化的理论范式去诠释小人物的时候,往往有着削足适履的嫌疑。所以,这也昭示着艺术博物馆在选择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小人物历史作为叙事主题的时候,其叙事情节的安排不能仅仅围绕人物本身进行,而应该以小人物的个体历史作为立足点,结合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进行叙事的展开,否则对于小人物的叙述免不了要滑向小说家的窠臼,亦或者因为选择的小人物太过平淡,无法与艺术发展的整体历史接续上。
三、小人物叙事的“厚描述”呈现
虽然对于小人物的叙事介入有着上述的质疑,但从侧面上也显示出微观史学乃至于艺术博物馆当选择以小人物作为叙事主题的时候,其叙事内容的安排所面临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理论可成为艺术博物馆进行小人物叙事内容安排时的有效支撑。吉尔兹从民族志的角度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对个体进行考察,继而由所谓的“显微例证”转向对整体文化的诠释[8](P48)。在他看来那些小人物的不为多数人所重视的私人生活,往往是各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现象的细致体现,其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往往隐藏着解开社会秘密的钥匙。也就是说,小人物的历史并不是独立于整体或者社会全体历史的存在,由这些一个个小人物相关联的网络恰恰才是社会集体乃至全体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如吉尔兹所言,对小人物的介入“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具体的分析而论证, 以求得出一种狭义的、专门化的,从而也是——我这样想像——理论上更为有力的文化概念, 以取代E.B.泰勒著名的‘最复杂的整体’的概念”[9](P9)。所以对小人物的重视对于理解和还原完整的社会历史及其文化来说十分重要且十分必要。
此处不得不提的是,对于艺术史学而言,在研究中援引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似乎并非新论,早在19世纪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t)所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已被奉为文化艺术史的扛鼎之作,在布克哈特看来自然环境、经济状况、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都应该成为艺术史学者的关注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布克哈特的文化艺术史方法论所针对的仍然是艺术发展的全景式关照,与吉尔兹所强调的对小人物的“厚描述”有着本质的区别。如前所述,借助文化社会学的“厚描述”理论,从小处着眼透视整个社会的历史,以此来彰显大历史的发展,是艺术博物馆进行小人物历史故事叙述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艺术博物馆对小人物的历史展开叙事时,其叙事情节的安排是借助厚描述理论,以个体生活为切入点,突出小人物在艺术发展史所受处的位置,以及小人物对艺术发展种种之现象的反馈作为叙事文本。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个人生活史的呈现,并非只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罗列,而是要在小人物的生活史中,体现出其在重要的艺术转变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境况。以个人生活史作为叙事内容其主要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体现在艺术发展大环境下的小人物的个人历史,更是要通过对小人物的个人历史的呈现去反衬出艺术整体历史的走向,艺术发展中小人物的个人历史是印证艺术大历史的一个重要媒介,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如果有责难认为这种以小人物为角度的叙事在反映艺术发展面貌的时候虽然可以起以一见多的作用,但仍然力度偏小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愈来愈多的小人物在艺术博物馆出现,就会呈现出“群像”的特征,凸显出在整体艺术史的维度下,小人物的丰富多彩和特殊性,这对于我们从小人物角度去更深层次地理解艺术大历史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尽管从总体上来看,艺术博物馆能够体现出对艺术发展中小人物重视的展览仍然很少,但在叙事主题方面选择以小人物作为切入点已经成为了部分国内外博物馆的实践尝试,在展览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相关博物馆在这方面的努力。如2015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同大张》展览便是借助艺术浪潮中小人物的呈现去审思20世纪末期中国前卫艺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大同大张》这一展览作为小人物的艺术博物馆叙事的代表案例,其典型性就在于,首先博物馆对于主角的选择并不像既有的艺术展览那样选择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就已经大红大紫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其呈现的是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很小的一个来自于山西大同的激进艺术青年——张盛泉,通过对这位非主流艺术家甚至是十分普通艺术青年去窥视当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生态情况。其二,展览现场的布置并不是既有的所谓“文献展”那样,按照历史脉络简单陈列艺术家的个人作品,而是将展厅分为了生平、绘画、邮寄艺术、行为艺术、手稿五个部分,并在展厅内部布置了影像厅来回重复播放大张在1989年以行为艺术参加89’现代艺术大展的影像资料以及艺术家大量的生活照片和日记、书信等私人物品,在复原大张的个人生活史的基础上,回顾了这位艺术青年选择前卫艺术并殉道前卫艺术的短暂人生。在具体的展出内容中,观者不难体会到一个对前卫艺术怀有崇高理想的边缘地区艺术青年的所想、所思、所作。虽然大张只是当年百千艺术青年中的一个存在,但通过还原大同大张这样一个小人物,折射出的却是当年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集体历史。
结语
艺术博物馆作为社会公众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其在展陈叙事观念的选择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学发展的影响下,经过了从宏观陈述到逐步介入个体历史的观念变化,亦即是在既有的宏观叙事的基础上,对艺术发展中小人物的介入开始受到重视,从各艺术博物馆近些年的实践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宏观和精英历史叙事的观念是艺术博物馆把握艺术发展规律呈现艺术演变之路的前提和基础,而小人物叙事则是艺术博物馆还原艺术史发展细节,印证艺术史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