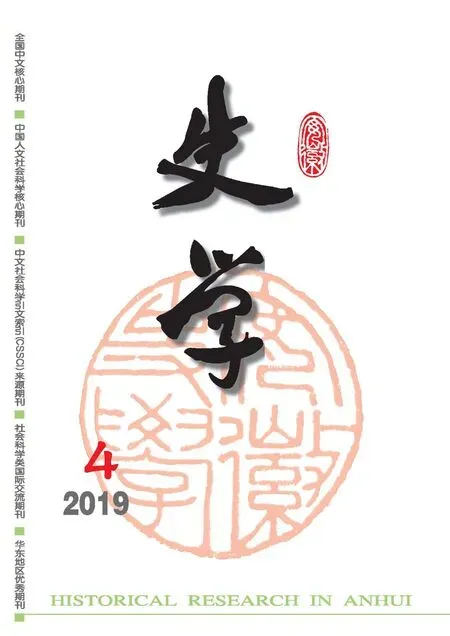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与实践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公元前4世纪,在古希腊是泛希腊主义盛行的一个时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心目中都有一套自己的泛希腊主义;但在众多提倡泛希腊主义的精英人物之中,学者们大多关注伊索克拉底,却相对忽视了德摩斯梯尼。[注]“泛希腊主义”一词是现代学者的发明(根据Peter Green的考证,首创这一名词的学者是19世纪的英国史家George Grote, 见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4, pp.104—105),用来描述古希腊人对希腊人共同利益和共同身份的强调以及对希腊人与蛮族人之对立的认识。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认为,作为希腊人之对立面的“蛮族人”(barbaros)更多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中希腊人联合起来抵抗波斯帝国入侵的产物,但是,“全希腊人”(panhellenes)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的公元前6世纪,见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9—10。国外学界关于“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的专论主要见S. Perlman, “Panhellenism, Polis and Imperialism”, Historia, Vol. 25, 1976(1), pp.1—30;M. B. Sakellariou, “Panhellenism: From Concept to Policy”, in M. B. Hatzpoulos & L. D. Loukopoulos, eds., Philip of Macedon, London: Heinemann, 1981, pp.119—139;Polly Low,“Panhellenism without Imperialism? Athens and the Greeks before and after Chaeronea”, Historia, Vol. 67, 2018(4), pp.454—471;Peter Green,“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Barbarian: Athenian Panhellenism in a Changing World”,i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p.104—132;L. Mitchell, Panhellenism and the Barbarian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 pp.xv—xxv;徐晓旭:《古希腊民族认同中的个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63—70页。上述论著是对“泛希腊主义”的宏观考察,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的专论只有H. B. Dunkel,“Was Demosthenes A Panhellenist? ”Classical Philology, Vol.33, No. 3(July, 1938), pp.291—305; J. Luccioni,Démosthène et le panhellénis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1.而德摩斯梯尼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德摩斯梯尼怀有“最强烈的泛希腊情感”,否认他维护雅典利益的立场;要么将他定性为彻头彻尾的“雅典爱国者”,否认他的泛希腊情感的真实性。[注]持前一种看法的有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皮卡德-坎布里奇(A. Picard-Cambrige)、卢西奥尼(J. Luccioni)、克洛塞(P. Cloché)等人,持后一种看法的有敦克尔(H. B. Dunkel)、汤因比(A. J. Toynbee)以及贝洛赫(K. J. Beloch)、德罗伊森(J. G. Droysen)、德雷鲁普(E. Drerup)、凯斯特(J. Kaerst)等不少德国学者,参见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106以及H. B. Dunkel, “Was Demosthenes A Panhellenist? ”pp.291—292.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影响到人们对德摩斯梯尼的政治目标和道德品质的评价,同时也是研究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政治史所无法绕开的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在雅典政坛活跃将近20年并最终因为抵抗失败而自杀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的政策会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偏执一端而毫无合理性可言吗?雅典公民在如此长的时间中会信任一个持有极端主张并不断欺骗民众的演说家吗?希腊人在喀罗尼亚和拉米亚的战败是德摩斯梯尼泛希腊政策本身的失败吗?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注]德摩斯梯尼是政治家(演说家),并非思想家,他的“泛希腊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政策主张中。因此,本文使用“泛希腊政策”一词来替代“泛希腊主义”,指德摩斯梯尼提出来的能够体现“泛希腊主义”精神的政策主张,同时,也以此来表示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与从事修辞教育的书斋学者伊索克拉底的区别。关于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思想的相关研究,见S. Perlman,“Isocrates‘Philippus’and Panhellenism”, Historia 18, pp.370—374; M. B. Sakellariou,“Panhellenism: from Concept to Policy”, pp.128—145; 何珵:《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第126—138页;李渊:《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与民族认同观念》,《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6期,第128—132页。及其实践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
按照现代学者们的定义,政治上的泛希腊主义就是“相信希腊各邦可以通过联合和征服波斯帝国来解决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注]M.A.Flower,“Alexander the Great and Panhellenism”, in Alexander the Great in Fact and Fiction,edited by A. B. Bosworth and E.J. Bayn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7—98.换句话说,泛希腊主义包含了两大要素:一是希腊城邦的联合,二是攻打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以是非希腊人,也可以是希腊人,随着希腊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动而变动。[注]Polly Low,“Panhellenism without Imperialism? Athens and the Greeks before and after Chaeronea”, pp.455—459.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所经历的演变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政治生涯初期,他与伊索克拉底一样,也将波斯人、小亚细亚土著人等视作需要防范和攻击的对象。
公元前356年,投靠波斯国王的卡里亚国王摩索洛斯成功鼓动罗德岛、开俄斯岛、科斯岛和拜占庭等盟邦发动暴动,叛离了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同盟战争”(the Social War, 公元前357—前355年)爆发。公元前355年,雅典将军卡瑞斯在平叛过程中,曾支持弗里基亚总督阿塔巴祖斯发动叛乱,使波斯大王对雅典非常不满,扬言要出兵攻打雅典。在谣言四起的背景下,雅典的政治家们纷纷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而德摩斯梯尼的建议最终得到了认可。这是德摩斯梯尼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演说题目是《论海军筹建会》(OntheSymmories或OntheNavy-boards)。在发言中,德摩斯梯尼首先强调波斯大王是全希腊共同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武力威胁希腊,还通过贿赂挑起希腊人的内讧。[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3. 本文所引的德摩斯梯尼演说词以及其他古典作品均来自于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以下引用将只注明章节,不再注明出版信息。然后,他强调雅典所要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合理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不会单兵作战,其它希腊城邦会出于对雅典的感激,而与雅典并肩作战。[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4—5;5—6,10,12;6;6,13,37—38,41.但同时,希腊世界的分立与彼此间的仇隙又为雅典参加这场战争带来了可能要两线作战的困境,既要抵挡波斯人的进攻,又要防备希腊叛徒们的袭击。[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4—5;5—6,10,12;6;6,13,37—38,41.面对这种困境,承担保卫希腊之责任的雅典人应该从全局出发:首先,不能对那些出卖希腊共同利益的城邦进行惩罚,要采取说服感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4—5;5—6,10,12;6;6,13,37—38,41.其次,雅典人要警惕自身的帝国主义倾向,修复与其他希腊城邦间的关系,消弭它们对雅典的恐惧和妒忌;[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4—5;5—6,10,12;6;6,13,37—38,41.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加强自身的军备建设,尤其是扩建海军,通过提高自身实力招徕希腊各邦、威慑敌人和鼓舞士气。[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13, 29—30, 35, 41; 39, 40.德摩斯梯尼还用祖先们的光辉事迹来鼓励雅典人:他们在拯救了希腊的同时,也给雅典带来了利益。雅典人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只要战争胜利,我们就会财富充足”。[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13, 29—30, 35, 41; 39, 40.在德摩斯梯尼看来,雅典人关于波斯问题的决策,应该从全希腊的利益出发,并赢得其他希腊城邦的支持。没有其他希腊城邦的普遍支持,雅典不可能赢得胜利。换句话说,雅典对波斯政策应该以全希腊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希腊人的普遍支持也是雅典获得胜利的保证,雅典要拿出诚意确保其他希腊城邦对共同行动的支持。在德摩斯梯尼的说服之下,雅典公民大会并未仓猝对波斯宣战,还在公元前354年承认了罗德岛等邦退出同盟的结果。
但是,罗德岛在获得独立后,很快就对摩索洛斯的控制表现出不满。罗德岛民主派夺取了政权,并在公元前351年派使者到雅典请求保护。面对此前不久还与雅典兵戎相见的罗德岛,雅典公民大会并不支持罗德岛人的请求。然而,德摩斯梯尼主张原谅并保护罗德岛。德摩斯梯尼首先抨击中立政策:罗德岛人是希腊人,属自由人;而埃及人则是波斯臣民,与波斯人同属于应该被奴役的野蛮人。如今,雅典支持埃及人反抗波斯的斗争,却不支持罗德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令人颇感诧异。它与“希腊自由捍卫者”的身份毫不相符。作为“希腊人中的佼佼者”,雅典人有责任去拯救罗德人。[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5—16;5,13—15;18;21;29.其次,从利害关系来看,罗德岛事件不仅关乎罗德岛民主派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关乎雅典人乃至所有希腊人的集体利益。任由波斯大王收回他曾经统治过的土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至极”。[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5—16;5,13—15;18;21;29.非但如此,罗德岛的民主制一旦被颠覆,在政治制度上也会对雅典造成威胁。寡头政体的罗德岛即使对雅典友好或保持中立,仍是一种威胁,因为与寡头政体所缔结的和约没有保障。在德摩斯梯尼看来,希腊城邦普遍实行民主制是雅典外部安全的根本所系;对雅典来说,希腊城邦都建立与雅典为敌的民主制,要比都建立与雅典友善的寡头制更好。[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5—16;5,13—15;18;21;29.再次,从命运无常的角度看,雅典也应该援助罗德岛。“尽管罗德岛人受奴役是罪有应得,但是,现在不是取笑他们的时候,因为,幸运的城邦应该积极援助那些不走运的城邦;要知道,人类无法预测未来之事。”[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5—16;5,13—15;18;21;29.也就是说,希腊城邦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幸运者应该帮助不幸者。最后,德摩斯梯尼又一次用可以看得见的好处激励雅典人。“在城邦内部事务中,城邦法律授予所有人以同样的无差别权利,无论强弱都会得到同等对待;而城邦之间的事务中,弱者却不得不服从于强者。”[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5—16;5,13—15;18;21;29.如果雅典人援助罗德岛成功,便能够继续控制罗德岛,100年前的雅典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走向强大繁荣的吗?而此时,以优布鲁斯为首的主和派赢得了雅典公民大会的支持[注]G. L. Cawkwell, “Eubul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83), 1963, pp.47—67.,德摩斯梯尼的建议并未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
可见,德摩斯梯尼在其政治生涯初期的两篇演说词中,就已经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泛希腊倾向:他对雅典外交政策的评判和建议,始终是从希腊世界的整体利益与雅典利益之间的互动角度去考量的。尽管雅典的利益仍然是其政策构建的重要基点,无论是政策的出发点,还是最终的落脚点,均以雅典的安全为依归,但在德摩斯梯尼看来,希腊世界的安全利益与雅典利益并不矛盾。而且,雅典人有责任保卫希腊世界,也有必要团结希腊各邦,各邦的支持有利于雅典保卫自身的安全。德摩斯梯尼还公然使用了经典的泛希腊话语(“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区别)来论证雅典人应该摒弃前嫌保护罗德岛人的理由。因此,可以说,在其政治生涯初期,德摩斯梯尼的政策建议就开始具有明显的泛希腊倾向,除了雅典利益之外,希腊世界的安全、自由、和平、团结,也是他追求的目标。[注]学者们在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情感是否真诚的问题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主要因为德摩斯梯尼的大部分政治演说辞都同时包含了维护雅典与鼓吹泛希腊联合的两种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们在现实中的政治立场也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尤其是19—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批评德摩斯梯尼、赞扬伊索克拉底并歌颂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大帝,显然是他们支持普鲁士王国统一德意志的政治立场在学术研究上的反映,参见H. B. Dunkel, “Was Demosthenes A Panhellenist?”p.292;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p.105—106.
二
随着马其顿在北希腊的崛起,其势力迅速向南部的希腊城邦世界扩张,开始威胁到了雅典、底比斯等希腊大邦的安全。当雅典的许多政治家还在将腓力二世贬低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时,德摩斯梯尼便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北方邻国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世界的威胁。[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辞《诉阿里斯托克拉底》(Against Aristocrates)公布于公元前352/1年,数次提到了腓力二世在北方的活动(107—109, 111—112, 116, 121),而主要抨击腓力的演说辞《反腓力第一辞》(First Philippic)公布于公元前351/0年,也就是腓力二世登上马其顿王位仅仅8年之后。当时,雅典的其他政治家们还在忙于处理“同盟战争”遗留的烂摊子,波斯及其统治下的小亚土著国家仍然是大部分雅典人心中最有代表性的异邦敌人。参见Raphael Sealey, Demosthenes and his Time: A Study in Defea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5—126.为此,他利用泛希腊主义定义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将在公元前5世纪的泛希腊主义中作为希腊敌人的“蛮族”波斯置换为马其顿,从而重新定义了泛希腊主义,提出了一种以马其顿为敌的泛希腊政策(与伊索克拉底仍然以传统蛮族敌人波斯为攻击对象的进攻型泛希腊主义截然不同,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是防御型的),呼吁希腊城邦联合起来共同抵抗马其顿。[注]彼得·格林和波利·洛都已经指出了政治泛希腊主义在定义上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参见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p.114—115;Polly Low,“Panhellenism without Imperialism? Athens and the Greeks before and after Chaeronea”, pp.457—459.关于德摩斯梯尼的反马其顿政策的起源,见Ian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0—128.
德摩斯梯尼的反马其顿演说,在最初仍然以维护雅典安全为中心;随着马其顿对希腊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德摩斯梯尼才越来越多地使用泛希腊话语来构建自己的政策。从公元前351年到公元前349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连续攻占了北希腊重镇安菲波利斯与奥林托斯,严重损害了雅典的利益。德摩斯梯尼连续发表了4次演说,号召雅典人抵抗马其顿扩张,捍卫雅典安全,其中除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也不乏以抨击腓力二世和马其顿为中心的泛希腊宣传。他在演说辞中指出,腓力二世威胁的不是某一个希腊城邦,而是全体希腊人的安全。在《反腓力第一辞》中,雅典的霸权仍旧是德摩斯梯尼泛希腊思想的核心,但是他在否定腓力二世干预希腊城邦事务的权利时,却是以全体希腊人的安全为前提的。[注]Demosthenes, First Philippic, 10.马其顿人是蛮族,而希腊人是文明人,二者存在根本区别。所以,腓力二世没有资格干涉希腊城邦事务的处理,他是奥林托斯与雅典的敌人,也就是全希腊的敌人,希腊人应该团结起来抗击马其顿的侵略。[注]Demosthenes, Third Olynthiac, 20.
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签订了《菲洛克拉底和约》(ThePeaceofPhilocrates)。但是,德摩斯梯尼很快就发现马其顿仍在继续扩张。不久,他便重拾以组建泛希腊同盟抵抗马其顿为核心的政策,从公元前346年到公元前330年,他连续发表了7次反马其顿演说,大部分都具有强烈的泛希腊倾向,并且随着德摩斯梯尼政治声望的提高,逐渐从单纯的宣传变成了雅典的对外政策。如果说在《反腓力第二辞》(SecondPhilippic, 公元前344年)中,德摩斯梯尼还在强调雅典帝国的辉煌历史[注]Demosthenes, Second Philippic, 7—11.,到了《论刻索尼苏斯》(OntheChersonesus, 公元前341年),他就表现出了对其他希腊城邦更多的关心。他批评了雅典人对其他希腊城邦的冷漠态度:“你们为了自己轻松,放任腓力奴役希腊人,考虑到你们祖先的光辉历史以及你们城市所拥有的资源,你们应该为这种行为感到羞愧。我宁愿死掉也不会提议这样的犯罪性政策。同理,如果有人提议这样的政策,并赢得了你们的支持,结果就是,放弃抵抗,失去一切。”[注]Demosthenes, On the Chersonesus, 48—49.雅典人的懒散态度让马其顿越来越强大。因此,雅典要坚决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团结希腊人的政策,给其它城邦带来抵抗马其顿的信心。总的来说,在这篇演说辞中,德摩斯梯尼已经不再刻意强调雅典的领导,而是开始提倡一种更为开放和务实的泛希腊政策。
同样发表于公元前341年的《反腓力第三辞》(ThirdPhilippc)显现出了更为浓烈的泛希腊情感。[注]维尔纳·耶格尔认为《反腓力第三辞》是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发展的转折点,见Werner Jaeger, Demosthenes: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is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8, p.49.德摩斯梯尼频繁地强调马其顿人的“蛮族”身份,否认腓力二世拥有参与希腊城邦事务的权利。在他看来,希腊霸权只能归属拥有希腊血统的人,任何蛮族人谋求希腊霸权都是不正当行为,如果泛希腊赛会、泛希腊神谕、泛希腊城邦组织都被一个蛮族人所控制,对于希腊人来说,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情吗?[注]Demosthenes, Third Philippic, 30—32;38—40.这是最能体现德摩斯梯尼政策的泛希腊特征的地方,他明确诉诸于希腊人的共同血缘和共同习俗以及马其顿人的“蛮族”身份等泛希腊认同要素,以此证明组建反马其顿的泛希腊同盟的必要性。腓力二世在不断地侵害希腊人的利益,而希腊人却彼此猜疑、互相拆台,每个城邦都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宁可信任腓力二世,也不信任希腊邻人。德摩斯梯尼认为是亲马其顿派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希腊人只有驱逐这些无耻叛国的政客,才能打败马其顿人。[注]Demosthenes, Third Philippic, 30—32;38—40.作为希腊最有责任感的城邦[注]德摩斯梯尼认为雅典一直都是希腊人共同利益的忠实守护者,见Demosthenes, On the Crown, 64; 71—72.,雅典人应该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做好战争准备,二是将准备情况告知各个城邦,派遣使节到所有希腊城邦,号召它们起来抵抗马其顿的侵略。因此,语言的热烈与政策上的明晰是《反腓力第三辞》的主要特征,尽管德摩斯梯尼仍旧强调雅典在泛希腊同盟共同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但这种强调主要是为了激励雅典人,与《反腓力第二辞》中认为只有雅典有资格掌握希腊霸权、对其他城邦不屑一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从基本原则上,还是从具体的政策建议上,德摩斯梯尼都摆出了坚定地组建泛希腊同盟抵抗马其顿的姿态。
到了《反腓力第四辞》(FourthPhilippic, 公元前341年),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又有所发展。首先,提出了联合波斯的建议。在德摩斯梯尼眼中,波斯人虽也是蛮族人,但通过争取他们的资助,可以为抵抗马其顿的泛希腊战争提供帮助。[注]Demosthenes, The Fourth Phillipic, 32;16;70—74.其次,雅典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向希腊盟邦表示善意,团结希腊人,改变希腊人彼此提防导致的涣散状况。[注]Demosthenes, The Fourth Phillipic, 32;16;70—74.第三,打击城邦内部的亲马其顿派,他们是腓力二世的支持者,是组织泛希腊同盟的内部障碍。[注]Demosthenes, The Fourth Phillipic, 32;16;70—74.从这三点来看,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已经发展到了较为完备的形态,不仅明确了组建泛希腊同盟抵抗马其顿的总目标,也提出了通过解决内部亲马其顿派来加强对外政策选择的路径,甚至还暗示了一种完全现实主义的政策,即与传统的“蛮族”敌人波斯结盟共同抵抗新敌人马其顿,相当于重新定义了传统的泛希腊主义。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贯穿于其政治生涯之始终,而且经历了从反波斯的泛希腊政策到反马其顿的泛希腊政策之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主要是希腊世界及其周边政治局势变化的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反马其顿政策构成了德摩斯梯尼泛希腊政策的主流。再考虑到反波斯政策只出现在德摩斯梯尼的政治生涯初期,对雅典政策未产生过实质性影响,下文对他的泛希腊政策的合理性分析主要以他的反马其顿政策为中心。
三
从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辞来看,维护雅典城邦利益的论调并不鲜见。有的学者由此就得出结论,完全否认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情感的真实性,认为他只是一个“雅典爱国者”[注]H. B. Dunkel,“Was Demosthens a Panhellenist? ”p.305.,他的泛希腊政策只不过是为雅典霸权服务的一种政治宣传话语,甚至说德摩斯梯尼是伯里克利帝国主义政策的继承人。[注]S. Perlman, “Panhellenism, Polis and Imperialism”, pp.23—25. 在很多学者眼中,所有的希腊政治家都是习惯撒谎和自私自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将“泛希腊主义”视作为本邦谋利的工具。但是,这种工具主义判断很难说符合真实的政治游戏。彼得·格林指出,在真实的政治世界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总是与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情感上的矛盾是所有理想主义的共同特征。如果要操弄某种理想或原则来服务于政治目的,前提是人们会严肃对待这种理想或原则。如果人们不会当真,也就不可能达到利用它们的目的。参见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p.106—107.从最后结果来看,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因为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的失利而宣告失败,而伊索克拉底提出的由腓力二世率领希腊人征服波斯的泛希腊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但是,这些评判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喀罗尼亚战役的失利无法完全抹杀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所蕴含的合理性;[注]喀罗尼亚战役对阵双方的军队人数相近,主力均由重装步兵和骑兵构成:腓力二世拥有2.4万名马其顿步兵、6000名盟邦步兵和2000名骑兵。在希腊一方,拥有1.2万名底比斯人、6000名雅典人和1.2万名盟邦步兵以及3800名骑兵,这些士兵来自约占希腊世界总人口(400万)四分之一的城邦。可以认为德摩斯梯尼并未成功组织起像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同盟来抵抗马其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带来了相当大的成果。关于希腊世界的总人口以及喀罗尼亚战役参战双方的人数规模,见Josiah Ober,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74—81, 275—276;John Ma,“Chaironeia 338: Topographies of Commemoration”,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8), pp.72—91.他对雅典利益的维护和伸张也不能完全否认他的泛希腊情感的真实性,他的泛希腊情感与维护雅典利益的爱国情怀难分彼此,是互相支持和强化的关系。
首先,德摩斯梯尼维护雅典利益的想法和做法无可厚非。他首先是雅典人,其次才是希腊人。生活在邦民一体的城邦中,城邦的安危与公民的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基于古希腊的历史传统,亚里士多德作出了“人类天生是城邦的动物”[注]Aristotle, Politics, 1253a3.这一著名论断。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体系,城邦之间的界限远远超出了现代国家的边境线所包含的意义;从原则上讲,一个城邦的公民在另一个城邦是不为所容的。这种城邦之间的隔绝状态,致使一个公民离开了母邦,便意味着他将失去作为一个“人”所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完全被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甚至不如奴隶。城邦内的温情和城邦外的无情,必然使公民对城邦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爱国心。作为雅典公民,德摩斯梯尼应该关心其母邦的安危利害;作为政治家,他的目标是说服公民大会接受自己的政策主张,这就决定了他的基本立场和策略:要想赢得雅典公民大会的支持,就必须在演说中体现他对雅典城邦利益的关切。这种选择既是增强说服力的修辞策略,也是一位公民热爱本邦的天然情感。正如摩西·芬利所言:“德摩斯梯尼终其一生都在为组织希腊人联合抵抗腓力和亚历山大而奋斗;但是,他只是想让希腊人联合起来抵抗一个潜在的征服者,从而继续作为独立城邦而存在下去,而非创造一个统一的希腊国家。”[注]M. I. Finley,“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s: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Britain Journal of Sociology 5, 1954, p.262.
其次,德摩斯梯尼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雅典利益本身,也看出了希腊城邦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尤其是雅典与其盟邦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在演说中,他反复劝说雅典人要尽其所能地担负起泛希腊同盟的领导责任;[注]Demosthenes, On the Navy-boards, 12-13;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30.不能做挑起希腊内部争端的蠢事,而应该积极援助那些受到波斯或马其顿威胁和进攻的城邦。[注]Demosthenes, First Olynthiac, 15;First Philippic, 50.为了争取更多的盟邦,德摩斯梯尼不仅不再一味地强调雅典的特殊利益,甚至建议雅典人应该对那些心存疑虑的城邦展示出更多的“善意”,并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此,德摩斯梯尼认定马其顿人是道德败坏的“蛮族”,是在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迥异于希腊人的敌人。这显然属于泛希腊主义话语的范畴,只不过“敌人”的身份从波斯变成了马其顿[注]Demosthenes, Third Philippic, 30—46是德摩斯梯尼关于腓力二世的非希腊人身份的集中描述,他认为当前这场抵抗马其顿的新斗争无异于公元前5世纪抵抗“蛮族”波斯人的那场战争。关于公元前4世纪的泛希腊主义中“敌人”身份的变化以及德摩斯梯尼对泛希腊敌人的再定义,见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p.114—116; Polly Low,“Panhellenism without Imperialism? Athens and the Greeks before and after Chaeronea”, pp. 458—459.,它的逻辑结果必然是组建泛希腊的城邦同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马其顿。鉴于马其顿王国的规模和实力,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无法与之相匹敌。可以说,希腊人要想击败马其顿,而又不改变他们的城邦制度,德摩斯梯尼的建议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第三,德摩斯梯尼认识到了希腊城邦与马其顿之间在政治(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层面的根本差别,将民主制引入了他的泛希腊认同机制。他说道,“民主政体下的自由人是热爱和平的,而寡头政体所缔结的和平是没有保障的”;进言之,寡头政体是“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共同敌人”。[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8, 20—21;14.实质上,他的泛希腊政策是在雅典的领导下实现希腊民主城邦的联合。根据这一原则,在麦加罗波利斯向雅典求援时,他提出了一个旨在同时削弱斯巴达和底比斯的政策。[注]Demosthenes, For the People of Megalopolis, 6—19, 30—32. 根据德摩斯梯尼的这项提议,敦克尔得出结论,认为德摩斯梯尼在运用“均势”(Balance of Power)策略,以图确保雅典在希腊世界的优势。参见:H. B. Dunkel, “Was Demosthenes A Panhellenist?”Classical Philology, Vol. 33, No. 3 (Jul., 1938), p. 296.在罗德岛的民主派向雅典求援时,他说道:“让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你们会使所有城邦的民主派明白,与你们交善是他们安全的保障;赢得他们所有人的真诚善意是你的最好的收获”。[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18, 20—21;14.当马其顿开始威胁到希腊城邦的安全之后,德摩斯梯尼之所以放弃削弱底比斯和斯巴达的政策转而主张组建抵抗马其顿的泛希腊同盟,是因为:与波斯、马其顿的君主制相比,大多数希腊城邦的政体是以公民为中心的具有不同程度民主色彩的共和制度。这一制度才是希腊人按照现有生活方式生存并保持繁荣的根本所在。[注]美国学者约西亚·奥伯(Josiah Ober)认为,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去中心化的城邦体系和以公民为中心的城邦制度。城邦制度确立了公平的规则,鼓励人力资本投资,降低交易成本,而公民之间以及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制度与技术的持续创新,也促进了城邦之间以及公民之间的理性合作,最终创造出了在古代世界特别突出的经济增长和文明繁荣。参见Josiah Ober,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pp.xiii—xx.但是,在实行君主制的马其顿的统治下,这一制度不太可能存续下去。腓力二世父子的目标是建立处于马其顿武力控制之下的自治城市同盟。在这一同盟中,马其顿国王是当然的盟主,希腊城邦将会失去主权的完整和独立。德摩斯梯尼深知这一点。因此,从支持和捍卫城邦制度的角度来看,他的泛希腊政策既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更为符合希腊城邦的根本利益。与之相比,为了解决希腊城邦的贫困和内讧问题,伊索克拉底提出了由腓力二世率领希腊人征服波斯的方案。尽管这一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希腊城邦也从此失去了独立和自治,希腊文明的独立城邦(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注]即使是伊索克拉底,也认为雅典人的天性不适合君主制。沙洛姆·佩尔曼甚至通过分析伊索克拉底的《致腓力书》(Philippus)得出结论:伊索克拉底的终极目标并非让腓力二世来统治希腊城邦,而是说服腓力二世停止对希腊事务的干涉和对希腊的征服行动,转而去攻打波斯,从而保住希腊城邦的自由和自治。参见S. Perlman, “Isocrates‘Philippus’—A Reinterpretation”, Historia (6), 1957, pp.306—307; “Isocrates‘Philippus’and Panhellenism”, Historia (18), 1969, pp.370—374.
四
上文分析了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喀罗尼亚战役和拉米亚战役的失利,还是宣告了德摩斯梯尼的努力最终功败垂成。正如彼得·格林所言,对于大多数希腊人来说,难以捉摸的泛希腊主义都只是一种理想,从未实现过。[注]Peter Green, From Ikaria to the Stars, p.107.在某种程度上,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也有着同样的特点和命运。下文从雅典实力衰退、希腊政治格局碎片化以及马其顿王国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尝试分析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未能在战场上击败马其顿的原因。
德摩斯梯尼的理想远大,“他的目标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但是,他却生活在优布鲁斯时代的雅典”;[注]J. B. Bury and Russell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 Macmilan, 1975, p.426;p.363;p.357.德摩斯梯尼所面对的雅典公民和伯里克利所面对的雅典公民有着截然的不同。伯里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虽然缺少了一些抱负和光荣,却多了几许幸福和自由[注]J. B. Bury and Russell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 Macmilan, 1975, p.426;p.363;p.357.,这指的就是雅典公民精神的退化。公元前4世纪,个人主义开始在雅典抬头,“爱国主义不再是毋庸置疑的最高品德”,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他对自身作为“人”这一个体的责任发生冲突;[注]J. B. Bury and Russell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 Macmilan, 1975, p.426;p.363;p.357.在个人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公民更关心的是城邦为“我”带来了什么实惠,而不是“我”应该为城邦做出哪些贡献。享乐主义取代了公民的进取精神,城邦财政盈余部分不再留下来应急,转而成为供公民在宗教节庆中娱乐的观剧基金(the Theoric Fund)。[注]关于观剧基金的情况,见J. J. Buchanan, Theorika: A Study of Monetary Distributions to the Athenian Citizenry during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Locust Valley, N.Y.: Augustin, 1962; Raphael Sealey, Demosthenes and his Time: A Study in Defeat, pp.256—258;德摩斯梯尼对观剧基金用途的看法,见Raphael Sealey, pp.112—135.公元前349年,阿波罗多洛斯建议将财政盈余转用作军费,遭到斯忒法诺斯的控诉并被罚以重金。[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辞《诉尼埃拉》(Against Neaera)提到了这件事,见Demosthenes, Against Neaera, 3—8.与享乐主义盛行相对应的是公益精神的退化,这时的雅典公民不愿服兵役,甚至不愿出资找雇佣兵代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例如,公元前355年,雅典将军卡瑞斯不得不通过参加波斯总督阿塔巴祖斯的叛乱活动来筹集雇佣兵的薪酬;提摩修斯、伊菲克拉底与卡布里阿斯等雅典将军都曾遭遇过这种困境。更糟糕的是,普通公民不愿为城邦服务而乐于从城邦获得享受的时候,政治领袖又往往顺从民意而不去引导民意;在德摩斯梯尼时代,雅典的大小宗教节庆竟然多达100多种[注]英国古典学家戴维斯(J. K. Davies)估算,雅典每年宗教节庆的数量在97至118之间,参见:J. K. Davies, Demosthenes on Liturgies: A Not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87, (1967), p.40.,极大地消耗了城邦本已严重下滑的实力。总而言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及随后的长期战争耗尽了雅典城邦的实力,而公民精神的退化则从内部抑制了雅典公民集体的活力。[注]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Vol. 4 Bristol: Thommes, 2000, p.275.
与此同时,面对危局,雅典的政治精英们却掀起了更激烈的党争。例如,公元前356年,卡瑞斯、提摩修斯和伊菲克拉底一同指挥军队镇压开俄斯等邦的暴动时遇到挫败,卡瑞斯便出于个人私怨而将其他两人告上公民大会,致使雅典损失了两位优秀的将军。政见上的不一致甚至会发展成恶意的身体伤害。公元前348年,支持优布鲁斯的梅狄阿斯就在酒神节上掌掴了德摩斯梯尼。[注]这一事件详见D. M. Macdowell, Demosthenes: Against Meidias (Oration 2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13.这种恶性党争给雅典造成的危害要比100年前严重得多。德摩斯梯尼也意识到了这一危害,提出雅典需要同时进行两场斗争:对抗外敌入侵和制止城邦内部的党争,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注]Demosthenes, 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odians, 31.然而,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雅典政治精英们面对马其顿威胁却始终无法实现合作[注]雅典的主和派和主战派唯一一次统一意见是,公元前448年奥林托斯被攻破、雅典援军被俘,腓力二世利用这批雅典俘虏作为和平谈判的筹码,雅典决定媾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德摩斯梯尼在内也不得不屈从整个城邦的意志,与主和派成员组成使团与腓力二世谈判。,使雅典在危机时刻无法使政治决策贯彻一致,总是在战与和之间摇摆,进退失据,“要么做得太过,要么力度不够”。[注]J. B. Bury and Russell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p.430. 更典型的例子是德摩斯梯尼与埃斯基涅斯的冲突。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两个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也就是说,喀罗尼亚战役惨败之后,反马其顿派的代表与亲马其顿派的代表仍然在互相攻击,缠斗不已。参见Ian Worthington, pp.295—309.
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更加混乱。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底比斯、雅典等城邦联合挑战斯巴达的霸权,经过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之战,遭遇惨败的斯巴达一蹶不振。此后,雅典转变政策,扶持斯巴达,遏制底比斯;随着伯罗庇达斯和伊帕米农达等领袖的意外身亡,底比斯在60年代末迅速衰落。最终,希腊世界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三强相对衰落,而原先较为落后的帖撒利、阿尔戈斯、阿凯亚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纷纷组建了较为强大的地方同盟。[注]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499—520.因此,随着底比斯霸权的崩溃,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进一步碎片化。在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能够称霸的碎片化格局中,希腊城邦的“自治”观念得到了强化,连被斯巴达人奴役了数百年的美塞尼亚人都赢得了完整的独立权利,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公元前378年,雅典组建了第二次海上同盟(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为打消盟邦的疑虑,雅典人并未照搬公元前5世纪的提洛同盟的各项制度,尤其是纳贡制度,而是建立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组织。[注]关于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组织结构,见Jack Cargill,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Empire or Free Alli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97—128; P. J. Rhodes,“Ancient Athens: Democracy and Empire”,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Vol. 16, No. 2, April 2009, pp.214—215.然而,一旦雅典开始尝试恢复强征贡税,盟邦马上就开始了反抗。经过 “同盟战争”后,第二次海上同盟宣告解体,仅维持了20年左右。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期,主张希腊人联合对付波斯的泛希腊主义,已经蜕变为一个含义极其模糊的概念,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指向性,它的敌人可以是波斯人或卡里亚人,也可以是马其顿人或色雷斯人,甚至也可以是希腊人。主张讨伐波斯的伊索克拉底与主张抵抗马其顿的德摩斯梯尼可以共存于这个时代,甚至是同一个城邦之中。主张组织泛希腊同盟抵抗马其顿扩张的德摩斯梯尼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他的泛希腊政策未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不乏 “均势政治”的想法,不失掉任何削弱斯巴达和底比斯的时机,经常有提防其它希腊城邦背叛的话语;另一方面,尽管他从公元前351年之后就以坚定的反马其顿立场贯穿于他的泛希腊政策之始终,却很难完全克服希腊人固有的“自治”观念,也就难以促成广泛和有效的联合。
最后,德摩斯梯尼所面对的敌人——腓力二世统治的马其顿王国,并不同于100多年前的波斯帝国。尽管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并不认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但与波斯帝国相比,腓力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在各个方面都更接近希腊城邦世界。波斯帝国未能征服希腊半岛中南部的城邦,但腓力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做到了,原因就在于此。具体说来:第一,马其顿利用了希腊城邦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在财政管理和军事组织方面。有资料证明,腓力二世雇佣了大批的希腊专家来为马其顿服务,包括财政专家、采矿专家、海军专家、攻城器械专家等。[注]关于马其顿,尤其是在腓力二世治下的马其顿,引进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自身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参见P. C. Millet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edonia”,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edited by Joseph Roisman and Ian Worthington,Chichester, U.K., an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p.472—504.例如,腓力二世不仅在底比斯大方阵的基础上,经过改良之后,创造出了攻击力极强的马其顿方阵,还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请来教育尚未成年的亚历山大。第二,马其顿开发了境内蕴藏丰富的战略资源,主要是人力、木材和矿产资源。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马其顿境内拥有丰富的木材矿产资源。木材是古代造船用的主要材料。金、银矿用来铸造钱币,铁矿、铜矿用来铸造兵器。[注]关于马其顿的资源,见R. A. Billows, Kings and Colonists: Aspects of Macedonian Imperialism, E. J. Brill, 1995, pp.5—10; E. N. Borza,“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Early Macedonia”, Philip II,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acedonian Heritage, edited by W. L. Adams and E. N. Borz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pp.1—20.在希腊专家的辅助下,这些资源得到了有力开发,从而使马其顿的军队规模和财政收入很快就扩张到了相当的规模,马其顿仿造雅典的金银币也开始流行于东地中海各国。[注]戴维斯也认为,马其顿王国在希腊化时代广泛借鉴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财政制度,尤其在税收领域,见J. K. Davies,“Athenian Fiscal Expertise and Its Influence”, Mediterraneo Antico, 7 (2),pp.491—512.第三,马其顿王国的贵族君主制有利于高效的外交和军事行动。马其顿的政体既不是波斯那种东方式的专制,也不是以公民为中心的城邦制度,而是一种以国王为中心的贵族集团统治。“在腓力统治下的马其顿,所有安全、财富和正义都来源于中央王权”。[注]R. M. Errington, A History of Macedo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01.在这种体制下,腓力二世作为国王,既享有希腊城邦公民大会领袖们所没有的集中决策权力,也通过向地方领主和农民封授战利品和土地而拥有了波斯帝国组织所缺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注]德摩斯梯尼也注意到了马其顿国王权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优势,见Demosthenes, Response to the Letter of Philip, 47—50.除了集权带来的外交和军事优势之外,腓力还可以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来神化王权,这是希腊城邦公民领袖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见Ian Worthington, Philip II of Mace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94—203; E. N. Borza, In the Shadow of Olympus: The Emergence of Mace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48—251.综合以上三点,腓力治下的马其顿,既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又在财政制度、军事组织和技术领域受惠于希腊城邦的专业知识,还在政府制度上拥有希腊城邦所没有的迅速决策和行动的优势。公元前338年,希腊联军在喀罗尼亚战场上所面对的马其顿军队,在武器、盔甲、士气方面与他们不相上下,但是后者经验更丰富、装备更精良、训练更充分、指挥更合理。因此,马其顿王国并不是100多年前的波斯帝国,希腊联军失去了公元前5世纪与波斯军队交战时的全部优势,战败难以避免。
结 语
德摩斯梯尼去世于公元前322年,但他的泛希腊政策终结于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希腊联军的惨败,标志着德摩斯梯尼组建泛希腊同盟抵抗马其顿的事业已经失败,而希腊城邦在东地中海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时代也就此结束。尽管如此,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德摩斯梯尼的政策的确包含了突出的泛希腊主义元素,而且逐渐成为他的政策的主要目标;第二,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并非完全失败,在他的努力下,一部分希腊城邦实现了联合对敌;第三,德摩斯梯尼的泛希腊政策不同于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前者更符合希腊城邦的历史传统和根本利益;第四,希腊联军的失败是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潮流使然,随着一系列帝国(王国)的兴起,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已经失去了在军事上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拉斐尔·希莱所言,“德摩斯梯尼的政治生涯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是这位政治家个人的失败,更是他的城邦的失败。”[注]Raphael Sealey, Demosthenes and His Time: A Study in Defeat, 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