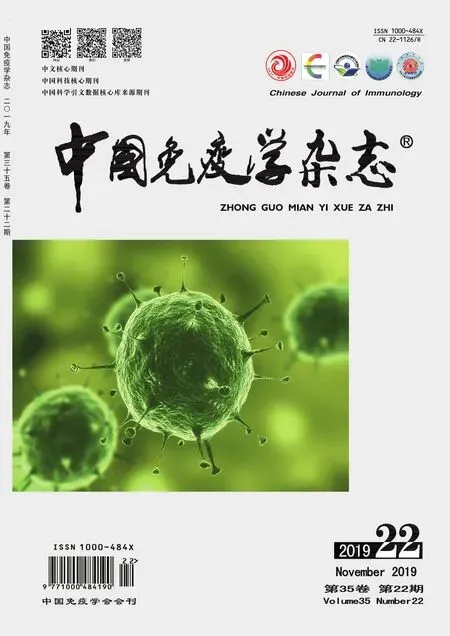巨噬细胞及其在术后腹腔粘连中的作用①
赵 敏 杨丽丽 李文林 曾 莉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210046)
巨噬细胞大量存在于人体所有组织中,在监测和调节局部组织微环境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它对代谢物浓度、基质、毒素、氧含量、酸化、渗透度以及与微环境改变相关的其他分子成分(如细胞因子)高度敏感,因此巨噬细胞的代谢变化可以作为改变组织稳态的重要指标[1,2]。活化的巨噬细胞产生各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酶,并表现出多种及与之相互矛盾的功能,包括促炎反应和抗炎反应、组织修复和破坏,以及杀死肿瘤、促血管生成和促肿瘤发生[3,4]。巨噬细胞的功能可塑性与极化激活状态密切相关,它通常极化为两个主要极端,即经典激活导致M1型巨噬细胞(M1)和替代激活导致M2型巨噬细胞(M2)。细胞因子和介体表达谱可用于评估巨噬细胞是否分化为宿主防御期的促炎性M1表型,或者是主要参与下调炎症、促进伤口修复和吞噬凋亡的中性粒细胞和细胞碎片的M2表型[5]。巨噬细胞在不同的组织器官中有不同的名称,与腹腔粘连关系最密切的是腹膜腔内的巨噬细胞,称为腹腔巨噬细胞[6]。本文将主要阐述巨噬细胞的相关信息及巨噬细胞对术后腹腔粘连形成的影响。
1 M1/M2巨噬细胞的激活与特征性标记物
巨噬细胞表型参与疾病意味着检测或调节巨噬细胞反应对于诊断和(或)治疗疾病意义重大。目前在体外实验中,多使用LPS和IFN-γ诱导巨噬细胞从M0型至M1型,IFN-γ的浓度为20 ng/ml[7,8],LPS的浓度文献报道不一,分别可见10 ng/ml[9]、100 ng/ml[7,8]、1 μg/ml[10]和10 μg/ml[11];IL-4诱导巨噬细胞从M0型至M2型,常用浓度为20 ng/ml[12,13]。它们的诱导途径和受控的生物过程都不是简单模式,并且在环境变化时极化状态是可逆的[14]。更好地了解巨噬细胞不同亚型以及巨噬细胞表型可靠标记物的相关分子途径和转录程序,对于巨噬细胞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必需的。针对巨噬细胞极化表型特异性标记物的研究,Jablonski等[7]完成了M1和M2巨噬细胞的转录组分析并且验证了相关的M1和M2标记物,CD38、Fpr2、Gpr18可用于LPS+IFN-γ诱导的M1型巨噬细胞的特异性标记,c-Myc和Egr2可用于IL-4诱导的M2型巨噬细胞的特异性标记,皆优于传统的iNos、Arg-1、CD206;另有研究表明CD68或CD163结合pSTAT1或RBP-J可用于鉴定M1极化巨噬细胞,而结合CMAF可用于鉴定M2巨噬细胞,CD163不是M2特异性标记[15]。
2 巨噬细胞表型的调控
巨噬细胞在功能上非常复杂,几乎涉及生命的各个方面,从免疫和宿主防御到体内平衡、组织修复和发育。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巨噬细胞形成了不同的极化状态。了解它们的转录调控和表型异质性是必要的,因为巨噬细胞在许多疾病中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已成为很有吸引力的治疗靶标。多种基质相互作用从而调控巨噬细胞的可塑化和极化状态,如应激信号转导、转录因子调节、表观遗传机制及转录后调节、代谢变化等[16,17]。
2.1应激信号转导 数据表明M1/M2极化状态可以被复杂和相互作用的内源性细胞信号传导途径及其调节剂快速诱导和完全逆转或重新极化[18]。
关于急性应激信号相关的巨噬细胞活化状态。在局部环境中任何形式的损伤都可以诱导炎症信号的产生,巨噬细胞感知这些变化并整合这些新的应激信号以改变它们的整体转录程序,从而改变它们的生物效应器[19]。现在研究较多的是ERK1/2-PPAR-γ通路[20]、PI3K/Akt通路[21]、JNK通路[22]、Notch 通路[23]、JAK/STAT通路[24]等。
关于慢性应激相关的巨噬细胞活化状态。在慢性炎症过程中,其特征是在微环境中长期存在非生理信号[25],这些信号通常比急性应激反应时弱得多,并且它的激活与营养素的非生理摄取有关,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盐、胆固醇和游离脂肪酸[26]。
2.2转录因子调节 特定转录因子被发现促进特定基因的表达,决定巨噬细胞的功能极化,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PPARs)、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s,IRFs)、Kruppel样因子、GATA结合蛋白3、NF-κB和c-MYC[27,28]。这些转录因子可以通过微小RNA(miRNA)调节,miRNA是一组小的非编码RNA,其通过翻译抑制或mRNA降解调节基因表达,以此调节响应微环境信号的转录因子来控制巨噬细胞的极化[29]。例如,Ⅰ型干扰素可以激活STAT1,并有助于诱导M1相关基因表达,如iNOS;IRF5促进巨噬细胞向M1极化,IRF4促进巨噬细胞向M2极化[30,31];M2极化表型突变的完全缺失包括IL-4、IL-13、IL-4R、STAT6以及控制M2基因表达的关键下游转录因子:IRF4、JMJD3、PPARδ和PPARγ,在编码这些因子的任何基因中,功能缺失等位基因导致M2极化基因表达的全部或大量丧失或M2巨噬细胞的明显丧失;同时NF-κB也参与巨噬细胞极化过程,但是不同的NF-κB亚基(如c-Rel或p65)在极化中的确切作用并没有通过研究缺乏这些蛋白的巨噬细胞得到证明[32]。
2.3表观遗传机制及转录后调节 表观遗传机制越来越被认为是巨噬细胞表型的关键调控者。表观遗传过程是指通过调节转化密集的异染色质进入转录因子可及的常染色质来改变基因表达,但并没有影响DNA序列本身。虽然DNA甲基化通常导致基因沉默,但组蛋白修饰可以标记开放或封闭的状态。赖氨酸(K)残基的乙酰化由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s,HATs)决定,通常增加转录活性。HATs的活性可以通过抑制因子复合物被抵消,同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活性去除赖氨酸乙酰化。通过组蛋白甲基化调节基因表达可以与转录激活或压制相关联,这取决于甲基化位点和甲基数。组蛋白H3在赖氨酸-4、赖氨酸-36和赖氨酸中的二甲基化或三甲基化与转录激活相关,而H3K9me2/3和H3K27me3被认为是抑制性标记。这些不同位置的组蛋白甲基化状态由组蛋白甲基转移酶(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s,HMTs)和相反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Histone demethylases,HDMS)调节。大量的组蛋白修饰酶(Histone-modifying enzymes,HMEs)合作在增强子区域中设置所谓的组蛋白密码,从而调节巨噬细胞分化、激活和极化[33]。例如在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小鼠的肝脏中,PSTPIP2的高甲基化通过抑制STAT1活性从而抑制M1标志物的表达,并通过促进STAT6活性增强M2标志物的表达。相反,在体外实验中,敲低PSTPIP2促进M1极化并抑制M2极化[34]。
2.4代谢变化 代谢变化在控制巨噬细胞活化和获取环境依赖性的活性效应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通过CD36、脂蛋白脂肪酶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摄取的代谢脂肪酸是IL-4介导的外源性途径发育和活化的M2巨噬细胞所必需的[35]。相比之下,M1巨噬细胞是通过糖酵解的[36]。驱动巨噬细胞活化的信号影响代谢途径,协调控制巨噬细胞的活化和代谢。例如,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1(mTORC1)和蛋白激酶B(Akt)整合到JAK-STAT或TLR4信号通路中发现, mTORC1和Akt能够与信号通路共同作用,确保巨噬细胞活化和活性效应的执行[37]。
3 巨噬细胞与术后腹腔粘连
腹腔粘连是指通常在大网膜、肠袢、内脏和腹壁之间形成的病理性“连接”。 它们的存在形式从细小的无血管的薄膜到可能包含血管和神经结构的实际结缔组织桥,或者邻近器官之间的直接粘连接触。腹膜在经过手术、感染、外伤或辐射继发的任何干扰后,都可能导致腹部组织的损伤和炎症。通过浸润炎症细胞和氧化应激释放的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导致粘连形成的触发机制和初始步骤;细胞外基质的沉积导致后期纤维蛋白溶解失衡并促进粘连的形成[38]。因此,粘连形成过程简要描述如下:涉及腹膜的组织损伤引起炎症和纤维蛋白沉积,其将受损组织连接到相对器官[39,40]。
一旦经历手术操作,即会启动复杂的免疫应答,导致驻留巨噬细胞的募集和激活[41]。巨噬细胞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NKT细胞以及IgE和选定的IgG亚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炎症、血管生成、细胞募集和肌成纤维细胞的胶原蛋白沉积[42]。巨噬细胞是一种动态和功能异质的细胞群,组织学数据显示巨噬细胞在粘连形成早期就存在[43],它们不同极化状态所占的细胞比例在腹腔粘连的发生和/或修复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以下从炎症和胶原蛋白沉积方面阐述巨噬细胞极化状态在腹腔粘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3.1炎症 在粘连组织中可以观察到大量的单核圆形细胞浸润,这些细胞被鉴定为巨噬细胞和T淋巴细胞[44]。巨噬细胞是先天免疫细胞,在炎症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充当急性和慢性炎症的细胞介质,并且是炎症起始、持续和消退的关键细胞[45-47]。经典活化的M1巨噬细胞与引发和维持炎症有关,M2或M2样巨噬细胞与消退慢性炎症有关[48]。在粘连组织和M1型巨噬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如TNF-α、IL-6和INF-γ升高,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M2表型内,M2表型改变后细胞因子和标记物也发生变化,如CD206、YM1和Arg-1等[40]。M2表型的驱动因子包括Th2衍生的IL-4、IL-10和PPAR-γ,PPAR-γ是一种具有强效抗炎作用的配体激活的核受体[49]。一项研究表明,内源性巨噬细胞特异性PPAR-γ信号传导影响精氨酸酶活性和巨噬细胞极化,并且反向调节腹膜粘连情况。药理性的PPAR-γ激动诱导巨噬细胞向M2极化,并以巨噬细胞依赖的方式改善粘连[40]。
3.2纤维蛋白沉积 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术后渗出液中的巨噬细胞在腹膜创伤愈合期间的纤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是通过产生和分泌纤溶酶原激活物(uPA和tPA)和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剂(PAI-1和PAI-2)以及TNF、EGF等其他物质[50]。EGF促腹膜间皮细胞有丝分裂,诱导其向成纤维细胞表型改变,还能够促进细胞迁移和细胞外基质分子的粘附[51,52]。纤维蛋白原在腹膜创伤后释放,可能影响腹腔巨噬细胞的表达模式,从而降低巨噬细胞的纤维蛋白溶解活性,这可能使粘连持续存在[53]。活化M1巨噬细胞分泌许多炎症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54]。TGF-β1在损伤和随后的炎症和纤维化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它可以破坏腹膜损伤后纤维蛋白形成与降解的平衡,进而引起细胞外基质沉积,为粘附形成提供基础[55]。Ar′Rajab等也发现蛋白酶胨对M2型腹腔巨噬细胞的增强及巨噬细胞移植到非增强的巨噬细胞腹膜中都降低了术后粘连形成的程度[56]。粘连形成的程度与M2标记表达成反比,在粘连形成过程中,通过改变巨噬细胞极化状态,可以调节此过程[57]。M2巨噬细胞诱导的Arg-1可以减少肝纤维化和胶原沉积[58]。Pesce等[59]假设巨噬细胞内的精氨酸酶活性与成纤维细胞竞争胶原产生的底物L-精氨酸,导致胶原产生减少。
4 结语
以上研究表明巨噬细胞在调节腹腔粘连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它影响的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索。更成功地预防粘连技术很可能是从深入了解细胞、分子诱导和调节粘连形成及修复的机制发展而来的。因此,不断探寻巨噬细胞在腹腔粘连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希冀在围手术期从巨噬细胞层面能够制定防治腹部手术后粘连形成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