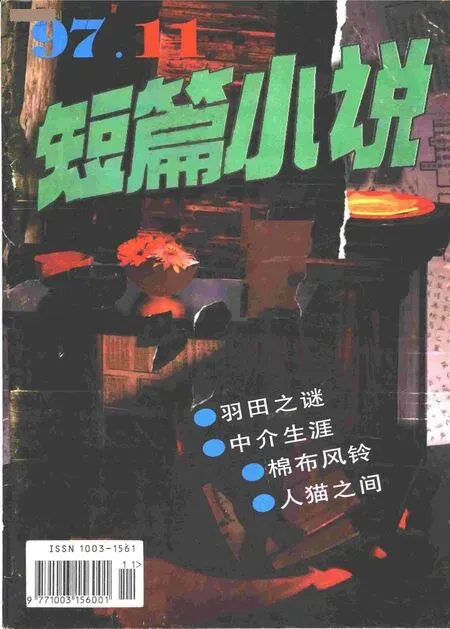与村长有关
◎余书林
村长的面子
水月村的村长还小的时候,当然他还不是村长。他的父亲是水月村乡剧团的一位演员。他演过荆州花鼓戏《王瞎子闹店》里的一个“花旦”角色——小幺姑,演戏嘛,演了也就演了。可他走路的神态,说话的声音的确像个女孩子,因此,水月村的人,干脆把他叫成了小幺姑。到他的年岁有些大了的时候,村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又顺理成章地改口把他叫成了幺姑大叔。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红白喜事也像地里的庄稼——产量陡增。不管是这家生孩子,还是那家死人,不管是儿子去当兵还是孙子上大学,不管是儿子结婚还是姑娘出嫁……都兴整个酒宴。乡里乡亲,虽然不是亲戚,但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得去凑个份子,送个人情,增个人光。幺姑大叔如水月村的村民一样,频频出现在这种“凑份子”的场合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些酒宴上,随着早些时 “除四旧”,消失了的“叫花子赶酒”,也如一种传统的乡风民俗,顺应时代而复苏,在民间悄然兴起。
哪家有喜事,叫花子来到华堂前,先燃放一小节鞭炮(他们往往是把一挂鞭炮,分成若干小段,所到之处,放上那么一小节),再念几句喜词。据说,这种喜词有讲究,多达360句。当然都是一些奉承之语。叫花子念完喜词后,紧接着从腰包里掏出烟来,忙去寻找东家管事的支宾先生打交涉:表示他们已上门送过恭贺。叫花子的目的很明确,不外乎要“支宾先生”到时候给他们一点“喜钱”——就是放了那几个鞭炮、说了那几句好话的钱。原先农村穷的时候,这种钱是以元计算的,现在,则是以十元为起点。对了,他给了支宾先生一支烟,支宾先生要给他两包烟——名曰“喜烟”。接着他们会直奔厨房,拜见厨师。至于找厨师,目的只有一个,要厨师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们炒几个菜,喝餐酒。厨师也是有规矩的,一般打发叫花子:四个菜,一个汤。这几道菜,是酒宴上“十碗”的综合。他们往往是吃不完,兜着走。
给叫花子吃饭的规矩:是不兴用桌子,不在屋里。一般都是把两条大板凳合并在一起,,摆在门前。饭、菜、酒,一道放在上面。酒壶不兴盖盖子,敞开着,意喻:敞开喝。其实,就壶内那么多——大方一点的支宾先生会多装一些酒到里面,遇到小气人,也许只给你小半壶。不论多少,喝完为止,是不兴添加的。
幺姑大叔在凑份子的场合上,没少见过“叫花子赶酒”。幺姑大叔并且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现象:现在农村富裕了,做红白喜事的东家,对赶酒的叫花子也舍得施舍了。这种施舍对幺姑大叔,产生了一种诱惑。他而且是每每见到,必想到那件事——如果利用花鼓戏中的道情,去给东家送“恭贺”,比“叫花子赶酒”要有档次一些。叫花子赶酒只是说白,唱道情,是唱、是表演。间或还有简板、道情筒的敲击声,比单一的叫花子“赶酒”的气氛要浓郁得多。
幺姑大叔虽然年事已高,他家地里的活路还是他老两口在做,但空余时间还是有一些的,遇到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去凑个热闹,也是抽得出空来的。
幺姑大叔是演员,唱道情犹如木匠师傅“拣板上肖”,轻车熟路,不必去拜师学艺。
幺姑大叔做出了如此决定,从此,村里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他总是手握简板,怀抱道情筒,不慌不忙地迈着他那有些老练了的“花旦”步,乐呵呵地到东家去唱道情送恭贺。
幺姑大叔有本事把东家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即兴创作道情词来唱。最多的时候,他还是唱些插科打诨的段子。这些词儿,是村人们最喜欢听的:
说白话,讲白话,红火太阳把雨下。孤老儿子放八卦(风筝名称),鸡公下蛋抱鸡娃。
麻风细雨满天星,开水锅里结凌冰。正月怀胎来年生,气死寡妇的男人。
听到狗子说人话,看到公猫把儿下。两个石滚打死架,青石板上种芝麻……
幺姑大叔唱这些“闲词”时,乡邻们和者必众。还会有人夺过他的简板和道情,唱些其它的词儿。幺姑大叔还不时在一边“指点指点”。这种气氛,让乡邻们的喜宴活跃欢快。
幺姑大叔唱完道情后,东家也用招待“叫花子”一样的礼节招待他,在喜堂前摆上四个菜、一壶酒让他自斟自饮。他走时东家同样拿出喜钱喜烟来谢他。
这时,幺叔大叔会不失时机地用答谢词来答谢东家,与酒宴上的亲朋好友道别。他仍然是一躬到底,满脸笑靥:
多谢东家的烟和酒,
得罪满堂的亲朋和好友;
今天难免要分手,
下次相会再叙旧。
幺姑大叔唱道情,时间长了,也攒下了不少钱。他逢人总是笑脸相迎,以烟相奉。有时,乡邻们遇到手头紧时,便来找他周济一下,他总是有求必应。
幺姑大叔在水月村唱道情,唱得人缘极好,口碑不错。他的儿子,人也实成,长大成人后,村里换届选举时,村民们不约而同地选了他的儿子当村长。
幺姑大叔的儿子当上了水月村的村长,幺姑大叔不喜不忧,不当回事,仍然唱他的道情。
幺姑大叔的儿子当了村长,村民们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坐上席,喝喜酒,并以请到村长为荣。
暑假的一天,一位村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请村长去喝喜酒,坐上席。
幺姑大叔不请自去地到那家唱道情、送恭贺。
幺姑大叔来到喜堂前,往门前一站,面向高堂,也不管上首坐得人是谁,双手抱住道情简两头,向屋里的宾客深深地鞠一躬。接着,就唱开了道情。得意时,还像他年轻时在舞台上那样,摇头跺脚。
坐在上席的村长,觉得他父亲的这种做法,很丑陋,屋里坐着的不只是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子领导下的那么多村民。这很让他没面子,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一下子,村长的脸由羞耻到愤怒,红到了脖子根。他不敢抬头、正眼看门前唱道情的父亲,他以为他父亲跟那么多村民行大礼,不应该,他以为他父亲唱道情就是叫花子赶酒,太丢人。村长顿时感到酒席上的烟、酒、菜全他妈的不是味道。
幺姑大叔唱完了道情,在门前就着四个菜,从从容容、有滋有味地喝干了那壶没盖酒壶盖子的酒,顺手把他没吃完的菜倒进了他随身带来的一个大饭盒里。
乡亲们见幺姑大叔又吃又带,同他开玩笑说:“幺姑大叔好像不懂江湖,我们吃酒,都是只准肚饱,不准怀揣。哪像你又吃又带。”
幺姑大叔笑着回答乡邻:“如果我不带走,厨倌师傅定会疑心他做得菜味道不好。凭你们说,‘叫花子’都不愿意吃,哪有什么好东西。还有一个理由,如果我不剩下一些带走,东家是怕别人说他小气的,连打发‘叫花子’的东西都不充足。”
村长不知是怎么吃完那顿酒席的。
村长下席后,出门正准备走时,正好碰上东家管事的支宾先生,拿着一张20元的钞票,四包黄鹤楼的香烟,在与他父亲交涉:“这点喜烟喜钱,望幺姑大叔‘笑纳’。”
幺姑大叔伸手接过钱和烟,双手抱着道情一躬:“多谢多谢!”幺姑大叔心知肚明:自从儿子当了村长以来,乡亲们给他的喜钱和喜烟不仅数量加了倍,质量也上了一个台阶。不是那些赶酒的叫花子所能享受的。
村民们见了村长,善意地开着玩笑说:“村长,你把乡政府给你们村干部缴纳了提留款,拿回扣的方式也带到了我们水月村的酒席上来了——您送了人情,要父亲来领回扣呀!”
村长听了村民的这句玩笑话,不以为是玩笑,而是以为村民对他的讥讽,甚至是刻薄和挖苦。他感到这时受到了奇耻大辱。越想越觉得他父亲在村人面前,给他丢尽了面子,心中的怒火难以按捺。
村长用鄙夷而且仇视的目光斜睨了他父亲一眼,背上双手,急忙离开了这喜堂。
儿子不用正眼看父亲,幺姑大叔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完全没把儿子当村长看,他以为儿子和其他来喝喜酒的人一样,不也就是一个来随礼的乡亲么,没一点特别。
晚上,村长回到家里,看到桌子上的道情筒,感到那道情的神情同他父亲一样孤傲,简直是在傲视他。
幺姑大叔端着那碗煮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从厨房里出来,走进堂屋,准备吃晚饭。这碗杂烩汤,是幺姑大叔在酒席宴上带回来的那些菜肴烹煮的。
村长看到那碗冒热气的杂烩汤,气不打一处来,他冲着幺姑大叔吼道,您以后别在村里唱道情了,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幺姑大叔听了,大吃一惊。把刚举到嘴边的酒杯往桌上一墩,两眼紧紧的瞪着儿子,好一会才问:“面子?你知道你的面子是从哪来的吗?你的面子就是我唱道情唱来的。我唱道情有情于乡邻们,乡亲们才选你当村长的。你以为我唱道情丢了你的面子,是那种下九流的人?我告诉你,我是民间艺人。”
村长说:“不管您是民间艺人,还是叫花子,我好歹是在当村长,有丢我面子的事,就不要做了。”
幺姑大叔听了儿子的话,说:“好,好、好!你真要说我丢了你的面子,我以后不唱道情了。可我一天要两包烟、两斤酒的钱你得给我。如果你不答应我,我还有我的面子,也不会管你面不面子。”
村长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答应了幺姑大叔的条件:“都依你的,只要你不再唱道情。”
幺姑大叔拿着村长给他的钱,不再唱道情了,在家里买烟、打酒对付一日三餐。
幺姑大叔知道,他儿子当村长,一年的工资只不过是一张白纸。当村长的人,一年到头上上下下地跑,少不了要钱;那些上面的领导还得罪不起,三不之一还要请他们喝酒。孙子现在已经读高中,要不了两年就要上大学,更要钱。他区区一个“狗腿子”村倌,又有多大的能耐。就如外面说的,上交提留款时拿些回扣,有时候占点村里的“便宜”,又能有几多呢。平时汤里来,也水里去了。
幺姑大叔除了唱道情之外,没有其他赚钱的本领。要给孙子攒钱,没有门路。只有省吃俭用,只有节衣缩食。幺姑大叔有了这种想法,再去店里打酒,就只打半壶,然后回家,悄悄地兑进半壶凉开水;又把原先抽的两元一包的芙蓉香烟,改为一块二一包的君健烟。为了不让儿子和外人发现他这个变化,幺姑大叔把君健烟买回来后,立马拆开包装,装进芙蓉烟盒里。在别人眼里,幺姑大叔抽的还是芙蓉烟。
幺姑大叔这么拮据地过着日子,把那烟酒省出来的钱,一块一块地攒着。又过了两年,村长家的积蓄被儿子读高中花得差不多了。接着儿子又考上了大学,村长不得不借债。早先,给幺姑大叔承诺的烟酒钱,兑现也不是那么及时、按数了。
幺姑大叔也不计较,自己的儿子,钱要留着办正事。
村长的儿子上了大学后,他父亲幺姑大叔在家中闲出了重疾。
儿子读书,父亲看病,村长的债台筑高了。眼看父亲行将就木,拿什么把父亲送上山呢?村长在家里发愁。这才感到他真正地要在村民们的面前丢面子了。村长悔恨交加地想:要是当时不阻止父亲唱道情,他现在肯定不致于穷成这样。他好懊悔。
幺姑大叔在回光返照的时候,把还在当村长的儿子叫到床边,有些吃力地从床铺草里边掏出他从烟、酒中积攒起来、一直没肯拿出来的5000元钱,接着又拿出来那只道情、一本道情词谱《见人说》来,他像交给儿子遗产那样,郑重地对当村长的儿子说,我最后给你一次面子。让你拿这钱把我揾下土。希望你也给我留点面子,接下这几样东西。你上了年纪,不当村长了,就拿它为自己挣面子。
当村长的儿子接过父亲的钱币和遗物,泣不成声。
村民们都来给幺姑大叔送行。在村长家幺姑大叔的丧事前,他们拿起幺姑大叔的道情和简板,翻着幺姑大叔撰写的那本《见人说》,热热闹闹地唱着道情,为他送行。
无论是村长还是村民,他们都觉得很有面子……
村长的麦子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垄黄。
水月村的闵龙夫妻俩天未亮,就着满天的星星吃了早饭,忙下地割麦子。
麦子要趁早上露气未干,还没被太阳烤焦时收割。麦子若被太阳蒸干了水分,再来收割,不仅麦穗容易折断,而且麦粒也容易脱落。
闵龙的麦地与村长的麦地挨着,就像两只眼睛隔着一道鼻梁那样隔着一条田埂。他们来到麦田边,看到村长套种着西瓜的麦地,西瓜藤蔓高昂着头,虬须已快触到了麦垄边的麦杆上了。它们虎视眈眈地盯着眼前的那些麦子,打算往麦林里蹿。
要是再过一、二天,西瓜藤蔓蹿进麦林后,西瓜的藤蔓与麦子缠绕的如热恋中的男孩女孩,再去割麦子,要分开它们,不说两败俱伤,西瓜藤蔓是会受到损失的。这麦子必须立即割掉。
闵龙未过门的媳妇怀上了毛毛,儿子要结婚,但没到结婚的年龄。要找村长出面到派出所帮忙改一下年龄,要村长出介绍信,儿子才能拿结婚证,两口子一合计,决定粗工掉细工——先帮村长把这3亩田的麦子割掉,日后好跟村长开口。再说,割完村长的麦子,再去割自己的麦子,也迟不了多长时间。
没一会工夫,田山夫妻也来割麦子,他们要从闵龙和村长之间的田埂上穿过。田山看到闵龙夫妻在村长的地里割麦子,以为他们弄错了田块。指着闵龙的田,疑惑的问:“好像这边是你们的麦地呀。”
闵龙尴尬地一笑,把自己有求于村长的事说给田山听了。
田山听后,想到他两个儿子,还差一个宅基地,也有求于村长。何不趁这个机会帮上一把,日后也好开口。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哪好意思!
这两对夫妻都是干庄稼活的里手。他们达成默契后,往握镰刀的手心里啐上一口唾沫,接着,握着镰刀把的手腕一扭一扭一扭的,那镰刀把便在他们松而不散的拳中旋转起来。就那么几下,刚才啐在手心里的唾沫,便均匀地粘附在手掌和镰刀把上了。他们攥紧镰刀,张开两腿,似马步;弯下腰,如箭弓。摆开收割的架式。他们手中的镰刀,伸进麦林里,将一小片麦子集拢,同时,左手虎口张开朝下,胳膊肘向外一反挽,刚才镰刀集拢的那一绺麦秆,自然、如数地抓在了手中。说时迟,那时快,握住镰刀的右手似顺手牵羊,带着旋转的动作往回收,左手中的麦秸秆“沙沙”的响过之后,一小片麦子便被拦腰斩断。这时,右手的镰刀又伸了出去,钩住左手麦秸秆的下部,接着左手渐渐放松,用指头把松开的那绺麦秸秆把往左带动,右手的镰刀同时向右一勾搭,那把麦子就均匀整齐的铺在了身后的麦茬上。
闵龙和田山两对夫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村长的地里割着麦子,挥汗如雨。虽然他们吃着不该吃的亏,但是心里挺舒坦。他们想得是,要是村长和他的家人知道他们两家把地里的麦子给割了,一定会感动得不得了的——要是他们两家向村长提出点什么要求,即使村长不同意,村长的妻子定会在旁边提醒说:“他们给我家割过麦子呢……”
闵龙和田山快把村长家的麦子割完时,村长和他的家里人,还一点也不知道地里的麦子有人在收割。闵龙和田山暂时还不想张扬——就是中午回家吃饭,也不想让村长家里知道这事。他们知道,这事,村长家里不久就会知道的。他们两家商量:上午把村长家的麦子割完,下午把麦子捆好,运到村长家里,给村长家一个惊喜。
太阳还没当顶的时候,村长家3亩地的小麦,早被闵龙田山两家斩尽割绝。
天有不测风云。闵龙田山割完村长家的3亩小麦回家时,太阳还望着他们在笑呢。他们回到家,沉浸在帮了村长的一次大忙的喜悦中,吃着香甜可口的午饭时,老天爷不知道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忽然把脸沉了下来,并且有要大哭一场的样子。没等他们吃完饭,大雨如桶倒一般泼了下来。村长家的麦子先是被雨水淋湿,接着便“水涨船高”,全都浮在水面上,村长家的麦子,先是铺着一地的金子,此时,它们随波逐流,变成了一“池”觅食的鸭子。
麦收时节,下了一场大雨,农人个个感到焦虑和自危。他们没等雨停,就往地里跑。看他们地里的麦子倒没倒在水里。
村长家的麦子浮在水上,下地的人都看见了。有好事者,跑到村长家里,告诉他家的麦子“放鸭子”了。
村长的老婆听了,还有些好奇:“我们根本没人去割麦子,怎么会有‘放鸭子的事’呢。”于是,村长的老婆催着村长,要村长陪她到地里去看个究竟。当她看着她家的麦子全部浮在水上时,村长的老婆紧接着就是愤怒,撒泼的泼妇劲上来了,便有粪便一样脏的语言,像农人泼大粪那样从她的嘴里洒出来:“我知道村长这些年收粮收款时,赶你们的猪子,巴你们的粮食;计划生育,劁了你们的女人,得罪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复他?我告诉你们,村长也不愿意这么做,都是上面要他这么做的,你们有狠,就去找上面。除了这,再就是村长搞了你家的嫩丫头,你们对他不满,想方设法地陷害他……”
当村长婆娘知道了她家的麦子是闵龙田山给割倒的,更是怒火万丈。她咒闵龙、田山逞能,不得好死,要他们赔偿损失。
闵龙和田山好心办成了坏事,只得给村长老婆赔礼,应承赔她家的麦子。
村长的老婆说:“你们的麦子没有我的麦子长得好。”要他们增加面积赔她。
闵龙和田山不好辩解。其实他们两家的的麦子都比村长家的长得好。并且他们两家的麦子种得是全幅,村长家的麦地留有套种西瓜的空地,只有半幅麦子。何况村长家的麦地,由于他老婆整天只忙于打麻将,麦林中的杂草没除,燕麦没扯,地里一直是草荒苗的现象,本来产量就不高。闵龙、田山就是用他们的一亩地的麦子,去赔村长家的一亩地的麦子,也是吃亏的。为了让村长老婆满意,他们两家决定用4亩地的麦子赔偿村长。
雨过天晴,闵龙和田山各自割了自己的2亩麦子,作为赔偿。请村长老婆过目验收。
村长的老婆掐下闵农和田山的麦子,看了一眼,口里没说什么,心里像是发现了什么,回头就往她家的麦地里跑。村长的老婆把她地里被水浸泡得涨鼓鼓的麦子,剥落了一些,和闵龙田山家的麦粒一道摊在手心里,伸到闵农和田山的眼皮底下,说:“你们看清楚,我家的麦粒比你们的要饱满得多。”
闵农和田山弄巧成拙,没得办法,只好跟村长的老婆说好话、赔不是。决定他们两家再各加5分田的麦子作赔偿。
村长3亩地的麦子,就这样换了闵农和田山两家5亩地的麦子。其实他们两家的麦子完全是送给村长家的——村长家的麦子,他们哪有还有心思去收回来。
暴雨来的快,去的也快。村长家3亩地的麦子,在夏日的阳光下,很快就晒干了,虽然损坏了一些,并不是颗粒不收。
村里的宁仁想生二胎,看到村长的麦子放倒在地里,经雨后,几天没人管、没人收,以为是村长公事多,顾不了地里的粮食。宁仁有心巴结村长,手里又有手扶拖拉机、脱扬机。于是,宁仁把村长的那3亩田的麦子收回去,脱掉、扬净、晒干,并拖到粮站里卖了500元钱。宁仁见村长家的麦子钱太少,又往里凑了1000元。宁仁拿着一把票子找到村长的老婆,说:“村长日夜为村里操劳,麦子烂在地里也没工夫收。我有空,帮忙收了,卖了。这是麦子钱,您先清点一下,等村长回来了,您告诉村长一声。”
村长的老婆接过宁仁手中的钱,数了数,不多不少,一千五。她数完钱,又是一惊。村长老婆把那钱装进她的坤包里后,接着又咒骂闵农和田山黑良心:他们赔给她家的麦子只卖了1250块钱,比宁仁送来的钱整整少250元。
村长的老婆决定去找闵农和田山两家讨要她那“二百五”。